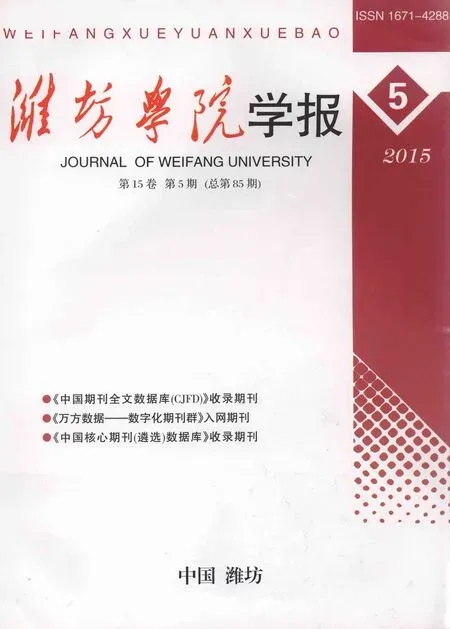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化表达
王 欣
(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任何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会受到既存文学的影响。在莫言的小说中,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存在,这其中既有中国本土文化的浸润,又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熏染。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文学逐步突破禁区走向开放,大量西方文学也不断被翻译、介绍,“魔幻现实主义”开始进入作家视野,中国作家也呈现出“魔幻写作”的繁盛景观。莫言在这种“魔幻”旗帜下创作,却走出了这种“影响的焦虑”,吸收了异域文化的营养,却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本土化天地。2012 年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评价恰恰是对莫言如何处理与魔幻现实主义关系的最佳概括。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中,受文化过滤等方面的影响,不再维持原样。80 年代初,莫言开始接触西方文学,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川端康成的《雪国》等作品,这些作品使莫言对小说创作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或许这种启发是莫言文学道路上的一次偶遇,其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并发现类似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故乡。莫言在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进行创作,起初虽然有不同程度的仿效,但却区别于传统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莫言终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以本土化的表达方式呈现“中国式魔幻”,在融合与创新中实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性转化。
一、“魔幻”影响下的创作
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有多种构成要素产生了作品的魔幻效果,既包括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又包括神奇多元的宗教信仰,还有新颖独特的魔幻叙事,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等。而在诸多构成魔幻效果的要素中,神奇而超乎现实的魔幻意象世界最为重要。[1]魔幻意象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艺术营构的重要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在以莫言为代表的20 世纪后期中国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中也随处可见。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审美范畴早已有之,春秋时期的《易经》中便有“立象以尽意”之说,即用感性的物象表达理性的意义;魏晋时期王弼的《易经略例·明象》中进一步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即用可见的物象表现不可见的事物。直到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明确地将“意象”组合成一词并应用到文学的审美中,表现作家的主观情志。可见,在我国的意象理论体系中,意象是主体借助客观事物表达主观情愫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象征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为文章渲染了一种特殊的氛围。中国古代文人一直长于意象的表达和使用,不管日月风云,亦是花草虫鱼,都是他们意象营构过程中形诸笔端的重要素材,由于受到特定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等因素影响,这些普遍的意象传达的意义也约定俗成。而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魔幻意象,则是作家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通过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象,在此基础上进行夸张、变形和扭曲,使现实魔幻化和魔幻现实化,具有奇幻性、荒诞性和神秘性等特征。
莫言小说中不乏各种意象的使用,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莫言的特色在于“意象”。[2]在莫言营构的诸多意象中,区别于传统意象营构的方式,不难看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在讲到拉美文学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其创作的指导意义时指出:“《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3]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的莫言,其小说中的意象已经超越了现实,那些发生在故土上的一切,都被作家以一种不可思议、闻所未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神秘而诡异、神奇而魔幻。
莫言小说中有一些奇特的植物意象,他们的形态已经超越植物的原有形态而具有魔幻性,这些意象并不是莫言对现实物象的故意扭曲,而是审视现实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也恰好符合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营构魔幻意象的意图。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红萝卜”曾是一个普通的物象,但在某一特殊的时间、地点,在黑孩的眼里,却变成有带点神秘、虚幻和童话色彩的“红萝卜”,这个“红萝卜”玲珑剔透,它有金色的根须和光芒,并且能够发出幽蓝的光。然而,莫言对这个“红萝卜”加以魔幻性表现,意在窥看动荡岁月下黑孩隐秘的心里,以及在一个残破的家庭和缺失的母爱环境下形成的冷淡却倔强不屈的个性。《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有一种异乎普通高粱的色彩,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植物特性,甚至拥有了动作、表情、声音和思想等“人”的特征。一株株无拘无束、自由生长的“红高粱”,是“我爷爷”、“我奶奶”的化身,是整个民族的图腾,是伟大民族精神和蓬勃生命力的象征。《生蹼的祖先》中有一个神秘的“红树林”,这个红树林有异境般的美丽,然而这样一个令无数人向往的地方却变成为之驻足的禁地,因为这片“红树林”总是发生超乎异常的事件,充满神奇与诡异。另外还有短篇小说《夜渔》中出现的“荷花”,河面上漂浮着的荷花,牵引出了那个面若银盆的女人,然而“荷花”和女人有共通之处,都给人倏忽而来,突忽而去的感觉,这种写法也使“荷花”有了女人的灵性,让人触及到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感。
在莫言的笔下,还有各种怪异的动物意象,他们在承担着为文本释义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魔幻色彩。莫言小说中随处可见“狗”意象,这些狗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家狗而多了几分通灵和诡异。《白狗秋千架》里的白狗总是与人为善,与人为伴,为人分忧,同时是整篇文章时空转换的重要线索,这只狗身上承载了一些复杂的联系,也是乡村复杂血缘关系的一种象征。而《狗道》中同样也有各种颜色的狗,这些狗有如同人一样的思维和动作,他们成为了人类的竞争者,不断与人类争夺地盘和战斗。这群狗的行为已经超过人类的预知而不可捉摸,这是莫言以魔幻化的“狗道”拟写残酷的“人道”的特殊用意。《酒国》中也有两只迥然不同的狗,一只是罗山矿场的看门狗,在丁钩儿推门的那刻,由如狼般的凶猛变得如羊般惊恐,可见它有同人一样依附权贵、见风使舵以及阿谀奉承的特点。另一只酒国烈士陵园管理处老革命的猎狗,虽然莫言对它着墨不多,但可以看出它凶猛、忠诚,有如同主人一样的品格。另外,《三匹马》、《马驹横穿沼泽》和《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等不断出现的“马”意象,特别是《马驹横穿沼泽》中不断出现的那个“红马驹”形象。这个红马驹双眼如水、四蹄如花,嘴唇也如同花瓣般美丽,它能够如同人一样的说话,有如同人一样的感情,生活在这里的世世代代人们都听说过并思念过这只奇特的红马驹。这匹红马驹后来变成了一个姑娘与一个男孩结婚并生儿育女,成为了整个“食草家族”的女祖先。在传统的文学中,马经常被赋予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坚韧不拔的寓意,而莫言却突破这种传统的意义范围,赋予了“马”家族始祖的意义,整个故事也呈现出亦真亦实、真真假假的魔幻特点。《红蝗》中还有不断出现的“红蝗”意象,蝗虫组成的群体如暗红色云团,发出的叫声繁杂而纷乱,它们有狼子野心,其来势不免让人惊惧、震撼。这里的蝗虫是人性邪恶、丑陋的象征,作者将蝗虫魔幻化借以表达对民族和种族深深的忧虑。《生死疲劳》中的驴、牛、猪、狗、猴等也通识人性,能用动物的视角观察整个人类的行为。
莫言笔下除了这些具有魔幻通灵色彩的动植物意象外,还有一些自然界无生命的事物,也突破常规物性而表现出魔幻性。《球状闪电》中的“闪电”超越常规形态,它是五个如同乒乓球一样的火球,把故事中的人物、动物所有的直觉、幻觉和所想所感交织在一起。《生死疲劳》中经常会出现“月亮”意象,月亮在拟人化的处理下而具有了人的形态,它能对“我”点点头,还能与“我”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莫言营构的这些充满魔幻色彩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意象,通过一些非理性的极度夸张,使之承载着具象之外的特殊寓意,这不仅在思想上增加了文本的意义深度,在艺术上也使小说超越现实与时空,造成真假难辨、虚幻神秘的美学风格。可见,这些意象区别于中国文学作品中传统意象的营构方式,具有强烈的魔幻性。
二、走出“影响的焦虑”
中国作家经历了“魔幻现实主义”从震撼到启发再到有意识模仿的整个探索过程,甚至出现了“魔幻附体”的病症,如何使这种向“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呈现出异于传统的魔幻表达方式,中国作家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探索。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如果只是趋同的艺术则必然丧失自我个性和民族特色,在《两座灼热的高炉》中就明确指出:“要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3]因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莫言没有食洋不化,而是以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方式,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象下找到了一条合适的本土化表达方式。莫言的这种做法,既弥补了自身经验的不足,又使传统的现实主义迸发出新的生机。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下,莫言虚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这里有高密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风情。高密在古代是齐国腹地,齐文化向来刚劲发达,不拘传统,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高密人具有刚健不屈、旷达豪放以及动植物崇拜等鲜明个性。莫言执着于神秘的“高密东北乡”,但是并没有局限于这个狭隘的地理空间,他精心挑选和改装相关的地域材料,将生活在这里的事物赋予中国式的魔幻色彩。莫言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魔幻的场景、事物,这些场景、事物总是与本民族的宗教、鬼神信仰等相联系。可见,具有本土特色的宗教观念和民间文化信仰,已经悄然渗入了本国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心理。
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经常会看到多元并存的宗教观念和文化心理,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基于本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创造。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是拉丁美洲这块神奇的大陆,这里生活着众多的土著居民和混血民众,生活在此的印第安人、吉普赛人大多信仰原始宗教,相信占卜术、宿命论以及崇拜图腾等。这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对待现实中的事物喜欢进行奇特、大胆的幻想,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种种光怪陆离的神奇想象,也被作家移植到文本中,并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变成了神奇诡异的魔幻现实。
莫言将魔幻的表达指向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国自古有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宗教观,莫言则选取佛家的观念、事物,来增强作品的神秘性与魔幻性。在佛教的教义中,有深入人心的生死轮回观念,这个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佛教认为,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不断流转,转生于六道(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阿修罗)。众生依照所作善恶业因,一直在这六道中生死相续,循环不已。而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则将这种对生死轮回的思考进行了集中的演绎,并充斥着一种神秘的东方想象。《生死疲劳》主要表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却借助佛教的生死轮回进行构思。西门闹是土改时的地主,享有财富却并无罪恶的他,只能在阴间为自己伸冤,他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的轮回。每次转世成不同的动物,他总是具备同类动物的个性:驴的欢乐与洒脱、牛的憨厚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调皮与机敏。就这样,西门闹通过动物的眼睛观察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变迁,此外,莫言还增加了蓝解放等现实中的人物,使小说与现实有了密切联系。莫言在这个人变为牲畜后又复归为人的轮回过程中,有规则、有步骤地经营历史故事,并借助佛教的神秘特征增强了小说的魔幻性。
除了《生死疲劳》利用佛家生死轮回的教义进行魔幻写作外,《四十一炮》则用寺庙这一佛家象征物来增加事件的神秘感。“寺庙”作为抵抗世俗的“安身之地”,是“清心寡欲”的立身之所,是僧徒的聚居地,也是佛学教旨的传播地。然而,在《四十一炮》中,这座“五通神庙”却“香火冷淡、门可罗雀,散发着一股陈旧的灰尘气息。小庙围墙上和那像被人爬出来的豁口上,趴着一个女人”。这个“寺庙”是莫言对一种超乎现实的理想世界的“假说”,他企图用这座寺庙来增加作品的神奇诡秘,因而作品也在这种环境下被讲述的更加虚实难辨。寺庙里坐着的“大和尚”倾听罗小通讲述世俗故事,从这个大和尚对一切事物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个有悖于传统观念的“荤和尚”。可见“寺庙”这个理想世界确藏污纳垢,这显然是对这个荒诞、龌龊的“神圣”之地的嘲讽,也使整部作品在魔幻表达中尽显荒诞意味。
作家言之凿凿地讲述佛家观念,使用佛教事物,意在为创作主题服务。作者借助佛教的思维和理念,关照现实中复杂的人和事物,并对人和社会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思想,其思想内涵一点都不逊色于魔幻现实主义。正是这一种充斥着东方想象的民间资源,使莫言的现实主义在本土中国找到了一种更加合适的表达。
除了在佛家思想中寻求作品的魔幻表达,莫言还善于挖掘中国本土文化中的鬼神观念。当然,有关鬼神文化的作品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玉米人》、《彼得罗?巴拉莫》、《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关于鬼神等怪异事件的精彩描写。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中,有神秘的玛雅文化影响下的鬼神观念,咒语能够杀人,人和玉米、土地以及森林能够自由地对话交流;胡安?鲁尔弗的《彼得罗·巴拉莫》中,有奇特的墨西哥文化中的鬼神观念,怨魂能够有记忆的功能,并且能够对话,死人也有听说和飞动的本领;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拉美各国神奇缤纷的鬼神文化,死人可以来到活人世界,鬼魂也像活人一样慢慢地衰老死亡等。在拉美地区人的文化信仰中,他们始终认为整个世界分为死人的世界和活人的世界,两个世界是可以彼此来往的,并且还相信人死后是有魂灵的,并且这些魂灵会定期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至今墨西哥仍然每年要过的鬼节,就是受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在中国的《礼记·祭礼》中,就有关于鬼的记录,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可见中国是鬼魂文化起源较早的国度。而人死后成为鬼,鬼有时又会出现在活人面前,或者借生者的身体说话,这是一种“灵现”现象。除此之外,古人还认为人有三魂七魄,疾病或死亡时人可能出现离魂的现象。在中国的《搜神记》、《太平广记》、《幽冥录》、《聊斋志异》等,对这些离奇怪异的现象也多有记载。在中国的农村,受地域和文化观念的限制,许多人头脑中依然保留着强烈的鬼魂观念和鬼神信仰,当代文学作品中,邓友梅的《临街的窗》、陈昌本的《觅鬼》、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秦腔》等,都在表现中国式鬼神观念和信仰,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当属莫言。
莫言写鬼魂神怪,是以中国人的鬼神信仰和观念认识为基础的,区别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鬼神描写。受齐文化等民间信仰的影响,那些鬼神共存、灵魂不死的观念得到当地人的普遍认同,基于这种观念、信仰,有许多关于灵现现象的“再生人”描写,它们极具神奇魔幻。中国文学史上有关于人鬼合一的“再生人”的故事,即这些人已经死去,在异时、异地又重新出现,早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牛成章”[4]一则关于此类故事的描写。在蒲松龄小说的启发下,莫言也将这种奇特的想象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在莫言的小说《战友重逢》中,“我”返回故乡,遇到在自卫还击战中已经牺牲的战友钱英豪,他足智多谋、英勇无比,却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成了敌人枪下的孤魂。虽然躯体已经死去,却能够栖身在河堤的柳树上,与“我”展开一场人与鬼心灵上的对话。我们一起回忆了十多年前的部队生活和战场上牺牲的整个过程。当钱英豪在讲述麻粟坡烈士陵园的“死人国”的生活时,发现那些已在墓穴的鬼魂生活也并不自由,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编制,还有同人类一样的矛盾和痛苦。《我们的七叔》中,“我”接到七叔遭遇车祸去世的消息后匆匆赶回老家,而七叔却在村头迎接“我”的到来,并告诉“我”有关存折的秘密;到达七叔家时所看到的,分明是七叔躺在一个破席上的尸体,更奇怪的是还看到他正在修理他的自行车,并与“我”和“七婶”展开聊天;在七叔墓前,“我”拿出酒祭奠他时,七叔能连声赞赏这酒,并一盅又一盅地往嘴里倒;“我”还尾随七叔进了他的坟墓,并闻到了发霉的气息和很多破败的衣物。还有《奇遇》中,“我”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大前天早晨死去的赵家三大爷,并与我进行了一场对话。莫言发挥想象编织的“再生人”的故事,将中国的鬼魂观念巧妙地运用到整个故事上,除了有一种光怪陆离的魔幻之外,还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充分地表现出来。
除了表现这些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鬼神之事,莫言还善于将对是非善恶的观念渗透到鬼魂神怪的描写中,使笔下的鬼神以及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有了善恶等价值判断,这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鬼神描写有明显区别。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鬼,大多不以善恶进行论断,他们大多不会做出对人类产生危害的事,活人对鬼大多没有恐惧之感;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鬼,则被赋予了是非善恶,并表现出与人类的冲突和斗争,活人大多对鬼神产生一些敬畏之心或厌恶之情。在莫言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莫言赋予鬼的善恶判断。如果对莫言笔下的鬼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孤魂野鬼”,另一种是“祖先之鬼”,而关于“祖先之鬼”的描写,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最为明显。《红高梁家族》中的二奶奶,被黄鼠狼魅住后疯癫,在李山人的抓妖驱邪下竟恢复,然而伺机报复黄鼠狼后又变疯癫;二奶奶死亡后,却开始了持续数天的冲天咒骂。在这里,莫言通过对二奶奶具有诡异色彩行为的描写,显示了二奶奶顽强的生命力,她鲜亮辉煌、敢爱敢恨,是女性解放的先驱。相比那些饱受人间世凉的孤魂野鬼,莫言对以二奶奶为代表的“祖先之鬼”充满了赞扬,并以祖先的激情爱憎映照现代人性的虚浮萎缩,表达对社会急剧发展下“种的退化”的忧虑。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鬼神”描写的传统,早在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的搜神志怪、宋代的烟粉灵怪,以及明清的神魔小说,都在进行着有关“鬼神”文学的写作。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这些古典文学也或多或少地熏陶着中国作家的内心,其中包含的诸多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也得到了传承。从“五四”时期开始,“科学”的倡导使崇信怪力乱神的文学作品难有一席之地,但是建国初期的文学却依然有“鬼”的创作,并一度被当代文学沿袭。这一方面源于新时期开放的时代语境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另一方面是中国乡土文化对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莫言作为中国式魔幻写作的作家,他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里观察到了如何处理传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的方法,并结合从小接触到的灵异文化,创造出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
从莫言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中外文学艺术在本质上有共通性,但具体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却各不相同。莫言在某些理念和技巧上学习魔幻现实主义,但在具体的创作上却立足于中国的地域文化观念。正如他所言:“一个作家独立自由地写作,不为外部所惑,那会是很好很理想的状态。”[5]莫言的中国式的魔幻写作摆脱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简单模仿,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底蕴,张扬了中国的文化个性。当然,在关于如何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方面,莫言也提供了独特的个案和有益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莫言文学创作的生存之道和发展脉路,虽有对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但绝不会简单模仿,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再创造。
[1](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7.
[2]李陀.现代小说中的意象——序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J].文学自由谈,1986,(1).
[3]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J].世界文学,1986,(3).
[4]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全两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396.
[5]莫言.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