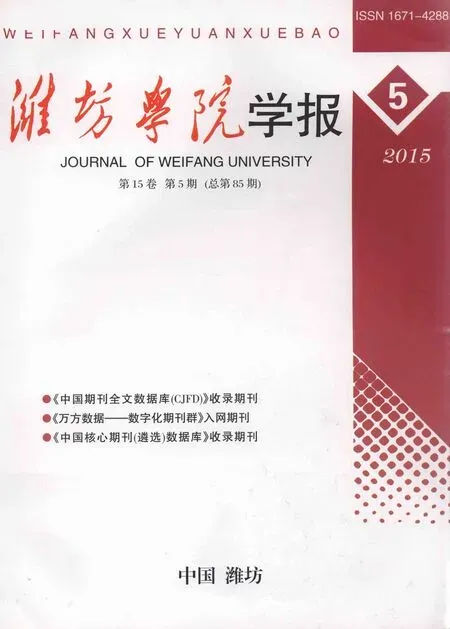社会语言学视界中的语言变体
慈建华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50000)
一、社会语言学产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自20 世纪初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人类交际范围的迅速扩大、交际内容的不断丰富和交际方式的多样化,已成为当今社会人类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语言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行为,越来越深刻地嵌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如影随形般地契合于人类日益扩大和复杂多元的社会交往中。社会是动态的,在不断变化中发展,而语言也受着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断产生着变异,以适应社会和人际交际的的需求。因此,从脱离社会的观点,以研究语言内部结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的语言观念和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空前的、多学科的关注。于是,一门横跨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 世纪60 年代在美国应运而生,而且发展迅速,成为语言科学中成果丰硕的领域。
Sociolinguistics 是社会语言学的英文名称,它是由社会学Sociology 和语言学Linguistics 复合而成。对于sociolinguistics 一词,学界有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Social Linguistics,这是一种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的观点,即以语言为出发点,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二是Sociology of Language,这是一种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的观点,即以社会为出发点,通过研究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前者是从社会研究语言,后者是从语言研究社会。”[1]两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有着很大的重叠区域。所以,不管是立足语言研究社会,还是立足社会研究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是“从社会生活变化引起的各种语言变异现象观察社会和语言的关系,研究语言的社会因素和语言应用中的变异原理,包括社会语境的变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2]因此,与社会生活同步相成的语言变体,因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而成了社会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对象。
二、语言学家对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体的阐述
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y),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示语言在被使用中产生的各种变异,即由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的语言形式或者行为的变异。使一种语言变体不同于另一种的是它所包含的语言项目,变体就是语言项目的集合。因此,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3]这个定义中涉及两个重要概念:语项和社会分布。
语项,指语言项目,社会语言学将其简称为“语项”并作为指代语言项目的一个术语使用。然而,对于语项的定义,却没有因为确定了这一术语而变得简单。因为,不同的语言观点对于语项的定义是不同的。持转换生成语言学观点的人认为语项包括词项、使词项的音和义在句子中结合起来的规则以及使用这些规则的制约。而持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人们则认为,语项除了词项、规则和制约,还应包括结构,因为,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言,研究的重点是结构而不是规则。这两种语言观点虽有不同,但两者都局限于一套自主的语言符号系统内部而不考虑社会因素的纯语言系统。这些观点不仅切断了语言与语境的联系,也没有在语言活动中给语言使用者安排适当的角色。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与前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它认为“语言完全是社会的”[4],是在社会环境中被使用的,任何语言规则都和社会对语言的制约相联系。因此语言项目就是在社会环境中语言的具体用法,是作为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交际片段的一部分而产生的语言片段”[5],即受社会环境中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话语、不同的说话风格、不同的语言色彩的语言片段,这些片段大到语篇,小到语句或者语词。
赫德森对语言变体定义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社会分布”。所谓社会分布是指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中说了什么。赫德森的这一概念把说话者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成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焦点,人际交往是人际关系的基础。“人”的介入成了社会语言学有别于其它语言学的标志性的特征。人,是社会交际的执行者,在交际中,是人们,而不是语言项目在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沟通。那么“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就是指相似的人在相似的情境中使用的一套语言项目。与“人”有关的一切都在语言情境中对语项起着作用,比如身份、阶级、性别、职业等,相似的情景是指相似的交际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使用的所有类型的语项“都以同样的方式同社会环境发生着联系”[6]。据此,语言变体就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指诸如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这样的总体语言范畴,也可以指一种语言的某种方言、某一语音、词汇或句法特征,或者某一交际场合所需要的言语结构或者语音语调的某些变化等等。
三、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用途是影响交际中语言形式的两大因素
社会,事实上是一个有着复杂层构的、动态的语言世界。人类的交际活动就是在这个复杂的语言世界里进行的,所以,应用于交际的语言随时都受着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因素往往是纵横交错,相互交织,千变万化,数不胜数。但是就交际活动产生的成因而言,主要有两大因素影响着交际中的语言形式: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用途。几乎所有的语言变体都与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社会语言学就把种类杂沓,数目繁多的语言变体按照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用途分为两大类:根据语言使用者的不同而界定的方言(dialect)变体和以语言的不同用途划分的语域变体(register)。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接下来将集中论述语域变体,关于方言,拟另文论及。
(一)语域的定义
语域,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学界对其有着十分宽泛的定义。《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的定义是:“具有某种具体用途的语言变体。”Peter Trudgill 把跟行业有关的语言变体称为语域。而Bernard Spolsky 以及Ronald Wardhaugh 等人都认为语域是与行业、职业和社会群体有关的行话。这些定义似乎涵盖了很宽阔的层面,但是从社会交际的角度审视这些定义,就会发现其欠缺,即这些定义都没有包括交际者之间的关系、话语传递方式以及话语场合等交际的重要因素。因此,上述定义都没有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只有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对语域的“三维”之说被认为是涵盖面最为宽泛的,因此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语域是“话语领域、话语模式、话语基调”的总称,并将其归纳为三个维度,即“场”(field)、“式”(mode)、“体”(tenor)。其中“场”指的是话语领域,即正在进行的话语活动,以及在特定的语境之内语言使用的目的;“式”是指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渠道和方式,比如是通过口语还是书面语或者体态语;“体”是指由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阶层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话语的正式程度。韩礼德的“三维”之说涵括了交际的场合、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话题、方式。也可以用更简约一些的方式表示:“场说的是‘为什么’进行交际和交际是“关于什么”的;式是关于‘怎样’进行交际;体是关于‘与谁’交际。”[7]
(二)语域的维度
从韩礼德对语域所做的“三维”描述中我们看到,交际是在一个多维、立体的交际空间中进行的,语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维,因为这个空间中的其他各维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8]由于各个维度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交际者为了在这个高度复杂的多维空间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并使自己的交际行为得以确定的维度,必须以异常敏感的方式,对具体使用的语言符号进行选择,使得交际语言中的每个词的用法、每句话的结构和音调等都与这个交际空间中的各个维度相符合。
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导致语言变体的重要因素。由于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的不同,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就包括多个维度,如“权势”维,表示交际双方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同级关系;“亲疏”维把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亲密和熟悉程度区分开来。在很多语言中,最明显的社会关系的语言标记是人名,决定用“约翰”还是用“史密斯先生”来称呼约翰. 史密斯这个人的依据就涉及到权势和亲密程度两个维度。第一种称呼说明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很熟悉的人或者亲密程度较深的人,第二种称呼说明听话人是说话人生疏的上司或者亲密程度很浅的人。而表现在句子结构和语音语调方面的体现这些维度语言标记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英语中,当一个人讲完一段话后,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已经听懂了,他可以这样发问,“Understand? ”或者“Do you understand me ?”(懂了吗?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但是也可用另一种口气和句子,“I wonder whether I have made myself understood.”(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了。) 这两句话在“场”与“式”方面是相同的,即交际目的和方式是相同的,都是以口语的方式询问对方是否听懂了说话者所说的话。但是“体”方面却不相同。前一句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师生关系,父子/母子关系,或者是彼此十分熟悉、关系很密切的朋友关系,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是一种平等或者上下级关系;而后一句则说明听话人可能是说话人的上级、长辈或者初次见面的尊贵的客人,因此说话人要使用表示谦恭、尊重、客气的变体。
由于不同的语项对交际行为的不同方面敏感。除了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交际的场合的正式程度也对语言变体的产生有着同样程度影响,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由此而产生的变体的数量几乎同由于交际者的社会关系导致的变体等量。这是因为,仅仅因为场合的不同,交际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一对夫妻,在家里他们会使用十分亲昵的变体称呼对方,但是假如他们同时出现在法庭上,一个是法官,一个是被告的辩护律师,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使用家中的变体来称呼对方,而只能使用法庭上的相关称呼或者术语来称呼对方或进行对话。由此可见语域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相互交织性,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化都会导致语域的变化,所产生的变体也是繁复多变,无穷无尽。
四、社会语言学中的话语规约约束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对语域的讨论使我们明白,话语是在一个多维的社会环境中说出的,而这个环境中的各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对语言的形式变化起着作用,于是就有了对同一个人的不同的称呼,或者同样的话语内容的不同表达形式。然而,作为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必须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必须使用这样的话语?其回答是很简单的:“这只不过是一个规约问题,而规约一旦形成便成为必需。”[9]即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形式被认为比其他形式更有优越性,所以被规定下来,而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只能遵守这些规约,因为它们已经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听话者是我们生疏的上级,我们不得不采用表示尊重的语项;在一些被公认为正式的场合,我们不得不使用正式的语言变体,必要时我们不得不使用术语。
规约对社会有着很强的限制力量,其力量之大甚至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比如各种语言中都有一些语词,受着很强的社会规约的约束和限制而不能被使用,以至于成为禁忌语。如英语中的“shit”(粪便)之类的四字母庸俗词就被禁止使用,如果出版物中有这样的词汇,甚至会被起诉,而其它表示同样意义的词汇就不被约束,不是禁忌语。由此可见,规约的约束和限制力能够赋予词语以社会价值。
规约赋予词语以社会价值还在于,一旦违反这些规约所产生的力量。比如,禁忌语的作用还在于一旦使用这些词语所产生的特别的涵义,比如,某些禁忌语可能被用作抗议的符号,有时会表示一种强烈情绪的发泄等。而表示权势和亲疏的变体也有一套规约,因此在特定的情景中,故意违反这些规约就会产生非常的意义和效果。如不久前曾经在网络上出现的“什锦八宝”粉丝团,利用违反规约的词语称呼最高国家领导人而引发了数以亿计的网民心中一份强烈的情感。他们用“涛涛”“宝宝”分别称呼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十八大后,网络上曾经用“习大大”称呼习近平主席,引发广大网友的疯狂点击和转发。按照规约,这样的称呼只能用于同阶层的并且是亲密无间的人之间,而用来称呼国家领导人绝对违反了语言规约。但是,正是这样的违规的语言行为,表达了人民群众和国家领导人之间“零距离”的情感亲密程度,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的热爱之情。仅从情感表达的角度看,这样的表达形式所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歌功颂德的鸿篇巨制,更超越了表达情感的规范语词。
五、对语言变体研究的意义
对语言变体的研究使我们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有了新的或更深刻的认识:
(一)实际的语言世界是很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是语言变体产生的基础。语言作为交流和交往的工具,成了确立和维系社会群体间和个体间的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纽带。所以说,语言是社会的,更是人际的。
(二)人在语言构造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和生命形式,是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得语言有着繁复多变无穷无尽的语言变体,正是这些变体为语言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并不断促动着语言的发展。正如陈原先生所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10]
(三)在社会语言学的视界里,语言行为与社会成员的其他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多维的、动态的、交互的关系。人,借助语言与他人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并通过语言派生出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因此,研究语言必须联系人的语言行为以及与这些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行为构成的整体,透过异彩纷呈的语言变体,便可研究风格迥异的社会群体和寄生在语言行为之上的社会行为。因为,“人,只要是社会中的人,就必然地、毫无选择地生活在语言所成就的行为世界中,并在其中成其所为。”[11]
[1]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高佑梅.英美语言变体及其社会交际功能[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7).
[3][4][5][6][7][8][9](英)赫德森.社会语言学[M].丁信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陈原.语言和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