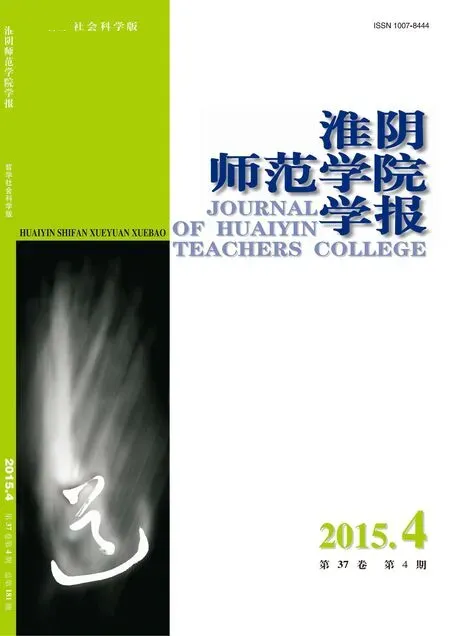晚清雅俗两派文学翻译观辨析
杜慧敏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上海201701)
一
晚清文学译介的“雅”“俗”之辨,客观上包含着从文本内部的译入语、译入文体、译介方式等方面分别对雅俗两派译作呈现方式的不同进行对比描述,对雅俗两派译作外部的译者(包括晚清众多小说期刊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交互往还及其与译作最终呈现方式的种种联系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由于这一研究课题本身具有比较文学译介学性质,探究并辨析晚清文学译介中雅俗两派的所有文化行为和结果背后的“文学翻译观”,则是一个根本性的任务。约瑟·朗贝尔说:“把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弄清哪些人从事翻译,以什么样的读者为对象,选择哪些文本,哪些体裁,哪种语言及言语,哪类文学风格和提纲,依据何种文学时尚、道德时尚、语言时尚和政治需求,此外,依据何种翻译观。”[1]194
所谓“文学翻译观”,指的是当时小说期刊编者、译者、译作读者如何看待“文学翻译”(包括如何看待原作、译作以及译者角色等)以及如何理解“译”的实质。译者认为翻译可以如此,读者也觉得翻译应该这样,那么“文学翻译”在他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再具体到晚清文学译介的雅俗两派,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又有哪些分歧和共通之处呢?苏珊·巴斯内特在谈到翻译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时曾说:“翻译学的第二阶段已经超越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而着重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的模式。其中的一大发展,是通过一个时期的翻译者在序言、书信、文章中谈及他们的译作时所使用的比喻,探讨当时的翻译观。”[2]190她以赫曼斯(Theo Hermans)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为例,强调了其对翻译的角色(role)和地位(status)的研究。可以说,她的这些观点为我们展开上述问题的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林译小说代表的是近代域外文学翻译文人化(雅化)的一脉,它与当时民间性的小说期刊译介代表的通俗方向(俗化)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于前者,这种研究思路尤其适用。当然,在面对这个既具有鲜明的晚清时代印记又表现为规整的个人翻译行为的重要研究对象时,我们会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作通盘考虑,而不仅仅局限在“比喻”上。
还需要补充的是,从晚清文学译介活动来看,不仅是译者,译作读者对于文学翻译也有他们的心理定位,虽然不及译者的那么清晰可辨,但也是了解译者翻译观非常重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译者和读者的翻译观最后都会集中地反映在译作之中,而译作所体现的正是译者在某种翻译观下的实际翻译操作。因此,从译作文本出发,对于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对翻译的观念和态度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
晚清文学译介中雅俗两派的翻译观的异同,可以从构成翻译过程的译者权限、译作与原作关系和“译”概念的实际应用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首先,从译者权限来说,小说期刊译者认为自己在文学(小说)翻译中有相当充分的主动权来决定译作的呈现形态。通过对晚清小说期刊具体译作文本的分析,我们知道小说期刊最主要的译介方式是“演述”和“译述”。“演述”是译者以原作的故事为本事,对原作内容或原作译稿更为丰富的重新讲述。“演”从“演义”之“演”,为敷衍、引申、发挥之意;“述”既是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口述、讲述,也是译者向中国读者描述自己在域外小说原作中所看到的东西。应该说,“演”“述”二字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翻译的含义比较远,它们不但没有强调要紧随原作的意义,而且在原作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给了译者更大的发挥空间。“译述”则是以充分凸显出原作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为重心,其“述”有概要讲述的意思。简单来说,前者是将原作充分扩大,后者是将原作合理缩小。在这两种模式中,译者都不是亦步亦趋、字斟句酌地紧随原作。译者认为自己有权利也应该不惜如何铺张敷衍、极尽所能地将原作的内容演说明白,或者删节原作的冗赘部分以使译作的情节发展更加紧凑。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小说期刊译者的观念中,译作虽然来自小说原作,但译者同作者同样享有处理作品的权利。
如果从林译小说序跋来看,林纾对于译者权限的理解更多的是保留在对原作内容的选择权上,“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鹰梯小豪杰》叙)[3]97。而且,正因为林纾自己不懂西文,反而增加了原作在他心中的分量,笔译所及,至少在态度上是遵从原作的。“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而又不解西文,则觅二三同志取西文口述,余为笔译。或喜或愕,一时颜色无定,似书中之人。即吾亲切之戚畹,遇难为悲,得志为喜,则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我牵丝矣。”(《鹰梯小豪杰》叙)[3]97林译《迦因小传》因此受到寅半生的批评:“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所百计弥缝而为迦因讳者,必欲历补之以彰其丑。”[3]116-117而林译小说译文的错误,一方面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3]134,“急就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亚郡主别传序》)[3]134。林译的删节原作、变换体例,应该主要与此相关;但另一方面“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3]260。对于林译增补原作的内里因由,钱先生谓“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3]263-264。
因此比较而言,雅俗两派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并不明确主张直译,也不认为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亦步亦趋的遵从原作。不同点则是观念和程度上的,即俗派的小说期刊译者挥舞着与原作者对等的权力,是“豪杰译”的风格;而雅派的林译对译者权限的滥用是有限制有规约的,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意译的范畴。
其次,从译作的文学地位来看,在晚清小说期刊上,虽然编者、译者和读者都知道这些小说作品译自域外,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重视原作而看轻译作。正相反,译者的任意删改不但不会因不忠实于原作而降低译作的地位,有时反而能够提升译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译作读者在对翻译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时,很少关心原作的情况;言之凿凿之处,仿佛译作(包括那些明确说明是经译者大量改动的译作)就是原作。可以说域外小说在经晚清小说期刊“媒介”引入晚清中国的普通读者阅读视野之时,其位置就被译作所占据。正如约瑟·朗贝尔所说的:“在文化生活与文学生活中,译作经常与很多范式有关,翻译家和/或他的读者们可以无视原作的存在,甚至把原作搁置一边。”[1]196晚清小说期刊的这种情况,当然和读者群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也就是阿英所说的读书人之外的“小市民层”[4]212,要让这些读者透过译作思考背后的原作如何,即使在今天都是相当困难的。
在这方面,林译小说的情况则更复杂一些,需要从译者和读者两方分别来考察。译者一方,单就林纾本人而言,他对所译原作及其作者的很大一部分都相当重视且尊敬,所写译作序跋字里行间推崇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因合作者的关系,对原作文学价值和作者水准的误判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曾锦漳先生在《林译的原本》一文中所梳理的那样[3]282;但究其本意,却没有如小说期刊翻译那般随意轻慢原作,甚至连原作者为谁、是哪个国家的都不晓得。读者一方,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3]145。可见林译小说读者对原作是接受且重视的。
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林译小说原作因译作的出色而被中国读者接受,而不是译作因原作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而被中国读者认可。回顾一下,林纾与人合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其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令人意外,“以华人之典科,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挥尘拾遗》)[3]244。这既鼓舞了林纾用他的文言继续翻译下去,也给了当时林译的读者阅读域外文学以巨大的信心。可以说,读者对林纾翻译的那些域外小说原作的承认,几乎完全是凭借了林纾文言笔传的功劳。这同时也解释了那些与林纾合作翻译的人,为什么他们读得懂原作,也已经口译了出来,却依然要依赖林纾文言的笔传。假设不是林纾这样的文笔,晚清的读书人阶层凭着自己的傲慢,大概是不那么愿意接受域外文学的。但也因为林译的读者多是阿英所谓的“知识阶层”[4]212,虽然对林纾的译本感兴趣,毕竟不肯仅仅满足于译作,于是又去探求原作的究竟。钱钟书就是典型的例子:“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3]259而小说期刊那样不顾原作的“豪杰译”,本身就缺乏对这类读者群的吸引力,自然也引不起他们探究原作的兴趣。
最后,“译”概念在晚清小说期刊上的应用多种多样,显示出小说期刊译介具有异常宽泛、内涵丰富的文学翻译观。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起首梳理了“译”和文学翻译的正统含义,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但译文总难免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也就是“讹”[3]256-257。然而晚清小说期刊上的所谓“译”却少见“化”,反而是“讹”更明显。“译”在晚清小说期刊译作中的称谓有“演述”(如《泰西历史演义》)、“演义”(如《好男儿》)、“衍义”(如《电术奇谈》)、“演”(如《山家奇遇》《理想美人》《斥候美谈》)、“译述”(如《二勇少年》《离魂病》《毒药案》《旅顺落难记》《八宝匣》《铁窗红泪记》)、“译意”(如《梅伦奎复仇案》《少女失父案》)、“译”(如《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中之人鬼》《宜春苑》《白丝线记》《毒蛇圈》)等,还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译意、润文”(如《海底旅行》)、“译意、润辞”(如《魔海》)、“口译、笔述”(如《紫绒冠》)、“述、笔”(如《血之花》)等。晚清小说期刊上对于并非译自原文,而是从其他译本转译之作的称谓也不一致,《绣像小说》上称吴梼转译自日译本的《山家奇遇》等为“重演”,而《新新小说》上则称冷血转译自日译本的《圣人欤盗贼欤》《巴黎之秘密》为“重译”。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文学翻译观中“演”和“译”有某些相通之处。将它们联系到其所指称的具体译作就知道,这些称谓都从某个角度丰富着“译”的“讹”的一面。有趣的是,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讹”是并不自以为病的理所当然。
如果说代表晚清文学译介俗派的小说期刊无论在“译”的称谓上还是在这些称谓的指称对象上都界限宽泛模糊的话,那么作为雅派代表的林译小说,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反映出当时文学翻译观的不明晰。林纾在自己译作的序跋中,有些时候笼统地把自己的翻译行为称为“译”“译述”,如“余译书近六十种”(《不如归》序),“虽然,吾译是书,吾意宁止是哉!”(《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余适译述此篇”(《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有些时候会明确说出与人合译的事实,如“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余泚笔记之”(《黑奴吁天录》序),“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黑奴吁天录》跋),“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而又不解西文,则觅二三同志取西文口述,余为笔译”(《鹰梯小豪杰》叙),林纾用了“口述笔记”“同译”“译著”“口述笔译”等,而这些对文学翻译的不同称谓仅指称一个清晰而单一的对象,就是“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3]134。
林纾不懂外文,在与人合作的文学翻译中他只能控制自己笔传的部分,而与他合作的人对文学翻译究竟作何理解,以及当时合译中的具体情形,因为几乎没有直接的材料,也无从得知。但林纾与原文隔了一层,在从口语到书面语、从口语到文言的信息转换过程中,其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性质非常突出。
三
通过这三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翻译观中,“译”有同文学创作非常接近的地方,由此可以把晚清小说期刊文学翻译观的核心概括为“重写”——确切地说是“戏谑的重写”。“重写”问题在当代翻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话题,安德烈·勒菲弗尔就(André Lefevere)认为:“重写(rewriting),不论其形式是评论还是翻译(或者还应加上撰史和结集),都已证明是一个文学的捍卫者用以改编(因时代或地理隔阂而)异于当时当地的文化规范的作品的重要手段,这个手段对于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可把重写视为一个文化接受‘外来’作品的证据,并从这个方面对之加以分析研究。”[2]191所谓“戏谑”,并非批判晚清小说期刊译者的态度不够认真,只是要点明小说期刊文学翻译观中没有特别强调对原作的绝对忠实,无论是为政治还是为消闲,都没有以原作为本位来看待翻译问题。与俗派相比较,我们把林译小说所代表的晚清时期雅派的文学翻译观概括为“创造性地笔传”。所谓“创造性”,并非指责林译删节增补原作等不能忠实于原作之处,而是强调其采用文言作译入语,开中国近代文言翻译域外小说之一代风气且蔚为大观,以及在当时中外两种缺乏沟通且彼此迥然不同的文学文化之间所形成的特殊而有效的传达。
将晚清雅俗两派的文学翻译观归纳为“创造性的笔传”和“戏谑的重写”,充分说明了文学翻译观是动态的、历史的,某个时代、某个文化领域的文学翻译观都会受到当时当地的整体文学风尚的影响和制约。这两种极具时代和文化特色的翻译观的形成,同当时文学翻译的民间性质关系极大。就小说期刊而言,他们的译稿主要是通过征稿启事从民间获得,尽管有编者把关,但稿源复杂,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更何况没有官方的介入,由吸引读者而获取现实经济利益仍然是多数译者们翻译小说来投稿的根本动力。如此一来,弊端当然很多。当时已经有人站出来批判,但形势还是无法扭转。比如新庵(周桂笙)《海底漫游记》:“而新译小说,则几几乎触处皆是。然欲求美备之作,亦大难事哉!……其尤黠者,稔知译书之价,信于著述之稿也,于是闭门杜造,面壁虚构,以欺人而自欺焉……惜乎其不能也,其技不过能加入一二口旁之人名而止矣。译者诸君,亦有漫不加察,而所译之书,往往与人雷同者。书贾不予调查,贸然印行者,亦往往而有。甚至学堂生徒,不专心肄业,而私译小说者,亦不一而足。”觚庵《觚庵漫笔》:“译者彼此重复,甚有此处出版已累月,而彼处又发行者,名称各异,黑白混淆,是真书之必须重译,而后来者果居上乘乎?实则操笔政者,卖稿以金钱为主义,买稿以得货尽义务;握财权者,类皆大腹贾人,更不问其中源委……彼此以市道相衡,而乃揭其假面具,日号于众曰:‘改良小说,改良社会。’呜呼!余欲无言……因艰于结构经营,运思布局,则以译书为便。”(《小说林》第七期,丁未年十一月)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之题名”:“种种方面,总以动人之注意为宗旨。今者竞尚译本,各不相侔,以致一册数译,彼此互见。”“综上年所印行者计之,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此著作与翻译之观念有等差,遂至影响于销行有等差,而使执笔者,亦不得不搜索诸东西籍,以迎合风尚。”(《小说林》第九期,戊申年正月)这是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文学翻译观得以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外因。晚清小说期刊译介一直都是民间行为,基本没有官方的参与,因此也不可能有硬性规则的介入。小说期刊译介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原作至上、尊重原作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尽管新小说家们都有域外小说有益民智和社会改良的模糊共识。从我们掌握的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相关材料来看,事实上,无论小说期刊编者还是小说译者,他们的理论文章和译作序跋大多数都在讨论如何改造小说原作来为我所用或者令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却很少有人注意强调原作的规范性。所以小说期刊译作的大部分都不能从是否遵守翻译规则的角度来看待,当时也不可能有明确而统一的文学翻译规范让译者们主动或被动地遵守。甚至在一般译者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翻译“规范”的概念。周桂笙在《月月小说》创刊之初,曾针对文学翻译规范化的问题倡议建立“译书交通公会”,以解“译书家声气不通,不相为谋”之弊。公会“简章”中规定:“凡各处会友开译一书,无论正书小说及无论何国文字,均须先将原书书名、译定书名及著书人之姓名用中西文详细开列,寄交本会书记注册。”(《月月小说》一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望日)但是,这种由某个译者以个人名义发起的倡议显然号召力和权威性都不足,“译书交通公会”仅在《月月小说》上报告了两次就难以为继了。如此基本的翻译规范在民间自发的状态下都难以执行,更无论其他。同小说期刊具有的松散集团性质不同,作为雅派代表的林译是一种更加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且从现有林纾亲自撰写的译作序跋中,也看不到涉及文言笔传的任何规则、规范性质的内容,林纾众多合译者分别或共同遵循何种翻译规则也不得而知。但很明显的是,这些合作者的外文水平、外国文学方面的修养是参差不齐的。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晚清十年以及后来的十来年间,林译小说主要是以单行本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同样没有官方的翻译规范介入,间接影响雅派文学翻译观的就只有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林译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了。而近代1900年以前有官方参与的西学译介的情况是值得参考的。至少在译者的素质方面,京师同文馆对翻译人员培训严格,《京师同文馆馆规》中有对生员八年学习的详细安排[5]338,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专门聘请外籍人士同中国比较精通科学的知识分子合作,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的规范化运作。而从翻译活动本身来说,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由于官方的扶植和参与,翻译规范作为一种观念得以在翻译人员之中确立,从而避免了很多无序的随意的想法和做法。如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叙述的翻译馆里十分严格的译书程序和方法,使得所译之书“讹则少而文法则精”[5]342。
对晚清小说期刊文学翻译观的这种总结是就整体而言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情况,如1906年创刊的《新世界小说社报》,其编者就规定所有小说译稿必须附寄译文原著,以保证作品质量。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小说期刊中影响并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研究也就是对晚清小说期刊如何重写域外小说的研究。如果将这些译作置于晚清小说期刊文学创作的背景下,所显现出的一些不易为人所发觉的问题就更能证明这一结论。首先,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作品中一直都存在着“译”同“著”和“编”杂糅一体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作家创作中可以有翻译的成分,在翻译时也可随意加入译者的创作。如《月月小说》中的《新庵译萃》,虽标为“译”,其实里面既有大量译者的时事评论,又有译者对国外报刊新闻的转述。再如《新小说》上以外国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有的就直接译自外国历史书。这种在文学作品的译、著和编之间自由穿梭的随意性做法,与晚清小说期刊所提供的文学格调和文学氛围非常一致。在晚清小说期刊的文学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榜》《镜花缘》等的几乎是无节制的续作和仿作。这些作品就着原来的人物或故事情节另外敷衍故事,虽然略有些讽刺现实的味道,但作者多是戏谑的态度,随意发挥又敷衍了事。从这里再来反观小说期刊译作的情形,就会发现二者几乎如出一辙。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从文学翻译出发论证了同一语言内部跨越时间段的理解也同样具有翻译的性质——“翻译过去的东西”[6]29。当然这种“翻译”也会有有意或无意地偏离“原作”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任何已有的小说文本,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看成原作,也都在晚清小说家们(翻译家们)的“戏谑”之列;而那些续作、仿作和译作只不过是晚清小说家们(译者们)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和另一种意图和需要下的重新叙述而已。区别在于一个是以外国小说为底本,一个是以中国小说为底本;一个发挥的程度有所拘束,一个毫无限制。
但是,这种表面的无序运作酝酿出晚清时期文学译介如此“特别”的文学翻译观,恰恰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本土文化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的一种态度,它们也是小说期刊这种具有鲜明民间性质的文化媒介给予文学翻译的某种特权,是大规模译介域外文学之初的“半真空”阶段给予文学翻译创造性的纵容。而在以小说期刊为媒介、以文言为译入语的中外文学文化发生关系时,这两种文学翻译观起到了既重要又十分微妙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特别”是相对于今天的域外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一般理论规范而言的。我们把小说期刊译介和林译看作晚清域外文学译介活动的两个典型代表,其不同的文学翻译观对晚清域外文学译介之整体具有表征意义。晚清的小说期刊、林纾及其众多合作者毕竟以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了域外小说译介活动,为那个时代奉献了、也为后世保留了那么多文学翻译作品,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译介的高潮亦由此而来。
[1] 马克·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 Bassnett,Susan.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M].Oxford:Blackwell,1993:146;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3] 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 Steiner,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