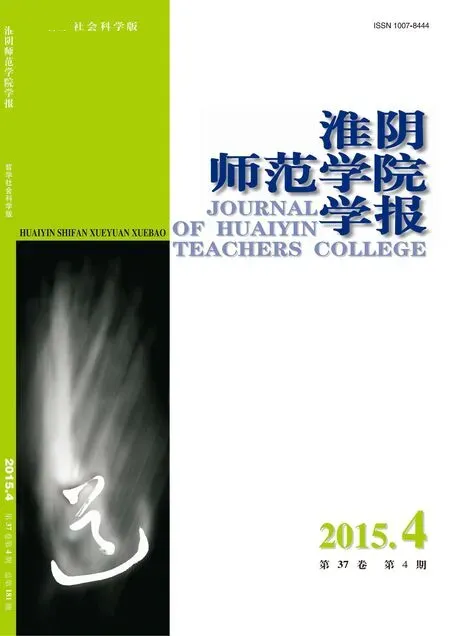论庄子哲学是可知论
——庄子认识论初探
周文华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争 鸣】
论庄子哲学是可知论
——庄子认识论初探
周文华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庄子是不可知论者,但对此的论证所依据的材料只是整个《庄子》的一部分,《庄子》中的很多其他材料都表明庄子是可知论者。通过仔细分析所有那些作为庄子哲学是不可知论的证据,发现对这些材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然而更为可信的解释,在新的解释下这些材料并不表明庄子哲学是不可知论。因此,庄子的认识论是可知论是唯一的且与所有的材料一致的合理的结论。通过分析《庄子》中对知与不知的关系的相关论述,指出《庄子》中貌似矛盾的陈述其实都有合理的解释。《庄子》所作的“知之所不知”与“知之所知”(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分,可以解决《庄子》中一方面主张“道不可言”,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对道的言说等悖论。
庄子;认识论;不可知论;怀疑论;悖论
一、前言
我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庄子的哲学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一点早被写进了影响颇大的教科书,如1982年出版的由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就明确指出:“相对主义是庄周哲学思想的核心”[1]162,“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必然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1]164。20年后,在2003年出版的北大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仍是持这样的观点[2]83。虽然学界不乏不同的声音,如李坚在1988年便论证说“庄子认识论不是不可知论”[3]95-98,杜志强在2006年也论证说“庄子认识论并非相对主义”[4]54-57,但应和者不多。原因除了他们的论证有较大漏洞外,主要在于:他们从《庄子》中的某些章句得出“庄子是可知论者”的结论,但另一些人则根据《庄子》中的另一些章句主张“庄子是不可知论者”,诚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这样的论证不能称为是证明,因为它没有用逻辑的力量让人真正信服。所以主流的观点并未有大的改变,如近来(2011)出版的张采民的新著《《庄子》研究》仍然说:“相对主义是庄子认识论的基本特征、理论核心”[5]119,“庄子过分地强调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的一面……就导致了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5]121。
但是,庄子究竟是可知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这是庄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在概念上,可以简单地说,可知论是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学说;而不可知论则否认这一点,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里的“世界”指存在者的总体,当然也包括现象世界或经验世界。从字面上看,任何不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要么是可知论者,要么是不可知论者。但实际上,他却可以既不是可知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怀疑论者。因为无论是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其立场都是独断的;因为你怎么知道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无论你怎么论证,你的论证是有前提的,甚至你的前提也是有其前提的,这些前提都是可以怀疑的。这里特别要强调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的区分,因为许多庄学论者认为,庄子是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法的自相矛盾或含糊性。例如,严金东就说:“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通常是等义的两个概念,本文也如此使用。”[6]36但我们将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分:主张任何事物都是可知的(对人类而言)、没有原则上不可知的事物,此即严格的或者说强可知论。主张至少有的事物是可知的(对人类而言)、而对是否有事物原则上是不可知的存而不论,此即一般的可知论。为可知论而非强可知论,就称为弱可知论。主张有的事物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如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此即一般的不可知论。主张任何客观事物(非人造的事物)都是不可知的(对人类而言),此即强不可知论。为不可知论而非强不可知论,就称为弱不可知论。一般认为,不可知论与可知论是对立的、矛盾的;但是,弱可知论与弱不可知论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同时成立。所以区分强弱可知论和强弱不可知论是必要的。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说一个人既是可知论者又是不可知论者(两者都在弱的意义上),而这种说法会引人误解。强可知论当然不是任何形式的不可知论,强不可知论也不会是任何形式的可知论,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界定弱可知论和弱不可知论。这时,我们需要追问:弱不可知论者认为的是什么东西不可知?康德区分现象和物自体。从概念上讲,现象就是向人显现的那一部分世界,或世界中向人显现的那些事物,它当然是可知的。康德只是说物自体不可知。神不可知论者通常也不否认我们知道很多事物。另一方面,那些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者,作为一种典型的可知论者,能不自相矛盾地说一切都可知吗?如果我们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物质,就要承认人的经验所及的世界很可能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部分;那样的话,那在人的经验世界之外的世界如何能被人们所认识?既然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范围并不超出经验世界,所以经验之外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种主张人们能认识经验之外的世界的人,就等于是主张人具有某种神秘的认识能力、人们不经过实践就能了解客观世界。为了论证一切都是可知的,就必须取消经验之外的客观世界。把经验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其理由实质上不过是“所谓的客观世界是经验的构造”的种种变形,这其实就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康德的“物自体”,所以黑格尔是强可知论者。因此,典型的可知论是说,经验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则上不可知的,却不说一切都是可知的。典型的可知论是一种弱可知论。
由于强不可知论者除了他们的这种不可知论的立场以外、还与怀疑论者一样对任何命题都是怀疑的,所以他们都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知识。而强可知论者认为一切可知。所以,很容易识别一个哲学家是不是强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者或强可知论者。区分可知与不可知的困难,当然是在弱的意义上,而这需要一个新的概念。
为了论证的简洁与清晰,本文后面把认为“经验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则上不可知的”的观点称为典型可知论,并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简称为“可知论”。而把认为“经验世界中存在原则上不可知的事物”的观点称为典型不可知论,并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简称为“不可知论”。典型可知论与典型不可知论是二分的。
本文的目的是证明庄子不是怀疑论者,而是典型可知论者。方法是从所有过去那些作为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证据出发,探其究竟,若仍能得出庄子是可知论者的结论,再加上已有的强有力的正面证据,这样,我们的结论与整个有关庄子的材料是一致的,不可推翻,从而使这样的结论成为定论,故为证明。当然,现今有关庄子的材料主要是《庄子》一书,其内容并非全部为庄子一人所作,因而其思想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它是庄子学派(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虽然研究庄子思想一般需要厘清哪些篇章是庄子自作,哪些为其后学所作,甚至是哪一类的后学所作;但在研究庄子的认识论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庄子》立场较为一致。而且,《庄子》有关认识论的思想主要集中于《齐物论》,其次是《秋水》与《知北游》。当今学界对《齐物论》代表庄子本人思想、对《秋水》和《知北游》属于庄子学派思想异议较少。因此,我们的证明不大依赖考证派对《庄子》各篇的考证结果,所以,行文中,为了简洁计,也不大区分庄子与其后学。在证明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已有的庄子是可知论者的主张及其论证。
二、回顾
现代学界中,也许严北溟和任继愈分别是“庄子不是不可知论者”和“庄子是可知论者”之说的开创者。严北溟(1980)说:“庄子并不怀疑客观世界的存在……庄子和其他道家一样,承认作为自然规律又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他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认识和掌握了‘道’的人……从这方面看,庄子就不算是真正的不可知论者。”[7]47。但他又留有余地地说:“很多同志同意庄子是不可知论者,这是有一定根据的”[7]47。那么,庄子究竟是不是不可知论者?严北溟对此态度暧昧。
任继愈(1981)明确地说:“庄子认为,世界是可知的”[8]359,其证据是《秋水》中的这一段: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但是,任继愈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的“《庄子》内篇代表后期庄学的思想,仅《庄子》的外、杂篇才可以看成庄子的思想”的观点上的,而这个观点与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正好相反。主流观点认为,《庄子》内篇更能代表庄子本人的思想,这在刘笑敢的文献疏证出来之后几成定论。但任继愈长期坚持认为内篇(尤其是《齐物论》)论证了不可知论[8]284;[8]322-326,所以,这对于相信内篇反映庄子本人思想的人来说,任继愈无异于是在说“庄子是不可知论者”。
如此看来,严北溟和任继愈只是提出了这种说法,却不实有其观点。那么,以“论庄子认识论不是不可知论”为论文题目的李坚似应实有其观点。该文对庄子的认识论有所阐发,但结合《庄子》文本的论证则嫌不足。且论文在最后一段总结说:“庄子……怀疑人们对具体事物现象的认识的真实性可靠性,怀疑人们通过认识具体事物现象进而认识道、认识本质的可能性……结果,他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论不可知论的倾向。”[3]98读到这里,人们似乎感到,李坚自己都没有力量坚持自己的论点,虽然他接着说:“其实,庄子认识论的主流和归宿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可知论,是包含某些不可知论因素的不彻底的可知论。”[3]98李坚的这个结论意味着,庄子的认识论包含着矛盾,或者李坚自己自相矛盾;而且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庄子那里不可知论不占主流。
刘笑敢(1988)也说过“庄子不是不可知论者”。他在其专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指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怀疑主义;另一方面是直觉主义”[9]162;认为“庄子的怀疑主义是不同于不可知主义的。不可知主义者是以确信现实为基础的……庄子却是以怀疑现实而著称于世的,他不相信感性经验……不可知主义所不知的是现实世界和现象背后的客观实在或客观本质,休谟认为引起人类感官印象的自在之物的有无是不可知的,康德虽然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却认为自在之物本身是不可认识的……只要我们不否认休谟、康德是不可知主义的主要代表,我们就应该承认庄子的认识论不同于不可知主义,庄子不是不可知论者”[9]174。所以,刘笑敢这里说的“不可知论”是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狭义的不可知论,而不是广义的不可知论。虽然刘笑敢已把庄子划为怀疑论,这等于已经把庄子排除在(广义的)不可知论和可知论之外;但刘笑敢又认为庄子主张“真知”,“真知即体道之知,即对道的直观体认”[9]162,所以“庄子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者”[9]167。实际上,庄子也不属于怀疑论,因为怀疑论是怀疑一切类型的知识。刘笑敢为了把庄子纳入怀疑论阵营,不惜修改“怀疑论”的概念,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似不可取。
之后,李纪轩(1990)便明确宣称庄子的认识论包含矛盾,“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矛盾交织及其统一,才是庄子认识论的基本特征”[10]1。李纪轩认为:“在庄子哲学中,道与物是相对立的范畴。他把对道的认识称为‘大知’、‘至知’或者‘真知’;而把对物的认识称为‘小知’”[10]1,进而论证说,庄子的观点是“小知”不可知,“真知”可知。张松辉(2009)的说法与此相近,他把与“真知”相对的世俗知识称为“俗知”,认为“庄子的认识论,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概括:排除俗知,追求真知,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者”[11]105。
但是,庄子的认识论真的自相矛盾吗?依李纪轩的解读,庄子认为物不可知而道可知,而非说同一对象既可知又不可知;依张松辉的解读,俗知是世俗人的知识,真知是真人的知识,而非说认识对象本身既可知又不可知。仔细读庄,可见其认识论条理井然,倒是我们对庄子的评价“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或统一”,显得不伦不类,或自相矛盾。
本来,可知与不可知,是针对认识对象(世界)而言的。若针对认识主体,仍用这种说法就犯了范畴错误,应改为“能知或不能知”。除非世人都是俗人,世上无真人或圣人,这就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但是,庄子显然认为,人们是可以得道的,世上是有真人的,虽然人数稀少;不然“得道”“心斋”之法就没有意义了。张松辉认为,“庄子……用事物的变化之快来否定事物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质,从而否定了世俗人正确认识事物的可能性,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当然这种不可知主要是针对世俗人讲的”[11]106,这似乎是在说庄子是不可知论者;但他又说:“庄子认为世俗人没有能力认识客观世界,而真人却具有这个能力。因此,把庄子认定为不可知论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1]108。张松辉的意思不难明白,但其说法却自相矛盾。针对某一类人来讲可知或不可知尤其错误。且他又说“庄子……没有完全否定世俗人的认识能力……”[11]106这也与其前述的说法自相矛盾。
以上简要的回顾表明,学界竟然没有人理直气壮地、首尾一致地对“庄子是可知论者”作出论证,尽管这一论题简单明白。
三、四问三不知
一般认为庄子持不可知论的典型证据在于《齐物论》中的这一段精彩对话(一共八句[段])。
(1)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2)曰:“吾恶乎知之?”
(3)“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4)曰:“吾恶乎知之?”
(5)“然则物无知邪?”
(6)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郩乱,吾恶能知其辩?”
(7)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8)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关锋(1961)对此处的评论是“不可知主义”[12]141;任继愈(1962)引此来证明:“对于主观认识能力,《齐物论》认为也是相对的,没有客观标准,因而得出认识不可能的结论”[8]323;萧萐父等引此来证明庄子认为“知与不知是不能证明和区分的”[1]166;冯友兰也认为,这一段“是论证知跟不知是没有什么分别”[13]406,且其中(6)的一部分表明了庄子的“相对主义的理论的一部分”[13]404,等等。这些对庄子的评价是中肯的吗?
纵然我们可以把王倪的观点等同于庄子本人的观点,但这里王倪是不是真的持不可知论呢?虽然他一连说了三句“吾恶乎知之?”(“我哪里知道呢?”或译为“我根据什么知道呢?”)但他在(6)中说得很清楚:“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不是知呢?)言下之意,他说不知其实正是一种知。这里并不是诡辩,因为他接下来对所谓“正处”“正味”“正色”的否定,表明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回答说知,因为,如果他是真正的完全的无知的话,则他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但他果断地否定了有所谓“正处”“正味”和“正色”。这表明,他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只是一种浅浅的有所知,比较常人之见甚至可以说他知之甚深。他说(6)这段话的意思是:“啮缺,如果我问你‘你知道天下的正色(正处、正味)是什么吗’,你能说你知道吗*因天下并无正色(正处、正味),故对此问题不能回答说“知道”。?所以,说知道的人难道不是一种无知吗!我说‘我不知’难道不正是一种知吗!因此我认为,像仁义是非这样更复杂的问题我是不知道它们的答案的。”
王倪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回答说知。因为,对于(1)(3)(5)这样的问题,回答说知道往往是一种无知和尚未深思的表现。例如,对于其中最简单的问题(3),如果译为“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吗?”很明显,一旦回答说“知道”,则必然导致矛盾:既知道A,又不知道A。
如果像孙雍长那样将(3)译为“您知道哪些是您所不知道的吗”[14]30,那么,回答说“知道”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你认为A、B、C、D都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么,你回答(3)说“知道”就说不通了。拿A来说,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A;我知道的只是‘我不知道A’,而不是A;我关于自己的知识状况是清楚的”。对你而言,你至少知道A与B、C、D等都不同,知道A的名字是“A”,还知道你不知道它,且不提对于具体事物A你还有许多其他你未意识到的知识,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A呢?你怎么能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A呢?因为不知道就应该是全部不知道,部分地不知道就是说部分地知道。也许你说:关于A我只知道这么多,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难道我们对于绝大部分事物的知识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即都是部分地知,而不是全部的知)?比如关于人,我们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是要死的;但是关于人,我们不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方面还不清楚吗?我们不是也承认未知的方面要比已知的方面多得多吗?谁能制定出这样的标准说知道多少才算知道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于A是有所知的,否则,都无法把它说出来。况且,要回答“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的问题,只说A、B、C、D并没有回答完这个问题,因为还有E、F、G你不知道;而且,你无法列举完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那是无穷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既然这样,你就不能说“你知道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对(3)的回答,不能是“我知道”。
可不可以对(3)回答“我不知道”呢?如果这样的回答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回答似乎没错。但是,如果这种回答被解读为“我不知道哪些是我所不知道的”,那么,这样的回答就是错的:因为事实上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而王倪的回答,则不会被这样错误地解读,反而可以激发人们的深入思考,所以是一种较高明的回答。
而(1)和(5)则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更复杂的哲学问题,同样不宜简单地回答一句“知道”。王倪的回答比较实际也比较高明:“我怎么知道呢(我根据什么知道呢)?”这并不是故作玄奥,因为他确实没有充足的理由说他知道。不可因他这样回答问题就说他是不可知论者。
第(8)句是王倪关于“至人”所说的,他知道“至人”如何如何,这也绝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所说的话。
再看这一对话,啮缺的前三问王倪,而王倪三次均答以“吾恶乎知之”,这固然与答以“吾知之”不同,但与回答以“吾不知”也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啮缺没有理会到其中的区别(我们还要注意这与回答以“吾人不可知之”也有微妙的重要的区别)。于是,啮缺便推断王倪认为利害也是不可知的,啮缺的确认为王倪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为了驳王倪,他抬出“至人”,因为他认为“至人”总应该是知道利害的吧。因此,啮缺并没有领悟王倪在(6)中所说的真正意思,对话者之间心灵并未真正沟通,这预示着这对话不会长续下去。所以在(8)中,王倪都不愿回答是否至人不知利害,而只是说,连死生对至人而言都算不了什么,何况微不足道的利害!
也许人们根据王倪的“一贯”回答“吾恶乎知之?”而断定他是怀疑论者而不是“不可知论者”,因为王倪并不是答以“吾不知之”。但我们并不认为王倪是怀疑论者。怀疑论的代表是古希腊的皮罗(Pyrrho,约BC360—BC270),他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我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的或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15]177。王倪则在(6)和(8)中发表了不少的看法,只是啮缺没有听出他的“不知”的底下的知。我们不能因为他对某三个或四个问题回答说不知道,就认为他对一切都不知道或他主张一切都不可知。我们任何人都有很多不知道的问题,但我们并不都是不可知论者。啮缺对于王倪从来没有简单地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的每个问题予以反诘这一点没有充分地注意(不可知论相当于主张“物无知”,但王倪对于啮缺的(5)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啮缺所以为的“物无知”而是“吾恶乎知之”)。但如果我们的认识水平也像啮缺一样,那就连王倪也达不到,更谈不上妄论庄子了。
值得注意的是,《齐物论》中的这一段明明是“四问三不知”,很多人却把它说成是“三问三不知”[12]140;而《应帝王》的首章却说“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如果《应帝王》中的对话不是另有所指,且这里的“四不知”也不像是“三不知”之笔误,那就说明,《应帝王》中这一章的作者并非《齐物论》的作者,而且《应帝王》较《齐物论》为晚出。因为作者大概不会弄错自己曾精心设计的写作细节。
四、是非
有人根据《齐物论》中的下面一段(9),说庄子认为“是非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不可知”[2]85。这一段是:
(9)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胜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我乎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任继愈认为庄子这里是表明“决定是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主客观的、共同的标准”[8]326;萧萐父等引此并由之而得出“庄周把对是、非的判断局限在主观领域,否认真理有客观标准,真理不是愈辩愈明而是永远说不清楚”[1]164-165。诸家对此看法较一致;但我们仔细读原文,却得出颇为不同的结论。
庄子(9)这里的确是在讲,辩论不能分出谁是谁非,辩论的胜方的观点不一定是真的,在辩论中没有人能代表正确的观点(或最高权威)来评判各方的是非(吾谁使正之?恶能正之?)。但这里恰恰是指出是非不能用主观标准来定,并没有说是非没有客观标准。当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们就和庄子一样主张没有哪个个人或权威是真理的标准。这里庄子丝毫没有否定有真假、有是非,即他所说的“果是”“果非”;也没有说一切是非均无法判断;只是说辩论不出是非来。在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是非之争,也有许多是非至今未能辩论出个结果来,我们也不主张靠辩论来定真理;但我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可知论者,因为有很多大家公认的知识。庄子也并没有说过在他的时代没有任何大家公认的知识,庄子从没有说过一切都不可知之类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要说庄子是不可知论呢?
当然,“知”的问题与“是非”关系很大。因为,可知与不可知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命题的真假可不可以确定的问题,这后者也就是“辨是非”的问题。如果一切均可知,那么一切“是非”均可辨。如果一切“是非”均可辨,那么一切也均可知。如果一切“是非”均不可辨,那么一切也均不可知。但是,如果情况是有的“是非”可辨、有的“是非”不可辨,那这仍然是可知论(是弱可知论)。所以,要论证庄子是不可知论者,先论证庄子认为“是非不可辨”,这一策略看来行得通,因为庄子借王倪之口在(6)中说了“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郩乱,吾恶能知其辩?”但是王倪的“是非莫辩”之论,毕竟不能等同于庄子之论,而且王倪是在特定语境下说的这话:一方面,王倪这里没有否定有是非,而只是说难以辨是非;另一方面,(6)中的“是非”,也不能理解为一切之是非,它只是当时人们分歧颇大的有关“仁义道德正邪美丑”这类价值论方面的是非。但认识论中的是非(真假),则横跨事实与价值两大领域。
何况庄子对于(9)中所述的是非莫辩的情况,提出了他的处理办法或态度,这就是《齐物论》中的:
(10)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
其中的关键是“化声之相待”,这里,它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由于(10)是接着前面(9)的“而待彼也邪”来的,“化声之相待”意思就是“停止是非争辩之声而‘待彼’”,“彼”是指现实或经验世界。因为言论不是空洞的,言论之“此”是涉及现实世界之“彼”的,故言论之是非有待于对现实世界的更深入的了解才能解决。因此,这里与今天说的“用实践或实验来解决争端”意思差不多。其二,把“化声之相待”解释为“是非两种对立意见彼此之相待”而言,“相待”就是并行不悖;“化声之相待”就是说看到,所谓“是”与“非”两种意见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同时成立、互相补充,它们只是语言形式上的对立而已。庄子对此有很多例子,拿前面句子(6)中的例子而言:鳅以“湿”为正处,猿猴以树为正处,人类说这二者都不是正处,问“三者孰知正处”?其实这里的“是”与“非”就是“相待”而不相悖的,答案是:“湿”是鳅之正处,树是猿猴之正处,二者对人而言均非正处。另一个《齐物论》中的例子是“彭祖为夭”。大家都以“彭祖寿”为是、“彭祖为夭”为非,但这里的“是”与“非”只是语言形式的对立,也是相待而不相悖的:因为彭祖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为寿,但相对于寿为彭祖百倍的存在者而言却为夭。我个人猜测,也许这第二种解释更符合庄子的本意。但无论哪种解释,都不是不可知论。
当然,是非之争并不都是这种情况,两种相互争论的意见,可能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对立,而确实是相互矛盾的。这时“化声之相待”就做不到了,对此,由(10)知,庄子的办法是“和之以天倪”。庄子解释说:
(11)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
所以,庄子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是不是,然不然”。关锋却说庄子这里“作出了绝对否定认识的结论”[12]144,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整个这一段的预设是“我与若辩”,见(9),即双方对某事物的是非看法不一致,但并没有认为双方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不一致。这个预设为(11)中的“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所印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事事争辩。而对于正在争辩的是非,庄子指出“倘若‘是’果真为‘是’,那么‘是’的异于‘不是’就无须争辩”[14]35,这实际是提醒人们,自己不一定是对的,对方不一定是错的,所以才要求人们“是不是,然不然”。孙雍长将此译为“在‘不是’中看到‘是’,在‘不然’中看到‘然’”[14]35,我很赞同。用庄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见《齐物论》)。这对当时的百家百派彼此争论不休,各自固执己见,却不愿意耐心听取对方的意见、汲取对方之长的情况而言,可谓切中时弊,堪称济世良方。但由此进而认为庄子这里持“否认是非有客观标准的不可知论的观点”[8]326,则是强加于庄子了。因为庄子并没有说,在双方观点一致时还要“是不是,然不然”。庄子的方法“和之以天倪”的运用是有前提的,见(10),这已为“若其不相待”中的“若”所挑明。
要而言之,庄子的“是不是”,不是把“不是”等同于“是”,不是“是非不分”。因为这里说的“是非”,并非抽象的是非,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是非,即关于某个特定事情的命题;实际中人们争论的也是具体的是非,即有的人认为这个命题为真(是)、有的人认为这个命题为假(非),而非没有特定命题的抽象的是非。人们对于在他们看来是“是非彰显”的事情,当然不会有真实的争辩。但是,无疑也有很多事情的是非,人们对之争论不休。
要论证庄子是不可知论者,就要论证庄子认为“一切是非均不可辨”的,对此的最好论证,也许就是证明庄子主张取消是非之分。而最能说明庄子主张取消是非之分的也许是《齐物论》中的这一段:
(12)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因为这里明确谈到“未始有是非”以及“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但是庄子这里却承认有知识:“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这当然是可知论者的论调。
撇开这一点不谈,既然庄子在其中讲了“未始有是非”,是否由此可以得出“庄子主张取消是非之分”呢?(12)中谈到四种知的境界或层次:最高的是认为“世界本无物”(简称“无物”),第二个层次是认为“有事物但事物与事物之间并无严格的界线”(简称“无界”),第三个层次是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界线但世界本无是非之分”(简称“无断”),最低的层次才认为“有是非之分”(简称“常见”)。这四种认识和境界,有高低之分却没有真假(是非)之分,尽管它们在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但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所以并行不悖、井然有序。世人或众人的认识是处在这最低的层次上,而真人、至人或神人则处在高的层次。最高层次的认识是得道者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从较低层次的认识发展而来的,类似的描述见《庄子》中的《大宗师》:
(13)吾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这里的“无古今”与(12)中的“无物”一样,是对处于最高层次(境界)认识的一种描述。此外,尚有“见独”“朝彻”“外生”“外物”“外天下”等阶段,而且都不在普通人的认识层次。它们与前面所述的四层次是如何对应的尚不清楚,这二者间的差异也许说明,(12)与(13)至少有一个只具有寓言的性质,而不可过于当真对待。显然(12)中的描述更有义理。这四个层次都是对世界的看法,都是认识,但只在“常见”的层次才有是非。但是,如果认为“常见”的认识是错的、更高层次的认识——例如“无物”层次的认识——才是对的,那么,这也是没有弄懂庄子,因为这也是“遣是非”,是一种常见。庄子虽然更崇尚“无物”的至知,却不以“常见”为误为非。崔大华认为庄子在(12)中的划分“实际是三个等级”[16]292,我们认为他这是对庄子的一种错误解读;他认为庄子对认识是按照三种不同的认识对象——即他所说的“道”“理”“万物”——来划分的,这不符合(12)的本义。我们认为,庄子所说的认识对象是同一个,这可以证之以《秋水》中北海若的下面一段话:
(14)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15)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16)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17)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这里众多“观之”中的“之”,当然指的是同一对象,只是视角不同,这里谈到六种不同视角。虽然庄子说“物无贵贱”,却认为视角有高低,站在道的视角是最高的。同样,(12)中所提到的四个层次的认识,认识对象都是这个世界,只是视角不同,所以所见不同。这正如我们因所处远近高低的不同,看同一个建筑物会有不同的形象一样。因此,这种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所见,并不矛盾。且(15)(16)(17)中,明确谈到“知……”又印证了“庄子是可知论者”之说。这一段也谈到“是非”的相对性,却没有将“是”与“非”等同,例如(17)中说“尧、桀之自然而相非”,显然不能改成说“尧、桀之自非而相然”。(17)中说万物可以为“然”也可以为“非”,但同时说明了其为“然”为“非”的条件。
所以,庄子在(12)中并非说“无是非”,而是说如何看待是非之争。他推崇站在道的角度看,但是“道”的“无物”之见,却是建立在“常见”的“有是非”的基础上。只有经过一番修炼或“心斋”,才能从“常见”进到“无断”,再进到“无界”,再进到“无物”或“道”见。“道”超越了“常见”,却不是简单的否定。如果说一般的知识论是平面的话,那么,庄子的知识论是立体的、有高低之分的,这高低之分却不是对错是非之分。不过,在最低层次上,还是有是非之分的。哲学上“可知”与“不可知”的界定,本身就是在有物、有界、有断(有判断之是非)的层次上,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庄子所描述的更高层次上。
《齐物论》中涉及是非之争的还有这一段:
(18)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19)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20)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21)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22)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23)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萧萐父等引用(23)以表明庄子认为“是非观念既然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是和真正的非”[1]165。任继愈认为(22)“是说是与非,彼与此,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对立面的关系,没有对立,自然也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分辨”[8]326;并指(23)意为“是非”是“搞不清楚”[8]326的。崔大华引用(22)表明庄子认为“对于作为宇宙总体的‘道’来说,彼此是非的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16]281。
真是如此吗?由(18)可以看出,“道”虽然无处不在(参见《知北游》),但有显隐之分。道显则其真无辩,道隐则众人对其真伪莫辨。同理,“言”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也有显隐之分。言显则其是非无辩,言隐则众人对其是非莫辨。所以(19)接着指出,儒墨的是非之争就是这个缘故。是非之争的过程就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过程。(20)指出,对待是非之争的办法最好是“以明”。“以明”就是使其由隐而显。对(21),各家解释差别不大。在(22)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表明人们到处都在作是非判断,或者说人们到处在争辩是非。(22)后四句意思是说:但这些人都只是各执一端,“彼是莫得其偶”,都没有抓住那“一端”的对立面,即“中心”,这个“中心”称为“道枢”;抓住了“中心”,就能应对周边的无穷之端。(23)指出:在是非之争中,为“是”的理由是无穷无尽的,为“非”的理由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解决是非之争的方法最好是“以明”。
以上是我们对这一段的不同于各家的解读。根据我们的解读,庄子只是认为人们对于事情的是与非的看法是变化的,但并非说“没有是与非这回事”。我们对“以明”的解释非常自然。让我们看看庄子本人对“以明”的解释(见《齐物论》):
(24)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大意是:“用华丽的言辞迷惑世人,炫耀自己(的才学或深奥),这种行为是圣人所鄙视的。因此,不用华丽的言辞,而用日常平直的语言来表明其中的意义,这就是‘以明’”。这里的译法参考了(18)中所说的“言隐于荣华”。我觉得这样解释“以明”较合乎庄子本意。
崔大华总结了历来对“以明”的三种不同的解释。他较认同第三种解释,即“以本然观照对立观点,则是非可泯”[16]281-282;认为庄子主张用“以明”来“泯除是非对立的界限”[16]281;并认为“这个‘明’实际上就是‘道’,就是‘天’”[16]282。其根据是(21)中的“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但这句话也不过是说:“所以圣人不用华丽的言辞,但其义理(道)则大白于天下,(如天日昭昭)”;这个意义与《知北游》中的“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有相通之处。在我看来,“以明”的本来意义并不直接涉及“是非”,他们的解释有些牵强。
因此,人们说庄子主张“无是非”“齐是非”[13]409“和是非”[16]280“是非无分别”[16]280等,都是对庄子的误读。《庄子》通篇没有这样的词句。认为庄子主张“和是非”的最大证据不过是《齐物论》中的这句话:
(25)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但(25)中的实际用词却是“和之以是非”,这与“和是非”当然不同。“和之以是非”在整个《庄子》中都找不到依据,与庄子思想不合。庄子只说过“和之以天倪”,此处的“和之以是非”甚至有些文理不通,我认为一定是在抄写中发生了错误。很可能(25)这句话本来是“是以圣人和之以天钧,而休乎是非,是之谓两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前疑尽释,“两行”就是指的“是”与“非”两行。
五、梦
《庄子》书中多次谈到梦。仅《齐物论》中就有两段完整的梦境描写,最著名的一段是:
(26)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有人认为,这也是庄子持不可知论的证据,因为“庄子认为甚至人究竟是在做梦还是醒着,人究竟是否可能有认识,也都是值得怀疑的”[2]84。任继愈指出庄子这是“用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说明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最后的结论是,不但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就是最高智慧的‘至人’也不能解答这个问题”[8]324。张松辉也引(26)说“正是由于不可知论在作怪,庄子竟然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个人呢?还是只蝴蝶?”[11]106
《齐物论》中另一段是长梧子对瞿鹊子说的:
(27)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萧萐父等引(27)来说明“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对人的认识能力,也抱绝对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人生与认识均如梦幻……庄子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自以为觉醒,自以为有知,其实在真正觉醒者看来,那是在做大梦啊!哪有什么可靠的知识呢?”[1]167
但在我们看来,(26)中庄子强调“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这绝不是不可知论的论调。而且,庄子以此来讲解有关“物化”的知识。不能区分梦与醒,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不独为不可知论者的主张。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实际在梦中、却自以为是醒的经历,只是醒来后才发觉原来是在做梦。刘笑敢认为,庄子这里是诡辩,“梦中不知,但醒来之后梦醒之分还是很清楚的,故意混淆梦与醒是一种诡辩”[9]185。但是,刘笑敢并没有给出区分梦与醒的标准,因为问题正在于我们现在是做梦还是醒着?醒来之后能区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梦中能区分,但刘笑敢却承认“梦中不知”。所以,刘笑敢没有弄懂庄子这里的论证力量。
(27)中明确地批评愚者的“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其实一切皆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人生如梦”或“人生是梦”论(简称“梦论”)与不可知论的区别。不可知论否认任何知识的可能性,它所唯一肯定的就是“一切皆不可知”。如果连它的基本命题“一切皆不可知”也否定,它就变成怀疑论,只好对一切“不作任何判断”。“梦论”认为的“一切皆梦”是指一切境遇(包括各种感觉)是梦境,“梦论”所否定的只是感性知识的真实性,而非否定一切知识。“梦论”甚至没有否定“不能区分醒和梦”。笛卡尔曾用一切可能是梦来作为他的普遍怀疑的根据,他考察了这个看来这么实实在在的又是我们经常所有的感觉:“比如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17]15-16但笛卡尔接着说:“有多少次我夜里梦见我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在炉火旁边,虽然(实际上)我是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被窝里……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17]16但不会有人认为笛卡尔是不可知论者,因为他通过怀疑一切而找到“我思故我在”这样一条无可怀疑的知识。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庄子或长梧子谈到难以分别梦与醒从而难以分别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不能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皆梦就认为这是不可知论,况且庄子没有像笛卡尔那样从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进展到怀疑一切。
六、认识的可能和必要
有人认为“庄子完全否定了认识的可能和必要”[2]85,其根据是《养生主》中的这一段:
(28)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任继愈(1962)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以‘不能知’来论证的不可知论”[8]325。刘笑敢(1988)认为这里“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9]163。张松辉(2009)从这里得出“庄子就告诫人们:客观事物是不可知的,因而也是不必知的”[11]110。
为了弄清庄子是否持不可知论,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庄子》中的这类论证。近来不少人较系统地梳理了《庄子》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的论证,如崔大华(1992)[16]270-273、王威威(2009)[18]106-109、张采民(2011)[5]114-119等,并把这归结为庄子对认识相对性的论证。但主张认识是相对的并不等于否定认识的可能,所以本文着重从它们与不可知论的关系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论证。
《庄子》对认识过程有较细致的刻画,《庚桑楚》中写道:
(29)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
就是说:“认识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接触和匹配;认识就是认识主体的思考和见解。认识主体有所不知,这正如人的眼睛斜视时有所未见。”这里谈到认识的三个方面:认识主体、认识对象、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接触和匹配。这三个方面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认识才有可能。《大宗师》中曾部分地谈及这个问题:
(30)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其大意是:“但是,认识是否可能仍是需要顾虑的:因为认识必须有认识对象才可能谈得上恰当与否,而认识对象却常常没有固定。例如,您怎么知道我所说的‘自然’不是‘人为’呢?我所说的‘人为’不是‘自然’的呢?再说,认识主体必须是‘真人’,然后才会有‘真知’。”当然,《大宗师》的主题是“真人”与其“道”,我们此处却更关注庄子是怎么看待“众人”与其“知”的。
让我们依次来探讨庄子所述的使(众人的)认识成为可能时这三个方面所要满足的条件,如此我们便很容易知道:只要这些条件有一个没有满足,认识将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能表明这些条件不可能都满足,那就完成了不可知论的论证。
首先是认识主体所要满足的条件。《逍遥游》中说:
(31)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
这就是说,认识主体必须有一定的感知能力和智力(统称为认识机能);缺乏某种认识机能,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认识之可能。《人间世》中也明确地说:
(32)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
这里的“有知”与“无知”分别指有智力与无智力。智力对知的作用正如鸟之翼对其飞的作用。《逍遥游》还说:
(33)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这是说:认识主体的智力越高越好,认识主体的寿命越长越好。也就是说,认识主体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相关的认识活动、获得相应的认识才有可能。庄子并没有专门从主体角度来论证不可知。
第二,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接触和匹配所要满足的条件。粗略地看,就是要考察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否接触和匹配。人们目前所提出的《庄子》中对不可知论的论证大多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证的。前面(28)中,认识主体是个人,其生命有限、能力有限,而认识对象是无限的知识领域,二者当然不匹配。所以,结论是个人要掌握全部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类似的观点见《秋水》:
(34)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根据二者是否接触和匹配,庄子甚至比(28)(34)的论证“人们有限的生命不能掌握无限的知识、不能对无限的对象有知识”更进一层,还论证了“人们也不能认识某些有限的事物”,如《逍遥游》中这一段:
(35)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朝菌的生命只有一个早晨,无法接触和体验一整天,当然不知道早晚之分;蟪蛄的生命只有一个季度,当然不知春秋之别。人们可以依理而推:人的生命不足百年,当然也不知道很多尽管有限但却时间要长得多的事物。又如《秋水》中的这两段:
(36)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37)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郛,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在(36)中说明认识主体所处的时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地点(井蛙不可以语于海)、教育背景(曲士不可以语于道)等都会造成他不能正确认识某些对象,尽管这些对象也都是有限的。关键是,主体从未经历过与这些认识对象相类似的对象,即认识对象超出了认识主体的眼界,所以这种情况也属于二者的一种不匹配。(37)则指出,认识对象对于认识主体过大或过小,都是不适于主体来认识的;且有些对象(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是不能被认识的。因此,(37)也是谈论某些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不匹配。
庄子还谈到人的认识机能所能达到的对对象的把握程度不及对象本身所拥有的程度,见《徐无鬼》中这一节:
(38)故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祸之长也兹萃。
崔大华对(38)前三句的解读是:“人的视力对于‘明’来说,听觉对于‘聪’来说,都是差之甚远的;人能够知道、想到的比起他不能知道、想到的,是很少的”[16]271;并指出生理学支持庄子的这种看法:“人类视力所能接受的光线波长是在400—700毫微米之间,只占整个电磁光谱的1/70;人类的耳只能听到20—2 000赫兹频率范围内的声音,而并不能听到弥漫于宇宙空间的所有的声音。”[16]271这可以看做庄子认为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不可能完全匹配。
以上所举的(28)(31)(34)—(38)这些论证,当然都是有道理的,但这是否证明了庄子是不可知论者呢?
(28)固然可以说是否定了认识的必要,但恰恰是承认了认识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庄子这里指出,知识是无穷的,人们要想拥有无穷的知识、要想全知是不可能的,哪个可知论者对此有异议呢?庄子不主张“为知”、不推崇求知,正是因为他承认人们有一定的(部分的)知识和有人在求知。当然,我们不同意庄子的“弃知”或“反知”之见。
(31)论证“正如人的形体有聋盲一样,人的智力或知识也是有缺陷的”。这个结论有两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指“有的人的智力或知识是有缺陷的”,对此可以反驳说:正如大多少人不是聋子盲人一样,大多数人的智力或知识也是正常水平;也许某些人是无知的,但至少有人是拥有知识的;就是说,知识(或认识)是可能的。另一是指“所有人的智力或知识是有缺陷的”,对此可以反驳说:这正是人的智力或知识的特点,每个人都是有限的生命,不是全知全能,而我们所说的“知识”正是指人的知识而不是神的知识。人拥有人的知识,这个结论不会因为这种知识有缺陷而改变。庄子这里恰恰是承认了“人拥有人的知识”。由于这些反驳的存在,从(31)得不出不可知论的结论。
(34)明确地说了,人有所知、有所不知,只不过“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这是可知论。
(35)论证了“朝菌不能认识晦朔,蟪蛄不能认识春秋”,从而“人们也不能认识某些有限的事物”。其原因是:晦朔超出了朝菌的经验,春秋也不在蟪蛄的经验范围之内。类似地,人们也不能认识人类经验之外的世界。但这正是典型可知论的观点。
对于(36),我们可以说:“井蛙不知海,然而海龟知海;某些人限于眼界等原因不知某些事,但是这不能否定另外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庄子这里论证的只是“某些人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哪怕是有限的某些事情”,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却是就人类而言的。而且,这里的井蛙不知海,是由于井蛙没有经验过海。所以(36)所讲的不可知,至多与(35)一样,是指人们对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无知,即也属于典型可知论的观点。
(37)指出有些事物难于认识,宏观和微观事物要比普通事物难于认识,这是符合实际的。有些事物(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无法认识,但这些事物连“意”都不能察,足以说明它在经验世界之外。所以,这并不与典型可知论有什么不同。
(38),即使按崔大华的解释,也不是不可知论的观点。而孙雍长把它译为:“所以追求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眼睛就危险了,追求对一切都听得明明白白那耳朵就危险了,追求对一切道理都能迅速想通那心灵就危险了。大凡才能对于那相应的脏腑器官都是一种危险,危险一旦形成便将后悔莫及,灾祸增长并将越来越积聚。”[14]340-341这就更不是不可知论的观点,而是“反知”的观点,即否认过分追求认识的必要性。这有点像“聪明反被聪明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话。人们对现代技术的发展也有这类担忧:汽车的普及会不会造成石油资源的枯竭?核技术的发展会不会造成人类的灭绝?
第三,认识对象所要满足的条件。例如,张松辉就说过“庄子……用事物的变化之快来否定事物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质,从而否定了世俗人正确认识事物的可能性,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11]106。这似乎意味着不变化、至少变化不太快,是一个对象可能被认识的一个条件。说变化快的事物比变化慢的事物更难认识,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不等于说“变化的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庄子也没有这样说过,怎么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呢?张松辉的依据是(30)这句话。张把它解释成:“因为认识必须依赖于所认识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刚才你认识某一事物是‘天’,可当你刚刚完成这一认识并把它表达出来时,‘天’已经变成了‘人’,认识对象已经变了,而你的认识还没有变,于是你就大错特错。”[11]106姑且不论张的解释是否符合(30),这里只是说“认识对象已经变了,而你的认识还没有变”,却没有论证“你的认识不可能随着认识对象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并不能得出认识对象不可知的结论。有趣的是,张松辉在同一处继续说“庄子承认客观事物可以认识,承认认识对象不断变化”,这也就是承认庄子是可知论者,承认庄子认为变化的对象也是可以认识的。这与他接着说的“庄子……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是矛盾的。
张松辉还举了一个《田子方》中的例子以说明庄子有“认识对象‘不断变化,难以认识’”的思想:
(39)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
张认为这个例子中的认识对象是孔子的思想,认识主体是颜回:“当颜回认识孔子的思想并想去效仿时,孔子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颜回对孔子的认识总是慢了半拍,因此颜回一生也没有能够真正认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11]107但是,我们必须注意,(39)是孔子的话中的一段,孔子当然明白自己的思想,即同一认识对象对另一认识主体(孔子)而言并不难以认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例证。
《秋水》中还有一段为诸家所提到:
(40)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见任继愈[8]360、崔大华[16]272、王威威[18]117、张松辉[11]111、刘苗[19]18、张采民[5]118。一般引此来论证庄子认为人的认识受时代的局限、“相同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不总是一样的,而是因‘时’而变的,相对的”[16]273;[19]18、“庄子……悟出认识是相对的”[8]360,即认为庄子这里是为相对主义作论证。甚至有的说:“因此,时代的局限,也会造成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5]119其实,(40)谈的仍然是认识对象的“因时而变”,而不是谈认识主体的;谈的是“争让”与“兴亡”关系的复杂性。同一类行为,有的称为“义”有的称为“不义”,也是在表明事物的复杂性。复杂的事物较难认识,但并非不可认识。当然,像张松辉那样,把(40)看成是在论证“事物在变、社会在变”[11]111,从而“企图把一种道理奉为绝对真理,应用于一切时代必然犯错误”[8]360,也未尚不可。
如果庄子真的认为“变化的对象不可认识”,那就可以论证庄子是强不可知论者,即他会认为任何对象都不可认识,因为可以找到庄子认为“万物皆变”的证据,《天下》篇云:
(41)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
《秋水》中也说:
(42)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就是说:万物的生长如同快马奔驰,没有哪一个活动不在变化,没有哪一个时刻不在变迁。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十分惊人,(21)中是这样描述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刘苗就是据此来论证庄子认为“认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认识对象的变易性就成为阻碍人们正确把握事物的首要的客观因素”[19]13。张采民也引(42)而替庄子论证说:“天地万物无一例外、无界限、无条件地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就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无限性。在瞬息万变的客观存在面前,人的认知是无法跟得上事物的迅疾变化的。”[5]117既然万物都快速变化,如果庄子认为变化的事物不可知,那么他就应该认为一切现实的对象都不可知。问题在于,我们找不到任何“庄子认为万物都不可认识”的证据;相反,在“濠梁之辩”中,庄子却认为鱼之乐都可知。再看《知北游》中这一句:
(43)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这里认为天地未有之前尚可知。能如此有信心地写出可知的理由的人,怎么可能是不可知论者呢?这反过来证明,庄子并不认为“变化的对象不可认识”,从而张松辉对(30)的解读并不符合庄子的本意;他、张采民和刘苗的这种“经验事物包括人自身都出迁流变化中,因而人无法认识和把握这个变动的世界”[19]14的不可知论的论证,就不可能属于庄子了。
综上所述,庄子的确就认识主体、认识对象、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接触和匹配,这三个方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认识才是可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和典型可知论一样地承认认识的可能。当然,他有一些否定认识必要性的言论,见(28)(34)(38),其原因是追求知识要花费时间、不利于“养生”、让人“不能自得”、会带来危险和灾祸。庄子“反知(智)”的言论还有:
(44)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
(45)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胠箧》)
(46)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在宥》)
等等。很明显,《庄子》中的反知思想源于老子。庄子反知的理由,是属于道德论和政治哲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不属于认识论和逻辑哲学。所以,反知恰恰证明了知是存在的和现实的,因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现实是可知的。不可知就不会有知,而无知就不需要反知。
七、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
如果在《庄子》中找不到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直接证据,那么,坚持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办法还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庄子是相对主义者。因为列宁曾指出过:“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20]137虽然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即使像列宁那样的权威也可以置疑,但当年引用权威却是论辩致胜的一个绝招。所以,有教材接着列宁的这句话这样说,“庄周正是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片面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走向怀疑论,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论”[1]167,仿佛从相对主义到不可知论有一道滑滑梯。
几乎所有的谈论庄子的人都认为庄子的确是相对主义者,除了极少数像爱莲心(Robert E. Allinson)这样的人(爱莲心曾指出用相对主义解释庄子会遇到困难[21]122)。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庄子》中的被称为是(认知)相对主义的论证:
1、不同类的认识主体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像(6)中关于“正处”“正味”“正色”的议论就可看成是对这一论题的论证。就是说,人、鳅、猿猴这三类认识主体对同一事物(什么是正处)的看法不同。崔大华指出这一段是“一曲认知相对性的千古绝唱……是一种‘类的主观性’”[16]270。
2、同类但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都是人,但儒墨对同一事物的是非看法就不同,(9)所述的人们对是非的争辩就是这一现象存在的证明。庄子甚至还进一步分析了人们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的原因,这就是:每个人都有其“成心”。《齐物论》说:
(47)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每个人因生长环境、教育背景等的不同,“成心”便不同,所以,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便不同。(36)中所说的“曲士”与得道的“真人”对道的看法当然也不同,可以看成是又一佐证。
3、同一认识主体在不同时间、地点或场合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例如《齐物论》中讲道:
(48)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这里是说丽之姬对她嫁到晋国一事前后看法不同;同理,人在生前和死后对于贪生的对错也可能看法不同。另一段说明人的认识的变化见《寓言》:
(49)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4、同一认识主体在同一时间、场合,视角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14)—(17)就说明了这一点。(14)说的是:对于“物之贵贱”这同一事物,同一认识主体站在“道”“物”“俗”这三种不同视角,就会得出三种不同的看法。为大家常引用的《德充符》中的:
(50)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也是说明这一点。
以上几点无非说明,关于事物(认识对象)的命题、对于事物的认识,依赖于是谁的认识(认识主体)、是谁在什么时间地点或场合的认识以及主体以何种角度看待该事物。这里说的是认识的相对性,而不是对认识的否定;这正如上节谈到认识对象是变化的,却仍然不是对认识可能性的否定一样。这只是说认识是怎么回事,却没有说认识不可能;反过来,这恰恰是在承认认识的可能,并且进一步描述认识的规律。如果说这是认识相对主义,那么这样的相对主义又有什么问题呢?“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这不正是辩证法的思想吗?它并没有进一步如列宁所说的“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20]137-138,因而不是列宁所要批评的相对主义。当人们读到(15)中的“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而认为庄子主张天地就是稊米,或毫末就是丘山,因而说庄子竟不能区分天地与稊米、毫末与丘山,这绝对是这个读庄子的人的理解力或智力有问题,而不是庄子智力有问题。这是把精妙的“齐物论”读成了荒谬的“物齐论”。而如果物真是齐的,则没有必要倡导“以道观之”,庄子也就没有必要作《齐物论》了。
“齐物论”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是认识论的齐物论,它说“天地为稊米”的意思是:存在物A,天地与A相比就如稊米与天地相比一样显得那么细小而不足道。并且还意味着:存在物B,稊米与B相比就如天地与稊米相比一样显得那么巨大。它的作用在于破除世人的俗见:“天地巨大,甚至天地至大,而稊米细小”,而揭示出“天地为大而稊米为小,其实都是相对的。因为相对于A,天地一样也很小;相对于B,稊米一样也很大”。这样就得出:就空间大小而言,虽然天地比稊米大,但天地与稊米也是“齐”的,即:地位是一样的,都不是绝对地大或小。另一种是价值论的齐物论,它说“天地为稊米”的意思是:存在物A,天地与A相比就如稊米与天地相比一样显得那么卑微而不足道。并且还意味着:存在物B,稊米与B相比就如天地与稊米相比一样显得那么高贵。它的作用在于破除世人的俗见:“天地重要高贵,而稊米轻微低贱”,而揭示出“天地为尊而稊米为贱,其实都是相对的。因为相对于A,天地一样也很低贱;相对于B,稊米一样也很高贵”。这样就得出:就价值贵贱而言,虽然天地比稊米高贵,但天地与稊米也是“齐”的,即:地位是一样的,都不是绝对地贵或贱。所以,齐物论也就是要求人们“以道观物”。认识论的齐物论是说,“天地为稊米”等于是说“天外有天”,因而“物无大小”;价值论的齐物论是说,“天地为稊米”等于是说“众生平等”,因而“物无贵贱”。所以,“以道观物”就会得出“万物一齐”这种与俗见迥异的结论。
认识论的齐物论意在开拓人们的眼界,其所谓“物无大小”就是说:“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大的物,也没有绝对小的物,‘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而不是否认“物与物相比,有大有小”。这种“大小”的相对主义,没有取消物有大小(物有大有小),是超越常识,而不是否定常识。“知天地之为稊米也”就是不以“天地”为大,不以“稊米”为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也有这类的意思,因为眼界开阔了。
价值论的齐物论意在破除人们的俗见,其所谓“物无贵贱”就是说:“贵贱是相对而言的,要看相对于谁而言,物‘自贵而相贱’,物没有绝对的贵贱”,而不是否认“物与物相比,有贵有贱”。这种“贵贱”的相对主义,没有取消物有贵贱(物有贵有贱),是超越常识,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常识。物“自贵而相贱”揭示了贵族的人为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向传统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以后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是这类意思。“知天地之为稊米也”就是不以“天地”为贵而“稊米”为贱,而是认为二者同贵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最受尊重,而“天地”居其首,这意味着,天地不仅为至大,而且为至尊。这种观念由来甚久。“天地为稊米”之说,当然有助于破除这种俗见,它颠覆了“天地”的至尊地位,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君王”了;另一方面,比稊米重要得多的百姓,与稊米一样多的芸芸众生,也就与天地一般重要并值得尊重和敬畏。
我们上述对(15)中的“知天地之为稊米也”这句话的解释和推衍,可能已经使读者倍感烦琐,但这样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更能体会庄子用句的凝炼和精彩。我们说得那么多,只是把庄子的一句话展开来说;那些人说庄子“否认客观事物性质的差异”[1]162,认为“大小、是非也就没有差别了”[13]405,“认为事物的性质、差异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不是来源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的认识,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是主体赋予客观的”[1]163,“认为事物的差别根本没有客观标准”[2]83,“一个事物既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无;既可以说大,又可以说小”[5]110,等等,却是歪曲了庄子的本意。
当然,庄子到底是不是相对主义,这是另一个需要仔细考察的问题。它依赖于我们怎么定义相对主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打算尽可能少地涉及它。既然我们的一些论争对手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少人引用列宁的话来论证“庄子既然是相对主义,那么他注定就会走向不可知论”,那么我们也不妨这样做。列宁曾说:“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20]138因此,可以这样说:“从相对主义可以走向辩证法,虽然它并不就是辩证法。”既然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不可知论,那么这也就表明相对主义也不是不可知论,因为不可能从不可知论走向可知论。
但是,认定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人,可能并没有心服。因为庄子说过“知”,如(43)等例;但也说过太多的“不知”,最为显著的是我们在第三节谈的“四问三不知”,(2)(4)(6)被认为是“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铁证”。我们前面已经说明(6)中的“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一句话就将这个“铁证”化解了,但是反对者可能用(6)中的另一句话“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来化解我们的论证。庄子是怎样看待“知”与“不知”的关系?这是任何想弄清庄子认识论的人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我们就着手考虑这个问题。
八、知与不知(上)
庄子对“知”与“不知”的关系的看法,其实是庄子认识论中最精彩和最深刻的部分之一。这一部分常常遭到许多人的不理解或者曲解。例如,张松辉说“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等是“怪论”、“违犯逻辑”[11]106,任继愈谈到《知北游》中的这一段寓言:
(51)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52)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53)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54)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闻之,以黄帝为知言。
评论说:“知道并能用语言表达道的恰恰离道最远;不知道,不会讲道的反而真是道。知乃不知,不知乃知,这是很荒谬的。”[8]363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王威威,她引的是《知北游》中这一段:
(55)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
(56)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57)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58)于是泰清仰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并将其中(57)无始的话解释为:“不知‘道’,是体道深,而知晓‘道’,则是浅显的认识。不知‘道’的,是把握了‘道’的内在,知晓‘道’,则只是知道‘道’的外在。”[18]126
《知北游》这里真的违犯了逻辑、是荒谬的吗?对于(51)—(54)这一段,当“知”问黄帝四人(无为谓、狂屈、黄帝、知)中谁是对的(“其孰是邪”),黄帝认为,“无为谓”才真正是对的,狂屈只是近似对的,黄帝自己和“知”都不对。在(54)中黄帝解释说:由于“无为谓”不知,所以他才真对;由于黄帝和“知”都知,所以都不对。因此,这并不是说“由于‘无为谓’不知,所以他才知;由于黄帝知,所以他才不知”。这一段并没有说“知乃不知,不知乃知”之类的、看起来违犯了逻辑的话,所以我们说任继愈曲解了这一段。如果说这一段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黄帝的言论。因为黄帝回答了“知”的问题“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知道这三问的答案,而“无为谓”不知如何回答这三问。因此在这一段中“实际”情况是:黄帝是知者且言,“无为谓”不知且不言。在(53)中黄帝却又点明说“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便是一个吊诡。黄帝说这话是否暗示他自己是“不知”者、而“无为谓”才是真知者呢?但(54)中黄帝又重复说“自己知、‘无为谓’不知,因而‘无为谓’已得道、自己离得道尚远”。难道黄帝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吗?
当然,黄帝只是这段寓言中的一个角色,他可以说假话或错话。而任何知,是“有所待”*见(30):“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的,即知都是关于某个对象或事情的知,而这里显然是关于“道”的。如果黄帝知“道”,由于黄帝有言,且这些言论是关于道的,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或“知道者不言道、言道者不知道”,便是错的。但庄子显然是赞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天道》中还有专门对此的论证:
(59)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知北游》中的这三句(段):
(60)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
(61)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62)弇堈吊闻之,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
更是明确地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论道而非道也”以及“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如果以为以上所引的只是属于庄子后学的思想,那么我们可看一看《齐物论》中的这一段:
(63)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
(64)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这里也明确地说“大道不称”(“大道没有称谓”*此处均采用孙雍长的译文,见《庄子》,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道昭而不道”(“说得明明白白便不是道”)、“不道之道”(“不可述说的大道”),并且这些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等思想一脉相承。既然如此,我们便只能得出:黄帝并不知“道”。这也逼得我们在《庄子》文本中,一定要注意所谓的“知”,是不是“自以为知”;以及所谓的“不知”,是不是“自以为不知”。这里,黄帝便是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
于是,我们看到,任继愈上述的对(51)—(54)段的评论是完全错误的。黄帝和“知”二人并不知“道”,只是自以为知“道”,当然他们离道最远;但这并不荒谬。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55)—(58)这一段。(57)中无始说的“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句,是指的“无穷的‘不知’要比无为的‘知’深和更加内行”,不是指的同一个人对一件事的“不知”要比“知”深,因为通常一个人对一件事是由“不知”进到“知”的,“知”当然比“不知”要深。所以,无始的言说没有任何违犯逻辑的地方。而按王威威上述对(57)中无始的话的解释,则无始的话就违背常理。但作违背常理的解释,一定要谨慎,并且要有充分的理由。我们这里的解释,既符合语言的规则又符合上下文语境,且不违背常理。所以,王威威上述的解释是一种曲解。
当然,脱离上下文,而把“不知深矣,知之浅矣”理解为同一个人的情况,仍然可以说得通。因为这里谈的并不是对普通事物的知,而是对“道”的知。对“道”的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也是由“不知”进展到“知”吗?但是,我们已经听说过对道的知完全不同于对物的知,黄帝说“无思无虑始知道”,而对物的知则需要思考、需要博闻强记,而想知“道”者则需要忘记、需要修炼到“坐忘”。见《大宗师》:
(65)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就是说,修道的过程是一个“离形去知”的过程;知“道”者无思无虑,“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于是,我们这里获得了一个对“知乃不知”的新的解读:知“道”者不知(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知如何回答问道,等等),这后面一个“知”指的是世人的知觉、好恶、自以为是的知识,等等,与知“道”的真知不属于同一个等级,不是一回事。当然,这个解读并不一定就是庄子用“知乃不知”所表达的意思。《庄子》中“知乃不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得结合其所在的上下文语境。
还有,王威威认为(55)—(58)这一段体现了庄子后学的“以不知为真知”的观点,说“体道为真知,而道不能够以世俗的认识方法把握,因此,不知方为真知”[18]126。这里的“不知方为真知”是根据什么逻辑推出来的呢?并且“不知方为真知”的表述,脱离上下文的话,是极易造成误解的。
不仅如此,王威威还把(1)—(6)中王倪的观点解释为“认为世俗的所谓知,实际是不知,而不知为真知”[18]125。按照这个表达,可以推出“俗知就是真知”了。当然,王威威会说她不是这个意思,但这样的现代汉语的表达真的很野蛮。撇开这种表达方式的问题不谈,王威威认为这里王倪的观点代表了庄子的观点,即“庄子认为无知才是真知,无知就是没有世俗所谓的耳目心知,没有对外物的分别之知”[18]125,大体上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是把其中的“无知”改成“不知”,就更准确一些。因为“无”没有主动的含义,而“不知”中的“不”,可以是故意的“不”,是主动的“不”。就是说,这里的“不知”,是通过“心斋”“坐忘”而获得的境界,是主动地修炼所获得的结果,这样的“不知”才可能是真知。于是,我们这里又得到了一个对“不知乃知”的解读。按这个解读,“不知乃知”中前后两个“知”不属于同一个等级,不是一回事。同样,这个解读也并不一定就是庄子用“不知乃知”所表达的意思。《庄子》中“不知乃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还得结合其所在的上下文语境。
那些简单地把“知乃不知,不知乃知”斥为荒谬的人,还不如泰清。(58)中泰清的感叹清楚地表明,他明白“知乃不知,不知乃知”字面上是自相矛盾的,但他也知道他所请教的无穷、无为与无始三人的智力与知识决不在他之下,无始既然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一定有其道理,只是泰清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泰清已经明白关键在于弄清楚“不知之知”,希望有人对他讲解“不知之知”。
其实,庄子并没有说“知乃不知,不知乃知”,也没有说“不知‘道’者体道深”之类的话。当然,《庄子》中有以“不知”为对、为深、为高的思想,这是“反知”的思想,但却也被庄子说得言之成理。人们为什么容易对这两段曲解呢?连剧中人泰清也以为无始的言说相当于是说“知乃不知,不知乃知”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因而很疑惑呢?我认为原因是,人们过于简单地解读庄子了,常常断章取义;或者轻信了流俗的对《庄子》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成见。例如,把(6)中“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简单地解释成王倪认为“知乃不知,不知乃知”,而不去深入分析其中的含义。
字面上“知乃不知”“不知乃知”都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无意义的;但它们出现在文本中可能有修辞的效果(例如更加精炼和引人深思),可以作非矛盾的解读,多数场合也应该作非矛盾的解读,就是说,其中的“知”与“不知”两者的“知”所指不同。
人们通常没有区分《庄子》中所说的“不知”或“知”,是不是“自以为不知”或“自以为知”的简写?通常“自以为不知”要比“自以为知”深;通常“自以为知乃不知,自以为不知乃知”也是正确的;这里没有矛盾。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记载,苏格拉底通过走访发现,政客等人自以为知,其实无知;苏格拉底自以为无知,却是当时雅典最智慧、最有知识的人。柏拉图的“自以为知乃不知,自以为不知乃知”,与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是两种不同的对知和智慧的见解。庄子思想异于孔子,不能说他一定没有与“自以为知乃不知,自以为不知乃知”相近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是有道理的:每个人在一个给定时刻,其全部知识是有限的,可以用一个圆表示,圆内是他的已知,圆外是他的未知。一个人对他的未知的了解就相当于他对这个圆的圆周的了解,所以,一个人知道得越多(这表明这个圆的面积增加了),他就越感到他所未知的事物越多(因为作为知与未知的边界的那个圆周,其周长也增加了)。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不知(无知)的自觉性越强,越是说明这个人知道得较多。所以,“知乃不知,不知乃知”可以被解读为“自以为知乃不知,自以为不知乃知”,因而可以是有意义的和正确的,并不一定就违犯逻辑或是荒谬的。
对比(51)—(54)与(55)—(58)两段,有趣的是,(57)中的无始之言与(54)中的黄帝之言如出一辙。我认为,(53)中“故圣人行不言之教”之后的“道不可致”到“圣人故贵一”这一大段,很可能是衍文,所以我全部用省略号代替。这两段中,“无为谓”对提问无言以对,不是不理睬,而是不知怎么回答;无穷则对以“吾不知”,所以“无为谓”与无穷都是“自以为不知”。从(53)中“知”所说的“我与若知之”和(54)中黄帝所说的“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可知,“知”与黄帝都是“自以为知”;从(56)中无为说的“吾知道”可知,无为也是“自以为知”。在黄帝的这种自以为知“道”的知当中,是有“是非”对错的,即“无为谓”是对的,其他人都不对。狂屈曾说过“予知之”,这说明他也曾自以为知“道”;后来他“以黄帝为知言”,这说明他认同黄帝的“是非”评价,并且也被黄帝列为“不对”的人当中,只不过离“对”不太远而已。在庄子的寓言中,知“道”和得道的真人有真知,却自以为不知或自称不知;那些自以为知“道”和自称知“道”的人,却是一些无真知和未得道的人,这样的设计可以看做庄子有“自以为知乃不知,自以为不知乃知”之类看法的辅证。
既然我们已经论证过黄帝并不真的知“道”,那么黄帝关于道的那些言论就不足为凭了,甚至可以把(53)中黄帝的回答“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看成是黄帝不知“道”的表现,虽然他的那些言论并不一定都是错的。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跳出“是非对错”才能更好地理解庄子。让我们再看看泰清的那一段。泰清也问“孰是而孰非乎?”不过无始却没有回答孰是孰非,却发了一番关于知的“深浅内外”之论以及关于道的“道不可言”之论。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吊诡:无始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千古以来还没有人透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无始不知“道”,那么他关于道的那些言论也不足为凭;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认可(60)~(61)中“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之类的话;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说无始不知“道”(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根据说无始知“道”)?如果我们是根据老子、庄子的“可道非常道”“大道不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类的言论来说的,由于无始在(57)(60)(61)中有言“道”,所以无始不知“道”。这样的话,老子、庄子也于道有言,因而他们也便不知“道”了。如果老子、庄子都不知“道”,则道就真的没有来由了,什么是道也就没有任何依据,关于道的一切言论都“是非莫辨”,甚至任何言论是否在谈论道也“是非莫辨”,这时的言论,真如《齐物论》所说的:
(66)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因此,我们必须同意老子、庄子是知“道”的。如果从无始不知“道”可以推出老庄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无始知“道”。由于整个《庄子》中无始的故事只出现在(55)~(61)这一段,犹如神龙不见首尾,而其论之高、其气之霸、其神态之逍遥、其话语之权威,俨然是庄子自己在说话,所以,如果说有理由认为无始不知“道”,那么同样的理由便表明庄子也不知“道”。所以,结论只能是“无始知‘道’”。
如果无始知“道”,那他为什么一方面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另一方面却也在(60)(61)中言“道”?如果无始知“道”,那么,是不是可以根据他自己说的“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而断定无始并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泰清并没有问道于无始,他只是就无穷与无为的言论来请教无始,无始也没有回答说谁是谁非,而只是说谁深谁浅,这时无始的言论就不是一种对“问道”的回应,因而可以避免推出“无始不知‘道’”。我们也可以说,无始的话不算数,他为什么一定要说真话呢?但他有必要说假话吗?无论如何,无始说过“道不可言”。根据语言交流的通常约定,如果无始真的知“道”,那么“道”就应如他所说的“不可言”。既然道不可言,那么,任何人对道的言说、任何关于道的言说,都应该受到质疑和批判,包括老子、庄子对道的言说,也包括无始自己对道的言说,包括“道不可言”这句话本身。“道不可言”这句话恰恰是关于“道”的言说,恰恰表明“道可言”;不仅可言,而且已经言。就是说,“道不可言”是自我否定的,任何人说“道不可言”其实就在表明“道可言”。既然道可言,那么无始的说法就是错的,这种错误表明,其实无始不知“道”。
通过以上的思考,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悖论P:“如果无始不知‘道’,那么无始知‘道’;如果无始知‘道’,那么无始不知‘道’”。这个悖论使我们不禁想起泰清的感叹:“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因为“不知乃知,知乃不知”形式上也是一个悖论(记为Q)。认识是有对象的,当认识对象是“道”、认识主体是“无始”时,Q就成了P。前面我们指出,在许多场合,Q其实可以不是悖论,而是合乎逻辑的,有时甚至很有道理。这些解决悖论Q的方法的共同之处是,指出Q中的“知”与“不知”两者的“知”所指不同。但这一招似乎不能用来解决悖论P。那么如何解决悖论P呢?
九、知与不知(中)
要想解决这个悖论,显然我们先要弄清庄子究竟是怎么看“知”的,或者说庄子的“知”概念究竟如何。庄子认为,“知”有两部分,即“知之所知”和“知之所不知”,这种说法见《则阳》:
(67)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
因此,“知之所知”是可以感知的,而“知之所不知”则是不可感知的部分,二者的关系有如植物的地面上的茎干、枝叶与地面下的根,人们只能看到地面上的部分而看不到地下的部分;但看不到的部分同样重要,它起着支撑(供养)那看得见的部分的作用,二者组成植物的整体。知也和植物一样有这样两个部分。为了避开“知之所不知”这一概念给人造成的矛盾困惑,我们可以称“知之所知”为显性知识,称“知之所不知”为隐性知识。这样,(67)说的是:人们都重视显性知识,却不知道有赖于隐性知识人才有所知,这能不说是大问题吗!
在《徐无鬼》中,是这样描述这两部分关系的:
(68)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
因此,道分为两部分:不道之道和可道之道;辩论分为两部分:言语的辩论和无言的辩论;知识也分为两部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不能言说的;言说直到隐性知识而止,言说就到顶了。孙雍长把“知之所知”译为“智慧所知道的”,把“知之所不知”译为“智慧所不知道的”[14]355,由于人的智慧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这样(68)中所指出的言说的边界便也随时而变,因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就算(67)(68)这样翻译勉强可以说得通,那么《徐无鬼》的下面这一段:
(69)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
(70)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71)尽有天,循有照,冥有枢,始有彼。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后知之。
就会遇到问题。其中,(69)中所说的“所不知”,并不是一般的不知,而是“知之所不知”。它和“知之所知”的关系,正如未被足踏的地和正被足踏的地一样,前二者都属于“知”这个整体,后二者都属于“地”这个整体。未被足踏的地和正被足踏的地有共同点,即都是地;“知之所不知”与“知之所知”,作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也有共同点,即都是知识;但“智慧所不知道的”与“智慧所知道的”却可以没有任何共同点。因此(69)要说的是:“知之所知”与“知之所不知”相比,是很小很小的,但没有这“不知之知”,人们就不可能“知天之所谓”。(71)进一步说,“知之所不知”与“知之所知”是相似的,但有了这“知之所不知”,人们才能有所知。不过,只有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才是相似的,“智慧所不知道的”与“智慧所知道的”谈不上相似。说“智慧所不知道的东西使知识成为可能”是大而无当,说“隐性知识使知识成为可能”则有相当证据。人们具有隐性知识被《天道》说得十分透彻:
(72)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轮扁具有斫轮的知识,但这种知识不能言说,无法言传给他的儿子,所以这是一种隐性知识。而且轮扁认为,隐性知识更为重要,与隐性知识相比,显性知识只是“糟粕”。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存在和作用及其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关系,直到20世纪中叶才由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重新提出、揭示和阐发,所以我们不能不赞叹在其前2300年的庄子的深刻和智慧。因为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庄子的“知之所不知”,例如崔大华是这样评论(67)的:“《庄子》这个表述的奇特性在于,这里的‘知之所知’实际上是指经验的对象和感性的认知方法,‘知之所不知’则是意味着超验的认识对象和理性的、抽象的认识方法。”[16]288不过,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则是属于要晚得多的西方哲学范畴。理性认识,虽然是抽象的却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但(68)明确了“知之所不知”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和知识并不都是抽象的,如斫轮就是很具体的,相关的知识应该是感性认识。所以,用“感性认识”套“知之所知”“理性认识”套“知之所不知”,就显得很不合适,顾此失彼。
既然“知”有“知之所知”和“知之所不知”两部分,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部分,而“知之所不知”又可以说成是“不知之知”,甚至可以简称为“不知”,那么,说到“知”,就有可能是指这个“不知之知”,即“不知”。因此,(6)中王倪说“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是有道理的。同样,当说到“不知”,就有可能是指这个“不知之知”,即一种“知”。因此,(6)中王倪说“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汉语的“不知之知”并不限于指“知之所不知”,即不限于指隐性知识。它还可以指自以为对A不知、其实是知道A的人的那种关于A的知识。
“不知之知”还有一种解释。对于任何人a,任何命题R、K,设a不知道R,则a可以说“我不知道R”,这里R属于a的“不知”之域。设a知道K,则a可以说“我知道K”,这里K属于a的“知”之域。根据认知逻辑的负内省公理,我们还可以说“我知道我不知道R”,也就是说,“我不知道R”属于a的“知”之域。换句话说,在a的“知”之域中,有一些知识是“我不知道R”这类命题,这就是一种“不知之知”。
另一方面,汉语的“知之不知”也并不限于指“知之所不知”,即不限于隐性知识,它还可以指任何知识的有限性、相对性。因为,对于任何非人造对象的知,如我曾指出的那样[22]182,是有着多种层次的。有很多对象我们都没有达到对其有“真正的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这些对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这些对象,因为这些对象有很多我们不知的地方。这些被认为是已知的对象的未知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将其简称为“知之不知”。
而且,我们要注意,在古汉语中,“知”除了作“知道”和“智慧”讲外,还可以作“感知到”或“感觉经验到”讲,例如“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庄子》中的用法更是多样,如《德充符》中的:
(73)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兀者也。
孙雍长译作“我跟随老师已经十来年了,但老师从来没有感到我是缺一只脚的人”[14]71。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老师知道我是缺一只脚的人”也是真的,就是说,这里的“未尝知”与“知”并不矛盾。同样,“子三月不知肉味”与“子知肉味”也不矛盾。这里的“未尝知”和“不知”,并不表示真的“没有感知到”,而是那种感觉不受重视甚至受排斥。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它是“被压抑”的知识或“潜”知识。如此一来,“不知之知”便可以意为“被压抑的、遮蔽的知识”,相应的“知之知”便意为“未被压抑的、本来的知识”或“被意识到的知识”。这种“被压抑的、遮蔽的知识”与隐性知识相近,却不是隐性知识,因为它是可以表述的。这种“被压抑”的知识由于没有被意识到或未受关注,所以是一种“不知”;但它究竟是可以意识到的,甚至已经被意识到,只是不受关注而已,所以又是一种“知”。
在每种上述这些“不知之知”或“知之不知”的情况下,王倪都有理由说“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并且,相应的Q形式的“悖论”也容易被化解和被理解。
十、知与不知(下)
了解到庄子将“知”区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就会明白对道的知也有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分。人们关于道所说的一切,包括老子、庄子等人所说的一切,充其量也只是关于道的显性知识。只是拥有这些显性的关于道的知识,并不能让人真正地懂得道,它只是轮扁所说的“糟粕”。人们必须同时拥有那无法言说的关于道的隐性知识,才可能真正地懂得道,才算是拥有真知。(69)中“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就是说:依赖于人们对道的隐性知识,人们才能知“天之所谓”,才能知“道”。《大宗师》对此也有说明:
(74)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这里的“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便是讲显性知识的作用,即显性知识可以引导、培育隐性知识,而不一味地是“糟粕”。轮扁显然过于极端,并不代表庄子本人的观点。
正因为关于道的关键知识是隐性知识,所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但是道也有很多显性知识,所以人们关于道所说的一切,并非都是错的。从显性知识的角度看:“道可言”。但仅仅拥有道的一些显性知识,当然谈不上对道的真知。这些关于道的显性知识由于没有关于道的隐性知识的支撑,见(67)(69),所以它们刻画的不一定是道,而可能是非道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道不可言”。
知道一些关于道的显性知识,当然不是难事。例如(53)中,“知”从黄帝那儿听到一些关于道的说法(当然是显性知识),便自以为知“道”。这种道听途说而来的知识,便是没有任何隐性知识来支撑的,只是“纯粹”的“知”(这也许是“知”的名称由来),而与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无始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这便是对“知”这类人的断然棒喝。黄帝作为历史上(传说中)有成就的帝王,以智慧著称,是世人崇拜的对象,被世人认为是得道的人物。庄子却认为这样的人并未得道。《庄子》中对他的定位可见于《盗跖》:
(75)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知北游》用他来代表又一类自以为知“道”之人,这类人貌似拥有智慧,好为人师,喜欢论道,喜欢教别人什么是道,其实一知半解、并未得道。“论道而非道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就是对这类人的当头棒喝!这类人对道有一些体验,较对道毫无体验的“知”为深,但对道仍然没有深刻的领悟、没有真知。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得道,却以为自己知“道”;甚至以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得道,是因为自己知“道”,见(54)。《列御寇》中,
(76)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就好像是在开导黄帝这类人。(76)中的“知”,都是指的对道的一些显性知识的知,是可言之知。对这类关于道的知识的知是容易的。为什么“勿言难”?因为言者自以为知“道”,在问道者的恳求之下难保不开口言“道”。能做到“知而不言”,并非是出于对问道者的保留和谨慎,而是不以为自己真的知“道”,因为道太博大精深了,感到道难以穷尽、无从开口、难以言说。这种自以为不知才是真知的征兆,所以有(57)(58)中的“不知深矣”“弗知乃知”“不知之知”等说。
在(51)—(54)、(55)—(58)这两段中,“无为谓”和“无穷”是两个得道者的形象,那么“无始”呢?无始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而言道,这种自相矛盾是不是说明无始不知“道”呢?根据(59)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不是可以断定无始不知“道”呢?现在有了道的显、隐知识之分,道的隐性知识不可言,却可以言道的显性知识,所以这里没有矛盾。如果坚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真的,由于无始言道,那么,可以推出无始不知“道”。但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言;如果它为真,那么,谁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谁(包括《天道》的作者、甚至庄子本人)都是不知“道”,从而这句话不足为凭,包括不足以凭它来断定无始不知“道”。
既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自我否定的,那么,知者不一定不言,言者也不一定不知。不仅老子关于道有五千言的《道德经》,庄子关于道有八万言的《庄子》,就连在宣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知北游》中,也有老子、庄子分别在讲道的段子:
(77)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
(78)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
不仅老庄在讲道,《庄子》中很多有道的真人、至人也在讲,如《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大宗师》中的女偊、《应帝王》中的壶子,等等,有趣的是,无始在(60)中讲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也讲过“道不可闻、闻而非也!”前面我们讲过“道不可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自我否定的,道可言、言者可知、知者可言。其实还有:道可闻。证据见《大宗师》:
(79)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只是他们讲的闻的都只能是显性知识,要真知“道”,还得有关于“道”的隐性知识,而这些是看不到、听不见的,不可讲也不可闻的。但这些显性知识也不全归无用,(74)告诉我们,它们有助于养育我们关于道的隐性知识。所以,读《老子》《庄子》还是有用的,有助于我们知“道”。
由上可知,借助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分,我们便化解了《庄子》中一方面说“道不可闻”“道不可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另一方面又有材料表明道可闻、道可言、知者言、言者知等明显的矛盾;或至少让这些矛盾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庄子》中的故事大多只能当寓言看,庄子也期待我们“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言”,即得其精神大义之宏旨,而不纠缠于其只言片语之微疵。庄子的这个妙语见《外物》:
(80)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过于纠缠,就是一种执,而未达忘言之境,如此便不能解庄子之言。
借助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分,我们也能化解悖论P。因为从“无始知‘道’”,得不出“无始不知‘道’”。因为在第八节的那个论证中,“道不可言”可以不是自我否定的:“道不可言”是对的,它说的是“道的隐性知识不可言”,而这不是自我否定的;“道可言”也是对的,它说的是“道的显性知识可言”;二者并不矛盾。因此,无始的说法“道不可言”没有错,无始的做法——言“道”——更没有错,二者也不矛盾。所以,我们在第八节得出“无始不知‘道’”的理由不成立了。这样P就被化解了。
那么,无始知“道”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能根据的只能是无始的言和行,因为《庄子》中并没有明言无始是得道之人、知“道”之人。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只是无始的片言只语,如(57)(60)(61)。但是,关于道的言语,至多都只是关于道的显性知识,而更为重要的关于道的隐性知识,却是无法从言语而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无始知‘道’”。
但是,我们更没有证据表明无始不知“道”。至少,无始有一些道的显性知识。像无始一样言道的人中不乏得道、知“道“之士,如前面提到的女偊、壶子就是。即使无始不知“道”,只要有人知“道”,道就是可知的。
道的隐性知识的存在并不表明道不可知,没有人认为主张有隐性知识的波兰尼是不可知论者。《庄子》中没说“道不可知”,没有说道的隐性知识不可知,只是说道的隐性知识不可言;何况道的显性知识是可言而可知的。大部分人(如刘笑敢、李纪轩、张松辉等)承认庄子认为道是可知的,因为庄子主张有“真知”,而“真知”指的就是知“道”,是得道之人的知识状态。明显的证据有《大宗师》:
(81)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不利的证据。我们这里,通过指明庄子对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划分,通过阐明庄子的“知”与“不知”的关系,瓦解了《庄子》中所有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有利于“道不可知”的证据。这些证据有“道不可闻”“道不可言”“言者不知”“道无问”,等等。
既然道是可知的,那么无始知不知“道”就不那么重要了。
十一、结语
庄子对哲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对“知”的见解。他是第一个把“知”与“不知”用一种极特别的方式——他称之为:“知之所不知”、“不知之知”——连在一起的哲学家。他第一个揭示了隐性知识的存在、并能以非神秘的方式来说明它(见(72))。他不仅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而且用他独特的知论极大地丰富了道论的内涵。其思想之深刻和超前,令人惊叹。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1)—(81)中,包含了所有的《庄子》中迄今为止人们用来证明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材料,但在我们对其的重新审视和分析中,却发现它们无论是单独看、还是合在一起看,都不是支持庄子是不可知论者的确凿证据;相反,其中不少倒是可以用来证明庄子是可知论者。例如,李纪轩认为庄子“公开地提出了不可知论的观点”[10]2,其依据的材料是(1)—(6)这一段,认为“这里不仅三问三不知,而且连‘知’是不是‘知’和‘不知’是不是‘不知’也不知道”[10]2。我想,我们上述对庄子关于“知”与“不知”的关系的看法的分析,充分表明了李纪轩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他还把(64)中的“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解释为“思辨的终结,终止在不可知上”[10]2,其实这句话也就是“故知止于知之所不知,至矣”,而“知之所不知”并非不可知,它恰恰是一种知,即隐性知识。结合上下文,(64)说的是,隐性知识是知识的极致,这正如不言之辩是辩的极致、不道之道是道的极致一样。这当然是可知论的说法。退一步讲,就算我们的译法不对,其中的“知”应该作“智”讲,那么“知止其所不知”的意思也就是“智慧止于智慧所不知晓的事物”,但这也不是不可知论的观点。
我们在上节已经充分表明,庄子认为道是可知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反驳了一切作为“庄子认为物不可知”的证据。其实,还有很多“庄子认为物也是可知的”正面证据。例如已列举的庄子认为鱼之乐可知、天地未有之前可知等材料。《知北游》中更是有“万物一气”的说法:
(82)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连这都知道的庄子,是多么强的可知论者啊!强得不亚于任何典型可知论者,尽管他并非主张一切都可知的强可知论。即使去掉外、杂篇的材料,甚至只从《齐物论》来看,庄子较为肯定的人物南郭子綦也是主张有知的,他除了地籁和人籁,还知天籁:
(83)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庄子是可知论者。
[1] 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李坚.论庄子认识论不是不可知论[J].辽宁大学学报,1988(5).
[4] 杜志强.庄子认识论新探[J].甘肃理论学刊,2006(1).
[5] 张采民.《庄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严金东.评庄子相对主义思想中的怀疑论[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1).
[7] 严北溟.应对庄子重新评价[J].哲学研究,1980(1).
[8]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 李纪轩.庄子认识论的内在矛盾[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0(3).
[11] 张松辉.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 孙雍长.庄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1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6] 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7]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 王威威.庄子学派的思想演变与百家争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刘苗.庄子的“反知”与“真知”[D].重庆:西南大学,2011.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 [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2] 周文华.“知”的问题与笛卡尔的蜡论证[J].当代经理人,2006(3).
责任编辑:王荣江
B223.5
A
1007-8444(2015)04-0457-25
2015-01-20
周文华(1966-),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