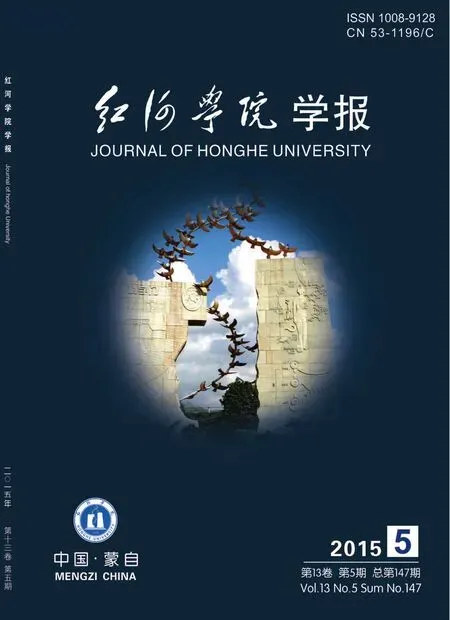中原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河南作家民俗文化创作取向研究
孙拥军
(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河南焦作454000)
中原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河南作家民俗文化创作取向研究
孙拥军
(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河南焦作454000)
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当代河南作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用文学怀乡的方式表达着自我独特的乡土情结,同时将中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进行理性的呈现,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以建构起新的中原文明体系。
中原文化;河南作家;民俗取向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原在很长的时期,一直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千年来,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中原不断积淀,形成了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逐渐向中华大地辐射,构建起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体系。因此,中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形成其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传统——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文化体系。由此而言,中原文化又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其自我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并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由于中原文化的历史积蕴,自古以来,文人骚客历代辈出,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刘震云、刘庆邦、李佩甫、张宇、李洱、乔典运、周大新、郑彦英、杨东明等“文学豫军”的快速崛起,并将一篇篇震撼人心、凝聚着其乡土情结的作品,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坛,同时也展现出河南作家独特的创作取向和价值追求。
一
这些从中原大地走出的河南作家,都曾经生长于中原这块黄土地,虽然在其成年后相继都离开了故土,走向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但这些作家在创作上仍然以家乡为中心来取材,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视角,反观父老乡亲生存下的当代乡村,以文学追忆的方式来寄托自我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与怀念。因此,在他们的乡土作品中,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情结,每篇文字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对故土的难舍之情。正如作家刘庆邦所言:“我的故乡在豫东人平原。我曾经说过,那块地方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和草根养活了我,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陌、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1]
当代河南作家坚持写乡土,写家乡,写故乡的人、事、景、情,通过一个个带有浓郁家乡风俗和地域特色的父老日常生活故事的讲述,阐释着自我独特的乡土情感。然而他们都是文化守成者,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无限留恋。改革开放后,现代文明逐渐浸入中国乡土农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乡村的农耕文明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只在历史记忆中存在的文化。从乡土中原走出的这些作家,对这些即将逝去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曾经辉煌的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地消失,感到嗟叹与惋惜,因而,在他们的乡土作品中,都致力挖掘中原文化传统中的民俗美,用文学怀乡的形式,将历史上的中原民俗文化展示出来。
虽然“文学豫军”都来自中原,但来自于中原的不同地域。中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相同的文化形式,有着地域性的民俗与民风,如刘庆邦笔下的豫东大平原、周大新笔下的南阳大盆地、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系、刘震云笔下的黄河古道……,都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诚然,每个地域的民俗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而这些作家就是通过乡土小说的创作,将这些中原民俗、民风融合于作品中,呈现出自我对中原传统
文化的不懈追求与坚守。我们以作家刘庆邦的乡土小说为例,来阐释这些作家对中原民俗文化的独特追求。
有着“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王”美誉的作家刘庆邦的大部分作品坚持写乡土,其也是当代河南作家中写民俗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所写民俗难以胜数,如三月三庙会(《春天的仪式》)、闹洞房(《摸鱼儿》)、新女婿拜岳父(《走新客》)、新娘子回门(《回门》)、踩高跷(《踩高跷》)、送葬(《响器》、《黄花绣》)、唱大戏(《听戏》)、二胡演奏(《曲胡》)、做碗灯(《灯》)、捕鱼(《起塘》、《拉网》)、给牲口刷牙(《刷牙》)等等,都在小说中展示一种中原传统的民俗文化。但作者在展示一种民俗文化时,并非是简单的呈现出这种民俗文化,而是在讲述这些民俗文化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在内心深处的不懈思索与追问,将民俗文化的展示与自我的独到思索紧紧扣在一起。以《响器》为例,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刘庆邦给读者讲述了豫东大平原为死者送殡的传统风俗。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风俗文化,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将这种风俗讲述的至为感人,让人动容。刘庆邦在小说的一开头,就叙述豫东与中原其他地域不同的送葬形式:
“庄上死了人,照例要请响器班子吹一他们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张扬一番。”
紧接着,其叙述了豫东乡村人对死者送葬的隆重场面:
“响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体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吹奏。他们一共是三个人,一个老头儿,一个中年人,还有一个小伙子。这是镇上崔豁子的响器班子,那个老头儿就是四乡闻名的崔豁子。据说从崔豁子的曾祖父那一辈起就开始吹响器,到崔豁子的儿子这一辈,他们家已吹了五代。周围村庄祖祖辈辈的许多人最终都是由他们送走的。他们用高亢的大笛,加上轻曼的笙管,织成一种类似祥云一样的东西,悠悠地就把人的魂灵过渡到传说中的天国去了。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他们像是只对死者负责,或者说只用音乐和死者对话,对还在站立着的听众并不怎么注意。他们吹奏出的曲调一点也不现代和复杂,有着古朴单纯的风格。不消说曲调代表的是人类悲痛的哭声,并分成接引、送别和安魂等不同的段落,以哭出不同的内容来。它又绝不模仿任何哭声,要说取材的话,它更接近旷野里万众的欢呼,天地间隆隆滚动的春雷。人们静默地听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有人不甘心自我迷失,就仰起头往天上找。天空深远无比,太阳还在,风里带了一点苍凉的霜意。极高处还有一只孤鸟,眨眼间就不见了。应该说这个人死得时机不错,你看,庄稼收割了,粮食入仓了,大地沉静了,他就老了,死了。他的死是顺乎自然的。”
刘庆邦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讲述了用吹奏响器的形式为死者送葬的传统风俗,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尊重,生孩不吹,娶亲不吹,全村人为死者在阳间的最后一程送行。响器的吹奏者也用最精湛的表演来为死者送行,吹奏的乐曲也很成熟和完善,分成接引、送别和安魂等不同的段落。作者的这种描述,表现出为死者送殡时吹奏响器这种中原风俗已经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并为乡村所接受。作者之所以这样详细的描述吹奏响器的隆重场面,在这些文字的的背后我们可以感悟到作者的隐忧,那就是随着现代文明的浸入,乡村的传统民俗在逐渐的改变,尤其是当代殡葬制度的实施,移风易俗,作者已经敏锐的意识到吹奏响器为死者安葬的这种传统民俗不久将会消失。因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传统风俗文化消失的哀叹与惋惜。
作家李佩甫的乡土作品中也体现了其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记述,被看作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源远流长。其也讲述了豫北乡村人婚丧嫁娶的礼仪,尤其是为死者送殡的严格程序,要行“二十四叩礼”。在《城的灯》中,当冯家昌母亲去世后,作为老大的他就要带着弟弟们学习“二十四叩礼”,去一家一家地磕头,这既表达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对生者为死者送行的一种感谢。
二
中原作家对中原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消失感到惋惜,都在用文学的方式追忆中原大地曾经的乡俗美和乡情美。这些作家虽然都是文化守成者,但并非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后,对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糟粕给予排斥。正如学者张岱年所说:“与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两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也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2]河南作家也在其乡土作品中记述了一些风俗文化中应当舍弃的糟粕,如李洱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一文中,就用大量的文字来讲述在中原农村所流行的“骂街”和“看热闹”的丑陋传统民俗。在宗法制的乡土农村,男权占有绝对的优势,妇女们没有话语权,是一个集体失语的弱势群体。她们对这种不公的权力分配所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违背中国儒家文化数千来所沿袭的纲常传统,无奈只好采用“骂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也试图将这些粗俗的辱骂,变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雪娥怀孕被村长发现之后,认为是有人告密,有意欺负她,跑到大街上破口大骂,一副母夜叉的泼妇模样。作家李洱
在讲述这种丑陋风俗时,虽然从内心深处对这种民俗的不认可,但还是站在中国传统纲常文化的视角下,对乡村妇女沿袭下来的这种陋俗给予宽容的批判,对数千年来倍受压抑与欺辱的乡村妇女因找不到正确的途径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委屈,特别是当吃了大亏又找不着倾诉对象的时候,采取这种无奈的宣泄方式给予了理解,纵然如此,作者还是在小说中多次暗示这种陋俗必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逐渐走向消亡。
李洱在这篇小说中还写到另一种陋俗——“看热闹”。现代乡土小说的肇事者鲁迅先生就在其小说中多次描述一种“看客”文化,看杀头,看热闹,在鲁迅先生看来这种民俗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乡村人爱看热闹,凑热闹,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人围观。小说中的雪娥一开骂,门口就围了一群女人和孩子,这些人大都是非常闲,巴不得周围出个什么事端,可以供他们茶余饭后闲谈消遣。他们爱看闲事,爱散播是非。还有“每逢村里死了人,人们都要围过去,名义上是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其实是要看热闹,看孝子们怎么哭,谁是真哭,谁是假哭,谁哭的最凶,谁哭的最动听。”这种“看热闹”中原民俗,也就是鲁迅先生曾经批判的乡村“看客”文化。
这些中原作家虽然在创作取向上都是通过乡土小说的形式,致力寻找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民俗美和乡情美,但他们对现代文明下新的民俗、民风并不反对,而是理性的接受。因而,这些作家在创作理念上,又是与时俱进的作家,关注着当代中原农村在现代文明的关照下传统民俗的演进与变迁,以及新的民俗文化的诞生。作家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一文中,用细腻、老道的笔法极力讲述了豫西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一群备受传统民俗折磨而又最终不屈服于这些民俗的三姓村村民。三姓村由于地处山岭,海拔较高,常年干旱无雨,耙耧山区处处是“焦干的黄土,饿孩娃吸奶似的吞着流水。水本来很小。已经两个来月滴雨不落了,田地都龟裂成坚硬的板块,裂纹指头一般粗,曲曲弯弯,网卷豫西的山岭和平原”,“土地的裂纹,纵横交错地罩了耙褛山的世界,一团团黄土的尘埃在那山坡上雾样滚着,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而且耙耧山地下水质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致使三姓村村民们一代代患上喉堵症,在村史上没有人能活过四十岁,都是在英年去世。村民沿袭着世代传下来的向上天拜神求雨民俗传统,没人去改变这种乡村陋俗。1980年,随着现代文明浸入到耙耧山区,村长司马蓝面对生命的的短暂与生存的艰难,决定抛弃陈旧的求雨风俗,毅然带领村民开山修渠,将干净的水源引到村内,与命运、与自然、与疾病抗争,以延长村民们的宝贵生命。
三
中原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在这些河南作家的笔下展现了中原的人、事以及风俗文化,表达了他们对故土深深的依恋之情。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原民俗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过程中的演变,其中有优秀的乡土民俗,也有落后的、愚昧的乡风陋俗。在乡村现代化的变迁中,中原文化要真正融入到新时代中华文化之中,就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那些优秀的因子不断地延传下去。同时也要加入一些新的优秀因子,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吸收和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我们的地域文化精髓才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流传下来,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作出新的贡献。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既守成,又创新,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3]
[1]杨建兵刘庆邦.“我的创作是诚实的品格”——刘庆邦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9(3).
[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宗桂.传统与现代之间[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贺良林]
The Research on Folk Culture of Henan Writ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Culture
SUN Yo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broad and profound,contemporary Henan writers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nostalgic literature expression self unique native complex,and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 the folk culture of rational show,absorb the essence,reject the dross and to construct the new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system.
Central Plains Culture;Henan writers;Folk custom orientation
I207
A
1008-9128(2015)05-0090-03
2015-01-01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原文化背景下河南当代作家创作取向研究(142400410398)
孙拥军(1978-)男,河南夏邑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作家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