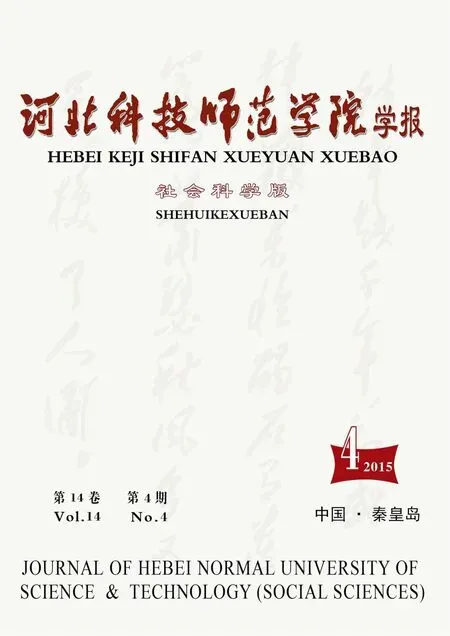《刑法》立法解释的类推倾向实证研究
——兼为实质解释论正名
杨 楠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70)
《刑法》立法解释的类推倾向实证研究
——兼为实质解释论正名
杨 楠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70)
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出台的13部刑法立法解释中存在不少类推解释。其类推解释的症候主要集中在行为要素、主体要素、对象要素和责任承担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构成要件行为、主体和对象的解释突破了立法对相关犯罪确定的观念定型,对责任承担机制的重新分配也本应采用立法程序确立。类推解释的产生,根源于法律对某类行为欠缺明文规定,直接归因于司法活动的功利目的。刑事司法活动着眼于对危害行为的规制和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在唯恐自身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形下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的。所以,只有满足司法的功利目的,才能最大限度扭转类推解释倾向。对此,立法主体一方面可以采用实质解释方法,将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勾联起来;另一方面,在无法用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应对司法实践的情形下,要善于使用立法手段,用严整的立法程序将行为犯罪化。
刑法立法解释;类推解释;功利性;实质解释论
立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形式之一,独具中国特色。立法主体解释法律决定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立法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既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其合理性,那么断然废止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制度并非明智之举。如果能在承认立法解释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展开对问题微观方面的研讨,关注解释方法的规范化、解释结论的科学化,才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解释的标的是“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解释就是要探求这项意义[1]。现代刑法的铁则——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立法解释必须在可得文意射程之内对《刑法》文本做出阐明,不得同类相推。类推解释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及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2]45。自2000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出台《刑法》立法解释13部*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解释;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关于《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特别是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性颁行《刑法》立法解释4部,立法解释在刑事法治中被进一步重视的趋势又一次引发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激烈论争。通过梳理,在这13部刑法立法解释中,解释主体超出《刑法》文本语义范围,做出类推解释结论的不乏少数。
一、类推解释的症候
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基本蕴含。所谓的“类推”,通常是指在两个事实具有共同性质的基础上,用一种正确的事实来推论另一事实也是正确的解释。刑法中所说的类推解释,是对法律上没有给予规定的事实与法律给予规定的事实,是同质性的事实,根据其相同性质,来适用其法律的情况。成为这种类推解释根据的相同性质,通常据说是被当做法益保护目的的法律精神。[3]
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形式理性,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4]。而类推解释极端地追求实质理性,只关注是否存在法益受到侵害的结果,不关注行为是否违反既定规范,忽视形式理性。类推思维所得出解释的结论往往会超出文义的可能范围,弱化法律的确定性,使司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大肆扩张,随意出入人罪,侵犯公民自由。但是,从2000~2014年陆续出台的刑法立法解释,无论在对行为类型的明确上,还是对行为客体的阐释上,抑或对行为主体的规定上,甚至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机制上,都呈现出超越国民预测可能的征兆。
(一)类推解释的类型划归
1.对构成要件行为的类推解释
示例一: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做出了说明*《解释》认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含以下三种情形: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由于单位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这一解释的出台的确对一些单位挪用公款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将“归个人使用”解释为“单位使用”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个人”意指一个人,是和集体相对的概念,而“单位”是指机关、团体或属于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是“集体”这一概念的外延,因此“个人”和“单位”两组概念是相离并且是相对的关系,既没有当然解释的可能也不存在扩大解释的空间,这种解释结论只能评价为类推解释。我国《刑法》对单位挪用公款没有规定,由于单位挪用公款也会导致与个人挪用公款类似的使国家和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以及危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管理制度的后果,解释主体认为这种侵害法益的行为值得刑法做出否定性评价,所以在比照了结果同质性的基础上将“归单位使用”的两种情形纳入“个人使用”的文意范围,用挪用公款罪予以规制。
2.对行为主体的类推解释
示例二: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用以明确职务犯罪的主体问题。在1997年《刑法》实施后,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挪用公共财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增多。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立法解释,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七种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行为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作为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主体。解释出台之后的出台,对进一步保障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和维护国家、集体财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本质上的差别,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有类推解释的嫌疑。
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根据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的选举和任用程序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同;而且,村委会成员也不脱离生产,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正如刘仁文教授指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传统意义上确实不被视作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农民……还需要注意,立法机关只是对司法机关反映突出、亟待解决的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何种情形下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做出解释[5]。所以,“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语词无法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包含进去。
示例三:1997年修改《刑法》时,将渎职犯罪的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主要考虑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着国家公权力,若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危害。但在做出立法解释之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其中的新情况包括:一是法律授权规定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如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二是在机构改革中,有的地方将原来的一些国家机关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其行使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三是有些国家机关将自己行使的职权依法委托给一些组织行使。四是实践中有的国家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聘用了一部分国家机关以外的人员从事公务。,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做出明确解释。立法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采用“公务论”,明确了依法律、法规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纳入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当中。苏彩霞认为这属于扩张解释,可以应对新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打击渎职犯罪[6],但笔者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对于守法主体和司法者而言,要明确国家机关的外延,最可靠的就是参见其他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是在上述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立法解释结论和我国《宪法》相关规定不能吻合,不但超出普通人对《刑法》文本的理解范围,而且没有做到法律体系的统一,甚至有违宪之嫌。如果要对依法律、法规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进行刑法规制,必须用刑事立法程序做出。
3.对行为对象的类推解释
示例四: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一些地方出现了走私、盗窃、损毁、倒卖、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严重违法行为做出立法解释,认为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笔者认为,将“化石”解释为“文物”是类推解释。首先,化石和文物的形成机理不相同。化石是通过地球运动等自然原因在地下形成的古生物遗体、遗迹等,没有人的参与作用;文物则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物,可留存于社会也可能掩藏于地下。其次,二者价值属性不同,化石更多的是具有科学研究价值,而文物主要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再次,我国《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外延的列举并未将“化石”纳入,相反对“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的保护是和文物分条规定的,这也说明在行政法规上将“化石”和“文物”视为不同。这一解释的做出只考虑到了走私、盗窃、损毁、倒卖、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所造成的和走私、盗窃、损毁、倒卖、非法转让文物造成的国家珍贵资源流失的危害结果,并未考察“化石”是否在“文物”的文意射程之内。所以,该解释是为了用《刑法》加紧应对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流失现象所做出的类推解释,不但有悖于国民预测可能,而且导致法律体系不协调,解释结论欠妥。
4.对责任承担机制的类推解释
示例五:2014年新出台对单位犯罪处罚机制做了新的规定,明确了对由单位实施的但《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犯罪行为如何规制的问题。立法解释明确指出,在此种情形下对组织、策划、直接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责。这种解释事实上是对我国现行单位犯罪处罚机制的再造。依照《刑法》文本规定,在定罪上,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单位犯罪就不会再对相关自然人的危害行为进行否定评价;处罚上存在吸收关系,在单位犯罪的情形下对自然人的惩处一般要轻于普通的自然人犯罪,主要基于单位已经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这种责任承担方式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瑕疵,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困境,如上述的由单位实施的但《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犯罪行为如何规制的问题即使如此。立法解释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进行区隔,让单位和自然人对其行为各负其责,这对于处理单位犯罪案件确实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诸如这种关涉处罚机制的问题,能否由立法解释是否可以对此问题做出规定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可以转化出单位犯罪的概念: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那么,自然人基于单位意志,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犯罪时,就应属于单位犯罪。其行为构造与普通的自然人犯罪的行为构造并不完全相同,利益归属也有差异,行为的隐蔽性也不同,因为《刑法》没有对单位犯罪有明文规定,而将单位责任完全转嫁到个人身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种解释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理解可能性。易言之,无法从《刑法》第三十条和三十一条中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中推得,由单位实施的但《刑法》未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对相关个人予以处罚这一结论。在此,解释主体完全没有依照《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则本身进行严格解释,而是针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机制进行了再造,用解释的形式完成了本该由刑事立法做的工作。
(二)二次划归
通过上一部分的划归笔者进行了初次类型化的努力,立足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类,还能再一次进行类型化建构。
首先,行为、主体和对象都属于对构成要件要素的类推。构成要件属于一种观念形象,它将同类犯罪的恒定特征抽离出来,为具体判断行为性质提供指导。对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现存争议,但行为、结果、因果关系、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是其不变的要素,所以上述第一种对行为的类推,第二种对主体的类推和第三章对对象的类推都可以为构成要件要素所包含。
构成要件要素是犯罪论的内容,对构成要件要素的类推也就意欲将行为做入罪化。如果以事前为视角,不满足构成要件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评价为犯罪的,因为其没有违反刑法规范,完全得不出否定性的结论,那为什么非要逾越文本既定含义而将特定行为入罪呢?笔者认为是因为视角不同,类推解释的主体是以危害结果为视角,关注对法益造成的现实侵害或者对法益造成的威胁,从结果的角度对行为做出了否定性评价。如果在此视角之下,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都具有同质性,而且解释不会超出文意可得范围。可如果缺少上述三个要件(行为同质、结果同质和文意可得范围)中的任意一个,都会得出类推解释结论。在此论者不再赘述。
如果对作为类型化的观念形象所蕴含的要素进行随意类推,就会使得既定的观念形象模糊化,使人不易识别甚至无从把握。观念形象也是一种指导形象,不但具有裁判作用也发挥行为导向作用,观念形象的模糊会使守法主体无从知晓自己的行为方式,使《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就无从发挥;同时,立法者做出类推解释,看似对其进行了具化,其实是模糊了观念形象,更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司法主体越来越不能把握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核,增强对立法解释的依赖性。
其次,对归责的类推。这里的责任不意指大陆法系犯罪阶层理论中的“有责性”,而是在归属和归咎意义上确定将责任加给谁担负。归责问题是宏观的理论建构问题,对归责原则的调整会波及整个《刑法》各论,也会影响《刑法》总论理论间的协调配合,如共犯理论。所以,归责机制调整根本不是解释所能完成的。如上所述,在“单位犯罪”中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与自然承担刑事责任是相斥的,量刑上也是吸收的,从单位不负刑事责任不能解释为个人也必须负责一样。质言之,归责机制是非创造活动所不能推及的。
综上,通过对《刑法》立法解释的分析发现,在为数不多的13部刑法立法解释中,有5部解释的结论存在类推的嫌疑,类推解释的比重约占解释总体数量的38.5%。或许,数据还不一定能呈现出其危害性,但不妨这样思考:从宏观上看,不当的解释结论跨越总论和分论,对总论的不当解释有两部。总论作为原则性规定,要适用于整个分则。详言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规定适用于分则规定的所有公务犯罪,对“单位责任”的解释规定适用于分则除单位犯罪外的所有罪名。所以,对总论相关问题的解释会发散性地辐射到各论的相关罪名当中,其作用范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从微观上看,立法主体对分论不当解释有三部,解释对象也覆盖了主要的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主体和对象,这些要素都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要素,对这些要素的类推解释必然会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模糊文本的用语范围,削弱刑法的规范机能。
要发挥立法解释在刑事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遏制其类推倾向。而意欲寻找消解类推解释的路径,首先需要分析做出类推解释的因由。
二、类推解释的肇端
对《刑法》立法做出类推解释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源上讲,类推解释的发生是因为法无正条;从现实意义上将,类推解释是基于制度的功利性,因为司法要用既定的法律条文应对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上述两方面原因存在递进关系:法律条文不明确使得具体个案适用存在疑问,而司法主体又不能因为法无规定而拒绝裁判,为了使得个案得以有效处理立法机关依申请或者自行对法律文本做出解释。
(一)根本原因:法无正条
《刑法》不可能与任何侵害法益的行为都存在严丝合缝地对应关系。这一方面源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亦即《刑法》主要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危害行为做出的规范,刑事立法对犯罪的预测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基于《刑法》规范追求体例完整条文简约,避免长篇累牍的自我品质;还有一方面归因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外在地受物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内在地受知识构造以及个人情感的影响;同时,立法技术也不得不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刑法》立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性。理想状态下,如果事实完全合于法律规定,直接适用相关规定即可得出结论;倘若发生新的社会现实,而这些社会现实会与既定的规范存在行为类型或者危害后果上的相似性,是否能以相关条文论处就应进行判断。
对这种类似的社会现实进行评价无非出现两种结果:其一,倘若被评价对象与参照标准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时,而这种社会现实也需要用《刑法》做出规制时,则可对刑法条文做扩大解释,将被评价对象纳入此法律条文中,做出否定性评价。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中就采用了扩大解释方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刑法规定的“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虽然,根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海关代征增值税款书不属于行政法规意义上的发票之列。但他们都属于制式票据,海关代征增值税款书可抵扣税款发票具有相同功能,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而且对于此类犯罪的行为人,大都明确了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的用途,不可能超出去预测可能。所以,解释主体运用了扩大解释的方法,将“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纳入“发票”之列,使刑法得以应对新型税收类犯罪。
其二,倘若被评价对象与参照标准是相离或相交的关系但也具有可罚性时,就存在两种途径,要么继续使用解释的方法,突破文字意思将行为用最为相似的《刑法》条文进行规制,要么启动立法程序将之入罪。对与第一种路径的具体操作,就是将被评价对象类型化之后纳入参照标准之中,使得两种某些方面有相似性但本质上并不同的行为被定为相同的罪名,适用相同的量刑标准。例如,前述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质意义上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只因为可能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流失以及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仅仅因为具有造成的结果与贿赂犯罪相似就被解释为职务犯罪的主体。第二种路径即通过建议立法的方式,将危害行为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审议、表决,以立法程序规定为新的犯罪类型。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
通过上述分析,法无正条是类推解释的必要条件。易言之,《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可能会导致类推解释,而只要有类推解释结论的做出必然是《刑法》对被解释对象没有明文规定。当然,《刑法》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向做出准确而完备地预设,多变的社会生活和既定刑法文本之间的疏离会长期存在,类推解释根植的土壤也不会因为立法技术的提高而改观。这一原因是根本性的,是法律的先天缺陷,无法克服。
(二)现实原因:司法功利
所谓功利性是指立法解释的颁布在根本上是为了解决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其终极的目的指向于司法主体在处理某类案件时的有据可循。而且,刑法解释学的生存空间是刑法适用过程,其着力研究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或与刑法适用有关系的问题[7]。在此过程中,《刑法》立法解释还考虑刑事政策因素,顾及《刑法》实施的社会效果,更要积极协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正是对这些功利性目的满足,大大增加了做出类推解释结论的可能性。
首先,对于主动解释。立法机关自己发现所颁布的法律条文中存在不明确或者需要对如何应对新的社会现象需要做出阐释和说明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文本做出解释,以有力规制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这期间,立法机关主要着眼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特定的危害行为纳入现有的刑法规范之中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有效惩处此类行为。例如,虽然《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随着经济生活中欠债不还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债务人有能力还债而不还,甚至在人民法院裁判之后,仍采取转移财产等方式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裁定”是否包括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仲裁决定、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有不同认识,影响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这些裁定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再者,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利用职权严重干扰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致使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不能执行。为了化解上述司法困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要求下,对“判决”和“裁定”做出了解释,详尽列举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在主体上,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协助执行人借口不协助司法机关执行的现象十分严重,立法解释突破了1998年的司法解释将本罪主体限定为被执行人的规定,将担保人和协助执行义务人也纳入本罪规制;对象上,解释将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为执行各类生效法律文书所制作的裁定书纳入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扩大了“裁定”的范围。不难发现,立法解释扩大了该罪的处罚范围。
其次,这种功利性在被动解释的情形下体现地更加明显。被动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所提请的解释申请做出阐释的行为,被动解释又可根据提请方式的差异分为为共同提请解释和单独提请解释两种类型*共同提请解释是指,对于有争议的解释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单独提请解释是指,对于有争议的解释结论,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方单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事实上,此类解释的内容已经过最高司法机关研究,从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因为相关问题已经在实践中高发且适用中问题较大,这也预示着解释难度较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罪与非罪不明。当一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且与《刑法》规范禁止的行为类型具有相似性但能否用《刑法》非难行为人无法明确时,如果不做出解释则可能会导致当罚的未罚,增加了刑事处罚的偶然性,抑或不当罚的被科以刑事制裁,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在立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对食用珍贵野生动物是否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认定为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野生动物制品罪,司法机关存在不同意见,之后通过立法解释才使之明确。其二,此罪与彼罪模糊。一些罪名在学理区分上较为容易,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进行判断则颇为棘手。特别地,在构成要件的要素存在不完全重合情况下,重合的要素越多越不容易区分,再加上现实案件中表现出的行为手段不典型时,就更难准确认定。又如,司法实践中对使用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金的案件处理不一致,有的按诈骗罪处理,有的按保险诈骗罪处理,也有的给予行政处分,还有的在追回社保基金后不做处理。为了统一司法适用,“两高”提请立法立法机关做出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做出了对此类行为以诈骗罪论的立法解释。其三,罪重与罪轻误判。对于一些法定情节与结果刑法往往采用概括式或兜底性的规定,如“情节严重的,处……”、“后果严重的,处……”、“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倘若不能叙明此类开放的构成要件要素,就无法对行为情节和危害后果的程度进行划归,进而无法准确量刑。面对司法实践中的上述诸多问题,司法机关未选择自行做出司法解释而是提请立法机关解释,笔者认为这便是类推解释的祸端。
无解释则无适用,司法实践活动天然地包括对法律的解释。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将抽象化和类型化的法律条文应用于具体的个案当中,其目光要在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件来回穿梭,这期间包含对条文的明晰和对事物实质特征的抽离,所以解释活动实为必不可少。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授权两大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具有解释的权利。对于同一法律条文,况且是基于实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缘何会得出不一致的解释结论,缘何又要放弃解释的权利而将其让渡给立法机关? 对于案件的处理,通常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即将法律规定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在此基础上经过内部证成得出结论。形式逻辑的方法操作较为简单,所得结论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差异,最高司法机关也很少在此类情形发生定性冲突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可案件事实并不必然会和法律条文严丝合缝,特别是对一些疑难案件更是适用困难。当司法机关无法用形式逻辑的基本思路将大前提和小前提有效结合而得出结论之时,实质推理的思维路径就呼之欲出了。
实质推理若考虑到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所得出的解释结论应值得肯定,它会在文意可得范围之内兼顾处罚的必要性而做出的扩张性解释结论;但极端的实质性推理只关注行为的危害本质,会超越既定的《刑法》文本含义而惩处危害社会的行为,侵犯公民自由,从而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悖。质言之,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要对案件处理时,一方面可以将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相结合,自己对法律条文做出扩大解释,如果在扩大解释结论做出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问题认识不一致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出于将危害行为入罪或者出于某一类案件的现实需要,只能进行实质推理才能达到目的时,为了避免自己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请求立法者对某类问题出台立法解释规定,以满足司法实践需求。前述的后一种情形所及的功利性目的在立法机关做出类推解释中占绝大多数。由于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都运用了实质推理的思路,加之文字的模糊性,解释活动也多发于文意的边缘地带,这就导致二者的界限很难区分。大多数的解释权让渡就是在实质推理的必要和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嫌疑的冲突下,司法机关试图将刑法解释的包袱甩给立法机关,希求以其立法者的主体地位为司法实务做出功利性地解释结论。[2]79
由于国权主义理念在我国的刑事法治进程中依旧盛行,司法机关面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当然地会考虑怎样用《刑法》做出否定性评价,在寻找法律条文无果时,就会要求立法解释将其入罪。同时,在“和谐”与“稳定”的政策导引下,积压的案件应得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必须迅速化解。再者,当两大最高司法机关在对法律适用问题上发生冲突之时,作为其上级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理应对二者的解释结论做出评断,并以立法者的身份做出更高位阶的解释结论,为案件处理提供依据来消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事业务中存在的矛盾。但是,法律以其正当性而获得了合法性,政策则是以其合法性获取了正当性,政策的贯彻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圭臬,必须以法律的规范性为前提。立法机关不能只为了顺应民众呼声,满足社会惩治犯罪的迫切需要以及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而颁布突破刑法条文本身的解释规定。《刑法》的社会实效和法律实效必须有机统一起来,不能偏废和割裂。
综上所述,《刑法》立法解释类推现象的产生,多是由于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而在司法实务中又存在需要打击犯罪行为,处理相关疑难案件的功利性目的所致。这种功利性主要体现在对危害社会行为的非难需要和对民众意见的回应上,其主要目标指向于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和对社会公众朴素刑罚观的支持和认可,以期达到犯罪人得以非难、民众情绪得以有效安抚的状态。
三、阻绝类推解释的路径
《刑法》解释能最大限度克服刑法的滞后性,维护刑法的安定性,使刑法能不断适用新的社会现实,满足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功利性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不能成为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做出类推解释的理由。要避免立法主体超出《刑法》文本的字面含义做逾越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解释结论必须从法律解释的立场以及立法与解释的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思考。
(一)实质解释论的提倡
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相对。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涉及刑法解释的方法论问题,形式解释的方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通过形式要件,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排斥在犯罪范围之外。形式解释论主张忠于罪状的核心意思,有时甚至仅是自己熟悉的法条含义[8]。实质的刑法解释是对作为形式正义之体现的《刑法》规范进行解释,以阐明其蕴含的实质正义[9]。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需要立法主体进行解释的,都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与现有规定有些许关联的定罪或者量刑要素。由于要做出价值判断而又不能准确地把握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界限,才提交请求立法机关做出解释。由此可见,立法解释所面临的解释对象都是刑法文本自身不能直接推导出来的解释结论,而必须要进行价值判断,从二者的法益侵害性和立法目的上进行思考。法官要猜测对这个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10]。法律是原创者——企图创设完全或部分的法律规整之——意志的具体化,此中既有“主观的”想法及意志目标,同时也包含——立法者当时不能(全部)认识之——“客观的”目标及事物必然的要求。如果想充分了解法律,就不能不同时兼顾两者[1]199。也只有这种价值判断,解释者才能透过形式上的差异而找寻出被解释对象和与现有刑法规范的共通之处,并将二者结合起来。
实质解释的方法不是极端地只注重实质理性而抛弃形式理性,而是在以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前提下展开对实质正义的实现。邓子斌担心的权力偏爱实质解释……若要约束权力,就要约束解释,尤其约束实质解释的担心略有多余[11]。当某一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与既定的《刑法》规范中所明确的法益侵害的类型化行为相似时,不能直接用解释的形式将该行为纳入《刑法》规范之中。解释主体应继续考虑法益侵害的程度是否相似,进而判断各项形式的要素是否达标,在此需要将该行为与既定刑法文本的各项定罪和量刑要素抽离出来进行比较,看各项要素是否能够和《刑法》文本含义存在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论者不妨举例说明,对于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行为,会造成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相同的侵害公共款项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使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到损害,二者在法益侵害上没有本质差异。但是,只在实质上宏观地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就做出将“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构成要件行为,进而以挪用公款罪论处是不科学的。在比较完法益侵害性之后,解释者必须再考察“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是否合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法益侵害程度、行为构造和条文含义。首先,在危害结果上,自然人势单力薄而单位有独立的资产,自然人挪用公款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单位,特别地对于国有公司企业而言,相互之间的拆借行为都只是为了运营和周转,没有侵犯职务廉洁性的可能,甚至是在保有或者增加国有财产。另外,这种在国有公司、企业之间的挪用无异于将钱从左边的口袋又换到了右边的口袋,没有像个人挪用公款那么大的法益侵害性。其次,在行为构造上,个人使用是指自然人主体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将公共款项占有、使用和收益,其利利益属于自然人,而单位使用则是在集体意志支配下将公共款项占有、使用和收益,其利益归属于单位。最后,在语义上,“个人”和“单位”本就是一组相离的概念,不仅没有交集更没有包含关系,“个人使用”的文意无法涵摄 “单位使用”的概念。所以,将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论处是类推解释,违背了罪刑法定主义。再如,对于以食用或者其他非法用途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都会危害国家对珍贵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危害生物多样性,二行为在本质上侵害了同一法益,在程度上没有差异。而且“收购”行为是指大量或从各方面收集购买的行为,由此可见“收购”行为被“购买”行为所包含,有做出扩大解释的空间,故立法机关将“食用或其他非法用途而购买”解释为“收购”行为,并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制是充分运用的实质解释的方法做出的扩大解释结论妥当且未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
实质解释论本质上是实质推理与罪刑法定主义形式侧面的结合,这种解释方法不但考虑到了实质正义,可以应对司法活动功利性的要求,将新的犯罪行为用《刑法》进行规制,而且能够将解释限定在文意可得的范围之内,克制其在功利性目的的诱导下发生类推化的劣变。
(二)明确立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界限
立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本质区别,二者在功能上不能混同。《刑法》立法属于法律保留内容,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表决才能颁行实施,而解释法律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是较为经济、高效地满足司法实践对法律需求的活动,它能经过充分论证而迅速出台规定,规制犯罪行为。但是,这种程序的简洁性也要求解释内容必须符合公民预测的可能,如果在进行价值判断,运用实质推理的思维也不能在案件事实和既定的《刑法》规范之间建立联系时,就只能启动立法程序,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行为入罪,切不可进行极端地实质推理活动,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特别地,当司法机关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刑法》解释时大都需要实质推理,故很难把握扩张和类推的界限,立法机关必须保持警惕,将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作为衡量解释结论的一票否决项。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善于将无法做出解释结论而又需要《刑法》规制的危害行为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并提出立法建议,不断完善《刑法》规范,多管齐下地应对司法的功利性目的。例如,对于一些侵犯人身财产权利方面的犯罪,如杀人、伤害、非法拘禁,以及普通的诈骗、盗窃等,《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此类的“单位犯罪”,总则第三十条中又明确单位犯罪的惩罚以法有明文规定为限,在这种情况下做出 “对组织、策划、直接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责”的规定,尽管其具有合理性,但其没有形式上的依据。应该用立法的程序对司法实践中的此类问题进行充分地酝酿、论证,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做出规定。
立法虽然是最不经济也最不效率的手段,但立法确实最公正最科学的手段。在理想状态下,自然希望效率和公正两大价值要素能有效协同,但在二者相互排斥时无法衡平时,就必须做出取舍。论者认为,控制刑法处罚范围以保障公民自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基于刑事责任的严厉性,也基于基本人权的考虑,必须对“效率”这一价值做“定义排除”。简言之,对《刑法》而言,自由和公正是其不能突破的底线。
结 论
《刑法》立法解释的类推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这不但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反,更是对解释活动与创造活动的彻底混淆,更存在违宪的嫌疑。为了满足司法活动的功利性,克服《刑法》立法解释的类推倾向,一方面要充分运用解释技巧,榨干法律条文蕴含的所有意思,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运用实质解释的方法将事实与法律做最大限度的勾联;另一方面要善于将一些危害行为纳入刑事立法的视野中,通过严整的程序从根本上完善刑法规范。总之,《刑法》立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必须各行其事,让立法解释发挥有限的弥合作用,让刑事立法发挥其对规范的建构功能。
[1]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94-199.
[2]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郑树周,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85.
[4]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
[5]刘仁文.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立法演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22-31.
[6]苏彩霞.我国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174-185.
[7]徐岱.刑法解释的独立品格[J].法学研究,2009(3):23-38.
[8]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27-48.
[9]刘艳红.实质刑法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7.
[10]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
[11]邓子斌.中国实质刑罚观批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1.
(责任编辑:杨燕萍)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riminal Law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alogy Tendency ——And to Justify the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Yang Nan
(School of Law,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 73070, China)
Thirteen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s approved by NPC developed some analogy interpretations, which focus on four aspects: the behavioral elements, the subject elements, the object element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ssumption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to these broke the concept of crime, the reloc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assumption mechanisms also should adopt legislative process. Analogy interpretation resulted from the lacking of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behavior or directly from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judicial activities. Criminal justice activities focus on the regulation and harmful behavior in a specific case processing, in case that they are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ase, they submit it to NPC to get the interpretation. Thus, only to meet the judicial utilitarian purpose, can we reverse analogy interpretation tendency in a maximum level. On the one hand, legislative subjects can adopt a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to connect the norms of criminal law with the case facts,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can't use the interpretations to fill the legal loopholes or to deal with the judicial practice, we must be good at using the means of legislation to make the behavior crime with rigorous legislation process.
criminal law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utilitarianism;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10.3969/j.issn.1672-7991.2015.04.014
2015-10-21;
2015-11-20
杨 楠(1989-),男,陕西省洋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
D914
A
1672-7991(2015)04-00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