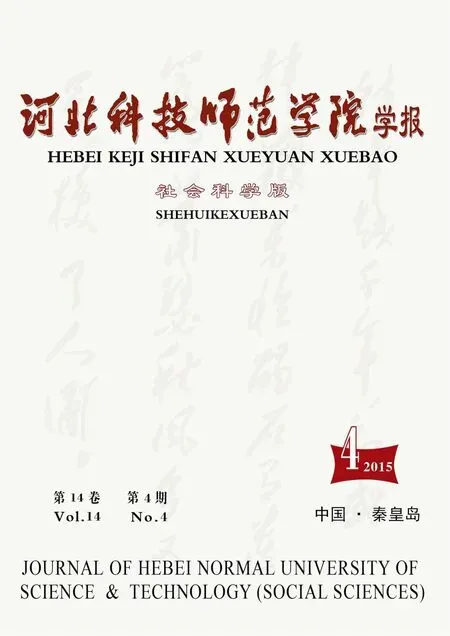聆听语词的声音
——细读朱朱诗歌《小镇的萨克斯》
林 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聆听语词的声音
——细读朱朱诗歌《小镇的萨克斯》
林 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选取诗人朱朱早期代表作《小镇的萨克斯》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切入点,结合其创作的早期诗歌作品,以20世纪90年代诗歌转型为背景,在具体细读诗歌的基础上,对朱朱早期诗作中的典型意象进行了分析。同时,重点把握诗人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展现出诗人对语词的重视。
《小镇的萨克斯》;朱朱;语词;90年代诗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社会文化转型的情境与诗歌地位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情况。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研究,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十分必要。相比于影像、音乐、网络等各种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和迎合大众趣味而粗制滥造的大量“快餐文学”,诗歌往往无法在最初接触时便获得某种急功近利的愉悦与满足。即便面临如此境况,依然无法撼动许多在喧哗中坚持诗歌探索的诗人,以坚定的步伐在诗歌发展道路上一步步前行,诗人朱朱便是其中的一位。90年代,诗人朱朱在创作中展现了较多的的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这些创作于90年代的诗作大多收录在他的诗集《枯草上的盐》中。出版于2000年的这本诗集,不仅代表着他诗歌风格的初步确立,也彰显了他对诗歌写作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创作于1992年的《小镇的萨克斯》,不仅体现出了其对语言精致的追求,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篇面向诗歌自身的诗作。
一、“多么强大的风”
1989年,诗人海子选择了卧轨自杀。随后不久,诗人骆一禾也不幸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一系列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件,引起了诗坛不小的震颤。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阶段。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席卷和消费主义对人们愈发强烈的熏染,社会文化也进入了全面转型的阶段。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和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在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高扬的理想主义热情逐渐消退,“经历90年代初期的震荡之后,诗歌与社会、时代之间的‘整体性’关系遭到了破坏,开始变得若即若离直至全然崩溃,其所谓的‘中心’位置也渐渐被其他文化力量(如影像)所取代,诗歌其实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1]历史话语,从而获得一种阅读的普遍性:比如它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反文化,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走向世界的文学梦,纯诗主义,语言的表层化(它的两个变体是反语义和口语化)等等。而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2]70的确,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的“个人化”倾向逐渐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诗歌尽管弱化了与社会、历史保持某种紧密的张力关系,却以介入日常经验的姿态开始了新的发展。面对着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环境和逐渐膨胀浮躁的社会环境,在创作中,诗人们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对个人存在所持有的焦虑也逐渐浮出。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面对社会文化转型的情境与诗歌地位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情况,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显得十分必要。
1991年,诗人朱朱写下了这样简短却意味深长的诗句:“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3]85这首创作于在90年代初的短诗,形象地反映出处于年代切换阶段诗人们所处的“艰难”处境。面对前人创下的高峰和未知的探求空间,俯视当下所处的复杂环境,是选择在“修远”的道路上“走着我自己”,还是就此放弃,向浮躁的现实处境缴械妥协。
90年代,诗人朱朱在创作中展现了较多的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这些创作于90年代的诗作大多收录在他的诗集《枯草上的盐》中。出版于2000年的这本诗集,不仅代表着他诗歌风格的初步确立,也彰显了他对诗歌写作的许多观点和看法。“枯草上的盐”这个独特的意象出现在其1998年创作的诗作《厨房之歌》中。厨房作为典型的参与日常生活的空间,紧密地联系着人们的“食”。而“食”,也有生理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两个方面。进入90年代,诗歌日趋“边缘化”。相比于影像、音乐、网络等各种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和迎合大众趣味而粗制滥造的大量“快餐文学”,诗歌往往无法在最初接触时便获得某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愉悦与满足。但是,作为精神食粮的制造者之一,诗人却坚持更加镇定地在“枯草上撒盐”,不仅是对诗歌创作的坚持,更是对日臻完美的诗歌技艺的追求。“盐”除了是调味品,也有延长食物贮存期的作用。在这里,精细的“盐”意味着对诗歌语言的臻美追求,同时也对诗歌价值的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对语词的重视不仅体现了90年代诗歌的一大特点,也表明了朱朱个人偏向精致的美学追求。正如论者张桃洲所言:“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朱朱将精细的刻绘功能臻于极致的诗歌语言,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自己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以来,诗人们无限向往却无力实现的诗歌理想境界。”[3]177在笔者看来,《厨房之歌》是一首关于诗的诗。“诗”是它的主题。“多么强大的风/从对面的群山/吹拂到厨房里悬挂的围裙上”[ 4]57,“强大的风”代表着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更具体一点来说,是诗歌的发展趋向。90年代的诗歌发展从宏大、高昂的英雄主义或者对抗、反英雄的激情姿态中解放,转向了“个人化”和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当这股“强大的风”“又把围裙吹倒在脚边”的时候,意味着诗人对“个人化”倾向的认同与顺应。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对浮躁的、充斥着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的顺应,诗人所选择的是像“刮除了灶台边的污垢”一样,剔除影响诗歌创作的杂质,纯净地进入诗歌创作中。依然秉持着对语言的精美追求,“我们要更镇定地往枯草上撒盐,/将胡椒拌进睡眠。”[4]58在日常生活中,枯草并不是食物,然而却是诗歌本身的隐喻。
创作于1992年的诗作《小镇的萨克斯》,不仅体现出了其对语言精致的追求,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篇面向自我的诗作。臧棣曾这样表达他对90年代诗歌的看法:“我认为90年代诗歌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审美转向:从情感到意识。换句话说,人的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开始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动机。许多变化都与此有关。”[2]71朱朱的这首《小镇的萨克斯》不仅保持了其对语词的精细、简约、准确的要求,也体现出了他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体悟。
二、“我走到人的唇与萨克斯相触的门”
《小镇的萨克斯》以超现实的手法描绘出了类似于南方小镇的安详与静谧。通过“细雨”、“街道”、“屋顶”、“树叶”、“墙壁”、“光线”等等具体的意象营造出了类似梦幻般的若即若离的情境。初读全诗,不由得被其所吸引,简洁而准确的语词营造没有喧闹和世俗的打扰的圣地,柔和地如似人声的萨克斯曲风无形地成为全诗阅读背景乐,柔和地走进人心。迷离的道路、雨丝的微光、潮湿沁凉的空气和悠然点燃的灯光。全诗展现出了一种语词、音乐、绘画的融合。单纯的布景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雨中小镇特有的宁静与安详,一种空灵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平静、舒缓的叙述中体现出了一种语词的节制和情感的克制之美。
这首诗内定了一个地域范围——“小镇”。小镇往往指居民不多的集中地,比城市小,自然环境通常来说比较好,相对于大城市而言较为僻静幽闭。这首诗从题目开始便内蕴着一股意味和幽静。如果将地域范围“小镇”替换为其他地点,比如“都市”或“乡村”,其从诗题开始所奠定的基调便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是熟人的社会,都市则是陌生人的社会。介于二者之间的小镇既不完全是熟人的社会,也不绝对属于陌生人。它处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是连接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既是小型化的城市,又是扩大版的乡村,既拥有村庄不拥挤不喧闹、生活节奏缓慢的特点,又具有相对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小镇”这样一个意象给予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明显的:宁静、祥和的生活氛围和较为适宜的生活环境,使人放松。处于小镇的环境之中,既不会有都市漂泊的感触,又不会置于太过亲密熟悉的环境中而失去相对私密和自由的个人空间。
萨克斯作为一种经典乐器,音色圆润柔和,是管乐中最接近人声的乐器。萨克斯音乐深沉而平静、富有感情,轻柔而略带忧伤。此外,萨克斯的造型,从喇叭口向笛口看,十分类似弯曲的街道由近及远的形状,也与小镇的意象更为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首诗从诗题开始,便奠定了这样相对平和、舒缓的叙述基调。
全诗共分为三节,在第一节中,一笔勾勒出小镇的中心意象,如同萨克斯管的街道成为全诗生发的基点,奠定了静谧的氛围。“雨中的男人,有一圈细密的茸毛,”这里描写了在细雨中没有撑伞的男人的形象,一个“圈”字,将他们被细雨包围的景象表现了出来,用“茸毛”来形容细小雨珠纷纷落在他们身上的景象,不仅保留了茸毛和细雨各自的特点,更是在其中建立起了某种巧妙的联系。使感觉在干燥柔软和冰凉湿润中穿梭。“他们行走时像褐色的树,那么稀疏”,在这一句中,雨中行走的男人与坚守一方土地的树之间取得了联系,在一动一静之中富有张力。男人的在雨中行走的形象幻化为一个大致的轮廓,在纷纷的细雨中各自孤独地走着,如同树的稀疏与静谧。“褐色”所给人的深沉与稳重感与树的稀疏、挺拔相结合,准确、细致地刻画出了诗中男人雨中行走时的画面感。而句末的“那么稀疏”,则将这种幽静甚至略带些许忧郁的韵致散发出来。
“整条街道像粗大的萨克斯伸过”,这一句不仅从视觉效果上十分形象,并且非常自然地将音乐元素引入了雨中小镇的情景中。“伸过”这个动词,富有动感,并且使得街道展现缓慢而轻盈。“街道”这个意象相对频繁地出现在《枯草中的盐》这本诗集中,例如:“沿着街道/并肩穿行狄兰·托马斯的蓝色诗集”[4]89(《金钩子》);“经过同样的街道,有些疲倦/当我就要沉浸于记忆,从山坡上/突然传来他越来越完美的琴声”[4]98(《幻影》);“此刻你不在。/正像你不在此刻的电话机旁,/我愿意向你描述窗外的街道,一家亮灯的缝纫铺”[4]136(《父亲的回忆录——致罗玛》)。作为城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既为民众出行提供了便利,也将城镇进行了“分割”。街道是进入小镇的途径,也为来访者提供了观察的路径。沿着街道的轨迹,诗人将读者的视野引入他的“秘密王国”。
整体上看,从全诗的伊始,便奠定了舒缓的节奏和幽静的氛围。前两句分别以一个逗号,放慢了诗歌的节奏,在第一节的末尾,动词“伸过”的出现及延续了缓慢轻柔的节奏,又内蕴力感。准确而又简洁的语词,使得这种舒缓的节奏显得张弛有度,丝毫不拖泥带水。
诗的第二节,诗人着重描写了“光”和“雨”交融下的街场画面。调亮了诗歌画面的光感,与第一节由“褐色”延伸出的暗与深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暗一明的视觉切换之中彰显出诗歌内蕴的节奏感与张力。“有一道光线沿着起伏的屋顶铺展,/雨丝落向孩子和狗。”在这一句中,两大意象——“光线”和“屋顶”,是朱朱早期诗歌创作中比较钟爱的两个意象,在《枯草上的盐》中,这两大意象并不鲜见。可以说,朱朱对“光”有着特别的敏感。无论是刺目的光“打开了琴盒/山坡上是刺目的光线/仿佛夏天的幻影,正要驱散/夏天”[4]98(《幻影》),还是柔和的光“阳光慢慢渗透灰色的调子,我/一动不动地凝视”[4]31(《飓风》),都成为朱朱诗句中的常客,是他细致刻画的对象。“光”能够感知,却往往无形,然而朱朱却竭力刻画出了“光”的种种形态:“阳光沿着这棵树,漫开,/像一架风车里飞出的鹤群/抬高我的视线”[4]21(《石头城》);“一夜的雪积满梢头,/阳光像丰满的百合”[4]13(《我梦见一头狮子的相互撕咬》);“光不在玻璃上返回,/而是到来”[4]66(《和一位瑞典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飓风掠过庭院/阳光中落叶犹如黑色的线”[4]31(《飓风》)。由于朱朱早期诗歌中对色彩的使用十分谨慎,像“黄色”这样暖色调的颜色使用较少,更多地是诸如“褐色”、“蓝色”、“灰色”这样的冷色调偏暗的颜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光”这个独特意象,不仅点亮了朱朱诗歌的视觉即视感,而且也指引出他观察事物的细致方式以及其独特的感知方式。
“屋顶”则是朱朱视线的常落点:“彩色而细小的屋顶像几面镜子/将柜台和蜡人似的伙计搬运”[4]15(《我梦见一头狮子的相互撕咬》);“琉璃瓦的屋顶下/那些阴森的褶皱展开了”[4]66(《和一位瑞典朋友在一起的日子》);“订购单;我常在去东郊的途中,/观看不同的屋顶,从一个男人的身上/看见几个女人的夜晚”[4 ]105(《带耳环的女人》)。往往只有从高于房屋之上的角度才能观察到屋顶,屋顶所遮蔽的是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是隐蔽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屋顶”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隐喻。在这一句中,“光线”与“屋顶”共同配合,将观察视线拉至相对的高处,在“光”的配合下静态的屋顶由其本有的近似波浪形的外观而形成了“起伏”的动感,“铺展”一词则将光的速度放缓,使其呈现出相对具体、饱满的质感来。“雨丝落向孩子和狗”则又将视线拉至低处,在静态的“孩子”与“狗”这两个意象的无声并置中,呈现出一种相对轻松、静谧的氛围。在这里,“孩子”与“狗”的意象,与上一节中“雨中的男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孩子”与“狗”的活泼与纯净明亮,与“褐色”的“雨中的男人”的深沉和黯淡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凸显出了诗歌的张力。
紧接着,“树叶和墙壁的灯无声地点燃。”,在这一句中,朱朱以部分代整体,用“树叶”和“墙壁”这两个意象,非常自然而妥帖地展现了小镇中树木与房屋的雨中之景。置于纷纷细雨中的树与屋,本身就笼罩在静谧与清冷之中。这里单独拿出了“灯”这个意象,使得雨中幽暗的天色与屋内的灯光平静地共存。“点燃”一词使用地十分精妙。雨中的一草一木都不可能被“点燃”,“灯光”也并非火光,然而“点燃”一词不仅呼应了这一节首句中的“光线”,继续将此节诗句的色调调亮,同时,又巧妙地舒缓了雨带给人的微凉之感。
整体上看,这一节以三组意象的无声并置的方式呈现出三幅特写画面,延续了舒缓幽静的氛围和相对克制的语调。
诗的最后一节,在平静克制的叙述中暗藏了情感的微妙起伏。相比于最初的版本,在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版本中,这一部分的诗句有所改动。诗人将“我走进平原上的小镇/镇上放着一篮栗子”[4]19改为了“我走进平原上的小镇,/沿着楼梯,走上房屋,窗口放着一篮栗子”[5]。修改版以一种十分精细的观察来逐步展现所察,不同于初版中直接给出的“栗子”所在的大范围,后者随着镜头的缓慢推移,展现出更为细致的描述。由“小镇”—“楼梯”—“房屋”—“窗口”的逐层推进,节奏极其舒缓,语词平静所造就了情感的克制与冷静。“栗子”的意象较为独特,在色调上,它呼应了第一节中的“褐色的树”,从而使的全诗呈现出一种由视觉上“暗”—“明”—“暗”的巧妙切换。此外,“栗子”的意象也并非这首诗所独有,在《怀念安妮·塞克斯顿》中,朱朱写下这样的诗句:“每当我第一次吻你总是在夏末/栗树下明亮的夜幕。”[4]23在《希腊》这首诗中,则这样描述:“灯光照耀着你,栗子树一样浓密的/发丝。屋顶下,自己的气息/像从家乡带来音信的陌生人/在眼前无所顾忌地走动。”[3]86笔者看来,在朱朱早期诗歌中,“栗子”的意象与诗歌创作紧密相关,“栗子”作为一种食物,意味着收获,栗子树丰收的时候,不仅需要采摘,还需要将其外层的形如针状的外壳去掉,才能获得果实。而这种艰辛的过程也亦如一首好的诗歌的创作过程,不仅需要精神养料的长时间培育,还需要语言的锤炼和打磨。因此,“栗子”在这首诗中可以视为诗的隐喻。
“窗”似乎成为朱朱早期诗歌中常常伫足的地点:“从这扇窗望过去,/在炽热的街道上,能听见抖动的铠甲声”[4]36(《小瓷人》);“我躺在窗台上,不会因为爱你/而有激情”[4]15(《过去生活的片断》)。“在窗前的晨风中我稍稍恢复了强壮/房间的角落里投下的那一道道高大的影子”[4]13(《我梦见一头狮子的相互撕咬》),等等。“窗”是屋内和屋外世界的通道之一,透过窗,既能观察屋外的景象,也会被屋外所窥视和查探。正如此节诗中所给出的设定:“沿着楼梯,走上房屋,窗口放着一篮栗子。”可见,窗口的所在地是“楼上”的情景。90年代诗歌发展的情景和诗人的处境,正如朱朱创作于1991年的诗歌《楼梯上》:“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4]85“在楼上”意味着对诗歌道路的坚守,继续在“修远”的道路上摸索攀爬。然而不同于1991年创作《楼梯上》这首诗时,对“楼上”未知领域的“黑暗”感受,1992年,朱朱在诗作《小镇的萨克斯》中,对于诗歌自身的看法逐渐乐观。“窗口”的出现意味着“楼上”看似有限的空间领域却能够依仗其较高的地势而俯视“楼下”的面貌,同时也意味着“楼上”的世界尽管处于艰苦的探索之中,却独立而不封闭,与外界并没有隔阂开来,处于一种可以相互的观照之中。“窗口放着一篮栗子”意味着诗歌所获的成果,也将是有目共睹且共同认可的。这是一种对诗歌发展的自信和坚定的信念。
最后一句“我走到人的唇与萨克斯相触的门”呼应了诗题与第一节中出现的“萨克斯”这一意象。不仅首尾呼应,使得萨克斯曲风成为全诗的暗含背景乐,增加了诗的韵致。同时,“人的唇与萨克斯相触”仿佛一首乐曲即将吹响,笔落至此,一首诗也刚刚写完。这种巧妙的安排,使得诗作在结束时依然显得意犹未尽,更增添了诗韵。
三、“一只狼寻找话语的森林”
《小镇的萨克斯》一诗,总体上来看,既具体,又抽象。语词简洁,画面纯净清透而富有音乐性。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进一步咀嚼诗句和统观朱朱于90年代创作的诗作。不难发现,这首诗更多地是面向诗歌自身。正如蔡天新所言:“朱朱比较擅长的是把一件抽象的事物镶嵌到一个真实的画面中。”[6]朱朱在其诗歌中曾明确地表示过:“诗是诗的主题”的观点:“请教我如何写水晶的诗,/诗是诗的主题,/写一种神经质的魔术,它撑起你们圣诗上的穹窿,/我要得到你们的办法,/能够有一次超尘世的凝视。”[4]155(《更高的目标》)他所要竭力保持的是诗歌自身的完整和纯净。此外,在其诗作中,也多次涉及到关于诗歌本身的看法。“漫长的冬天,/一只狼寻找话语的森林。”[4]65(《我是弗朗索瓦·维庸》)由此,亦可以进一步体味朱朱对语词的重视程度,其对语词精致地追求亦如冬日里一只狼的坚持和凶猛。对语词的重视对于朱朱而言并非只是一时之兴,而是贯穿于他创作历程的一个重要命题:“我找到了自己的弦 它在我的手拿不动的橡木里/聆听我的声音。”[4]94(《雨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我走过大风,也走过一下午的纬度/和海——语言,语言的尾巴/长满孔雀响亮的啼叫。”[4]25(《沙滩》)对语词的精准把握和细心发掘,使得朱朱早期诗集《枯草上的盐》面向了对诗歌本身的保卫和对“诗是诗的主题”的力行。“‘诗是诗的主题’显然意味着,诗最终必须回归到它自身,哪怕再重大的主题也决不应损害诗,这几乎是一条无形的律令。”[3]17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镇的萨克斯》也是一首以“诗”为主题的诗,尽管《小镇的萨克斯》所具有的一种内向性,使得诗歌面向的是诗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和其所观的诗歌空间,但是并不因其的内蕴而影响到了诗作为诗自身的完整而存在,他以其清洁而克制的语词运用,将诗意与诗韵不着痕迹地完美结合起来。而这种对诗完整性的维护也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朱朱在诗作中对语词的精致把握。
作为一只寻找话语的森林的“狼”,朱朱在《小镇的萨克斯》中所表现出的对语词的节制、准确和细致,也不禁令人赞叹。纵观其诗作,新奇的比喻时常可见:“树木躺在冬天的睫毛上/被这女神拔去头发。”[4]23(《怀念安妮·塞克斯顿》)贴切的表达准确而细致:“人的意识就是飞蛾/丛林里轰响的马达。”[4]32(《人的意识就是飞蛾》)对语言节制的把控也更显谨慎:“朱朱比他的同代人更知道节制的必要,他小心地避开铺叙和为文而造情的似是而非,尽量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力;往返于大自然和城市之间,他采集、冶游,用物类的眼光观看,虽然难以每次做到预期的成功,却对想象之翼可以‘展翅在最小的损失中’满怀自信。”[7]由节制也通常造成朱朱诗歌中节奏的缓慢,节奏舒缓充分体现在《小镇的萨克斯》中:“朱朱的慵倦或惰性促使他缓慢地思考问题,表现在谈话上是一种时间上的滞后,这无意中收到了逼迫对方注意倾听的效果;表现在文字上则让他得以比较从容地控制语言的节奏,进而获得一种抽象的特质。”[6]160
蔡天新指出:“朱朱对当代汉语诗歌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他的作品里,诗歌的形象既不是为了发泄内心的压抑,也不是为了批评的需要营造的虚拟,而是作为语言的一种发现存在。”[6]163臧棣说:“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2]70“个人化”写作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改善着曾经一部分追随着宏大主题的诗歌表露出的语言上的空洞与贫乏,然而激情的放纵和宣泄所带来的语词的泛滥和随意在当时却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语言”向来是现代诗歌的一大重心。然而,在一些顺时的潮流之下,一些过分看重语言的不及物性而游戏语词的现象时而浮现,放空了诗歌的内核。一些没有充分驾驭语言的诗作又疏于对语词的把握。作为自觉的“语言发现者”,朱朱对语词的发现与营造超脱了浮泛的技巧炫示和过度的情感宣泄,它面向的是诗歌本身的完整,直入人的精神世界,发掘诗歌本身举足轻重的构成部分,呈现出语词本身构成关系的意外与奇妙。正如论者张桃洲所言:“‘发现’意味着一种语言潜能的唤醒,显示写作已经触及语言最鲜活的区域,实现了对于语言的再度创造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重新构建,从而带来阅读上的惊异感。”[3]175在朱朱笔下,诗歌秉持着它自身难以比拟的纯粹性,诗歌创作并非是轻松的,语词的发现之旅更是充满着艰辛,在每一次全新的创作路径上,它不断地刷新着创作者的忍耐强度。即便如诗人自己所意识到的:“至于进入到真正的写作过程里,词语之间的构成关系仍然是意外的、难以把握和超出控制的。”[8]他也依然坚持在这样的“灵魂的奇遇”之旅中虔诚求索。
在告别了早期诗歌创作阶段后,朱朱后期的诗歌创作转向了对主题的深度开掘,语词也逐渐由简约而转向丰富。作为自觉的“语言发现者”,朱朱以其独特的风格自90年代开始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诗歌所显现出来的独特魅力,值得反复回味和品读。
[1]张桃洲. 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92-102.
[2]臧棣. 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0-71.
[3]张桃洲.寻找话语的森林——论朱朱诗中的词与物[J].诗探索,2004(Z2): 169-189.
[4]朱朱.枯草上的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蔡天新.现代汉诗100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02.
[6]蔡天新. 在耳朵的悬崖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宋琳.朱朱诗歌的具象方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80-82.
[8]朱朱,木朵.杜鹃的啼哭已经够久了——朱朱访谈录[J].诗探索,2004(Z2):207-216.
(责任编辑:杨燕萍)
本刊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
《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声明
为了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继续扩大学术交流的渠道,《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3年上半年续签了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协议。在本刊上发表的文章,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不同意文章编入该光盘版和数据库,请另投他刊或特别声明,需另作处理。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Words ——Reading the PoemTownofSaxWritten by Zhu Zhu
Lin Lin
(College of Li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On the basis of his early poems and the concrete peru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etry transformation in 1990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ypical images in the early poems of Zhu Zhu taking his early masterpieceTownofSaxas the main object and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ing on Zhu Zhu’s reflection on the poems, we tri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words the poet selected.
TownofSax; Zhu Zhu; words; poetry in1990s
10.3969/j.issn.1672-7991.2015.04.010
2015-10-29;
2015-11-18
林 琳(1991-),女,湖北省应城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
A
1672-7991(2015)04-0055-06
臧棣曾说:“80年代的诗歌主题因为受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