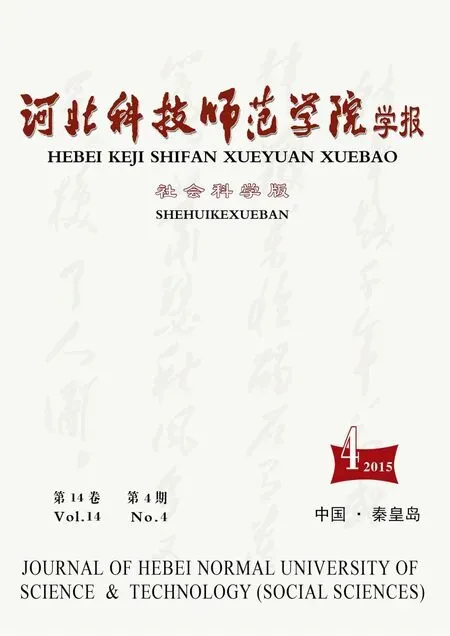欠发达丘陵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以西充县为例
白 俊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欠发达丘陵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以西充县为例
白 俊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基于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证调研,对四川丘陵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农民文化素质低、政策法规不到位、培训项目和内容缺乏创新、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问题。提出从立法引导、政策扶持、资格准入、资金帮扶、社会保障五个方面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期推动四川丘陵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业的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欠发达丘陵区;培育;路径构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聚,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1]。截至2011年末,中国人口总数为13.473 5亿人(除港澳台),城镇人口6.907 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1.27%,城镇人口在数量上首次超过农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4.98%,与此相对应的城镇为11.69%[2],农业从业者人数2001年的36 399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26 593万人,相同年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34.8%[3]。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农业生产后继无人,未来“谁来种田”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2012年首倡“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时代正在呼唤以农业生产作为终身职业的新型职业农民[4];2013年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强调建设现代农业需要人才智力支撑;2014年又提出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有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
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现代农业的经营性人才。因此,笔者以四川省西充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剖析当前欠发达丘陵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以加快四川丘陵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一、西充县概况
西充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偏北部,属典型山地丘陵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沟谷纵横,丘陵密布,属典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热量充足,年均降水量959.2mm,年均气温16.8℃,年日照时总数1 302.5h;嘉陵江、涪江等水系川流而过,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2013年统计表明,全县地上水资源3.3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0.41亿m3,全县水资源总量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8.70%,在发展农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5]。西充县下辖15镇29乡,总面积约1.1万km2,人口约68万,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该县资源稀缺、交通不畅、矿产贫瘠、工业发展滞后、经济基础薄弱[6]。1994年,西充被评定为四川省省级贫困县。
西充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优势,以“绿色、有机、生态、集约”理念为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经营,积极培育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懂政策的新型职业农民,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目前,西充依托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截至目前,西充县已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6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型150人,社会服务型150人,生产经营型300人。此外,该县在现代有机农业发展方面成绩斐然:2010年被列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披上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国”字号“战袍”,90多种农产品获国家有机农产品资格认证。
二、西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现实困境
(一)职业农民来源单一,文化素质参差不齐
1.职业农民来源单一,劳动力结构劣质化
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正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危机,首先,男女结构不协调。在受调查的对象中,男性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多于女性,约占65.2%,女性则占34.8%,男女对比差异明显。其次,职业农民来源单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避免对培育对象设置限制条件,吸收农业生产的经营型人才,夯实农业生产队伍。但调查发现,新型职业农民来源单一,主要以留守农民和返乡创业农民工为主。通过对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结构调查发现:留守农民占37.8%,返乡创业农民工占33.9%,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占2.7%,退伍转业军人占16.5%,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的城镇居民占1.7%,其他群体占7.4%。留守农民和返乡创业农民工占到新兴职业农民总数的71.7%,是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力军。但作为掌握知识和资金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城镇居民仅占5.4%,这说明该县新型职业农民来源结构单一。
2. 劳动力素质偏低,弱质化问题严重
农民是文化素质的高低,对我国农业的改造转型有着决定性意义[7]。目前,我国具有小学及初中文化水平比例高达67.99%,高中文化水平为16.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0.59%[8],而这仅仅是当前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平均水平。而对于位置偏远、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更是低于平均水平。据中央农广校对全国农民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务农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年,初中学历以下占82.1%、高中学历占16.8%、大专学历以上占1.1%[9],这与国外绝大部分农民文化程度在本科之上的情况相差甚远,形成明显的“洼地”。
通过对375个调查样本分析表明:西充县劳动力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为主,占劳动力总量的80.1%,超过一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约占19.9%,其中高中文化程度占15.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1%,说明农村高学历劳动力严重短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充县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群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符合现阶段欠发达丘陵区农民现状,但就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上来看,西充县低于全国6.49个百分点,说明西充高层次农业人才培育方面存在短板。
(二)国家政策性扶持缺位,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
1.缺乏政策法律支持,职业农民认定困难
农民职业培育,是加快农民实用性人才队伍建设、带动农民创业兴业、适应新型下我国农业改造升级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农民职业教育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加之政府在强农、惠农等方面政策倾斜不明显,缺乏良好的政策保障服务环境,主要原因有:
第一,国家涉农法律制定滞后,相关的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目前为止,我国仍没制定涉及职业农民教育的专门法律,对农民教育的组织管理、经费投入、受训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资质认证等更是无从谈起[10]。
第二,教育优惠政策倾斜不明显,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农民对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需求明显,但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不仅受身份和时间的限定性,还受经济、生活、地点等多重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中等职业教育大门之外,有失教育的公平性。调查发现,超过70%的农民渴望获得学习的机会,但是受国家教育政策影响,农民无法进入中职院校继续深造。
第三,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建设滞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是农业朝着“四化”(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保障,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民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建设发展缓慢。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在职业农民认定标准、认定程序、保障措施中存在较大差距,直接影响了培育目标的制定、培育措施的选择以及培育效果的达成,不利于激发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 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公共服务意识淡薄
地方政府是职业农民培育的决策者、实践者和主导者。西充县在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工作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第一,职业农民培育管理混乱,行政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在培育中突出“管理”而非“治理”,没有制定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也未能切实承担起引导、指导、服务培育农民的职责,使得职业农民培育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无序性、随意性”,行政效率不高。
第二,部门之间各行其是,推诿扯皮现象严重。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鼎力配合、通力合作。但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在职权的分散性,导致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踢皮球“现象时有发生,出现“有利相互争、无利相互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机关作风严重。
第三,地方政府宣传引导不力。地方干部没有吃透中央政策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村实用型人才队伍建设,合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本”的精神要义;没有充分利用政府的宣传工具,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营造良好的培育氛围;没有把农民增收创收与兴业创业有机结合起来,突破农民固有的身份属性,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没有把履行本职工作与服务农民、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相衔接,疏于对职业农民政策方面的宣传引导,工作主动性较差。
第四,农村保障体系建设、基础施设建设落后,社会服务水平低下,留住农业人才后劲不足[11]。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方面差异化待遇,同时由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相配套的农业信息化服务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速度,高素质农业人才留在农村的意愿度不高。
(三) 培训项目缺乏创新,培训内容乏善可陈
培育职业农民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的实际,创新培育路径和方法。但是受经济因素和农村职业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培训内容和内容上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通过对西充县大全、凤鸣、莲池等8个乡镇种植业大户、家庭农产、养殖业大户的实地调查,发现该县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以下问题:
1.培训方式落后,实效性不高
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走过场、排形式问题严重。开展的农民培育课程,从形式上看,70%以上为短期集中培训,这种授课形式时间短、任务重,农民学到的知识有限,53.3%的调查对象认为培训效果不明显;从地点上看,授课地点多在乡镇政府,远离农村,农民参加培训的交通成本较高,影响农民参训的意愿度;从时间上看,短期培训班在特定时间集中教学,调查发现68%的培训项目集中在7~9月,这种培训时间安排脱离农民生产实际,较为不合理。
2.内容缺乏新意,实用性不大
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理论教学轻实践应用,过于注重农民学历的获得,教授的内容局限在传统种养技术方面,没有培育农民树立全产业链农业经营理念,对农产品品牌化经营、营销策略、产品加工和家庭农产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更是少之又少[12]。除此之外,对农民涉农政策法律、农业集约化经营、信息网络技术、农民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培训也十分匮乏。通过对西充8个乡镇的走访发现,26.7%的农民想要学习创新创业方面的知识,发展现代家庭农场,走农业产业化之路;31.5%想要学习信息网络技术,通过网络扩大农产的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40.1%想要学习种养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3.培训师资匮乏,专业性不强
实训基地缺乏、优秀师资匮乏、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比较普遍。调查发现,西充县职业农民培育师资队伍结构复杂,主要由高级农业农艺师、种养能手、农业技术带头人等临时抽调组成,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参次不齐,缺乏专业型教师。培训内容也仅仅局限在自身所从事的专业范围,碎片化问题严重,缺乏完整、系统、专业的知识架构。
(四)财政投入杯水车薪,人才培养难以为继
1.资金投入不足,经费难以保障
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职业农民经费投入增长较快,但是从全国农民培训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看,资金投入不足问题仍然突出[13]。第一,财政资金来源结构单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资金来源主要以财政投入为主,企业和个人投入为辅。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规模庞大,农业人口众多,在没有充分调动社会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培育职业农民,对于一个农业、工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的西充县而言,无疑加重了地方政府财政的负担。第二,财政资金使用分散。新型职业农民涉及多个部门,由于部门之间的分散性,在资金使用上容易出现交叉重叠,在资金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导致财政资金低效使用。西充县政府部门也存在权利重叠,职能重合的现象,地方财政资金在拨付使用上存在着疏于监管、低效配置的问题。
2.培训费用虚高,农民负担过重
在我国职业教育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财政拨款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农村经营型人才,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在西充县走访调查中,发现多数乡镇采用“5+3+2”的培育模式,即政府补贴50%,农业经营组织出资30%,农民出资20%,用于完成整个职业教育。因西充县位于川东北丘陵地带,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是很优越,且属于省级贫困县,农民经济收入处于全省中下游水平。对于承担20%的费用完成职业教育的规定,群众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在单纯考虑费用的前提下,有65%的农民认为应扩大政府和农业经营组织的出资比例,农民不出或少出;2%的调查对象认为职业教育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参不参加无所谓。
三、完善西充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构建
(一)抓好法律政策顶层设计,创新政府宏观管控能力
1.加快国家立法,保障农民权益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14]。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体系,例如美国的《帕金斯法Ⅰ-Ⅳ》、《雷莫尔法案》、《史密斯-利费法》;日本的《青年振兴法》、《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本法》;韩国的《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农渔民发展特别措施法》等,为农民职业化教育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因此,在深入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经验之上,结合我国已有的《职业教育法》、《教育法》和《农业法》,抓紧出台与之相关的配套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司法解释,完善其中关于“人员选拔、培育标准、资格认定、跟踪服务、监管评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制定专门性的《新型职业农民保障法》、《农业经营型人才培养法》,着力构建内容全面、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2.加强政策扶持,优化培育环境
国家应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扶持政策顶层设计,加大国家政策对职业农民教育的倾斜度[15]。第一,丰富职业教育政策,加大惠农富农力度。将开展职业教育的单位、机构、学校作为政策扶持对象,发放职业教育补贴,同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或免税形式增加培训团体的收入,鼓励他们从事农民职业教育。第二,制定信贷优惠政策,缓解职业教育资金紧缺。通过专门的信贷政策,降低信贷的门槛,增加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资金。
3.创新政府管理,科学合理调控
各级政府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体,关系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成败[16]。政府部门应着力建设管理有序、运行高效、面向市场、多元开放的职业农民教育体系。第一,加强宣传,扩大影响范围。政府干部应破除僵化的管理思维,认真吃透中央政策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精神要义,提升农民对国家惠农政策的认知和理解,积极鼓励农村经营型人才创新创业,以创业代替就业,让农民享有创业的自豪感。第二,科学调控,提高办事效率。政府部门应加强自身行政体制改革,裁撤闲散重叠部门,减少部门间的职能交叉,提高组织运行效率;突出服务意识,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告别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形象危机,发挥好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主体作用;制定规范的管理措施,严格管理职业教育机构、团体、从业者的行为,保证职业教育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二) 科学规划职业培训内容,提升农民农业经营水平
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四川丘陵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职业教育的内容,秉承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农业与非农产业相结合,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17],优化培育路径,创新培育方式方法。
1.夯实培训力量,壮大师资队伍
建立职业教育人才库和专家库,广泛吸收农业专家学者、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种田能手等技能型人才,参与到职业农民培训中,加快建设一支结构合理、技术过硬、认识全面的师资队伍,提升西充县,乃至整个四川丘陵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竞争力。
2.坚持科学规划,提高农民素质
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精心设立一些“特色鲜明、内容全面、优势明显、重点突出”的精品课程,加强农民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农技培养、生产服务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加强农民创新创业方面的培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3.改进培训方式,创新培育路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采取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发展远程教育,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学习。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举办农业基地培训班或农民“田间学校”,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学,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三) 健全职业教育融资体制,建立农民培育长效机制
1.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预算体系
职业农民培育所需资金应在国家预算中明确列出,及时高效拨付,打消农民参与职业培训的后顾之忧。同时,职业教育培育机构要建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账户,健全资金支出手续,完善支出明细,规范使用资金,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2.加大对职业农民专项贷款支持
职业农民教育及农民创业需要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国家应出台相关的照顾性优惠政策,降低农业信贷的门槛,低息或无息等形式,增加扶持农村发展的资金总额。同时,建议政府减免农民创业型企业的经营性税,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资助。
3.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
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的发展,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融资体制,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的投资理念,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农村交通、水利、教育等领域,简化政府审批手续,打破传统投融资体制中主要依靠政府分配投资资金的局面,减轻农民费用负担,增强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主动性。
4.构建政府监管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对于投入到农业职业教育中的资金,各级政府明确应建立规范、完善、全面的监管机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禁截留、挪用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对于违规行为给予法律惩罚,保证投入资金利用效用最大化。
(四)构建农业社会保障机制,稳定农村农业生产大局
实现农民职业体面化,必须构建“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服务农民,扶持农民,保障农民享有生命健康和社会福利等权利[18]。
1.土地改革,实行土地流转集约经营
加快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就必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农村新一轮土地资源整合的工作重点。土地承载着农民太多的希望和寄托,但长期以来,农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付出与收益严重不成比例,且对土地的依附性较大。土地流转就是要对流转的土地实行集约、高效、生态利用,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将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鼓励农民以职业身份重回农业生产,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落实“十八大”精神中“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精神要义。
2.打破壁垒,探索城乡统一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制约城乡人才流动的基础性制度,也是落实我国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瓶颈。培育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经营型人才,就要突破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打通城乡间社会阶层自由流动的通道。一方面,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创业,享受与城市户口同样的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无差别待遇,缓解城市人才紧张局面。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城市专业型人才深入农村,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提升农民农业经营能力。同时,地方政府应改善农村引才政策、用才平台、留才环境,实行“刚柔并济”引才战略,打破户籍、档案、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的限制通过人才引进、智力借入、业余兼职和人才派遣等途径,夯实农村人才队伍。
3.扩大半径,丰富农村社保保障内容
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结合农村发展实际,实行“弹性”收费制度,丰富养老保险险种,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社会养老的覆盖比率,使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让农民农业生产生活无后顾之忧;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多渠道扶持的工作思路,走多元化的贫困资金筹集道路,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通过有奖募捐、发行福利彩票等形式的社会福利活动筹集保障资金;扩大农村失业保险: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组织,必须按照城市户口的统一的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享有与城市户口同样的失业保险待遇;深化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农村医疗定位应“以保大病和住院为主,适当兼顾部分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特殊门诊费用”[19],降低报销起付线,提高报销补偿比例,实施有区别的分级报销制度,注重发展基层医疗事业,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市”,提高农民享有的医疗服务质量。
[1]张桃林.让更多高素质农民成为职业农民[N].农民日报,2012-03-22(001).
[2]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
[3]朱广其.基于职业农民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考[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4):33-37.
[4]朱启臻,闻静超.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育[J].农业工程,2012(3):1-4.
[5]西充县人民政府网.自然地理[EB/OL].[2015-09-02].http://www.xichong.gov.cn/index.php?m= content&c=index&a=show&catid=20&id=5012.
[6]张媛,张娉婕,胡经伟.关于深化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学,2009,16(6):258-260.
[7]杨成明,张棉好.多重视阈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28):76-82.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9]郭智奇.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J].中国农业教育,2011(1):6-9.
[10]郭智奇,齐国,杨慧,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7-13.
[11]沈红梅,霍有光,张国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阈[J].现代经济探讨,2014(1):65-69.
[12]魏学文,刘文烈.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与培育机制[J].农业经济,2012(7):73-75.
[13]付铁峰.新农村建设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7.
[14]吴易雄.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28):70-75.
[15]王泰群,秦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与增加农民收入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17):5725-5726.
[16]张亮,张媛,赵邦宏.河北省农民培训的有效路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2):46-50.
[17]高苗.咸阳市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
[18]毛冠凤,宋鸿,刘伟.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理念、障碍和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3):108-113.
[19]谭湘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与模式选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4):132-137.
(责任编辑:刘 燕)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Undeveloped Hilly Areas: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Path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Xichong County
Bai Jun
(Management School,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 cultivation in Xichong county, this essay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 construction in hilly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jor problems include farmers’ low cultural quality, incomplet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 lack of training programs and content innovation and insufficient funds input that restrict the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 culti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the author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through five aspects as legislative guidance, policy support, qualification admittance, financial aid and social secur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 cultivation in Sichuan hilly areas.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 undeveloped hilly areas; cultivation; path construction.
10.3969/j.issn.1672-7991.2015.04.008
四川省教育厅2015年省级大学生创新项目“欠发达丘陵区培训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研究”(201510638058);西华师范大学2014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关于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的发展探讨”(427115)。
2015-11-03;
2015-11-10
白 俊(1990-),男,河南省南阳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G725
A
1672-7991(2015)04-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