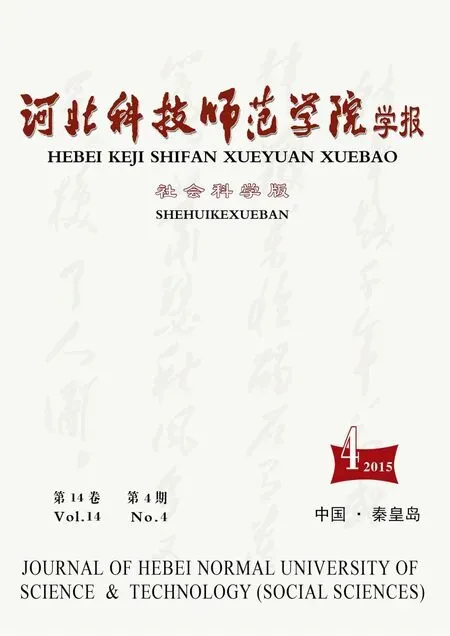“鹏鸠之比”与“忙闲之辨”
——南宋休闲思潮中的价值观嬗变
章 辉,李建萍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鹏鸠之比”与“忙闲之辨”
——南宋休闲思潮中的价值观嬗变
章 辉,李建萍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南宋文士具有求异型思维和怀疑、独创精神,这促发了当时具有时代特点的休闲思潮。“鹏鸠之比”和“忙闲之辨”便是这种思潮中的独特文化现象。作为对传统价值观的重估和对生活方式的反思与拷问,它显示了南宋文士价值观、人生观的嬗变。此种嬗变,直接造成了他们生涯中的“休闲转向”,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南宋休闲文化的面貌。
南宋;休闲;价值观
一、“认取自家身”:南宋文士的独特价值观
休闲观念在宋代思想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不了解宋人的休闲思想,就不能知晓宋代文化的某些成因,也就不能全面地把握宋代文化的面貌。对于南宋,情况尤其如此。历史证明,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之发生,大凡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先行。南宋休闲文化,首先就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潮流,即休闲思潮的兴起和自觉。
李泽厚认为,在东汉末年到魏晋,产生了一种新思潮、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1]89,“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90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赵树功提出:“魏晋时期……闲情,作为一个美学的观念与一种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之追求也因此而确立。”[2]2如果说魏晋是休闲观念的确立时期,那么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则可谓休闲思潮全面流行并得到充分实践展开的时代。南宋文士的休闲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思潮,对全民的生活、伦理及审美趣味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文士放弃了前代那种政治情怀,放弃了对中原、北方的政治情结。他们在南渡之后发现了江南的诗意山水,转而在休闲中实现精神自救,其结果是使宋代文化更加乐趣化、精致化、审美化。在南宋的诗词、文章中,休闲思潮如晶莹的泉水随地涌出。闲、疏、懒、拙、萧散、逍遥等大量字眼作为正面、褒义的词汇出现,突出地证明了对休闲的肯定。正是在休闲思潮的推动下,南宋休闲文化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一个高峰。
南宋为何能产生休闲思潮的兴起和自觉?这与南宋文士独特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宋人的理性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独创精神,已经得到学术界之公认。正如吴功正所言:“宋人的思维是求异型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看法,决不轻易认同前人和当代人。求异思维使其有独创性,他们对人、事以致国事的看法、见解总是与众不同,有自身独到的视域、观照点和论析方式。”[3]39由于理学大兴,南宋文士更加喜爱静心思理,具有特立独行的价值观。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看重个人的价值,清醒地力求成为“真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愿随波逐流,随时俯仰。请看他们的表白:“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朱敦儒《临江仙》),“宁作我,岂其卿”(辛弃疾《鹧鸪天》),“一着要我决,岂在他人评?”(张镃《小疾书兴》)如果说以上是诗人的诗化语言,那么思想家的论述则更加清楚,更具哲学理性:
“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众人汩没不自知觉,可怜,可怜!”[4]286(《五峰集》卷二,胡宏《与彪德美书》)
南宋文士的这种独特价值观也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休闲生活。胡寅称李似矩“轩冕倘来,岂随人而俯仰;山林独往,聊卒岁以优游”[5]247。陆游的休闲谋划很坚定,绝不为他人的价值观所转:“归哉不可迟,勿与妇子谋”(《初秋梦故山觉而有作》),“挂冠当自决,安用从人谋”(《还都》)。张镃则表示:“非求世上人看好,但要闲中句律昌。”(《次韵酬陈伯冶监仓》)他们对休闲生涯的一往情深,是来源于自家对休闲价值的体贴、比较和判断。这种判断导致了和前代不同的一种整体性价值观的嬗变,也导致了整个南宋时代的休闲取向。正如潘立勇先生等指出的那样:“过一种闲的生活并高度认同闲的价值,并非是士大夫消极的对外界、人生的逃避、否定, 而是更实在、更坚定、更真实地去拥抱生活、面向生活、面向自我生命。”[6]
这种南宋文士的价值观嬗变,是对传统功利人生观的颠覆。它让人们重新审视习焉不察的人生,促使人们从心所好地去过一种真实、智慧的生活。而此类南宋文士,以文学家、诗人、词人居多,代表人物有朱敦儒、陆游、范成大、辛弃疾、倪思、费衮、张镃等。平心而论,尽管他们中间也存在一定事功倾向(甚至具有一定官位,可称为政治家),如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但在宋代二重性文化心理影响下,他们同样积极倡导休闲人生,对于休闲思潮的自觉兴起最有推动。吴功正曾指出:“兼有剑气箫意,这也才是立体的陆游。”[3]313“(范成大)对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的观照意识颇得隐逸风味”[3]332,“豪气、雄才、闲情,构合为一个完整的辛弃疾的素质、心态、精神。”[3]347这可谓透露了对陆、范、辛等人休闲个性的某种意识和认可。此外,在宗教界人士中,禅门的宏智正觉、无准师范,道家的白玉蟾等,尽管他们主要不是在世俗立场而是站在宗教立场,为解脱涅槃或求道成仙等终极追求而倡导休闲,但同样揭示了休闲的高度价值,同样可以作为南宋倡导休闲思潮的某种代表。
在以上人群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之中,有一个非常富于趣味的文学现象,它最能反映出南宋休闲思潮中的价值观嬗变——那就是“鹏鸠之比”和“忙闲之辨”。
二、“鹏虽运海不如鸠”:传统价值观的重估
“鹏鸠之比”是南宋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它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对于激发南宋休闲思潮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庄子·逍遥游》里描绘了鲲鹏展翅的壮阔景象: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面对鲲鹏的伟大事功,庄子用蜩、学鸠、斥鷃反应加以对照: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历来认为,庄子在这里褒扬鲲鹏的壮举,赞扬了它们的伟大事功,而否定和嘲笑斥鷃的狭小视野。而在南宋,这种价值观却发生了明显的集体性的反思和重估。哲学家李侗的《吴方庆先生行状》:
公既得谢,优游旧隐,结庐号曰“真佚”,终日啸咏其间。……方知命之年,遂有告老之意,或谓之曰:“公血气方刚,事业未究,奚去之果?”公曰:“鹏鷃逍遥,各适其道。”平生仕宦,未尝有毫厘营进之心,卒遂所请。怡情崖壑,养逸丘樊,徜徉于闾里,以觞咏自娱,其古逸民之风欤?[7]168(《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一,《吴方庆先生行状》)
在吴方庆的话里,“鹏”隐喻着事业成功,而“鷃”代表着休闲自适。在他看来,这两者的价值是相等的,因为他们“各适其道”,均可自得其乐。正因如此,他才在别人看来“血气方刚”的年纪放弃“营进”,选择优游养逸。对此李侗深表赞赏,称其为“古逸民之风”。 胡寅也反复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鷃下蓬蒿,顾逍遥而已足;凫飞渤澥,计多少以何亏?”[8]119(《斐然集》卷六,《致仕谢表》)
“逐飞凫于渤海,从斥鷃于蓬蒿。”[8]255《《斐然集》卷七,谢赵盐启》)
“篷艾卑飞,自适鹪鹩之趣。”[8]257(《斐然集》卷七,《答刘帅启》)
“抢榆鷃翼,宜戢伏于一枝;击海鹏程,盍鶱翔于万里?”[8]260(《斐然集》卷七,《答邓倅柞启》)
“既无羡于飞扬,即自安于固陋。”[8]277(《斐然集》卷八,《代向深之上范漕书》)
另一位文士仲并也自称:“惓惓畎亩,每倾葵藿之心;碌碌蓬蒿,安知鸿鹄之志”[9]253(《浮山集》卷六,《代淮西守臣到任谢表》),貌似谦词,实则道出休闲选择之真实心志。他还祝愿友人张吏部“鹪鹩巢林,永遂一枝之乐。”[9]276(《浮山集》卷七,《贺湖州张吏部启》)
政治家、诗人范成大虽官居高位,但也认为:和鲲鹏的宏大事功相比,蜩、学鸠和斥鷃虽然只是安于蓬蒿的休闲生活,不过这种人生观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鹏鷃相安无可笑,熊鱼自古不容兼”(《丙午新正抒怀十首》),二者有其各自的意义,就和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一样,无法比较其价值:“春秋兰菊殊调,南北马牛异方。心醉井蛙海若,眼空鹏海鸠枋。”(《有叹二首》)而且,范成大的诗意还表露出另外一层:即休闲与事功是对立的。鲲鹏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休闲之乐,这正和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一样。而面对鲲鹏、鸠鷃所代表的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范成大多次明确表示:他愿意选择后者,因为自适自足的人生更让人快适:
身安腹果然,此外吾何求。《次韵温伯雨凉感怀》
身谋同斥鷃,政尔愿蒿莱。《除夜书怀》
大鹏上扶摇,南溟聒天沸。斥鷃有羽翼,意满蓬蒿里。《古风上知府秘书》
鲸漫横江无奈暟,鹏虽运海不如鸠。《偶然》
斥鷃蓬蒿元自足,世间何必卧高楼。《仲行再示新句,复次韵述怀》
而词人辛弃疾也在词里表示过类似的意思:“看取鵾鹏斥鷃,小大若为同。”(《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等等。
显然,大鹏和小雀所代表的就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事功型生活和休闲型生活,而前者就意味着多事和忙碌。因此,“鹏鸠之比”就必然地催生了“忙闲之辨”——南宋文士极喜谈及“忙”字并加以价值批判,这在文化史上同样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三、“底事随人作许忙”:生活方式的反思与拷问
在南宋文人眼中,“忙”是一种可笑的生命状态。例如,陆游诗全集中,“忙”字出现100余处,并且主要作为贬义出现。如陆游云“堪笑行人日日忙”(《过江山县浮桥有感》);范成大云“岭梅蜀柳笑人忙”(《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大笑羲娥转毂催”(《立春后一日作》),因而忙者堪愧:“腊浅犹赊十日春,官忙长愧百年身。”(《春前十日作》)南宋文人又认为忙更是悲剧性的,一种人世间注定的灾难,它随着每日太阳的升起而滋长。如陆游云“人事还随日出忙”(《桥南纳凉》),“万事可怜随日出,一生常是伴人忙”(《客多福院晨起》),甚至发出“人生各有时,何至终身忙!抚髀三太息,坠露湿衣裳”(《门外纳凉》)的悲凉哀叹。同样地,范成大感慨“日出尘生万劫忙,可怜虚费隙驹光”(《怀归寄题小艇》),张镃悲叹:“尘土奔忙举世人,无过白白鬓毛新。”(《鸥渚亭次韵茂洪西湖三诗》其三)
他们甚至将这种悲观的情绪投射到自然界。陆游云“更事多来见物情,世间常恨太忙生”(《春日杂兴》),辛弃疾云:“乱云扰扰水潺潺。笑溪山,几时闲?”(《江神子》)陆游对蜜蜂、蝴蝶、鸟雀的生存状态也持怜息的态度:“蜂蝶一春空自忙!”(《宇文子友闻予有西郊寻梅诗,以诗借观,次其韵》)“合合蛙何怒?翩翩蝶许忙!”(《雨霁》)“墙外蜜蜂来又去,可怜终日太忙生!”(《净智西窗》)“舒雁且为赊死计,鸣鸠便欲策勋忙!”(《久旱忽大雨凉甚小饮醉眠觉而有作》)范成大亦有“鸟雀有底忙?激弹过墙东”(《午坐》),“天公已许晴教好,说与鸣鸠一任忙”(《病起初见宾僚,时上疏丐未抱陆务观:春初多雨近方晴,碧鸡坊海棠全未及去年》)之句。
而禅门的释慧空也云:“天无所加,己日以劳。”[10]291(《雪峰空和尚外集》,《答灵空老辩韩书》)潘良贵对忙的状态描绘得更为具体:“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视耳听,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经营,杂然无一息暂止。……如是汩没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为静者之所怜悯。”[7]418(《默成文集》,卷三《静胜斋说》)还有两则短文,更为有趣:
“鄜延任子宁驻军瑞岩,拉王岩起、阮图、叶嗣忠杖履游石门,汲泉烹茶,清赏终日,超然有物外之想。回首尘劳,良可叹也。绍兴丙辰仲秋题。”[11]219(《闽中金石志》卷八,任子宁《瑞岩题名》)
“广都蒋城、吴大年,古郫李椿、秦亭、权师雄,大梁赵恂,阆中冯时,同谷米居约,以绍兴十八年九月十有四日访古菖蒲涧,观唐人武功子石刻,置酒碧岩溪,效柳子序饮。损其筹为一题,各以投之,或洄,或止,或沉者,皆赏,惟直前无坻滞则免。坐客率三四饮,笑歌谐嬉,终日乃罢。”[12]368(蒋城《碧岩题名》,《金石苑》)
很难想象,此类短小的即兴之语会被收入古籍,唯一的解释是,它们真实地表达了南宋人对忙碌生活的反思与对休闲生活的重视。这种反思,包括了探究这种事功型生活方式的起因与意义究竟何在。陆游发出这样的拷问:“底事随人作许忙?”(《东关》)“晓角昏钟为底忙?”(《冬暮》)“翻怜市朝客,扰扰为谁忙?”(《独意》)甚至采取某种黑色幽默来提问:“旧交散落无消息,借问黄尘有底忙?”(《即事》)范成大也质疑自己:“沐雨梳风有底忙?”(《百丈山》)张镃则自问:“百年劳役终奚为,一段风流忍独抛?”(《遊臞庵》)“遄经六六回,劳生竟何补?”(《重午》)在宗教世界观的浸染下,他们的结论颇具佛门色彩。陆游将人之所以忙归因于“业力”:“业力驱人举世忙”(《西林傅庵主求定庵诗》),而范成大则将之归因于“心境”:“心作万缘起,境生千劫忙。”(《舫斋晚憩》)但不论答案如何,其最终的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张镃所言的“世上尘劳忙若钻,想欲跳身脱羁绊”(《张郎中、尤少卿相继过访未果,往谢先成古诗寄呈》),究其实质,就是转向休闲。
因此,在对蓬间小雀生活方式的肯定和对“忙”的批判中,南宋人士的价值转向明确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休闲才是真理,是人间正道:
拙是天资懒是真。(范成大《有会而作》)
病笑春先老,闲怜懒是真。(辛弃疾《南歌子》)
人间乐事唯逍遥。(张镃《南园叔祖生日》)
人世只宜常放逸。(张镃《卧疾连日殊无聊赖,客有送二省闱试题者,因成四韵》)
水村居自乐,城市懒尤真。(张镃《代书回寄杨伯虎》)
同理,“闲人”才是卓越的人、智慧的人:
“世人学者急于爵禄之奉……穷年兀兀,老死章句,识者悲之。至于卓荦环奇之士,未始数数于此者,则必箕踞高吟,游心景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实锦囊,……”[13]134(《栟棕集》卷一四,邓肃《上龟山先生杨博士书》)
“人生如梦,无一实法,婆娑嬉游,以卒余景,不是痴人。”[14]23(《横浦先生文集》卷一八,张九成《与尚书书》二)
“时驾小车出,始知闲客真。”(陆游《车中作》)
“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15]3427(《说郛》卷七十三下,李之彦《东谷所见·闲》)
四、“要令闲健返耕桑”:人生道路的休闲转向
在“鹏鸠之比”与“忙闲之辨”的新型思维下,大部分的南宋文士都实现了“休闲转向”。第一个典型代表是朱敦儒。他本性恬退,早年就疏离仕途,自诩“清都山水郎”,过着闲雅的生活。后来被人向朝廷推荐,屡次推脱不得,方出仕为官。然而,复杂的官场生活使他无法适意,便又发出“我是卧云人,悔到红尘深处”(《如梦令》),“尘世悔重来,梦凄凉”(《蓦山溪》)的感慨,终于辞官而继续闲适生活。这时他的一首《减字木兰花》是他再度转向,重归休闲的思想总结:
无知老子,元住渔舟樵舍里。暂借权监,持节纡朱我甚惭。不能者止,免苦龟肠忧虎尾。身退心闲,剩向人间活几年。
“有何不可?依旧一枚闲底我。”(《减字木兰花》)
朱敦儒的转向深深影响了其后的南宋文士,为他们的出处取舍提供了依据和榜样。“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朱敦儒以后,涌现出大量的闲适隐逸词,以及‘效希真体’的词作。”[16]其后的陆游、范成大、辛弃疾、张镃等,莫不如是。
对陆游来说,《中国文学史》作者认为他写作诗词“是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寄托。……他只能在山水田园中寻求一时的解脱”[17]445,这恐怕是并非完全正确的。陆游自青少年时期便看重休闲的价值,而“渐老更知闲有味”(《看梅归马上戏作》),晚年的他在田园生活中更咀嚼出了休闲的深长滋味,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事多来见物情,世间常恨太忙生。花开款款宁为晚,日出迟迟却是晴。”(《春日杂兴》)在他看来,忙的、快的生活未必是好的,而晚的、慢的方式,更常常可能充满诗情画意。其对忙与闲的取舍,可谓泾渭分明。“历尽危机识天意,要令闲健返耕桑。”(《冬晴闲步东村由故塘还舍作》)作为一种完美而理想人生境界,休闲对他不是一时的解脱,而是觉悟后的终极追求。“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是他对休闲转向的诗意礼赞与恒久追求。
范成大的思想转向在“万境何如一丘壑,几时定解冠裳缚”(《胡宗伟罢官改秩,举将不及格,往谒金陵丹阳诸使者,遂朝行在,颇有倦游之叹,作诗送之》)之句中流露明显。而从《园林》一诗中则可明确认他转向的实现:“园林随分有清凉,走遍人间梦几场。铁砚磨成双鬓雪,桑弧射得一绳麻。光阴画纸为棋局,事业看题检药囊。受用切身如此尔,莫于身外更乾忙。”而从辛弃疾的“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临江仙》),“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临江仙》)来看,他同样也实现了休闲转向。
转向意味最浓的是张镃。且看:“要是从今后,休教枉却闲”(《冬至后五日,约客晨往极乐精舍,因寻梅湖山,作诗纪事》),“蜂巢蚁垤非吾乐,终买云扃种术餐”(《闲步游紫极观》),“会乞一闲归故隐,定因能赋结高人”(《苏堤观木芙蓉,因见净慈明上人,翌日惠诗,酬赠二绝》其二),“定将印绶弃掷归南湖,秋风与我还相娱”(《秋风》),等等。事实上,他的转向实践也是最富于风情,最可圈可点的。倘若细看他的《南湖集》和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相关记载,便会有详细的了解。
此外,南宋文士不但自己实现了休闲转向,还引导他人及时醒悟,得自在之乐。朱敦儒警醒友人:“虚空无碍,你自痴迷不自在”(《减字木兰花》),拷问友人“舍此萧闲,问君携杖安适”(《梦玉人引·和祝圣俞》),期待他们“放怀随分,各逍遥”(《梦玉人引·和祝圣俞》),“把俗儒故纸,推向一边,三界外、寻得一场好笑。”(《洞仙歌·赠太易》)陆游不但自己求闲,还要让子孙都得此中之乐:“岂惟自得闲中趣,要遣儿孙世作农”(《闲趣》),“更祝吾儿思早退,雨蓑烟笠事春耕。”(《读书》)无准禅师也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告诫他人走休闲之道:“山中坐,习闲成懒堕。”[18]946(《四威仪》,《佛鉴录》卷五)“我游江湖三十有四年,饱饭之余,一味闲打眠。子今迢迢苦寻讨,不知寻讨何慕焉?”[18]949(《送妷昭上人归乡》,《佛鉴录》卷五)张镃告诫高官:“风月属漁樵,真味岂能领?雍容补国手,斯宜理烟艇。”(《杂兴》其三十九)正是在这样的自觉与劝世下,南宋休闲思潮才会全面流行,南宋休闲文化才会高度繁荣与发展。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赵树功.闲意悠长——中国文人闲情审美观念演生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吴功正.宋代美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潘立勇,陆庆祥.中国传统休闲审美哲学的现代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2011 (4):168-173.
[7]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0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3]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18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陶宗仪.说郛三种(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季夫萍.乱离时代的“尘外之想”——朱敦儒隐逸思想和隐逸词研究[D].福州: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
[17]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45.
[18]前田慧云,中野达慧. 卍续藏:第12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责任编辑:刘 燕)
“A Metaphor on Pengornis and Turtledove” and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usy and Leis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Values of Leis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Hui,Li Jian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Chin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s had a special way of thinking with skepticism, which had an impact on the leisure tren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time. “A metaphor on pengornis” and “turtledove and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usy and leisure” was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is trend of thought. As a r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as a reflection and torture of life style, it showed the evolution on values and lifestyle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is evolution directly made the “Leisure Turn” in their careers, and deeply influenced the whole appearance of leisure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eisure; values
10.3969/j.issn.1672-7991.2015.04.002
2015-10-15
章 辉(1975- ),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中国美学研究。
C913.3
A
1672-7991(2015)04-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