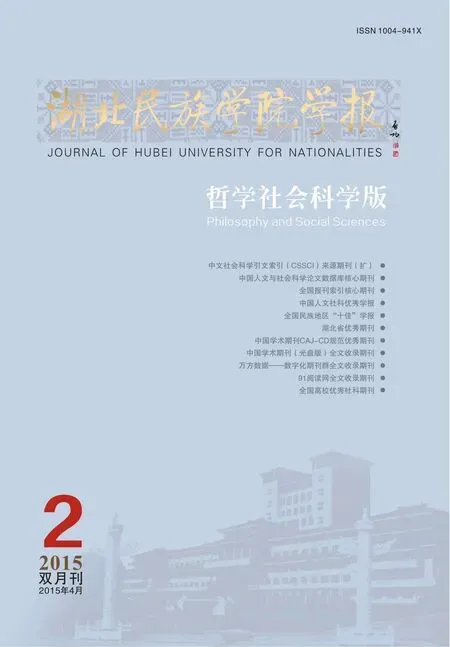原生态与现代性: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叙事研究
高焕静
(1.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原生态与现代性: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叙事研究
高焕静1,2
(1.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新世纪以来,以原生态文化为内核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通过对原生态与现代性冲突与协调的影像符码的运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这既有助于提高人们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识,也是少数民族电影实现大众化传播的路径之一。
原生态文化;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 叙事策略
少数民族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瑰丽风景,它丰富了我国当代电影的题材种类,并充分发挥了电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具体表现为不同时期影像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十七年”时期“充分传递出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不同,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原生态文化”的呈现为中心,以全球化和现代性作为影像叙事的背景,以原生态与现代性的张力来结构剧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文化反思和人文关怀,已成为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以原生态文化为核心: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
“原生态”一词与自然科学有关,最初指人类活动没有触及到的纯天然的自然景观或自然环境。[1]这一概念不断被移植嫁接,如今作为文化范畴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强调文化的一种初始的、质朴的、更贴近艺术源头的状态。[2]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化作为共享的意义,它的静止只是相对的,已有学者对“原生态文化”是保持其“原初模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把它理解为原封不动、原汁原味的东西,应在“流变”中来理解和把握。[3]文化的“流变性”不仅体现在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在作为符号而存在的文献式文化中。文化生活是一种具体、鲜活、生动、可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始终处于多重因素交错影响的动态发展格局中;当某一时期活生生的文化不再存活,便残存在记录中,成为文献的文化,文献的文化也因需要不断填充和重新阐释而具有动态性。这并不是反对“原生态文化”这一提法,而是需要换个角度对它重新界定和阐释。一般来说,命名是为了区分,正如人类社会早期,通过语言命名万事万物,使混沌不开的世界日渐清晰。以区分为目的的命名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是不重复,正是不同的命名产生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生态文化”,重要的不是“原生态文化是什么”,而在于“原生态文化不是什么”。
事实上,原生态文化是个新词汇,最早起源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末,田玉成写作《关于建立中国土家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意义及可行性》一文,对文化的“原生态”作了详尽论述。[4]国家文化部征用“原生态”这一概念后,“原生态文化”迅速在“民族文化村落保护”、“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层面使用。“原生态文化”的大热,与全球化和现代性所引发的传统文化的危机有密切关系。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浪潮中,随着外来文化和观念的不断介入和渗透,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原生态文化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为满足现实需要而对传统的再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原生态文化”本身也成了现代社会的表征之一,是“现代人向传统寻找生存智慧的体现”。[5]
少数民族地区大多远离现代都市,机械化生产、批量复制、商业化、市场化等现代元素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较少出现,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很少受现代文明的浸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是静态的、原始的和固定的,而是强调它与他种文化的区别,尤其区别于是现代都市文化。在人们的认知体系中,现代城市与主流文化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而少数民族与乡村自然也联系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在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少数民族角色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乡村,或者是讲述生长在农村的他们由于生活变化而流走于城市。
少数民族电影是文化学的概念,王志敏先生认为,在衡量少数民族电影的标准中,最根本的原则是文化原则。即断定是否存在少数民族电影,首先要断定是否存在少数民族文化。[6]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文化)的一种影像表达,理应具备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真实地洞察少数民族群众的情感诉求与生活状态。少数民族文化不是伪造的,而是少数民族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尤其注重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呈现。
原生态文化是少数族群的民族性的体现,在电影中,它具体表现在:一是主要演员的少数民族身份。《开水要烫、姑娘要胖》、《静静的嘛呢石》、《乡巴拉信使》、《滚拉拉的枪》、《鸟巢》、《碧罗雪山》等电影都是由本民族群众本色出演,由少数民族群众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文化,还原本民族人民当代生活的现实图景。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呈现,如《婼玛的十七岁》中的哈尼梯田、开秧门等仪式,《阿佤山》祭祀活动中的甩头舞,《滚拉拉的枪》中苗族细碎的歌舞、成人礼、丧葬仪式等。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具异质性。三是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的使用。语言是民族生存的象征,又是文化的形式、载体和容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运用,充分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电影中的人物、场景和语言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一定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的“在场”,如果影像出于“猎奇”的视角,将民族服饰风俗风情作为卖点,过度展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图像冲击语言,景观支配叙事,这不仅没有挖掘和诠释好少数民族文化,反而容易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
原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内核之所在,这种基于真实社会环境下对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影像再现,使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这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了解,进而引起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保护的重视。
二、少数民族电影原生态叙事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性通常被作为与传统相对举的概念,也就是说,现代性意味着告别传统的历史进程。一般来说,现代性从传统中脱胎而来,它在传统中演变,以及改变着传统,全球化浪潮中,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置身于现代性之外。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人员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商业气息和都市文化进入少数民族村寨,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被打破,少数民族地区被裹挟着开始现代化进程。换言之,少数族群的现代性不直接脱胎和演变于民族内部的文化传统,而是由外部力量所推动,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民族地区的变革,具体到文化上,就体现为现代文化与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故事讲述的内容是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接受故事的语境,讲述故事的当下性。[7]15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述故事的时代和语境决定了讲述什么故事,怎样讲述。不同于讲述一个久远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少数民族原生态电影中的故事产生于现代性的背景,故事讲述的时代和讲述故事的时代是一致的,都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经历的焦虑、疼痛、平静、欣喜、向往或者反思既是影像所表达的,也是现实存在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旅游文化产业得到充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各种自然景观被充分开发作为景点,少数民族的一些民俗、歌舞被收编为旅游文化产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不仅是少数民族长期栖身的生态环境和浓缩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表征,景观的命运也成为人的命运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婼玛的十七岁》中,哈尼梯田以及哈尼族姑娘都是被拍摄的“风景”,《阿佤山》中佤族传统歌舞表演及祭祀活动也成为民族村中的“景观”,借助自然景观和民间人文景观,发展地方经济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影像原生态叙事的现实背景之一。
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在空间叙事上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空间的呈现为主,空间成了沉默的叙事者,生活环境能反映真实的族群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活状态。
人物生活轨迹的变化通常以空间的转换来表征,如贾响马从黔东南苗族村寨到北京、其其格从北京回到大草原。这种空间位移还蕴含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较量,借助空间转换,重新思考少数民族命运的意图已不言自明。现代性最精彩的表现就是现代城市[8]109,城乡之间人员流动,打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格局,现代文明、都市文化进入乡村,少数民族个体也通过考学、务工等途径进入城市,两种文化的相遇,成为影像叙事的重点。《香巴拉信使》和《阿佤山》中考上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乡村新的希望,也是传统与现代连接的枢纽;《婼玛十七岁》中,婼玛的好朋友外出务工了解了外部世界,她是第一个向婼玛介绍城市生活的人;在《滚拉拉的枪》、《鸟巢》等剧中也设计了少数民族进城打工的剧情,只是前者着重表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后者则将二者交叉呈现,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共通性。
民族电影的原生态叙事不仅仅只是族群传统文化的呈现和展演,更重要的是将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性语境勾连起来,通过文化的视角表达社会变迁。语言和服饰是剧中人物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语言和服饰的变化通常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生活方式和人生境遇的变化,而人物的命运及喜怒哀乐又成为整体人群命运和文化变迁的缩影,《滚拉拉的枪》和《蓝色骑士》中的“换装”细节隐喻少数族群向现代化城市靠近以及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在语言方面,尽管大多数电影或者电影的大部分情节使用了少数民族语言,但随着民族融和、民族交流的日渐加深,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同时会使用本民族母语、当地汉族方言和普通话,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进行真实呈现,而不是一味追求某一民族语言的使用,也是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特征之一,如《香巴拉信使》主要就是使用云南本地方言拍摄,《图雅的婚礼》中的语言则近似于普通话。随着人物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改变,贾响马在家乡说苗语,在北京与当地人的对话时使用普通话;面对不同的言谈对象,剧中少数民族角色的话语也有所区别,婼玛和奶奶说的是本民族语言,和阿明等外来人交流时说普通话。从语言和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已受现代文明不同程度的浸染。
作为全球化的后果,现代性的影响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也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保护、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传承是当今世界的议题之一,少数民族电影将传统文化置于现代语境,再现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生活,表达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时的境遇。将时代主题纳入影像的原生态叙事中,是异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前提,是一种寻求“共通意义空间”的符号编码。
三、原生态与现代性的张力:影像叙事的策略
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卡西尔宣称:“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毋庸置疑,两种对立力量的渗透过程便是张力的表现过程,“对立、冲突的两极在撕扯、抵牾、拉伸中造成文本内部的某种紧张,并通过悖论式的逻辑达成某种出人意料的语义或意境。”[9]少数民族电影立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视角,将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置于现代性语境,通过鲜明的传统与现代的符号对比,讲述它在遭遇现代文明时的焦虑、疼痛、向往、适应的过程,其中既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甚至将传统看作是现代文明的救赎之地,又有对现代化的期盼和现代文明的向往。
哈萨克电影《美丽家园》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照集中体现在草原的“马”与城市的“车”上。其中两处剧情最能体现这种冲突:一是生活在草原上的阿曼泰去看望在城里上学的玛依拉,对于城市来说,骑着马的阿曼泰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与井然的秩序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骚动与混乱,引来众人异样的目光,传统被表征为不慎闯入现代文明的“他者”;二是玛依拉嫁给别人,心灰意冷的阿曼泰搭车奔向城市,绝望的父亲纵马追上山坡,只看到汽车绝尘而去,快马加鞭也追不上现代机器奔腾的步伐。与此相似的蒙古族电影《蓝色骑士》中,牧民对游牧文化的深深认同与眷恋,对传统文化流失消逝的焦虑与疼痛,在仪式化的影像符码的表述中更为刻骨铭心——父亲盛装骑马追上已换下民族服装的儿子,让他把马卖掉以换回新生活的第一笔钱——正是传统对现代文明接受和适应的仪式,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生活有了新的选择。有些影片在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已隐于其中。《成吉思汗的水站》敖特根杀死了试图引资将水站开发为娱乐城的弟弟,然后躺在他的尸体边,维护了彼时童年时代的誓言,以决绝的文化姿态坚守着成吉思汗的水站。《滚拉拉的枪》中,贾古旺在长途汽车站的厕所里,脱掉蛋清、骨胶和蓝靛捶制的、幽光闪动的苗衣,换上了西服,前往广州打工,迎接现代文明的洗礼。然而,工业文明用它一个飘忽的影子,就把贾古旺彻底拽倒了[10]178——他为了追逐印着公司名称的制度帽,纵身跳车受伤,贾古旺回到家乡的第二天,就离世了。这种对立、断然决绝的态度,包含了深深的反思和焦虑。《长调》是一部关于现代文明与自然文明的影片,在北京的草原长调演唱家其其格,因丈夫在车祸中丧生后,懊悔和悲痛使她一度失声,带着伤痕累累的心回到大草原,离开了长调演唱事业。草原的包容和宁静使她的伤口慢慢复原,其其格最终又唱出了“长调”。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的自然文明的较量中,现代化的脚步难以阻挡,但很多电影表达的是传统文化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忧虑意识,将亲近大自然的少数民族居住地作为在历经现代都市喧嚣与浮躁之后的心灵和自我的疗救之地。
现代性因素凭借国家力量、民营资本、大众传媒、外来文化等渗透进少数民族文化,很多时候,两种彼此陌生的文化相遇时的状态,不是简单的迎合或排拒的二元性可以解释的。《静静的嘛呢石》对现代文化采取的是温婉、包容的态度,使现代与传统处于一种并置的状态。小喇嘛可以将电视机和VCD带到寺庙,将孙悟空面具揣在怀里参加祈愿大法会。在演出传统藏戏《智美更登》时,另一边在放香港的枪战片,青年人穿着牛仔裤在扭迪斯科。[11]103《阿佤山》虽然也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一方是将红毛树当成守护村庄的神树的当地村民,另一方是想要购买红毛树的房地产开发商),但也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水火不容,二者相互纠葛,传统中隐含着现代的因素,现代也吸纳传统,这显然是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
随着各种表征现代文明的元素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引起了少数民族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婼玛的十七岁》中两组对比鲜明的符号,代表少数民族传统的如哈尼族的民居、纺车、服饰、开秧门仪式、民歌、打泥巴仗,属于现代都市的电梯、高跟鞋、随身听、口红、巧克力,它们对应的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表达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化城市的渴望与期盼。《绿草地》也同样表现出游牧文化对国家政治中心为表征的城市——北京的向往。《绿草地》中几个孩子试图将乒乓球送到北京这一情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画布前拍照,便是这一文化向往的隐喻,整部影片充满了对先进文化/国家(政治中心)的想象和追讨。[12]
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来结构剧情,直接诉诸于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焦虑、疼痛、欣喜、向往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这是少数民族电影最能打动人心、引发共鸣之处。
四、结语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甚至面临流失的危机,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电影中原生态文化的呈现,使少数民族电影更具异质性、陌生化和新鲜感,这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尤其关注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及其文化的存在状态的现实,时代特征被纳入影像的叙事结构中,“讲述故事的时代”不再只是背景,而且直接参与影像的叙事。少数民族电影不仅追求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寻求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在传播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时,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文化反思和人文关怀,以引起人们对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关照,能避免在挖掘深层族群文化的同时将“原生态文化”的影像叙事封闭于少数族群的狭小文化空间内,以原生态与现代性为张力的影像叙事策略,有助于拉近少数民族电影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实现少数民族电影的大众化传播。
[1] 傅安辉.论族群的原生性文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 吴仕民.原生态文化摭谈——兼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3] 刘宗碧.“原生态文化”问题及其研究的理论辨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1(3).
[4] 田玉成.文化“原生态”理论的提出与传播[J].民族大家庭,2008(5).
[5] 徐杰舜,等.原生态与传统文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6] 饶曙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念·策略·战略[J].当代文坛,2011(2).
[7] 陈林侠.文化理论与电影分析[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8] 彼得·汉密尔顿.表征社会: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与法国性[M]//斯图亚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图书馆,2003.
[9] 陈林侠.论影像叙事策略中的张力结构[J].戏剧,2002(4).
[10] 郑茜.边缘叙事: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 崔卫平.我们时代的叙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2] 周根红.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电影对民族文化境遇[J].民族艺术,2009(1).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4-12-18
高焕静(1980- ),女,彝族,贵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G206
A
1004-941(2015)02-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