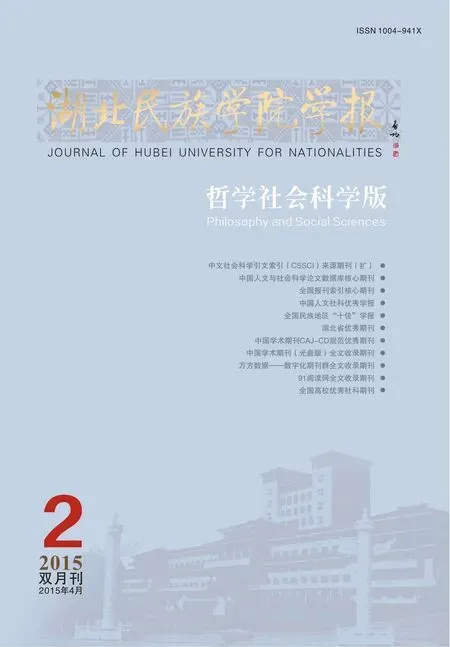论司马光的“独乐”精神
——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文化解读
向有强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论司马光的“独乐”精神
——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文化解读
向有强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独乐园”诗文是探索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生存状态的重要作品。对“独乐”的理解是解读独乐园诗文的关键所在。“独乐”作为一种精神,它首先是政治失意的产物,也是司马光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得与众同乐的自伤的精神胜利。作为一种超然的精神之乐,它绾和了儒家君子固穷中的“抱道守独”和道家自然无为中的适性自足。因为司马光始终怀有兼善天下的理想,独乐园诗文中也带有针砭时人、匡救时弊的政治文化内涵。
洛阳;迂叟;独乐园;文化解读
司马光(1019-1038),字君实,自号迂叟。宋神宗变法中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四年(1071年)自乞闲官退居洛阳,“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园中七景,曰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和见山台,“合而命之曰‘独乐园’”①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66《独乐园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76-1378页。后文所引司马光诗文皆据此版本,标注方式为:篇名/页码。①[1],并作《独乐园记》、《独乐园七题》等作品。“独乐园”诗文是探索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生存状态的重要作品。近来一些学者运用“文化解读”②文化诗学理论从文化之维诠释文学文本现象,将文学视为裹挟着主体情感意志、社会权利话语等多种文化信息的“通货”,将作家得以自我塑型的社会文化意识和文学活动经验视为关注的重点。杰诺韦塞将这种批评方法称为“文化解读”的批评方式。的批评方式对这些诗文进行了研究,从视野上拓展了“独乐园”诗文文本诠释的意义空间,生发了一些有趣的研究视点。学者们指出:“独乐园”既是司马光读书著史的场所,也是洛阳耆英诗人群体游赏唱和的文学发生场域和审美客体,更是司马光与耆英同道的政治立场、道德操守、人格理想和诗意生活的象征③主要成果有:刘方《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郝美娟《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北方论丛》2012年第4期)、宁群娣《论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等论文。。这些论述具有深度和启发意义。但是,如何理解司马光的“独乐”,学者们则是一种抽象而分散的论断,缺乏学理层面的论证和学术深度的具体阐释。对“独乐”的理解是解读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关键所在。司马光的“独乐”首先是政治失意的产物,也是他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得与众同乐的自伤的精神胜利,它融合了儒家的“抱道守独”与道家的“适性自足”,也隐约带有针砭时人、匡救时弊的政治动机。
一、自伤不得与众同乐
司马光将其园命名为“独乐园”,并作《独乐园记》等作品以示天下,显然不独在赋予它一个单纯的称谓符号。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命名是语言之“令”,能让某些隐在的、被遮蔽的涵义得以解蔽和澄明: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独乐园记》/1376-1378)
就思想传统而言,司马光的“独乐”显然是对先秦大儒孟子“众乐”思想的直接交锋;就时代精神而言,是对范仲淹以来北宋士子“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品格的有意背离,也与欧阳修“与民同乐”心忧天下的境界截然相反[2]。即就其自身而言,也是对他先前汲汲追求的“众乐”理想的背叛,“使君如独乐,众庶必深颦”(《寄题钱君倚明州重修众乐亭》/341),戏谑的言说是对“独乐”价值观的否定;“穷达有常分,得丧难豫言……要之白首期,壮烈施元元”(《古诗赠兴宗》/46),这是他失意中的矢志不移;他甚至在《集注太玄经》中斥责“小人独乐其身而不能与众共之”。但如今呢,他却“独乐”于“薄陋鄙野”,“取足于己,不以及人”,这是为什么?
其实,司马光并没有否定“王公大人之乐”与“圣贤之乐”。相反,他自嘲自己“贫贱”又“愚”,因此而“不及”这两类者之乐,所以只能“尽其分而安之”于“薄陋鄙野”,自足于“迂叟之所乐”。还原到司马光的人生遭际和当时的政治语境:由于政治上的失意,此时司马光退居洛阳已近三年,宦海浮沉的多年经验、读书著史的总结提炼、现实形势的难以作为,以及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意志,客观的政治环境迫使司马光选择退处闲官,抱道守穷以独善其身,韬光养晦待时而动。“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槖。纵横百余区,所识恨不博。身病尚未攻,何论聊民瘼?”(《酬赵少卿药园见赠》/132)自嘲的无奈与气愤溢出言表,既然无法“聊民瘼”、与众乐,那就“尽其分而安之”,适意当下吧。
就此进而言之,那么“世之所弃”的就不是“迂叟之所乐”,而是“贫贱”又“愚”的迂叟其人了。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上(神宗)谓晦叔(吕公著)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晦叔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3]卷7神宗认为司马光迂阔,大抵是说司马光在政治上不识时务,不晓变通,一根筋到底——这正是他遭“世之所弃”的主要原因。而司马光在给同年吴充的信中陈述他辞官退隐的原因说:“光愚戆迂僻,自知于世无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窃微禄,以庇身保家而已。”(《与吴相书》/1273)在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疑孟》中则这样表述他的仕宦动机:“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1]1492“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阳虎为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1]1486-1487这些自述充分表明,司马光正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朝廷所用而自乞投闲,尽管神宗依然对他宠幸眷恋,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决不与王安石等“恶人”同立于朝。如此说来,司马光遭“世之所弃”的也不是其人,而是其治国平天下之“道”了;道不见用,所以自弃高官富贵,闲居于洛阳。
道大志深言高的“古之人”,虽“所适龃龉,而或穷为布衣,贫贱困苦以终其身”,但绝不“狭道以求容,迩志以取合,庳言以趋功”,而以“其遗风余烈”余泽后世。[1]1502-1503这是司马光《迂书·释迂》中的誓词,他并不以“迂”为病,而是“患不能迂”;他自号“迂叟”,就是出于对古代儒家圣贤的景慕和追随,也是对自己身怀治道的自信和坚守。因此,《独乐园记》中“迂叟”自认“贫贱”又“愚”,这种自嘲乃是一种“愿望和自尊的伙伴”[4]130。“直缘迂僻求闲地,岂是孤高慕古人?英俊满朝皆稷契,太山何少一飞尘。”(《和白都官见赠》/416)对于退居洛阳之动机的辩解,精致的设问之下隐藏着一种自损自嘲的痛感,对执政者赤裸的歌颂变成了刺骨有深意的反讽。
司马光正是通过对“独乐园”的命名和写作《独乐园记》,诉说着他的个人遭遇,回应着他在政治上的失意,诠释着他对现实世界的洞察,文意表面的平静情绪隐藏着自嘲的痛感,却因此展示了一种消极的反抗和自信的姿态:“吾心自有乐,世俗岂能知?”(《乐》/382)这显然是在自高自售其不为世俗所知的“独乐”,他从“众乐”到“独乐”的变化由某种不可企及的外力所促成,这种变化却恰是其政治上无法实现“众乐”理想的精神折射。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温公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5]卷44可谓一语点破。
二、抱道守独的精神胜利
《独乐园记》中司马光将“王公大人之乐”、“圣贤之乐”与“迂叟之所乐”对话:一边是高贵的王公大人和圣贤,一边是贫贱愚陋的迂叟;一边是“与众乐”,一边是“独乐”。简洁的对立模式投射出作家对自己当下所处社会环境和秩序的感受与思考,也预设着某种身份定位。司马光是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家士大夫,“士之读书者,岂专为利禄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与薛子立秀才书》/1214);“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和子渊除夜》/252);“丹心终夜苦,白发诘朝生。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升平”(《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336),得位行道辅助君王建立天下太平的功业是他毕生的志向。但眼下已穷处洛阳,“志士喜功业,感时心易劳”(《书事》/232),“三十年来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初到洛中书怀》/370),几十年的仕宦奔走如随风飘荡的飞蓬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岁月飘忽,人生如梦,志士变成了迂叟,他劳累的心需要一个安顿休养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独乐园”: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源,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伐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惟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独乐园记》)
独乐园中的“迂叟之乐”,显然已褪去了外在的世俗功利色彩,有的只是读书穷理、师圣友贤、逍遥适意、行止无待、身心神志“悉为己有”的“独乐”,是《庄子·逍遥游》中鹪鹩、偃鼠“各尽其分而安之”的自足自乐。这是一种超然的精神之乐,是对现实政治中不得与众同乐的自伤的精神胜利,它绾和了儒家君子固穷中的“抱道守独”和道家自然无为中的适性自足。以儒修身,处穷有定,抱着“道高于势”的政治法则或价值原则以抗礼王权政治;以道安心,随性自适,“自放于丰草长林间”(《答陈师仲监簿书》/1270)。
这种抱道守独、适性自足的精神追求也表现在《独乐园七题》中。《独乐园七题》是一组组诗,咏“独乐园”七景,但与一般题咏诗的咏物不同。它的思想艺术渊源是晚唐皮日休的《七爱诗》,各题以“吾爱×××”起句,开篇点明对某历史人物的追慕和各景点的题属意图,与其说是咏物,不如说是咏史。《独乐园七题》组诗经过司马光的精心构思,每景的题咏隐栝一个历史人物,景点的命名又出自该历史人物的典故,这就把景与人的关系很妥帖自然地绾系在一起,像是从支持它的社会语境中滑开;但实际上,这是司马光将历史人物作为寄托自己情志的歌咏对象,不但没有滑出时代,反而在时代语境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解读这组诗的关键是找出贯穿组诗的主题。宁群娣认为:从诗歌所表达的情志看,组诗围绕“独”与“乐”两个主题展开,其中《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四首分别吟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和陶渊明,反映了抱道守独的主题;《弄水轩》、《种竹斋》和《浇花亭》三首依次吟咏杜牧之、王子猷和白乐天,是闲居自乐的主题[6]105。宁氏指出了解读这组诗的关键,但将“独”与“乐”判然两分则值得商榷:“独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主题贯穿这组诗,没有“独”,“乐”将失去特点和价值;没有“乐”,“独”也找不到归宿。
概言之,七题所咏的历史人物包括醇儒(董仲舒)、隐士(严光、韩康、陶渊明)和风流才俊(杜牧、王子猷、白居易)三类。《读书堂》诗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114此诗依据《汉书·董仲舒传》撰成,诗人用精炼的语言凝聚了董仲舒“穷经守独-圣言充腹-对策汉庭-消伏百家”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代鸿儒由“内圣”到“外王”的德业事功。以董仲舒题咏“读书堂”,是司马光对董仲舒的认同和追慕。在北宋理学六君子中,司马光是程颢推崇的醇儒,他的思想和理想都是儒家的典范,他无疑在用董仲舒砥砺自己,表达自己穷经守独、抱道自守的政治道德品格和探究资治之道的学术自信,以及排辟邪说、消伏百家的决心和勇气。对三位隐士的歌咏则主要表达了诗人不屈王权、不慕富贵、适性自足、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钓鱼庵》、《采药圃》歌咏《后汉书·逸民列传》中的严光和韩康。严光不以富贵改变操守,耕于富春山,钓于严陵濑,自满自足;韩康淡薄名爵,采药卖于都市,以一女子知其姓名而“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最突出的是《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主命,牺牛惮金鞅。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1]115
《见山台》咏“隐逸词人之宗”陶渊明,“见山台”从渊明诗句“悠然见南山”中化出,“拂衣”句指其辞官归隐田园。“牺牛”二句用典本自《庄子·列御寇》,而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更为详细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实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7]655庄子认为高官厚禄不仅使自己失去人身自由,更有成为君主牺牲品的危险,因此他遵循“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本性,提出“无为有国者所羁”的隐逸原则,他追求的是人身和精神的绝对自由。
三、自比唐晋间人以救时弊
仕途的受挫使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抱道守独,但他并没有像唐代分司洛阳的白居易一样放弃了兼善天下的理想而惟求独善其身,追求更为率真洒脱狂放不羁的世俗享乐。尽管他也表现出士大夫的闲情雅趣和亦官亦隐的“吏隐”作风,并在诗歌中刻意疏远政治,但他依然身怀兼济之思,不论是仕途畅达还是独居守穷,忧国忧民是他作为优秀的儒家士人最基本的责任和理想。在《见山台》诗中,如果说前六句都是对庄子思想的讴歌,那么后两句“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就是他对陶渊明这一文化原型身上超出隐士意义之外的淑世情怀的发现,不,更应该说是诗人情志的自觉赋予和表现:诗人通过歌咏陶渊明的“爱君之心”,将他的脸朝向君王,借此眺望世界言说自己。但是,司马光歌咏陶渊明的爱君之心并不是对王权的屈服或趋附,而是对诗学意识形态中两种处境——服务朝廷与作为“隐士”生活——的个人选择,因为“从诗歌表达‘个人’价值开始,就存在对政府权威表达顺从与承认的强烈要求”[4]13。无论如何,这一诗意的表现正好表明闲居洛阳逍遥适意的司马光并没有忘怀世事,他居洛生活的生存状态与他“独乐”的精神追求还存在距离:
对食宁无愧,衔恩岂免忧?愚公欲转石,能者正操舟。衢路豺狼立,蓬蒿虺蜴游。松筠不荣落,天地有春秋。潭底寒蟾满,霜前红叶稠。要之无可奈,萍梗任漂流。(《感怀寄乐道》/1633)
闲官洛阳的司马光对这种有官无责于世无补又未能全身隐退的身份显得有些尴尬,对于一个心忧社稷的有志之士而言,无功食禄、受恩不报令他惭愧。家国与个人,均有运数;功名与事业,更奈际会。在当今朝廷中,“能者”把持朝政,他们豺狼当道,像毒蛇和蜥蜴一样横行草野,诗人却只能蹇滞闲官虚度光阴,在这国家多事民生多艰之秋无所作为无可奈何*这是依据诗歌从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心理上作出的阐释,并不是对熙丰变法所作的历史判断。。而这种现状暂时还不会改变也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黄河清浊定难变,白发新陈空复多。胜事眼前无计奈,不游不饮欲如何?”(《感怀》/1634)诗人满腔的愤慨和不平是透出纸面的,英雄迟暮不遇之感油然而生。但是,赋闲在外的诗人并没有像诗中所说的萍梗一样与世浮沉,他的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朝廷:“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晨夕寤寐,何尝不在先帝(神宗)之左右!”(《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989)他在《独乐园七题》中也含蓄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钓鱼庵》诗就鲜明地批判了当时的“夸毗子”: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旌岂非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禄穷百态。[1]115
“夸毗子”典出《诗·大雅·板》:“天之方懠,无为夸毗。”朱熹解释说:“夸,大。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则以谀言毗之也。”[8]267依此而言,“夸毗子”是指以大言谀言媚取君王善为进退的势利小人,他们为了升官发财丑态百出,与严子陵的不慕富贵操守如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方认为这首《钓鱼庵》诗中的“夸毗子”“并非所谓的泛泛而谈,而是具体所指”当时与民争利的新党贪利小人[9]116。诗人另一首《贻夸者》也抒发了对这些“夸者”的极端不满和势不两立:“我乐非君乐,君忧非我忧。蓬蒿与溟渤,终老不同游。”[1]409又如《读书堂》诗“邪说远去耳”一句,宁群娣认为是“斥责荆公新说为邪说”[6]105。“辟邪说,难壬人(作者按:“壬人”指巧言谄媚之人,意同“夸毗子”),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与王介甫)第三书》/1265)依此言,“邪说”似乎是指讲求货币之利的新党之说;但此中的“邪说”“壬人”,又何尝不是指王安石言?唐宋以来,几乎没有纯粹的诗人,司马光诗中的董仲舒、严子陵,又何尝不是他的自况,不是他的借古讽今呢?
当然,这是一组诗歌:诗歌在“语言中”发生,时空、语言、文明的变迁,艺术的语境——建立在同一时代的诗人和读者之间共享的背景——沉默,它依存于其中未言的假设、未表的焦虑、隐晦的暗示和超脱的想象,是我们难以重现的失落的世界[4]。因此,时人的解读,尤其是相熟相知人的解读,对后世读者来说就显得至为可贵和可信。刘安世这样诠释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诗歌:
老先生(司马光)既居洛,某从之盖十年。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弊也。[10]
刘安世是司马光最得意的门生,史载其“登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11]10952。以刘安世对恩师的相知之深,这个解说是可信的。南宋胡仔说的更加明白:“元城所云,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诮金陵(王安石)也。”[12]158看来宋人多认为司马光的独乐园诗有针砭时人、匡救时弊的政治动机。“当时君子”自然是暗讽以当今孔孟自期的王安石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与王介甫书》/1258)正是由于王安石的刚愎自是,言利天下却所用非人,满朝皆是迎合势利的“夸毗子”之流,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整个朝廷士风:“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务为奇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988)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光在诗中歌颂唐晋间人率性而为的潇洒胸襟和风流俊赏,来讽刺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之流: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弄水轩》/116)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萧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种竹斋》/116)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浇花亭》/116)
王子猷东晋名士,《世说新语》中他借宅种竹、雪夜访友、清溪笛吹的美谈常为后世文人所欣羡,这种潇洒脱俗、任真自然、不拘形迹的生活方式得到司马光的钦慕。吟咏杜牧之、白乐天事迹,“一方面出于对洛阳前贤的景慕;另一方面则出于司马光对(中)晚唐文人士大夫人生道路选择的认同”[6]106。杜牧曾在池州刺史任上筑弄水亭,取李白“饮弄水中月”之句为名,并写有多篇题咏之作。白居易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颐养天年,他在文人士大夫仕与隐的人生道路选择上开辟了一条“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13]2483的“中隐”之路,纵情山水,放意文酒,作“九老会”留名后世,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最为倾慕和模仿的典范。诗人正是通过激赏杜牧、白居易两位前贤诗酒雅趣、风流俊赏的闲居生活,来否定“石季伦”之流阿附争宠、贪图富贵的生活作风。
在独乐园诗文中,隐含着诗人欲以晋唐人任性自然、风流潇洒、颓然自适的生活方式,来矫正拯救当时士大夫务奇尚巧、急功近利、贪慕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司马光针砭时人、匡救时弊的政治动机的泄露。“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客到暂冠带,客还还上关。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独乐园二首》/446)“独乐园”的冷清与“朱门”的热闹不可同日而语,但“独乐园中客”一日之中颓然无事,比之思虑营营、抗尘走俗于权贵的“朱门之客”,无疑多了几分自我满足和率性洒脱。
四、余论
或许,司马光只是把唐晋间人的潇洒风神作为其“独乐”精神的诗意追慕。但是,我们却不能以他政治上的迂阔来否定其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品味。“昔杨元素学士常云端明司马公刚风劲节,耸动朝野,疑其金心铁意,不善吐婉辞。近得其席上所制《西江月》一篇,雅亦风情不薄。”(《西江月》词下注/1641)不仅此首《西江月》“风情不薄”,司马光现存五首词,首首妩媚凄婉。陶渊明有《闲情赋》,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立朝刚正,均有丽词绮语。文人的闲情逸致是古代士大夫自我排遣、自我解脱和自我超越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闲情逸致”这四个字,中国古代士大夫就是一群乏味无趣的人,就是政治的工具[14]177。
司马光的“独乐”精神,虽然是政治失意的产物,但他摒弃了卑职小吏的穷愁牢骚,他并不以贬谪为意:“适意遗轩冕,轻于一鸿毛。”(《答张伯常之郢州途中见寄》/452)他把官位爵禄看得淡薄,甚至还为闲置洛阳带来的清闲而庆幸快乐:“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再和尧夫年老逢春》/390)他过着嗜酒、耽诗、饱食、闲眠、读书、赏花、游山、玩水、投壶、养生等与勤于吏事毫不相干甚至相抵触的世俗享乐生活。早经悟入的“内圣”之学使他努力趋向于进退从容的境界,安于本分,自足自适。
他也标榜自己“决口不问世事”,但他显然不是这种信念的坚定执行者,关心国计民生,拯时济世是他始终难以放下的伟大抱负:“此心无所用,脱粟亦深惭。”(《光诗首句云饱食复闲眠又成二章》/437)他从未放弃儒者“帝王师”角色的尊严,抱着“道高于势”的坚定信念毅然闲居洛阳十五年,著书立说,韬光养晦。由于闲置洛阳的政治待遇“仍有起用、至于重用之可能”[15]609,这就决定了他密切关注朝政、留意民生的现实意义,并因此发出自己的声音:“独乐园”得到苏轼、苏辙、王尚恭等人的题咏呼应,司马光后来还因苏轼的题咏而牵涉“乌台诗案”,这一侧面也反映出独乐园诗文创作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其中蕴含的政治意识形态。
总之,司马光在洛阳构筑“独乐”精神世界,使他抛开了“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的传统士大夫二元相悖的人生抉择,在仕途逆境中“吏隐”于市,洞察世故,乐享闲情,以“邂逅升沉皆是命,逍遥出处本无愁”(《和乐道再以诗见寄》/442)的人生觉悟,达到了“道胜随宜足,身闲与世疏。何时容命驾,采蕨钓肥鱼”(《寄题傅钦之济源别业》/371)的人生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安达处穷均不改其变的兼善天下的抱负——作为传统优秀士大夫最基本的责任和理想——这正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失落的甚至觉得可笑的!
[1] 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 孙绍振.玉泉书屋审美沉思录·欧阳修《醉翁亭记》:与民同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3]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M].四部丛刊初编本史部第18册.
[4] (美)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 (宋)黄震.黄氏日抄[M].四库全书本.
[6] 宁群娣.论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政治和文化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3(3).
[7] (汉)司马迁.史记[M].卢苇,张赞煦,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8] (宋)朱熹.诗集传[M].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刘方.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J].江西社会科学,2008(1).
[10] (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M].(明)王崇庆,解.四库全书本.
[11] (元)脱脱,等.宋史·刘安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3]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 李春青.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J].江海学刊,2013(5).
[1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毕 曼
2014-12-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学思想与选本批评:宋明理学家选本编纂研究”(项目编号:14XZW040);湖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大学生科研扶持项目“熙丰变法中马马光的居洛生活与诗歌‘表演’艺术”。
向有强(1983- ),男,湖南邵阳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化。
I206.2
A
1004-941(2015)02-0107-06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