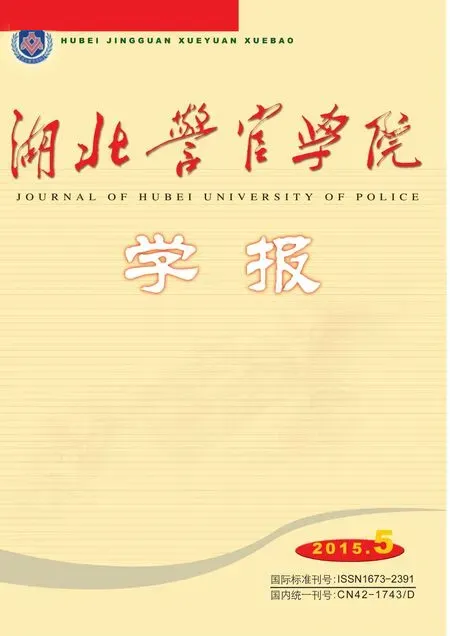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国刑法主观主义的生成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国刑法主观主义的生成
费翔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我国当前的理论和实务中,存在难以去除的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即将犯罪的本质定位为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意图,因而即便行为永远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也必须定罪处罚,结果因素无关紧要。这种主观归罪的逻辑生成于中国儒家法律传统之中,因而根深蒂固:“以礼入刑”导致刑法适用的伦理化倾向,与主观主义息息相通;“明刑弼教”使得刑罚成为人性教化的重要手段,刑法更加关注主观方面的改造。因此,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去主观主义”应当强化人权保障,改造刑法主观主义背后的社会统治思想,促进中国刑法的去伦理化。
【关键词】儒家法律传统;主观主义;以礼入刑;明刑弼教;刑法现代化
一、问题缘起:刑法主观主义何以根深蒂固?
从词源上看,刑法主观主义是舶自日本语的汉字词,但这一概念准确揭示的下述主张却是普遍存在的:犯罪的本质存在于行为人的内部,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或性格的危险性,或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但具有将来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的性格。[1]换言之,行为人若产生犯罪意图,那么即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或行为手段使得行为根本不可能产生现实危险或实害,行为人仍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是否造成现实的危害无关紧要。可见,刑法主观主义即“主观归罪”。新世纪以来,随着法学理论上的西学东渐,我国当前刑法学界正在进行着“去苏俄化”,引进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话语蔚然成风。然而,刑法主观主义的魅影始终在理论中存在着,并体现在现实判决中。
在刑法理论中,刑法主观主义的体现是社会危害性理论。根据社会危害性理论,犯罪乃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决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除客观情况之外,还包括“行为人的情况及其主观因素,如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故意还是过失,有预谋还是无预谋;动机、目的的卑劣程度;偶尔犯罪还是累犯、惯犯。”[2]在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中,只要具备主观要素,无论客观情况为何,没发生结果的均可以被认为有主观上的社会危害性,成立犯罪未遂。
在司法判决中,主观归罪也大行其道。以“张筠筠、张筠峰误把尸块当毒品而运输案”为例:胡斌故意杀害被害人韩某,将尸体肢解为五块,套上塑料袋后分别装入两只套有编织袋的纸箱中并用打包机封住;嗣后,胡斌以内装“毒品”为名,唆使张筠筠和张筠峰帮其将两只包裹送往南京。张筠筠、张筠峰按照胡斌的指示,从余姚市乘出租车驶抵南京,将两只包裹寄存于南京火车站小件寄存处。后因尸体腐烂,案发。在本案一审、二审中,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认为:被告人张筠筠、张筠峰,明知是“毒品”仍帮助运往异地,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依法应予处罚;但因二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未得逞,系未遂,应依法从轻处罚。
由此可见,行为人产生了犯罪的恶意并在恶意支配下有行动,正如“主观上想杀人,误把稻草人或尸体当做真人而射击”、“主观上想杀人,误把杏仁霜当做砒霜而投放”,无论该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实害结果,这些行为人都应当被处罚。我国刑法主观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可以断言,即便我国刑法体系完全实现“去苏俄化”,刑法主观主义也不会自动消失,驱逐刑法主观主义任重道远。本文将从儒家法律传统入手,考察刑法主观主义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原因。
二、以礼入刑:儒家法律传统对行为人内心的重视
针对我国的法律传统尤其是刑法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即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3]根据这一论述,在“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古代立法模式中衍生而来的法律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儒家化”。随后,瞿同祖先生进一步认为,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就已开始。虽因受条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经义决狱方面努力,但儒家化运动成为风气,日益根深蒂固,实胚胎酝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生。归纳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其间实经一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酝酿生长以底于成。”[4]可见,传统中国的人伦道德即儒家伦理或者说宗法伦理早已内化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支配着它的变化和发展,表现为儒家伦理成为国家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渗透了儒家伦理的意蕴。[5]这种古代法律与儒家伦理思想的融合形成了“法律儒家化”,因而我国的法律传统也可以直接称为“儒家法律传统”。
从儒家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上考察,儒家自汉代开始的“以礼入法”使得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于偏重对行为人主观内心的关注。先秦时期,诸子争鸣,此时儒法对立。出于当时的统治需要,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未被官方采纳,儒家学者备受打压,秦代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法家思想成为正统。自汉代起,法家衰落、“黄老之学”转瞬即逝,百家被罢黜,儒术被独尊,儒家思想终于开始普遍推广。但是,法制已经成为统治需要,这已经不容争辩,所以儒家必须与时俱进,他们的路径便是“以礼入法”,以儒家伦理引入法律,使之成为推行儒家思想的媒介,“法律儒家化”就此正式发端。其中,最经典的例证便是汉代的“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也叫“春秋断狱”、“春秋折狱”,简言之,就是将《春秋》等儒家经典中的故事和微言大义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董仲舒主张的原则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6]即,断狱时应当根据事实来推断行为人的主观心志;如果意志邪恶,则不需要等待行为完成,没有出现行为人期待的危害结果即“未得逞”(包括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不能犯),也要加以惩处;若行为人是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惩罚便加重;若行为人原本正直,惩罚应当要减轻。据此,法律适用的核心要素是“志”,必须“本其事而原其志”,根据意志与儒家伦理经义的对比决定行为的善恶,并以此来分配不同的刑罚。
董仲舒的引经决狱,虽不是主观归罪,但根据行为来推测行为人的道德意志与根据行为来推测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确实是同向逻辑,即“征表主义”。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指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哀帝纪》中也写道:“《春秋》之义,原心定罪。”所以,“汉代刑罚的主观主义,和所谓的春秋之义是可以相提并论而无法分离的。”[7]虽然至《唐律》以后,春秋决狱逐渐弱化,但作为儒家精髓的以礼入法、原心定罪、一准乎礼始终得以沿承。正如梁治平所言,“‘春秋决狱’是道德的法律化,是改造成法,重建古代法伦理结构的一种努力。由此导向了中国道德的法律化和中国法律的道德化。”[8]
所以,从先秦儒家创立到汉代独尊儒术,法律儒家化不断发展,儒家法律传统逐渐形成,至“唐律一准乎礼”成为儒家“以礼入刑”的典范。由此,法律随着儒家伦理道德将行为人主观方面作为考察重点,这与刑法主观主义息息相通。
三、明刑弼教:儒家法律传统对心性改造的推崇
与法家思想不同,儒家伦理向来对人的心性修养无比重视,而促进修养的方式,一为礼教,二为刑罚,最终“明刑弼教”得到推崇。“明刑弼教”语出《尚书·大禹谟》,舜帝禅让其位时,曾对禹说:“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所以,“明刑弼教”就是以刑罚来辅助心性教化,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教养,从而实现不用刑罚的“大治”。这也是儒家在处理礼法关系时的基本态度。
周公曾经提倡“明德慎罚”,这里的“德与罚”也即“教与刑”的关系。孔子在此基础上对“德”与“罚”、“教”与“刑”的关系进行了阐发。例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显然,“德”是孔子实现社会治理的第一手段,对统治者而言是“仁政”,对被统治者而言是“教”。但先秦儒家并不绝对排斥刑杀,如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只不过在刑罚与礼乐的关系中,礼乐始终处于统领地位。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礼法并非非此即彼的。隆礼重法的荀子指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这里的“教”即对人们的道德教化,而“诛”、“赏”均为达致“教”的手段,荀子此言指出了“刑”对于“教”的辅助、强化作用。故有学者认为:“荀子实际已拥有了礼法兼施、王霸统一的思想。这开启了汉代以来儒法合流、霸王道杂之的先河。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倡导‘以礼入法’的思想家。”[9]总之,先秦儒家坚信“德治”的力量,为了实现“德治”,“礼”是最重要的,但“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儒家对“法”的强调是为了影响或改造人之心性、提升人之修养,即刑罚的作用在于“弼教”。
汉代大儒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他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春秋繁露·实性》,可见董仲舒将外部教化作为重要任务。在以刑罚促进教化的问题上,董仲舒虽然说:“天之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但“不任刑”并非“不用刑”、“不要刑”,他在“天人合一”的纲领下主张:“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董仲舒在论述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明确了国家司法权的定位——辅助道德教化,正如自然界中有“阴”的力量一样,人间社会也必须有“刑”(含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力量,这样才能体现“天人相类”的特点。[10]由此,先秦儒家的“明刑弼教”得以发扬。
经过两汉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明刑弼教”思想影响至唐代,《唐律》开篇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后,朱熹把德礼、刑罚、政教的本用关系直接表述为“相为表里,如影随形”。他认为:“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因此,刑罚对于提升人们的心性修养的手段性更加突出,这种取向与朱熹的阴阳学说是一致的。到明太祖朱元璋,刑罚在“弼教”的名义下得到强化,“乱世用重典”成为提升人们心性教化的基本策略。由此可以看出,“明刑弼教”是一种消极预防思想,即主要是通过刑罚的威慑来促进人们心性的改变,消灭犯罪意图,因而它属于“目的刑”思想。
总之,儒家法律传统中的“明刑弼教”思想将刑罚视为教化的手段,教化则是对人们心性的改造,所以刑罚适用对行为人内心的关注是必然的。尤其在封建统治末期,统治者为了整顿“乱世”,刑罚被包装成实现“治世”的良方,刑罚的教化作用不断被强化,刑法伦理化、主观化有增无减。
四、结语: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去主观主义”路径
儒家法律传统沿袭到清末,面临着两次“掣肘”,但刑法主观主义思想从来没有得到改变:(1)1840年至1911年,西方思想开始不断传入中国,但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儒家法律传统丝毫未受影响;(2)1912至1949年,民国时期刑法学家多留学于当时主观主义盛行的日本,因而牧野英一的主观主义思想被引入,儒家法律传统中的主观主义被重新强化。可见,由于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已经深入法律之骨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儒家思想虽然被多次抨击,但儒家法律传统尤其刑法中的儒家伦理化却挥之不去,刑法主观主义很难消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以苏联为师”,如前所述,苏联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名义下,已经将主观因素作为犯罪本质的首要考察目标,根本没有摆脱主观归罪。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1997年第二部刑法典,“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威权刑法思想并未改观,直到德日刑法新思潮首次涌入中国,苏俄刑法理论的主观主义“疮疤”才被“德日派”学者揭开,[11]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全新时代才正式来临。可以说,当前下列公式是成立的:“中国刑法现代化=去苏俄化=去主观主义化”。当然,“去主观主义化”有赖于多种具体刑法制度、理论、思维模式的建构,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现代刑法的出发点是什么,它必须与儒家“以礼入法、明刑弼教”的刑法传统根本不同。
陈兴良教授曾经指出:“刑法是否把人权保障放在首要位置,是法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刑罚的根本区别所在。”[12]在中国古代、近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刑事法律的运行维护的是封建礼教统治、资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个人从来都是缺位的,这种“社会防卫论”思想偏爱于在发现行为人之犯罪意志之时进行干预。受到西方先哲的影响,刑法必须要“面对国家保护个人”,成为“犯罪人的大宪章”。因此,至少在刑法制度及其运行上,要尽可能摆脱儒家伦理纲常传统的束缚,①本文并非完全否定儒家法律传统,那样做太不明智,古代法律及其实践中的无数思想充满人本主义,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等。笔者反对的是以儒家伦理为由进行的入罪化活动,这是深刻影响主观归罪的文化根源。为此,必须有意识地全力追求与之根本不同的人权保障目的,而人权的保障又必须“从对国家权力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中,即对国家性刑罚权发动的限制上得到诠释”。[13]
所以,中国刑法的“去主观主义”只有“限制刑罚权”的路径可走,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刑法的去伦理化才会成为可能,儒家法律传统的负面影响才会被降至最低,客观主义刑法体系才能最终确立。就此而言,当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启蒙”,“启蒙”的核心在于“限制公权、保障私权”,这是中国刑法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此,我们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参考文献】
[1][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8.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0.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1-112.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373.
[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1.
[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92.
[7]刘艳红,马改然.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J].政法论坛,2012(3):28.
[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65.
[9]何永军.中国法律儒家化商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129.
[10]崔永东.董仲舒司法思想初探[J].北方法学,2011(6):128.
[11]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 2000(1):3.
[12]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41.
[13]蔡道通.刑事法治的基本立场——一种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的阐释[J].江苏社会科学,2004(1):219.
收稿日期:2015-02-02责任编校:陶范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91(2015)05―008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