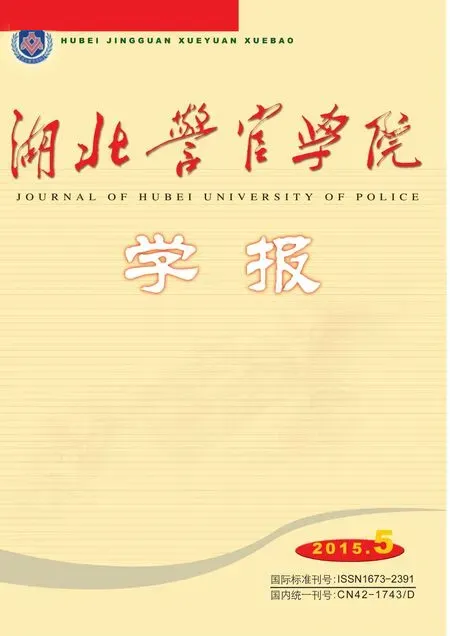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判定的几个问题
张代磊
(1.西南政法大学,四川 成都400031;2.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浙江 义乌322000)
近年来,新型贿赂犯罪逐渐呈现出隐蔽化、复杂化的趋势,突破了受贿者与行贿者“一对一”的传统贿赂犯罪的行为模式,犯罪主体也扩展至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身边人”。为了严密刑事法网,《刑法修正案(七)》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关系密切的人纳入刑法视野,在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期将长期处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囊括进去。然而该罪名实施以后,却是“叫好不叫座”,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乏力,且面临着许多亟待厘清的理论难题。本文拟就该罪主体判定等疑难问题略作梳理和探讨。
一、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范围
我国法律对“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的“近亲属”较民法的规定宽广一些,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的范围没有进行调整,仍旧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以上三种关于“近亲属”的解释在实践中都具有法律效力,而我国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时并没有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这导致了司法适用的无所依从。
理论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①此处系指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而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变更其内容,但条款数已变成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不仅与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民事、行政方面的法律规定相矛盾,而且缺乏现实合理性,也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不相符合,因此,从有利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这一立法目的出发,刑诉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明显失之于窄,目前应以民法中所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为宜,并做适当扩展。[1]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即便同一名称下,刑事法律中所使用的概念在外延上也未必与民事法律相一致,在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2]
三大部门法对“近亲属”范围界定的不一致,主要在于不同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在刑事法领域,所涉及到的往往是公民个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除了对当事人个人影响重大外,对当事人最亲近的亲属的影响同样重大,我国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近亲属可以代替当事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往往事关重大,不可不慎重,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较之民事、行政为窄,只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所涉之事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范围显然不能过窄,以免影响社会生活正常的伦常性,造成公民行为萎缩。在行政诉讼中,一方是力量微小的公民个人,另一方则是国家机关,悬殊巨大,有必要对行政诉讼双方进行平衡,况且在诉讼过程中,正当的诉讼程序往往有比实体更为重要的意义,行政机关因地址固定,参与诉讼程序更为便利,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对当事人的近亲属范围进行扩展,使当事人更为便利地参与诉讼过程就显得极为重要。
对“近亲属”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出罪入罪问题,不可不慎重对待。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近亲属”的范围不可随意扩大,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宽。笔者认为,“近亲属”的范围无论是参照民法还是行政法的规定均不妥当,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在刑事法律中不宜直接套用非刑事法律的相关概念,民事甚至是行政法中的概念出现在刑事法律中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虽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一个是实体法,一个是程序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并不相同,但两者都属于刑事法范畴,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为了保证刑事法系统内部的自洽性和有效运转,两者对“近亲属”的规定有必要保持一致。
二、如何界定“关系密切的人”
我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际关系极为纷繁复杂,司法实践中关系是否密切的认定显得困难复杂。立法者在设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时考虑到我国人情社会的现实,在犯罪主体上采用了列举加兜底的形式,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采用了列举式规定,而“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则属于兜底式规定,并用“密切”一词对“关系”进行限定,以限制处罚范围。这种兜底性的规定,为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难题。
有时候有没有“关系”容易判断,但对于“关系密切”的判断则未必。例如,张某是某市的一名医生,因给该市的国土局局长看病而两人相熟,该市某酒店因违法用地被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罚款一百多万元。为减少罚款,该酒店经理找到张某,给张某10万块钱请其帮忙。张某收下钱后向局长提出请托遭到拒绝,事后,该酒店被处罚,张某也因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法院判刑。在本案中,焦点集中在张某的“医生”身份是否属于关系密切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根据刑法规定,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仅在主体上要符合刑法规定,而且要求张某对局长具有影响力且利用了影响力。张某和局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医患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否归之为一种能够影响局长的“亲密关系”,不但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甚至用证据证明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从法理上加以探讨。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密切关系”主要有:地缘关系、血缘关系(除了近亲属之外的其他亲属)、工作学习关系、感情关系、利益关系、以及在任何情况下相识并产生互相借助、互相信任的其他关系。[3]有学者划分得更为细致,认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是亲戚关系(非近亲属)、情感关系、情人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经济利益关系、老乡关系、同事关系等几种关系。[4]当然,以上界定的各种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密切关系”,只能说按照正常人的理解其中出现密切关系的或然性比较高,上述界定的各种关系可以成为判断是否存在密切关系的一个依据或线索,但不能成为判断是否存在密切关系的关键根据。
笔者认为,对于“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应重点放在关系的内涵实质而非外在形式上,对是否有密切关系的判断应坚持综合判断的原则,即从关系的性质和程度两方面进行综合判断。第一,在判断是否属于“关系密切的人”时,可以将”特定关系人”作为参照,若能得出属于“特定关系人”的判断,则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看,“关系密切的人”均包含“特定关系人”,前者可以完全容纳后者。“特定关系人”中的“近亲属”自不待言,“情妇(夫)”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这种关系的存在,本身已经证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共同利益关系”一般系指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密切关系”形成的基础却不仅仅止于经济利益关系,有可能是基于血缘、地缘或者其他关系。因此,“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要大于“特定关系人”,只要能肯定行为人属于“特定关系人”就基本可以肯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二,是否存在影响力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可以从当事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交往情况进行考察。如A通过施加影响力,使国家工作人员B利用其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此时可以说A和B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反向推理过程,从国家工作人员B利用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一结果反向推出其与A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应该说,影响力的有无及大小已经成为判断两人之间关系是否密切的实质依据。影响力有无的证明可以通过当事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亲疏远近、交往的频繁程度、以及双方是否存在情感上、心理上或者利益上的一定的牵制能力等各种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如果能够肯定影响力的存在,则可以反向推出“关系密切的人”的存在。
三、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本罪
对此问题,理论界还没有取得共识。肯定论者认为本罪既可以由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也可以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如有人就认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影响力”与其自身职务无关,则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求。否定论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应构成斡旋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5]对此,笔者认为有讨论的必要。
为与斡旋型受贿罪相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型受贿罪共同构成《刑法》第388条,从实然上看,“公职人员固然可以基于现任公职而产生影响力,但也并不能排除公职人员作为一般人而产生影响力,因为公职人员作为一般人同样存在与其他公职人员的一般关系。”[6]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具有唯一性,任何人都有可能具有,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利用影响力受贿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就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求。如张三、李四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两人系夫妻关系,王五因有求于张三,就向李四行贿。因与李四的职务无关,李四就利用张三妻子的身份,向张三施加影响力,使张三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为王五提供了帮助。因此,就客观层面而言,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肯定说和否定说并没有实质的差异,两者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和着眼点不同,才导致不同的认识。
肯定说注意到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是就其形式意义上的身份而言,一般说来,在概念外延上,国家工作人员和其近亲属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存在交叉重合之处。但实际上,国家工作人员的称谓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只有行为人履行职务行为时才有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即使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其从事的却是与其职务行为毫不相关的行为时,将其身份与行为相提并论就不合适。否定说抓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内涵,在非履行职务场合,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便不具有特殊性。否定说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理由和肯定说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也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主体认定的分歧。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在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相交织的情况下,在具体案件的判定上,可能会存在困难。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与乙,甲是乙的上级,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甲收受请托人财物后请求乙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甲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斡旋型受贿罪呢?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自己对利用了什么关系不会去考虑,但在确定案件性质时,必须弄清楚。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证据充分,行为人利用了何种关系往往也很难确定,因为行为人不会傻到主动声明在行为时“利用了某某关系”,因此,这些难题需要运用理论加以解决。“从理论本身来看,‘权力性关系’与‘非权力性关系’比较,非权力性关系往往是一种社会化的关系,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关系,而权力性关系则往往是一种法律上的关系。”[7]换言之,非权力性关系的维系主要依靠伦理、亲情,如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等,这种关系带有更多的社会道德色彩;权力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从本源意义上而言,这种关系往往使行为人承载着更多的法律责任。非权力性关系的伦理性决定了它如果遭到背叛,承担的只是道德的非议和伦理的责难,权力性关系一旦遭到背叛则有可能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在两种关系相交织的情况下,权力性影响力的判断具有优先性,甲成立斡旋型受贿罪。
[1]赵秉志.反腐新罪名不会成为贪官的“免罪符”[N].法制日报,20 09-04-07.
[2]舒洪水,贾宇.《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理解与适用[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3).
[3]刘敬新.刑法学博士解析离职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斡旋受贿[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04-17.
[4]孙建民.如何理解《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密切关系的人”?[N].检察日报,2009-05-05.
[5]王荣利.详解《刑法修正案(七)》反腐新罪名[N].法制日报,2009-04-03.
[6]汪维才.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6).
[7]高铭暄,陈冉.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