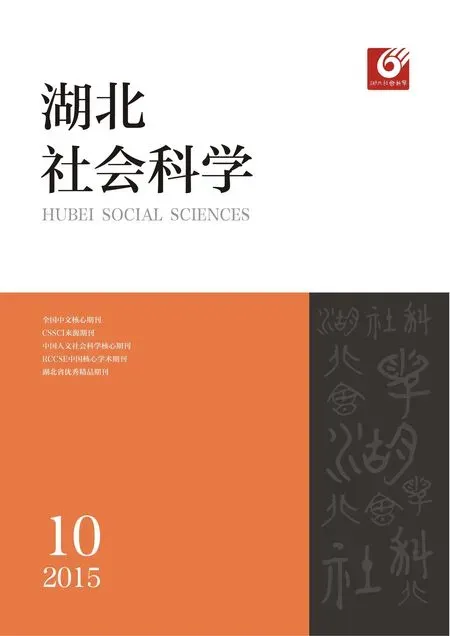歌词徘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边上的反思
陈宝琳
(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歌词是当下生活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它既是普通受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体验方式,也是研究者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关注焦点。它以某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博得了众多关注的眼球。然而,当我们回顾现当代歌词百年创作发展的历程,审视其研究现状时,不能不在赞叹其硕果累累时为其“身份”归属问题及发展前景而忧虑,这是歌词徘徊在现当代文学史边上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一、“身份认同”中的缺席
1987 年10 月,在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乔羽总结指出歌词创作的两大弱点:“一是我们的队伍太年轻,理论力量薄弱,有的人虽有朝气但不成熟,有的作者准备不足就匆忙上阵。二是有些歌词创作越来越文字化、表面化”。[1](p240)作为歌词创作与研究的“领军”人物,乔羽的点醒可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学界纷纷从歌词的创作、审美与传播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推动歌词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地解决。借用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术语讲,就是关于歌词“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西方文论中,“身份认同”指向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之间的认同,它在对“我”的根本来源与未来走向的追问中,揭示研究对象的内涵与本质,并获得其存在与发展关乎语言、文学、文化等层面的价值意义。[2](p465)对歌词而言,自近代以来它与“诗”发展分化成为独立的文体形态之后,其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悬浮状态,缺乏合法的研究出发点。尽管研究者对歌词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其间也不乏为歌词寻找“身份”的归属,但是,众声喧哗之中仍有无实质性结论之嫌。进而,与歌词相关的研究也就出现创作理论匮乏、批评标准缺失等问题。
试想,如果歌词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就意味着歌词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具有一种不完全的定义。而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者对其所作的研究就没有牢固的根基,即便这些研究走向了所谓的成熟,但也为某些研究结论留下了一个不扎实的缺口。所以,歌词的“身份”归属问题应该是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起点。
当然,我们深知,造成歌词身份尴尬的根源在于它与音乐无法割裂的联系。因为音乐,歌词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写作体式;因为音乐,歌词获得了价值生成的动力;因为音乐,歌词获得了广阔的读者群体;……正是因为音乐在歌词生命中无法舍弃的存在,在学科分化较为明晰的近现代,歌词步入了身份迷失的境地。当我们在歌词研究中,要追问“歌词是什么”、“歌词从何而来”、“歌词往何处去”的时候,如果不还给歌词一个“身份”,这将意味着之前对其所做的研究都缺乏文化分析的依托、价值生成的基础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歌词创作与研究的繁盛景象中重拾歌词“身份认同”的思考。
就目前学界的歌词研究成果来看,论文研究成果丰富,学术专著也开始增多,研究队伍逐步专业化,呈现出学科融合的态势。这体现出歌词研究发展的可喜景象。但是,在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归纳反思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中因歌词“身份”归属问题而出现的如下状况。
1.歌词属性称谓的反思。
梳理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对歌词的称谓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除直接的“歌词”称谓之外,有将歌词称作“歌诗”的,有将歌词称作“歌曲”或“歌曲歌词”的,还有将歌词称作“歌词诗”的。而时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不约而同地将歌词称为“歌词文学”,或者“音乐文学”。在这些不一致的称谓背后,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者对歌词研究切入角度的不同,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力求赋予歌词“身份”归属的倾向。而他们努力追求一致性称谓的背后更多体现出的还是对于歌词“身份认同”的焦虑——即使歌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态,有自己发展的路径与成就,但它内在的属性到底是姓“歌”还是姓“诗”?在“史”的书写中,它究竟该走进“文学史”还是“音乐史”?
认为歌词姓“诗”的研究者,有足够的文学史证据,因为歌词与“诗”同根同源,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分化。而认为歌词姓“歌”的自然侧重关注与歌词不可分离的音乐元素,认为歌词离开音乐就无法展示其思想的魅力。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既然歌词与“诗”同根同源,诗歌能够顺理成章地走进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何歌词只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出现过,却被现当代文学史拒之门外?或者,既然歌词与“歌”紧密相连,在“歌”中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为何在音乐史的书写中,它却又只能以一种依附的姿态出现,而无法获得独立的审美地位?
2.歌词研究方法的反思。
乔羽认为“歌词”概念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可诵的诗与可唱的歌正式分流,使歌词成了一种独立的语言艺术品种。他把70 年来的歌词艺术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p263)这一定位为现当代歌词理论研究拉开了序幕。
认真比对歌词百年发展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除歌词(或歌曲)音乐性的理论研究比照的是音乐理论知识外,对歌词进行写作、审美、传播的理论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将歌词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形态,借鉴现行成熟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本体研究、文化功能研究。研究者运用文学叙事理论对歌词进行叙事性研究;运用形象塑造及意象营造理论对歌词进行抒情性研究;运用韵律、节奏等语言学理论对歌词进行写作学方面的研究……总之,大量关于文学研究的艺术、文化、审美理论都被运用到歌词研究中去了。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论,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歌词纳入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中了?既然研究者对歌词研究方法的权重都更倾向于运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那为什么在文学史书写中对歌词登堂入室的合理性又如此地犹豫不决呢?
在如上的反思与质疑中,我们不能不感慨歌词发展顽强的生命力,同时,我们更应当认识到,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与追问中,才能够促进我们为歌词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与合法的“身份”归属,这样才不至于让歌词在百年的沧桑巨变中以丰硕的成就换来的依然是历史书写上的尴尬缺席。
二、“历史寻根”性的回归
目前各院校使用的各种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陈思和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用一节的篇幅讨论了摇滚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它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指出这首摇滚歌曲“表现的是一种艰难而痛楚的文化反抗的处境”。 这是歌词在正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的首次“露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带有突破性意义的文学史书写并没有推动歌词步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步伐。也因此,歌词回归中国文学史的构想也只能以零星的方式散落在单篇论文研究中,或者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将这种构想作为个人学术研究的前提。
事实上,随着歌词创作进入自我发展的瓶颈时期,专业词作者以及相关理论研究者也开始寻求歌词写作新的突破路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让歌词在文学上站起来”是纠正歌词少真情、缺个性、乏诗味之弊病的良方。[4](p60)另一方面,居于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诗歌也面临着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传播方式重建的尴尬处境,急需寻找改革的历史源动力。当歌词带着回归的自觉意识,我们也怀着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新希望重新对中国文学史做一种寻根式的反思时,歌词在历史书写中归向何处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1.歌词创作是中国诗歌结构的主体。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辉煌的诗歌史。诗歌是最早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文体,其源头是远古的歌谣,它以歌的形式出现,具有原初的音乐状态。由于没有科学的记谱方式,歌谣只能以文字的诗性形态保存了下来,虽然形式粗糙,但它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式雏形。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分别是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标杆,但究其实质,《诗经》是一部歌词总集,而“楚辞”是带有楚地宗教文化色彩的歌曲歌词,且后者标志着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步入文人独立创作的新时期。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乐府”由音乐机关演变成“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最初都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歌诗”、“乐诗”、“声诗”,通俗地讲,也就是“歌词”。同时,当乐府创作融注文人的智慧,经历不断地加工、定型,又逐渐产生一种脱离音乐束缚、不再合乐歌唱的徒诗形态。这种徒诗经由唐代诗词格律的严格规范,又生成了新体诗——律诗、绝句。但是,当新体诗严格的声律规范束缚了文人创作的自由时,晚唐至宋,诗歌又以“词”的面目出现。作为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词造就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新辉煌。当然,随着后来词、乐的分离,文人创作只依词调、词牌格式填词的时候,词自然又生出不合乐歌唱的形态。杂剧和元曲也可以合乐歌唱,其歌唱的文词理应属于“歌词”范畴,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被列入戏曲,和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从文体形态的角度共同支撑起了文学殿堂,故不纳入诗歌的范畴作深入说明。
扫描式的梳理,让我们了解到中国文学史中诗歌作品的主要类别构成。在中国古代史书写中,“诗歌”是个泛化的文体概念,它以多种具体形式体现了诗歌创作的实绩,总体包括入乐的歌词和不入乐的徒诗两大文体形态。同时,我们可以肯定“歌词”一直被冠以“诗歌”之名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书写范畴之中,是中国诗歌王国里不可或缺的结构主体。
沿着这个思路往后梳理,现当代文学史所提及的“诗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徒诗”,而合乐演唱的“歌词”则彻底与“诗歌”划清界限,偏离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意义上“诗歌”的书写轨迹,成为独立发展的一种文体。个中缘由自有近代以来因“诗界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关于“诗歌自觉”的认识分化,以及借鉴西方文艺观念整合中国文艺学科体系的现实要求。但是当“徒歌”彻底走向“纯诗化”的道路,以“诗歌”自居,它不仅不再延续历史的辉煌,反而越来越边缘化,而歌词最初多以徒诗的形式出现,并自觉以配曲歌唱为“期待视野”,迎来了自我发展的辉煌。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抹去“歌词”的印记,事实上是缩小了“诗歌”这一文体概念的适用范围,它不仅造成歌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所皈依的后果,而且以现代诗歌的“失聪”与“哑口”为代价。当学界呼吁向歌词寻求拯救诗歌的发展良药时,这其实深刻地体现了诗歌发展对歌词倚重的事实。
2.歌词形态是诗歌文体衍变的动力。
文学是一个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其指称对象的边界并不确定,由此,文学史书写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体的价值标准对诸多作品进行分类评价。如果在文学史书写意义上谈文学,其实首先必须正视“文体”的规定性问题。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具有“文学性”,其文体的自觉发展时期可追溯到先秦时代。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产生于何时,但可以肯定,最早的诗歌体式是二言体式,如《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
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狩猎生活的上古歌谣,以二言诗的形式刻画了先秦劳动人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颇为生动的劳动画面。类似这样的歌谣多用二言句式,押大致整齐的韵,于粗糙中包含了诗歌文体的基本元素。
《诗经》的出现不仅使中国文学有了确切的“诗歌”概念,也使诗歌作品有了最初的文体范式。它重视诗歌句式排列与音乐形式的四言体尝试,是文学史上第一次诗体大解放,后代诗歌基本的格式形态由此确立。
“楚辞”的产生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的诗句模式,取而代之是五言、六言、七言等长句,在音韵节奏方面也有了奇偶相配的变化,并且,诗歌的篇幅大幅增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容量。可以说,“楚辞”实现了诗歌艺术从形式到格律的新追求,建立了诗歌文体形态的新规范。
我们常说一种新文体形态的产生往往是对既有诗体形态的反拨与革新,汉乐府民歌即是如此。同《诗经》一样,它最初来自民间,用通俗的口语反映生活现实,但其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的形式,整散随意,体现出一种非规范的自由。当五言诗在民间创作增多,随着文人创作的加入,该时期诗歌创作体式渐趋走向五言、七言的形态,中国诗歌的重要诗体形态由此也得以成熟。
唐以前,中国古体诗歌发展到五言、七言大致定型,并且趋向使用大致整齐的韵辙,讲究节奏,但没有对篇章、音韵的严格规定。但唐以后的诗人开始对篇章、句式、音韵进行严格规范,催生了有别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格律诗,四句为绝句,八句为律诗。五言或七言,都要求各句的字数相等,且一韵到底、讲究对仗、合乎平仄。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严格的诗歌形态。但是,严格的束缚必然会限制诗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变革由此而生。中唐以后,词悄然兴起于民间,依照乐章的结构分片、曲拍分句、乐声用字,形成了一种句式长短不一而有定格的形式。它的韵律综错变化、句法参差不齐、抒情真挚浓烈,且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一时成为深受欢迎的文体形态。和之前的格律诗一样,词产生之初相对自由,文人的染指又使之与词乐分手,陷入一种“模式”:只按照词调、词牌格式填词,字句长短、声韵平仄也有一套相对严格的规范。所以,词在对格律诗的反拨之后,又重新陷入了格律的限制之中。
总体来讲,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形态经历了一个“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5](p13)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代的“徒诗”和“歌词”在“诗歌”文体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区别,“徒诗”句式整齐划一,句法相对固定,格律严密平整,而“歌词”句式参差不齐,句法灵活多样,韵律疏密不定。而从文体形态演变来看,文学史范畴内“诗歌”文体形态的衍变路径是“徒诗”和“歌词”交织并进,且以“歌词”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恰如陆正兰所言,“徒诗与歌词不断地转换位置:每当一种诗的样式充分发展,‘内转’到无可再转,需要新的形式时,诗就回过头来找歌词”。[6](p114)因而,时下理论界呼吁从歌词那里寻求诗歌创作的突破口在这里可以得到历史经验的证明。
3.歌词审美是文学创作发展的风向。
文学创作实践不仅成就了文体概念,也推动了文学意识的成熟,这是文学进行主观价值判断的前提。因为,文学关涉文体的特性归根到底还是关系到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诉求——是以个人诉求还是以社会诉求为皈依。
魏晋时期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核心在于对文学的重视。魏晋之前的文学创作多“舒心之愤懑”而“卒成于歌咏”。言下之意是当时的诗歌创作缺乏主体自觉意识,多属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就如“杭育杭育”的号子,它带有原初的歌唱特点,承载着人类共通的某种情感诉求。而创作主体意识的缺乏让我们可以肯定,“无意为诗”具有大众化的社会审美诉求,因为“那种非刻意的本色写作,使得被现实情景所勾引、所牵引,甚至所触痛的灵魂内核得以率意而真实的显露。而这种显露又恰暴露出人的终极向往和生命渴望与现实情景之间的矛盾纠葛,这样,即使从局部和片段的场景中,我们也能读出隽永和深远的韵味来”[7](p12),这恰恰是文学中“歌唱性”特质的体现。
诗歌就其本质而言,产生于劳动之中,也是以通俗化、大众化起家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宋词等诗歌文体形态无不是萌生于民间的。从文化主体审美的角度看,它们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原初的创作状态,迎合了大众化的审美心理需求。而徒诗每每处于遭遇自身文体发展的低谷时,在与这些具有大众化审美诉求的文体形态的融合中重新走向辉煌。这是诗歌在审美价值追求中向大众化靠拢的显在表现。
魏晋之后,文学创作进入了“有意为诗”,甚至“为文造情”的时代。当诗歌从集体创作进入到文人独立创作的阶段后,诗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对作品施以刻意创造的审美效果。文体规范的渐趋严密即是明证之一。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具有社会功利与文学超功利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追求,在诗歌创作发展过程中,除了社会赋予的功利价值外,它更多地体现了诗人个性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如情感表现的个体化、文体形态的求雅与求变等。这是文学创作进入自觉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使得外在的文体形态追求与内在的个人精神诉求合二为一,由此,文学内转到无法自控。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像格律诗的出现、文人词的变化等,貌似是文学文体形态发展的内在表现,但它却是以失却大众文化审美价值的魅力为代价的。
近代以来,当诗歌拒绝与音乐结合,它挣脱了传统的音韵格律母体,仅仅重视语言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化写作,淡化甚至忽视了人类共同情感的抒发。这种追求纯诗化道路的努力必然使得读者的需求与诗歌之间产生精神沟通与交流的障碍,也必定会使这些需求在某种层面上被其他的艺术形式所替代满足。与诗歌不同,歌词延续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创作的“歌唱性”特质,在文体表现上,它坚持用一种可唱、可诵的通俗化面貌自觉承担起讴歌人类内心共同情感的责任,由此,铸就了一种开放式的接受语境,收获了独立发展的骄人成绩。
尽管我们说激情是个体审美创作的动力,但我们也要说,创作不是为了自我陶醉,它必须诗意地栖居于现实之中。这或许是歌词审美发展所显示的文学创作的大方向,也是对时下诗歌寻求新突破具有前瞻性的提示。
结语
一种文体形态的衍变自有其外在的表现与内在的规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其做孤立的分析。割断历史即便能在短期内给予其显赫的历史地位、显示其突出的创作成就,但对其长远的发展来讲却是不利的。歌词即是如此。近百年来,歌词的发展成就不可谓不显著,然而,游弋于文学史与音乐史之间的尴尬不仅使其没有历史的合法归属,而且也削弱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本是同根生”的诗歌虽然依旧雄踞于文学史中,但割断历史寻求新的发展带来的也不是理想中的辉煌。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歌词回归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框架不仅是歌词发展的自觉皈依,而且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现实需求。
当我们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史是后来者根据自身对文学的理解,来对过去的文学进行一种历史角度的梳理”[8](p240)时,逼视当下,在理论界大声疾呼拯救歌词、诗歌时,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歌词理论研究的匮乏、歌词批评标准的缺失其根源在哪儿?诗歌读者群的流失、创作路径越走越狭隘的症结又在哪儿?通过如上一番反思,我们是否可以严肃而肯定地说:歌词真正的站立是应该首先让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名正言顺,而不是永远从属于音乐史、徘徊在文学史边上,同时,歌词回归文学史的未来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1]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2]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党永庵.歌词的真名叫歌诗[J].音乐天地,2010,(1).
[5]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陆正兰.中国诗能否回向歌词之根[J].江汉论坛,2007,(7).
[7]褚兢.透视现、当代中国诗歌——论新诗自身的两大暗疾是导致其远离大众的根本原因[J].创作评谭,2000,(3).
[8]张荣翼.文学史的退行性规则[J].中州学刊,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