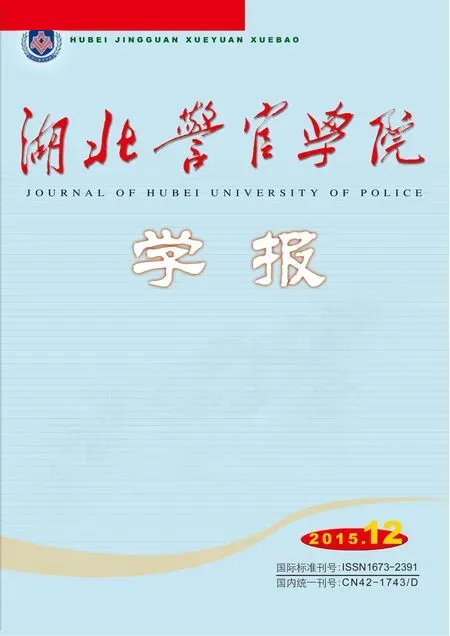信息社会警察文化的变迁
薛向君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江苏南京210031)
信息社会警察文化的变迁
薛向君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江苏南京210031)
警察文化的变迁意味着警察从社会角度感知、评判其工作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将其价值观付诸行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信息社会,随着警察任务与角色、限定警察权力的法律规则、警察的“经历”乃至警察周遭的权力关系网络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警察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
信息社会;警察文化;变迁
一、警察文化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警察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般认为,警察文化是以警察自由裁量权为基础,以巡警文化为核心,在基层警察的工作实践中后天习得、相互影响并加以传承的一套共同价值观。1966年,美国学者杰罗姆·斯科尔尼克在其关于警察巡逻工作的经典研究中,将警察角色的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危险——经常要提防暴力行为的出现;权力——能合法使用武力,并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效率——由产生执法结果的压力造成。[1]他认为,这些元素与警察组织的准军事性特点相互作用,在警察中生成了独特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工作人格”。这种“工作人格”是警察用来应对警察角色上述三个基本特点的一种手段,并经由无数社会化过程得以传播。英国学者罗伯特·莱纳将警察的“工作人格”理解为斯科尔尼克对警察文化的反思,在他看来,警察文化是警察这一特殊群体的“价值观、行为规范、观点和行业规则”,[2]用以帮助警察应对并适应外界压力与紧张状态。其主要特点包括:使命感——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弱者不受掠夺者侵害;犬儒主义与悲观情绪——警察所坚守的道德观正受到各方面的侵蚀;怀疑——警察总在寻找各种麻烦与危险迹象,后者往往以“可疑”的人或地点的形式出现;群体团结伴随社会孤立——警察往往依照“他们与我们”的分类行事,这促成其内部团结,也造成警察在社会上的孤立状态。[3]
关于影响警察文化的因素,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警察的角色和任务
在斯科尔尼克看来,警察的“工作人格”是由自由民主社会警察工作的环境特点以及警察的角色与任务造成的。他认为,“警察,作为其社会地位综合特点的产物,倾向于形成自己独特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通过这种认知透镜来看待各种局面和事情。”[4]警察的这种“工作人格”是作为应对公共警务的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一种手段得以发展的,任何对警察职业的任务与角色进行重新配置的做法都将引起警察文化的变革。
(二)法律规则
戈德史密斯认为,法律是形成警察文化所必须的结构性条件之一。[5]由于法律对警察权力的构想较为宽松又富于变通,使警察在执法上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警察文化得以滋生其中。毋庸置疑,法律和管理规则等结构性因素对警察文化的塑造极为重要,它们提供了文化赖以运行其中的框架、结构或话语。然而,法律并非警务的模板。由于基层警察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使用非正式的操作惯例指导其工作实践,歪曲甚至违背法律和警察管理规则,使其失去应有的效力。这些被誉为“博学的问题解决方案”的非正式规则包含着警察“对可接受行为的公约和共同理解”。[6]例如,“不要放弃另一位警察”“如果你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要牵连别的警察”等。[7]警察文化正是通过这些非正式规则得以表达的。
(三)经历
与以往那些把文化看作一套非正式规则的标准描述不同,谢林与埃里克森认为,警察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社会化过程或通过规则传播。他们重新定义了警察文化,将其视为通过经历(stories)而构建的一种敏感性。谢林与埃里克森关注很多警察研究者曾经听说过、嘲笑过、厌倦过、反复提及却往往视之为无关紧要的经历,他们将这些经历作为理解警察文化的关键,指出正是通过讲述或听到这些经历,警察才知道该如何行事。这些经历“构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感觉、一种行动从中产生的方式”。[8]谢林与埃里克森认为,经历对于实用知识的传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听众可以将其适用于其他情况的最佳做法,一个可循的先例。尽管听众在未来遇到的情况极有可能不同,但经历仍然适用。谢林与埃里克森对警察文化的解释,其价值在于将文化看作不断被生产与复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强加给警察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他们的论述丰富了理解街头警察行为的方法,但忽视了经历与规则其实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四)权力关系
珍妮特·陈针对上述影响警察文化的因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因素未能充分考虑警察组织内部的文化差异,也鲜有涉及警务的结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她将警察文化视为一种态度,后者通过警务的法律背景、政治背景与警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得以形成。在研究警务的结构状况时,陈吸收了皮埃尔·布迪厄的“领域”观,[9]将其定义为一种“冲突与竞争的社会空间,其中,参与者努力建立对特定权力与权威的控制,并在奋斗过程中修改该领域本身的结构”。[10]在一项关于警察与少数族群的关系的研究中,陈认为,该领域的不同因素(“游戏规则”)塑造了警察文化,包括政治环境、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政府政策以及对警察擅权的法律保护(如申诉机制)等。这些因素反映了通过竞争各种不同资源或“资本”而产生的权力关系,[11]包括社会资本(支持网络)、文化资本(知识与能力)、象征资本(信誉与合法性)等。[12]参与者可以为了增加资本或改变游戏规则置身其中,依照“习惯”(指“对游戏的感觉”,它“融合了过去的经验,使个人得以应对不可预见的复杂情况”[13])进行谈判。通过借鉴组织理论家的著作,[14]陈认为这种习惯通过各种“文化知识”的传播得以塑造,包括:不言自明的知识(警察的任务,如“对犯罪宣战”)、字典的知识(用来建构人物与事件类别,如“声名狼藉者”或“值得尊敬者”)、指导的知识(常规情况下的通用指导,如需要留意“不寻常的人”)、以及秘诀知识(具体情况下的指导,如“保持沉默”或“远离麻烦”)。[15]陈的这种分析承认了文化的解释性与创造性,也考虑到了多种警察文化的存在以及警察工作的政治背景和认知结构,她对文化具体组成要素的分析推动了关于警务变革的争论。
上述因素对警察文化的塑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警察从社会角度感知、评判其工作的方式,以及警察将其价值观付诸行动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引起警察文化的变迁。
二、信息社会影响警察文化变迁的因素
自斯科尔尼克等警察研究学者创造性地提出警察的“工作人格”以及警察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加以研究以来,警察工作于其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起到了主导作用,极大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在信息社会,警察的角色与任务、限定警察权力的法律规则、警察的“经历”乃至警察周遭的权力关系网络也随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后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信息时代的警察文化。
(一)警察角色与任务的变化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警察工作与斯科尔尼克及其他学者所描述的工作相比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警察组织内部的技术革新,尤其是处理嫌疑犯群体信息的大型数据集软件的开发应用,使警察工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形式上看,警察的工作重心由传统的执法转变为信息生成与加工处理,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模式的出现使警察用于信息工作的时间远远超出直接用于保护个人与财产免受犯罪侵害的时间。不仅如此,技术与情报收集的进步加速了警察功能的全球化过程,使警察角色日益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地方、国家与国际秩序维持者的特性。
随着警察工作方式与工作环境的改变,斯科尔尼克所描述的危险与权力因素不再成为警察职业文化得以产生的主要空间,仅围绕高速汽车追踪、酒吧斗殴、逮捕囚犯等执法活动来构想警察文化变得本末倒置,信息工作在现代警务中的核心地位使其在警察工作人格与职业文化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内容上看,警察过去一直扮演着公共秩序捍卫者的角色,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公共安全是警察组织的工作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此,警察依赖专业化的警力资源,采取内部分工的工作方式,各警种、各部门在各自专业范围内各司其职。信息社会的到来改变了警察组织的目标、资源与工作模式,警察不再仅仅扮演打击犯罪的保护神角色,还为公众提供各种紧急或非紧急的社会服务,预防打击犯罪、提供社会服务逐渐成为警察组织的双重目标。警察功能逐渐侵入各种社会机构,向历史上不在其强制力范围之内的领域扩张。他们参与构建社会安全网络、打击恐怖主义、干预家庭暴力、救助精神疾病患者与情感困扰者,参与安全教育以及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并且与管理机构及私人团体联手处置各种犯罪问题。信息社会警察在公民生活中角色与任务的这些转变必将带来警察文化的变革。
(二)法律规则的拓宽、滞后与缺失
作为形成警察文化所必须的结构性条件之一,法律规则的变化会对警察文化产生影响。在信息社会,连续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宽阔远景造成法律真空与模糊地带的出现。由于技术革新往往先于法律框架得到调整之前出现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各种非正式的问题解决办法随之形成,从而技术革新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警察亚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空间。此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商业的全球化也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受到挑战,超越地理界限的司法辖区概念得到了拓宽,网络犯罪和反恐行动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司法辖区的全球化,跨国警务的形成提升了各种国际条约与跨境协定的重要性。例如,海峡隧道法案将警务与边界草案、安全防御草案纳入英国与法国的法律体系,这些草案提供了警察与其他执法机构在外国土地上(只能在所限定的“控制地带”)行使执法权的法律框架,使法国警察可以在海峡的英国部分开展武装行动,英国警察可以在海峡的法国部分维持国家计算机终端。无独有偶,在北美的背景下,共同法律援助条约为大量的警察机构之间的例行工作、广泛的犯罪数据和犯罪情报交换以及其他跨国警察行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跨国警务合作的背景下,警察不仅要掌握所辖主权区域的法律规则与警务文化,也需要了解那些旨在促进跨境警务行动的国际法律框架,同时还得熟悉可能会寻求合作的其他警察辖区的法律规则与警务文化,否则跨国警务行动将很难开展。可以想象,以往在纯粹的国家层面,法律的复杂性已经造成警务的某些模糊性,进而改变了警察文化;在跨国背景下,交叠的司法管辖界限以及各种双边多边条约的签订造成法律规则的千变万化,各国不同的警务传统也会影响警察的执法方式,警察体制相近的国家由于警务运作模式接近,容易形成相近的警察文化并获得相互认同,但警察体制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客观存在,这终将影响警察文化的变革。
(三)对他者“经历”的借鉴
谢林与埃里克森将警察文化视为通过“经历”构建的一种敏感性,认为经历是理解警察文化的关键。在信息社会,警务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消费者(社区)满意的一种服务。为实现预防打击犯罪、提供社会服务的双重目标,警察组织所依赖的资源已经不再限于警察自身的专业化知识与技能,公众的常识、意见、经历等非专业化知识也开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警察在工作中开始优先考虑社区需求,通过强化自身的职业主义与行为规范,开展消费者调查来重建警察与地方社区之间的传统合意,地方咨询机构逐渐成为警民双方的交流论坛。通过借鉴他者的经历,警察用于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限于传统的惩罚手段,而是有了更多其他的替代选择。随着市场语汇对警务领域的渗透,警察部门经历了深刻的组织和管理变革,开始借鉴商业管理模式,以便削减部门开支,同时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在此过程中,企业部门对安全的理解以及在安全治理方面基于风险的思考逐渐渗入警务领域。对前者而言,风险意味着对企业经济效益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或是对企业声誉及法律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的安全任务不是为了控制犯罪,而是为了在尽量减少损失的同时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安全管理的战略导向背后是某种面向未来的敏感度,后者为企业管理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认知与情感基础。通过观察,学者们注意到了企业安全文化对警察部门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指出,公共警察朝信息收集、预期参与、主动介入、系统监控、合理计算结果方向的发展展示了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与在商业安全部门中发现的那种意识形态相比拟。[16]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反映了在安全治理过程中警察自身经历与他者经历或敏感性的相互“融合”,[17]后者必将对警察文化的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权力关系的碎化
在信息社会,警察周遭的权力关系网络出现了碎化的趋势。一方面,社区警务模式要求把原来集中在上层的警察权力分解到基层,让社区警察根据自身的判断力、智慧和专长,与社区民众共同探讨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这种分权式做法在那些固守专业化警务模式的人看来,是与传统警察文化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警察应该是在法治限度内让人们遵守法律的权威角色,而不应该是社区警务模式所倡导的“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不难想象,警务模式变革造成的这种警察权力分化必将对警察文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信息社会,科技的发展创造了以往任何体制下难以想象的机遇与前景,也带来了难以预测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安全越来越成为上至国家下至普通民众关注的首要问题,警务也随之成为一种后现代权力安排的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的治理形态中,国家与商业、民事、志愿性机构进行互动,这种互动既发生在国家司法管辖疆界之内,亦超越了这个疆界。超国家安全网络的出现质疑了由国家控制警务的神圣信念,并且对现代治理的基本性假定——国家是治理社会生活的工具——产生怀疑。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提供者,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包括企业、社区群体、非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开始承担起保护自己的责任,行使了安排、购买安全的权力;更多市民也开始参与邻里守望计划、合作伙伴关系之类基于社区自愿的安全倡议,安全“赞助者”与“提供者”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随着安全治理权力在不同公共与私人部门的扩散,以往安全领域的很多外围参与者逐渐承担了巡逻、情报工作、风险管理和调查等传统上与公共警务相联系的任务。这种多元的后现代警务实践给警察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警察必须摆脱以往在社会上较为“孤立”的地位,敏锐察觉周围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的变化,学会和形形色色的机构与个人相处,在多元化的安全治理网络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碎化显然也会带来警察文化的变革。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信息社会,影响警察文化的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警察文化也随之发生变革。一方面,警察角色与任务的改变及其对他者经历的借鉴,使警察文化由以往的惩罚性文化转变为更加包容的管理文化。警察将个体公民视为能够作出理性选择的行为者,对其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加以管理,他们重视有效伙伴关系的打造,使市民在维持社会治安、解决当地问题方面拥有真正的发言权;对结果问责的加强给警察部门带来了效率方面的更大压力,使警察的工作方式由以往的被动反应转变为积极接触社区的主动出击;开放进取、灵活热情、诚实敬业、文明执法、重视技能、鼓励创新逐渐成为信息社会警察文化的新元素。另一方面,尽管信息社会警察的核心职能依然是合法行使暴力——这种职能突出了前面提及的警察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强调勇敢进取的冒险以及对待工作的使命感与道德责任感,但随着法律规则的日益复杂和权力关系的碎化,警察不再简单地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各种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协调好保持独立、行使自由裁量权与忠于法律精神之间的内在矛盾,妥善应对周围的各种权力关系,努力在对需求者提供服务和对违法者严厉执法之间达成平衡。
[1][4]Jerome H Skolnick,Justice w ithout Trial,New York:Wiley, 1966:42,Chap.3.
[2][3]Reiner,R.,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Brighton:Wheatsheaf, 1985:139-46,86-93.
[5]Andrew Goldsm ith,Taking Police Culture Seriously:Police Discretion and the Lim its of Law,Policing and Society,1(1990).
[6][7]Reiss-Ianni,E.&Ianni,F.,Street Cops and Management Cops: the Two Cultures of Policing,in:Punch,M.(ed.)Control in Police Organization,M IT Press,1983:265,266-269.
[8]Shearing,C.&Ericson,R.,Culture as figurative Action,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2(1991):491.
[9][11]Bourdieu,P.&Wacquant,J.,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Chan,J.,Negotiating the Field:New Observations on the Making of Police Officers,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 inology,34(2001):118.
[12][15]Chan,J.,Devery,C.&Doran,S.,Fair Cop:Learning the Art of Policing,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36-38,30-34.
[13]Chan,J.,Changing Police Culture,British Journal of Crim inology,36(1996):115.
[14]Sackmann,S.,Cultural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Sage,Newbury Park,CA,1991.
[16]Ericson,R.V.&Haggerty,K.D.,Policing the Risk Societ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
[17]Johnston,L.,Policing Britain:Risk,Security and Governance, Longman,Harlow.2000:51.
D631
A
1673―2391(2015)12―0023―04
2015-07-12 责任编校:边草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全面深化公安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15JD710026);江苏省公安厅公安理论与软科学研究项目“英美当代警务模式研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创新团队(2015SJYTX03)课题“现代警察制度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