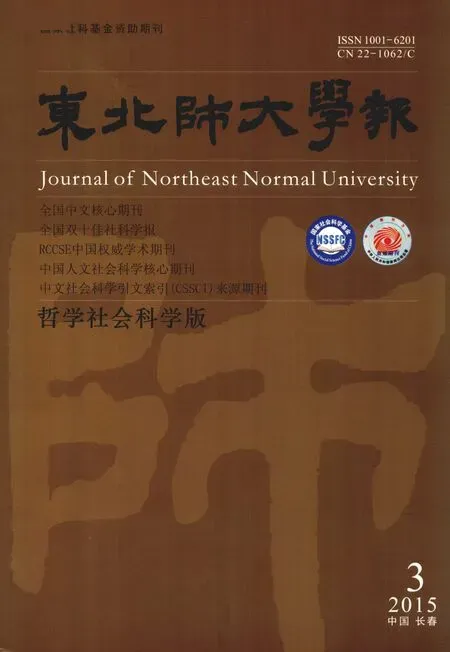“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
——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张文静,周颂伦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
——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张文静,周颂伦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白鸟库吉;顾颉刚;“疑古”;比较
1909年8月,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上刊载《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指出《尚书》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绝非记述当时之事实”,“以余辈观之,尧舜禹乃儒教之传说也”[1]。自此,白鸟库吉首倡的“尧舜禹抹杀论”引起日本汉学界的广泛重视,进而引发激烈讨论。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主张将尧舜禹的事迹当作传说而非史实看待,甚至提出:“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2]。此文一出,便在中国史学界掀起讨论古史的高潮。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前者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在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后,展开广泛的中国史研究工作,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后者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综观二者的研究事业,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作为其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由于“抹杀论”与“古史辨”的理论体系涵盖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诸多课题,因此,本文试图从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辨出发,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或可有助于明晰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一、“疑古”思想的由来
很多中国和日本学者试图从学术渊源上梳理白鸟氏与顾氏的承继关系,探讨顾颉刚的“古史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白鸟库吉“抹杀论”的提示。关于这一问题,李孝迁从《顾颉刚日记》分析,认为顾颉刚应当接触过“抹杀论”,然而“顾氏与白鸟氏虽然都怀疑尧舜禹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论证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两个学说的相似性,应当看作是中日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中先后独立提出某种相似的学术观点[3]。对于“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的影响问题,学界已经做了充分讨论[3-6]。从顾氏和白鸟氏的学术传承、“疑古”思想的具体构成入手,似乎也可以梳理出二者“疑古”思想产生的源头。
白鸟库吉的学术启蒙是在主张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治史的兰克学派的熏陶下完成的。白鸟氏发表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檀君考》就是从史籍、记载内容、时间等方面质疑檀君的真实性的论文,进而得出了檀君并非真实人物,而是传说的结论,从而开始了利用西方史学界的“科学的方法”考辨朝鲜古史的工作。1901—1903年,白鸟氏赴欧洲留学,他历访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在德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乌孙考》和《朝鲜古代王号考》,进一步提升了其与西方学界交流的经验。直到1909年发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白鸟氏立足兰克史学,质疑亚洲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这一“疑古”思想的学术来源清晰可辨。
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开头,白鸟氏指出:“西欧晚近之学风尚未浸染东亚之前,其所谓古传说并未被置于正确历史事实范围之外,盖将两者混同,(中略)世运一转,欧美文物频频涌入,诸般学术面目一新,史学研究之方针亦渐次革新,终至正确之历史事实成为基准,细致研习。至于传说,虽承认其作为传说之存在,却因其谬误过多,几乎被抛弃于史学范围之外,以至史家之考察甚为寥寥”[7]381-382。这段文字与其说是白鸟氏否定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如说是试图为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正名。对于将传说视为历史事实的传统,白鸟库吉显然持否定态度,他主张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而对于欧美史学方针传入之后,传说被置于史学研究视域之外的现象,白鸟库吉也持批判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白鸟看来,欧美文物涌入后,虽然纠正了将传说视为史实的谬误,却导致传说因谬误太多而被学界忽略的结果。白鸟氏似乎认同“传说=谬误”的逻辑,这个逻辑是白鸟展开“疑古”工作的前提之一。而这个在展开研究之初就被预设的逻辑来源于西方史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相对于白鸟氏的上述逻辑,顾颉刚对古史中传说的判定主要来源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经学辨伪。在论及自己“疑古”主张的来源时,顾颉刚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8]。这里说的“时势”、“个性”、“境遇”,首先是顾氏幼年时既有在父亲的命令下读《孟子》、《诗经》,也有坐在门槛上听祖父祖母讲传说故事的经历。顾氏对后者的兴趣格外浓厚,“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9]。看来,在知识启蒙时期,在顾氏的心中就孕育了“疑古”的种子——传说具有“积累性”。其次,来到北京之后,顾氏又迷上了戏剧。迷恋戏剧的经历使顾氏认识到,从真实的故事到戏剧性的演绎是经历了漫长的艺术加工的,这种认识对于其“疑古”思想的构筑,特别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的产生都是颇有影响的。再次,在北京大学期间,顾氏产生了超越今古文之争,突破经籍、门第、学科之藩篱,综而治学的愿望。在他的笔记中记道:“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独有家学为之障乎?”而关于“科学之成法”,顾氏总结为:“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做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10]。这些方法与兰克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找不到顾氏受到兰克史学直接影响的证据,但是从顾氏在大学时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信服”可见,顾氏所说的“科学之成法”必然是来源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之带来的西方史学与哲学思想中的“科学方法”。
在下决心研究古史之后,顾氏制定了推翻古史的“清楚的计划”:不仅要辨伪,更要辨明伪史是如何形成与变迁的。在这里,顾氏特别强调戏剧中的故事的形成是有一致性规律的,这种研究故事的方法也适用于古史辨伪,也就是说,在顾氏眼中,伪史、传说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珍贵史料。我们从顾氏对今文家、宋代和清代考据学、近代考古学的评价中可以窥见其“疑古”思想的构成:在吸收今文家和宋清考据学敢于质疑与辨伪的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今古文之争和经学系统,冲破传统疑古辨伪思想中的“信古”的藩篱,用源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对中国古史展开纯学术研究,在考辨伪史的同时,完成重建中国古史的工作。
对比白鸟库吉与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来源,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态度。白鸟库吉自从在那珂通世和三宅米吉那里接受史学启蒙教育开始,接触到的主要是启蒙主义史观和实证主义史观,根本没有将中国传统经史家在古籍整理训诂上的成就纳入其学术视线当中。在其主持日本东洋学之后,白鸟库吉试图达到的学术目标也是在全面掌握西方学者的东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追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对中国古史研究上,白鸟库吉要进行的工作是彻底推翻明治之前的“将传说视为信史”的观念,揭示中国古史的传说性质,这是一项彻底解构中国古史的工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则来源于年少时对历代古书的广泛涉猎。他的学术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史家疑古辨伪学术的整体研读基础上的。他特别重视《尚书》今古文之争和宋代、清代考据学敢于质疑与辨伪的学术成就。在主持“古史辨”之后,他主张用源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考古学成果,以中国古籍为核心资料,在考辨伪史的同时,完成重建中国古史的工作。与白鸟库吉的彻底抹杀不同,顾颉刚的“古史辨”是一项在传统“朴学考据”基础上对中国古史进行解构与重新建构的工程。我们从二者对《禹贡》的辨析中更能明确上述区别。
二、白鸟氏与顾氏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辨析
在《尚书之高等批判》中,白鸟氏认为尧舜禹的传说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以前”[11]。其依据是:“《书经》中可见关于禹九州之记述,齐之邹衍亦如是说,尧舜禹之事若以为孔子以尧拟于天,则与今日所传之相同,尧应于孔子时代即为人所知,于《诗经》之时代亦为所知矣。另,十二宫、二十八宿中之星相名称,于《诗经》中亦有所见,阴阳之思想虽未见于《诗经》中,亦未见于《论语》中,然若因未发现而全然否认其存在亦为不合理。且从其他事实类推,亦可得出其为同时代之结论。故此可以辨明,此思想意识于春秋时代,即孔子时代以前即已存在也”[3]396-397。
顾氏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尚书禹贡注释》中。通过对比五服制、九州制与战国时期的疆域和制度,顾氏下结论说:“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战国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战国时开始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又可以说:五服制似假而实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实假,由假而化真。《禹贡》篇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下,虽然显出了矛盾,可是它也就在这里自己说明了著作时代。”“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6]111-113。
白鸟库吉之所以从十二宫、二十八宿的星相名称入手推测尧舜禹传说的形成年代,是因为他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宫、二十八宿的记述并非立足于对天文的实地观测,而是从占星思想出发杜撰出来的,进而认为《禹贡》中对九州的记述也不是历史地理事实,而是依据《易经》中的山岳崇拜思想和五行思想对现实的演绎而已。在白鸟氏的“尧舜禹抹杀论”中,《禹贡》几乎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同视之,在论证制作年代时,自然未将《禹贡》与《尧典》等著作分开辨析,而是概而论之。因此,其证据也是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视角中可以看出,白鸟库吉并不认同《禹贡》作为地理学著作的价值,仅仅将其视为传说和古人的臆想。因此,在白鸟氏看来,只辨析《禹贡》一篇的成书年代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与白鸟氏上述立场不同,顾氏从开始研究古代地理沿革时就指出《禹贡》、《尧典》、《皋陶谟》在著作时间上的不同。关于《尧典》、《皋陶谟》二篇的成书年代,顾颉刚在《古代地理研究讲义》中就已经形成定论,他认为:“《尧典》、《皋陶谟》之著作时代,最早不能过秦,最迟当在汉武帝之世”。而对于《禹贡》的具体成书年代,此时的顾颉刚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仅提出“《禹贡》之编入《尚书》是在汉初,其著作时代必不能甚早可知”,又对照五行说的产生时间,认为“五行说始于战国,其著作时代要当在战国以下”,再对照《尧典》中之四宅,断定“《禹贡》之作疑在《尧典》之前”[7]7-10。可见,在讲授“古代地理历史研究”的课程时期,顾颉刚已经注意到与《禹贡》成书年代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禹贡》何时被编入《尚书》的;《禹贡》的成书时代要在战国以后;《禹贡》的成书要早于《尧典》。这三个问题是辨析《禹贡》具体成书时代的重要前提。顾颉刚将《禹贡》何时被编入《尚书》的问题与《禹贡》的具体成书时代区别对待,白鸟库吉显然并未做这样细致的区分。
1933年,顾颉刚在《州与岳的演变》中详细地考证了《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说苑辨物篇》中记载的“九州说”,列举了五个证据,证明春秋时代“只有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7]59。接下来,顾颉刚详细论证了《禹贡》中记述的九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最后下结论说:“我敢说:九州的名词及其具体的说明都是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的事。《禹贡》和《职方》等书的著作,只能后于这个时代而不能早于这个时代”[7]63。这样,顾颉刚考证的《禹贡》成书年代又一次被缩小了范围: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后,《尧典》成书之前(秦代之前)。顾颉刚最终提出《禹贡》具体成书年代是1958年撰写的《尚书禹贡注释》。顾颉刚共列举了六个证据:
其一,列举《导山章》里关于“内方”和“外方”的记载,认为内、外完全是楚国人根据防地的距离和设防的需要而定出的名词,西周时代是不可能存在这些名词的。其二,考证《禹贡徐州章》里说的贡道“浮于淮、泗,达于菏”的意思是由泗转到菏,由菏转到济,由济再转到河。其中的“菏”是吴王夫差为了舟运便利而开出的一条经过菏泽的人工河,由此断定《禹贡》的制作是在夫差开河之后很久的事情。其三,依据吴越争霸的历史地理沿革,认为《禹贡》中记载的“淮,海惟扬州”,证明了《禹贡》的作者不知道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和公元前5世纪初期越国还是远离淮水的,因此,《禹贡》的制作年代距离吴越争霸的时间也应当是很远的。其四,认为《禹贡》里的梁州应是蜀境,而春秋时代,中原和西南方民族并没有往来,战国初年,蜀国才开始与秦国交通,因此,《禹贡》记载的梁州是秦灭蜀之后的地理知识的反映。其五,从《禹贡》的梁州贡物中有铁和镂的记载,断定其应当是成书于中国由铁器时代取代青铜时代的春秋到战国时期,而绝不是尚处石器时代的夏代。上述5个证据可以得出《禹贡》既不是虞、夏时代成书的,也不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秦灭蜀以前成书的。那么,《禹贡》是否是秦始皇统一后的作品呢?顾颉刚对此也持否定观点,他举出的第6项证据是:对于秦统一后新开辟的疆土,在《禹贡》中完全没有论及。“不但始皇所拓新地没有记载,当公元前三□□年,赵武灵王攘地西至云中、九原,稍后燕国又开辟了上谷到辽东五郡,《禹贡》中也全没有这些迹象。可见,这篇文字的著作时代虽然不太早,也不会太迟。在《禹贡》里,东南方只到震泽(即今太湖),南方只到衡山,北方只到恒山,可见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二八□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6]111-113这样,《禹贡》的制作年代最终被顾颉刚锁定为公元前3世纪前期。
对照上述白鸟库吉和顾颉刚对《禹贡》成书年代问题的辨析,可以看出二者在论证视角、方式、考辨依据、辨析层次上都截然不同。首先,二者对《禹贡》具体成书年代的认定不同。白鸟氏认为《禹贡》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以前;顾氏认为《禹贡》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较秦始皇统一约早60年。其次,二者对待《禹贡》成书年代问题的方式不同。顾颉刚把考证《禹贡》的成书年代作为一个重要工程,并且在经历长时间的准备之后才最终考订完成,他不仅将《禹贡》与《尧典》和《皋陶谟》等《尚书》其他篇章相区别,而且注意到《禹贡》被编入《尚书》的时间与《禹贡》的成书年代也是不同的。白鸟氏并未将《禹贡》的成书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考证,而是将其与尧舜禹传说的产生年代等同视之。在白鸟氏眼中,《禹贡》的制作年代问题仅仅是“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论据而已。再次,二者对待中国古籍的方式不同。白鸟氏虽然列举了《书经》、《诗经》等相关史籍,却并未对这些史籍中的相关记述进行具体的对比性分析,而是在着重论证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基础上,从中国古籍中撷取一些相应记述,从而得出结论。顾颉刚则立足于中国古书,从对比不同时代的古籍中的相关记述出发,考证《禹贡》的成书年代。例如,在对《禹贡》“九州说”的产生时间的考证上,白鸟库吉仅列举“《书经》中可见关于禹九州之记述,齐之邹衍亦如是说”的论据,就断定尧舜禹的传说存在于孔子之前。顾颉刚则在详细考证了《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说苑辨物篇》中记载的“九州说”之后,列举了5个证据,证明“九州说”是战国时代产生的。因此,白鸟库吉将中国古籍作为能够得出结论的补充性事例,顾颉刚将中国史籍作为辨析与考据的核心资料。最后,二者展开论证的方式不同。白鸟库吉始终站在整体性辨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视角,在辨析《禹贡》和尧舜禹传说时,更多地论证了“易、阴阳、五行、十二宫、二十八宿”等中国传统思想智慧的形成。因此,他并不认同《禹贡》是对历史地理事实的记述,而将其视为传说和古人的臆想。顾颉刚则结合战国时代楚国防地、吴王夫差修凿运河、吴越争霸的历史沿革、战国时代的秦蜀交通、秦始皇开辟疆土等历史地理事实作为论证依据。
综上所述,白鸟库吉与顾颉刚辨析《禹贡》成书年代问题的诸多区别似乎可以证实,二者尽管在怀疑《禹贡》并非大禹时代所作这个前提下拥有一致性,但是,二者是以完全相异的学术素养为出发点,在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氛围下展开研究的,我们似乎不能断定顾颉刚与白鸟库吉之间在学术上存在某些继承关系。
三、白鸟氏与顾氏对《禹贡》的辨析依据
从辨析依据上看,为了证明《禹贡》的记述并非历史地理事实,而是传说,白鸟氏在主张尧舜禹传说并不是继续性的,而是并行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两类证据。其一,认为《禹贡》九州并非真实存在。白鸟氏指出:“东为青州,乃依据五行,东方为木德,色青;西为梁州,乃依据十二宫中正西为大梁(即太白金星),又称梁星,因此取梁州之名;南方为扬州,想来乃取阳扬相通之意;北为冀州,乃因冀字中包含北字而用之尔。可见,作者欲隐藏其马脚,可谓煞费苦心”[3]395。白鸟氏分别从五行、十二宫、字音、字形入手剖析青州、梁州、扬州、冀州名称的含义,据此论证这四州并非真实存在。进而从《禹贡》中记载的九州的土色出发,得出《禹贡》中包含了易的思想、汉民族的山岳崇拜思想和五行思想,由此下结论说:“不能够认为禹贡记载了历史地理史实”。
其二,质疑《禹贡》的五服制度。白鸟氏认为:“据此制度,去王畿四方五百里为甸服,去甸服四方五百里为侯服,去侯服四方五百里为绥服,去绥服四方五百里为要服,去要服四方五百里为荒服。规定上述五服各自向王宫服役。虽制定上述对国家之规定需实际测量,然自古至今,于支那国内均未有对领内土地进行实测之范例。故距今四千年以上之上古便实行实测,此事决不可信。又从实际之地理考虑,亦可判定此五服制乃空想,而非实际。据《书经》、《史记》等记载,尧舜禹之都城皆为冀州,即今之山西省。若以此为中心,国家分为五服,向四方扩展二千五百里,则东西南三方暂且不论,仅从北方论,此制度便甚为奇特。山西省乃中国北部之一州,其北部便为蒙古之地,此地自古至今均为游牧民之地,而非汉人之住处。而尧舜禹之时代,荒服尚且不论,其沙漠之地包含于其他服之四方五百里之内,服从王事之说法终究不可想象”[3]432-433。
与白鸟氏相比,顾氏对《禹贡》的辨析相对细致,证据与内容也丰富得多。在这里,我们对照白鸟氏的上述两个证据,梳理出顾氏的相应观点。首先,关于《禹贡》九州说,顾氏承认九州是真实存在:“九州制固然依据实际的地形而划分的,每州的土壤、产物等也都是科学性的记载,决不出于幻想。”接下来,顾氏梳理了九州制的确立过程,夏商周时期,九州制并不存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齐、燕、秦、楚等国开拓疆土,“中原人民移徙到的边区就远”,九州的大致规模与名称在战国时代逐渐形成,至于九州制在政治上被采用,要等到汉代以后[6]110-111。对照白鸟氏与顾氏对《禹贡》九州说的剖析,可以看出二者在观点上的截然不同。前者是从五行、十二宫、汉字的字音字形等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角度对九州说提出质疑,立足于古代汉民族的传统信仰;后者是从中原王朝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变迁的角度对九州说的存在进行考证,立足于史籍中的相关历史地理记述。一个是以强调传统信仰的传说性质作为立论前提,主张彻底的“抹杀”;一个是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朴学考据出发,以证实《禹贡》九州说的真实性作为前提,主张谨慎地“辨证”。可见,在对《禹贡》九州说的辨析上,二者的“疑古”思想从出发点到路径、结论都迥然不同。
在白鸟库吉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权存在形态、地理沿革过程等领域往往被忽视。这种视角无疑源于他对中国传统史书的彻底的怀疑态度,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白鸟库吉试图以这种彻底的怀疑来完全解构中国古史的迫切心情。正因为顾颉刚主张《禹贡》九州是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科学性”记述,所以,我们在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脉络中,很少能够看到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哲学思想入手进行的考证与对比,更多的是从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地理沿革、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权存在状态出发,对照《禹贡》九州的相关记述进行的考证。
其次,关于《禹贡》五服制度。顾氏的判断由两部分构成,第一:认为“这个五服之说,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只是假想的纸上文章,世界上哪有这样方方正正的区划!”顾氏还列举出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质疑:“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云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6]109。白鸟氏的怀疑与蔡氏的这个说法完全一致。尽管我们无从考证白鸟氏的是否受过蔡氏的启发,但是,五服说中的这个显而易见的谬误是很容易被质疑的。顾氏不仅提到了蔡氏的上述质疑,还指出方方正正的五服与不规则的九州很明显有矛盾的地方,由此断定这两种制度不是同时存在。第二,顾氏又说:“五服说不是一个假想的制度,是古代实际存在的。”他列举《国语》、《周语》的例子,认为“服”不是分疆划界的意思,五服实际上是周朝时期对待未隶属于周朝的土著国家和其他大大小小封建主的剥削方式而已。而《禹贡》的作者把五服的里数确定下来,反而使这种实际存在的制度变为一种幻想的制度了[6]110。
比较白鸟氏和顾氏对五服说的看法,与白鸟氏停留在对五服说的“四方五百里”疆域的质疑相比,顾氏进一步辨析五服说与九州说的不同,进而阐明五服制的实际状态。因此,在最终的结论上,白鸟氏从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误出发断定五服制度并不存在;顾氏在列举了蔡氏的质疑之后,结合其他古籍的记述,推断五服制在中国古代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禹贡》中对于五服相距里数的细致记述,使得其带上了幻想的色彩。由此可见,白鸟氏对五服制的质疑依据并非独创,二者在对五服制是否为实际存在的问题上也持相反观点。很显然,从学术视野上看,与白鸟氏的一味“抹杀”相比,顾氏的分析与辩证更加深入并富有层次。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日学界至今仍然存在对白鸟氏和顾氏在“疑古”问题上是否存在传承关系的争论,但在细致对照二者对《禹贡》的质疑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禹贡》的辨析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辩证方法,其“疑古”思想的逻辑体系也迥然不同。尽管二者在尧舜禹是古代传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致相同,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由此便断定顾氏的“古史辨”是在白鸟氏“抹杀论”的启发下提出的。
[1] 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全集:第9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0:384.
[2] 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白鸟库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0:183.
[3] 白鸟库吉.尚书之高等批判.白鸟库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0.
[4]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顾颉刚.尚书禹贡注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9[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李孝迁.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J].史学史研究,2010(4):5.
[9] 倪平英.相似外表下的不同内核——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就“尧、舜、禹”问题研究比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5.
[10] 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J].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3.
[11] 杨鹏,罗福惠.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J].探索与争鸣,2010(3):397.
“Denying the Reality of Emperors Yao,Shun and Yu” and “Suspecting the Past” of School of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Shiratori Kurakichi’s and Jiegang Gu’s Respective Research onYuGong
ZHANG Wen-jing,ZHOU Song-lun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Shiratori Kurakichi,founder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literature study,has made an extensiv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is students,after proposing the famous viewpoint of denying the reality of Three Emperors,i.e.Yao,Shun and Yu.He has obtained fruitful results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northeast China and Korea.Jiegang Gu,leader of the School of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in China,has initiated the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past” in historical research.He also established a popular magazineYuGongwhich issued semimonthly.This very magazine has popularized the study of borderland history of China.There are many common features between Shiratori and Gu’s research careers.Moreover,both of their academic studies derived from the idea of suspecting the pas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pare their attitudes towardYuGong,and find 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uspecting the past”,and hammer out ways to discriminate their methods and inclinations.Therefore,we may figure out whether there is an academical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cholars.
Shiratori Kurakichi;Jiegang Gu;“Suspecting the Past”;Comparison
2014-09-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SS008)。
张文静(1982-),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周颂伦(1952-),男,上海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K204
A
1001-6201(2015)03-0116-06
[责任编辑:王亚范]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