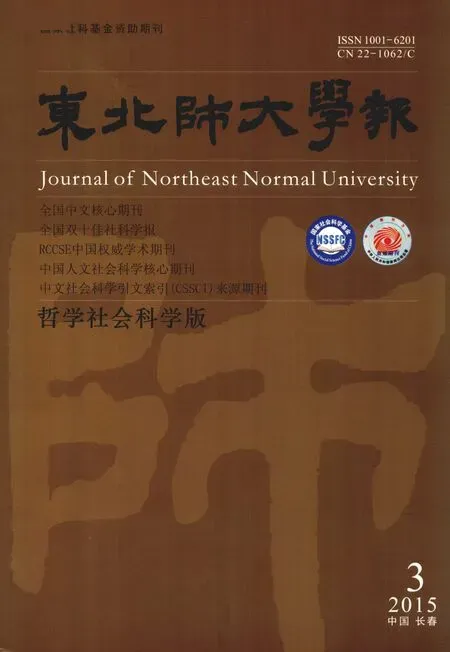“密纳发的猫头鹰”和“高卢的雄鸡”
——黑格尔和他的时代
赵 敦 华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100871)
“密纳发的猫头鹰”和“高卢的雄鸡”
——黑格尔和他的时代
赵 敦 华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100871)
通过对黑格尔生前和身后发表文本的努力挖掘,重在说明,黑格尔在青年时期是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同情者,中年时期是拿破仑的大力支持者,老年时期是时代精神的批判反思者。黑格尔的一生站在时代前列,逐步深入地认识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把黑格尔说成是德国专制的辩护者不符合历史事实。
黑格尔;书信;历史哲学法;哲学;现代国家
黑格尔在1820年版的《法哲学原理》序言结尾处说道: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3-14
24年以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结尾处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2]18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密纳发的猫头鹰”和“高卢的雄鸡”似乎代表了黑格尔哲学“解释世界”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根本差别:前者如黑格尔所说:“当哲学把它的灰色描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1]14;后者则预言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方兴未艾的法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将引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2]18。
但是,如果具体地理解黑格尔与他所处时代的联系,我们可以说明,“密纳发的猫头鹰”恰恰是在“高卢雄鸡的高鸣”之后才起飞。重要的是,前引黑格尔说的“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拿破仑时代的全部过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还说:
每一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12。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高卢雄鸡”开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是黑格尔起跳的罗陀斯岛,而在这个时代黄昏之际起飞的黑格尔哲学所认识、反思和把握的精神就是法国革命时代的精神。黑格尔在公开出版物中不时批判启蒙运动及其导致的法国大革命,在私人书信中却毫不掩饰地赞扬和支持拿破仑,这些书信不但让我们看到黑格尔亲身经历和直接认同的法国革命时代包括哪些重要事件,而且可以使我们理解黑格尔著作中间接、隐晦地评论法国革命时代的深刻含义。《黑格尔书信》收录了黑格尔一生中近700封信,其评论者克拉克·巴特勒说:
黑格尔的青年、成年和老年与他的时代青年、成年和老年显得正相契合,这是大革命的时代。17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可被看作年青年代,主观的观念急切地反对世界的颓废秩序。在拿破仑年代,成年时期的革命克服了无政府状态并自行组织起来。在复辟即我们熟悉的革命时代的老年,世界似乎满足于运行的停止[3]18。
这里所说的“大革命的时代”不限于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且包括随后相继的拿破仑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我们将借助这些书信材料,结合对黑格尔身前发表的著作和身后整理发表的手稿的解读,说明他的思想从青年和成年回应“高卢雄鸡的高鸣”演变到晚年“密纳发的猫头鹰”的历程。
一、法国大革命的年青支持者
1792年,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22岁的黑格尔与谢林、荷尔德林正在图平根神学院读书,谢林把《马赛曲》译为德文,黑格尔与同学一起传唱,种植“自由树”,组成政治俱乐部,阅读伏尔泰、卢梭的书和法国报刊[4]。
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不仅记载在同时代人零星的传记材料,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早期所写的手稿之中。在1792年写的《人民宗教和基督教》手稿中,黑格尔区分了“整个一大堆宗教知识”的客观宗教与“活生生的、在人的内心本质起作用、对他的外部活动有影响的”的主观宗教;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主观的个体的“私人宗教”与“人民宗教”。黑格尔说私人宗教提供“对于个人陷入苦难与不幸境况的安慰和慰藉”,而“人民宗教必须与生活的一切需要结合起来,必须与公众的政治行为结合起来”;从批判的角度说,人民宗教必须“避免拜物教”,避免“空谈启蒙之类的东西”和“对于教条和教义永无休止的相互争论”[5]5-6,22-23。
黑格尔之所以首先思考宗教,不仅他当时是神学院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对传统宗教的冲击,认识到“宗教是我们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他敏锐地觉察到现存宗教中有新旧两种精神:
一个民族的青春天才[不同于]一个日趋衰老的天才,前者富有热情,欢呼它自己的力量,如饥似渴地奔赴新事物,对新事物感到最生动活泼的兴趣,但是[不久]它也许又抛弃了这新事物,而抓住另外一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决不会是在他骄傲自由地脖子上套上枷锁的东西。那日趋衰老的天才则主要表现为在每一方面都固执地依赖于传统,所以他带着枷锁,就像一个老年人带着脚痛风[亦称蹠刑],尽管他呻吟叫苦,但他却不能摆脱它,只好听任他的统治者为所欲为地以此来折磨他。但他只是以半自觉的状态,不自由地、不公开地、怡然自得地享受自己所引起的别人的同情。——他以空谈来度过他的节日,就像对于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年人一样[5]5。
无须多加辨析,黑格尔这些文字鲜明地描绘了法国民族的“青春天才”与德国民族“老年人”的精神反差,他没有无保留地赞扬大革命中法国人的“骄傲自由”,但无情地批判德国人戴着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枷锁而呻吟叫苦又怡然自得的悲惨境地。
1793年,黑格尔从神学院毕业,不愿意当牧师,到伯尔尼当家庭教师。伯尔尼是属于哈怕斯堡王朝的贵族制城邦,1798年被法军占领。黑格尔依据在伯尔尼的经验,完成了对“卡特密信”的评论。1793年在巴黎出版的12封评论,揭露了伯尔尼贵族的黑暗统治。黑格尔的评论历数当地司法制度的罪恶。被告人没有辩护权,一个农民醉酒后与贵族发生口角,“表示愿法国人有朝一日终于能教训他们一场”,被控告后不敢把醉酒情节说出来,结果被判6年监禁,在更多的情况下,“数量如此多的人被处绞刑、轮刑、被斩首和烧死”,“伦理国家公民最珍贵的一项权利的余影也给消灭了”[6]5-6。行政长官按法律应由议会选举产生,实际上或由议员亲亲相授,“老子任命自己的儿子,甚至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他的兄弟,而如果他有一个女儿,他就选一个有钱的女婿”,或在最有权势的议员中投阄分配,“许多老军官相继成为行政长官”。这种制度尤其防范“叛国罪”,黑格尔评论说,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可以被看成喜欢法兰西民族幸运获得自由的征兆,或者看成也想享受这种自由的征兆,看成决心重新得到自己合法的、但却丧失的权利的征兆,看成企图用非法方式攻击政府合法权力的征兆”[6]9-10,7。黑格尔的评论1798年匿名发表,以表示对法国推翻这一政权的欢迎。
1798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撰写了《市参议院必须由公民选举》的政治改革提议。该文警告,在国家大厦即将崩溃之际,任何不图改变、盲目期待稳定将带来社会灾难。黑格尔说:
当一种制度的状况和部分,已不再被人相信,任何想用夸口的江湖骗术使人重新信赖它的企图,任何用漂亮词句粉饰尸虫的企图,都不会是仅仅使精明的策划者蒙受耻辱,而是会给一场远为更恐怖的爆发准备条件,那是改革的需要就会伴随报复,经受蒙蔽的被压迫的群众也将受到不测的惩罚[6]13。
这篇文章用法国王室拒绝激进改革而引发大革命恐怖的前车之鉴教训德国王室的用意十分明显,以致朋友们建议黑格尔不要公开发表。
拿破仑执政之后,德国各邦参加反法同盟,1801年惨遭失败,被迫屈服于拿破仑。在此形势下,黑格尔写了《德国法制》的长文,文章一开始宣布:“德国已不再是个国家”。在他看来,德国引以为荣的“神圣罗马帝国”早就名存实亡,但只是“在同法兰西共和国战争中切身体验到自己何以不再是个国家”[6]22-23。黑格尔从军事力量、财政、领土、司法、宗教、社会等级等方面,说明“这一国家政权等于零”:
每一个政治特权的成员、每一王室、每一等级、每一城市、行会等等,总之在对国家负有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方面,都给自己赢得了这些权利和义务,而国家在如此缩小自己权力的同时,除了确认自己权力已被剥夺,再没有别的职能了[6]28。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比英国、法国落后,甚至比意大利还要落后。对照先进国家的理念和做法,黑格尔提出现代国家要有“一个中心”,以便“监督”、“防范”和“保障自身”,更要允许公民在司法、管理、举荐官员、从业等方面“有自由活动范围”,允许“每一等级、城镇、乡村和社区等都可以享受自由,自己去完成自己范围内的事情。”[6]39。
二、成年的“波拿巴主义者”
黑格尔在1802年定稿的《德国法制》中尚不认可拿破仑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他说,法兰西共和国“一切都从上到下地加以安排,普遍事务不归对之关心的民众部门管理和实施,这将如何产生一个呆滞无精神的生活,这在将来才能体验到,如果这种古板的统治气氛能持久的话。”[6]42-43然而,随着拿破仑的统治在黑格尔所在的莱茵地区推行开来,他生活在拿破仑法典带来的自由、平等的气氛之中,在私人信件中热烈地表达对拿破仑的支持,以致《黑格尔书信》编者说他是“波拿巴主义者”。在当时德国知识阶层和民众中,这个称呼是“卖国者”的代名词,黑格尔只有在与密友尼塔麦(Niethammer)——一个与法国当局合作的文化官员的通信中才能直抒胸臆。
1806年10月法国与第三次反法同盟开战,拿破仑亲率大军歼灭退守耶拿的普鲁士主力,10月13日进入耶拿。黑格尔当日写信给尼塔麦说:
我看到了皇帝,这个世界精神,骑马巡察全城。这样一个人,他掌握着世界,主宰者世界,眼前却关注一点,踞于马上,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3]114。
当时黑格尔正在写《精神现象学》,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代过渡的时代。精神意见与这个绵延至今的世界决裂(…)渐进的、尚未改变整体面貌的零敲碎打,被一道突然升起的闪电中断了,这闪电一下子就树立了新世界的形象[7]7。
这些文字是在见到拿破仑之后写的,是否表达了黑格尔对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的感受呢?
法军占领耶拿之后,黑格尔失去了在大学的工作,他于1807年初接受了到《班贝克报》任编辑的工作。拿破仑在占领区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该报由亲法人士主办。黑格尔告知尼塔麦他接受这份工作的理由:“我的好奇心追踪世界事件”;“我们大部分报纸全比法国的低下,有一份接近法国风格的报纸会是有趣的事”;他补充说:“重要的是,这是德国的需要。”[3]126黑格尔在《班贝克报》积极倡导新闻自由,他向报社同仁提议创办效仿法国媒体的自由报刊。他在信中记载了他的提议。他批评德国媒体的世故、嬉戏、乡巴佬气。他说:“我们没有与这种嬉戏之风相抗衡的手段,因为我们没有的《忠告者》[Moniteur,法国大革命时创办的报纸,后成为拿破仑政府的官方报纸]”。他接着说:
我们没有政治性的《忠告者》,要点在于,我们有围栏和压制的自由——我不禁要说Fress-Freiheit[被喂养和要捕食的自由],而不是Press-Freiheit[新闻自由]。我们缺乏公共性。在国家所处状态、公共资金的配置、欠债、行政官吏等方面,把政府摆在人民的面前,政府与人民为了双方利益的对话是法国和英国人民最重要的一个资源[3]156-157。
黑格尔全力支持拿破仑在其控制的莱茵联盟推行《拿破仑法典》。他在信中记载了他与一位害怕拿破仑法典的地主的谈话:“我告诉他说,德国君主不对法国皇帝所做的事表示谢意是无礼的”。黑格尔认为,引进《拿破仑法典》并不是要强化法国的统治,而是为德国带来希望,“消除那流行至今的没有正义、没有保障、没有公众参与、只有单个人任意和狡猾的集中化的特别模式和体制”。黑格尔说,这种变化不会自愿发生,因为“德国人如同20年前一样盲目”,变化的希望“只能来自上天,即,来自法国皇帝的意志”[3]159-160。
1809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进行第四次战争,奥地利军队进入德国南部,激起了那里民众的反法情绪。当时在纽伦堡任文科中学校长的黑格尔在5月7日的信中,满怀轻蔑和厌恶地描绘了那里的局势:“无业无家的恶棍们,这些暴民[Pöbel],大多是年轻人,挤满在街上,对着进入纽伦堡的骑兵的长矛高呼:‘万岁,兄弟们!’噪音巨大,空闹一场,随即死寂。全部暴民肯定从现在起永远离开我们了。”[3]196
但黑格尔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拿破仑退位后,黑格尔在1814年4月29日的信中写道:“公众希望夺回[德意志]帝国的自由,暴民可以确信了,他们希望回到过去的好日子,这下子被批准了”[3]306-307。
在同一封信中,黑格尔说:
看到一个伟大天才的自我毁灭是可怕的场景。这不是希腊悲剧。平庸的群众全体以不可抗拒的沉重重力,不停地、不妥协地、最终成功地把在上的东西拉下到自身水平,甚至更低。全部的转折点以及群众为什么有力量的原因在于,伟大的个人自己赋予群众做如他们所做的权利,因而参与了自身的沦落[3]307。
黑格尔还说,他在1810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论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与恐怖”一节的结尾已经预示了拿破仑的结局。在那里,我们读到:“绝对自由从它的自我毁灭着的现实性过渡到另一片天地”[7]368。当时人们可能不知所云,现在可知“另一片天地”指德国,法国革命的绝对自由精神的现实性将过渡到德国才能实现。就是说,当“高卢的雄鸡”沉默下来,“密纳发的猫头鹰”终于在德国起飞了。
三、时代精神的老年反思者
黑格尔认为拿破仑之后的复辟时代毫无精神价值,在1816年7月的一封信中,他称复辟是“反对波拿巴的十分吓人的反动”,轻蔑地把复辟者称作“蚂蚁、苍蝇、虫子的人格”,他说:“造物主为他们安排的命运是当笑话、挖苦和恶意快乐的主体,如果需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意安排的光芒下,帮助这些寄生虫顺应他们的命运”[3]325。
黑格尔此后在海德堡大学和1818年后在柏林大学通过对革命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抵抗复辟时代的逆流。黑格尔说:“一种后思(Nachdenken),亦即反思”[8]。黑格尔对时代的后思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反思。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说,时代精神由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来开创承担,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就是这样世界历史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但是,“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他们或则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像亚历山大;或则被刺身亡,像凯撒;或则流放而死,像拿破仑在圣赫伦娜岛上”。黑格尔用“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回击复辟者对拿破仑的人身攻击:“我会加上一句”,“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只是仆人。”[9]30-32
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启蒙时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的时代,只有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10]他强调德国人在哲学上的贡献。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更强调法兰西民族的贡献,承认“启蒙运动从法兰西输入到日耳曼,创造了一个新思想、新观念的世界”。他问道,为什么只有法兰西人、而不是日耳曼人首先实现了自由的原则呢?他回答说,法国人得益于社会和国家的思想原则,并具体地论述法国革命按照政治思想的原则逐步开展的过程。
革命前夕,“当时法兰西的局面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特权,完全违犯了‘思想’和‘理性’”。大革命爆发了!“‘公理’这个概念,这个思想突然伸张它的权威,旧的不公平的制度无力抗拒它的进攻”。黑格尔热情讴歌大革命: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9]441。
在现实中,“封建关系带来的奴隶制状态的遗物现在是一扫而空”。公正的法律需要政府来实施,革命初期却没有有效的政府,罗伯斯庇尔依靠“德行”建筑在主观意见之上,“带来最恐怕的暴虐”[9]442,444。直到拿破仑用军事的权力恢复了政府的功能。黑格尔如此评价拿破仑:
拿破仑利用他性格上无限伟大的力量,转而注意到国际关系,他征服了整个欧洲,使他的开明的政制散播到了四面八方。古往今来,没有人赢过更大的胜利,没有人在征战中表现过更大的天才[9]445。
“可是,”黑格尔惋惜地说:“法兰西人民的意见,就是说,他们的宗教的意见和民族的意见,终于使这位巨人崩溃了”[9]445。如前引黑格尔私人信件所述,黑格尔始终认为,拿破仑的失败不在于军事失利,而在于他赋予平等权利的平庸群众们的意见压倒了他的伟大性格和才能。
晚期黑格尔用政治理性克服无原则的意见。他确立的原则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11第一句话用理性的标准衡量现实的政治制度,第二句话则揭示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包含的理性。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依次揭示了现实社会的所有权、道德习俗、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合乎自由理性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按照理性标准设计现实的国家制度。黑格尔论证合理的国家制度是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有机统一,其现实基础实际上是法国官僚体制和英国议会制度的综合,同时添加了德国政制的要素。
在“王权”部分,黑格尔认为王权是“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从而赋予君主个人更大的权威和最后决断权,而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形式和象征。但黑格尔同时强调,不能“把主权当做赤裸裸的权力和空虚的任性,从而把它同专制相混淆”;“专制就是无法无天”,而“主权却是在立宪的情况下,即在法制的统治下,构成特殊的领域和职能的理想性环节”[1]287,295。
在“行政权”部分,黑格尔指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法国革命所首创,曾经拿破仑加工,而今天仍然存在于法国”。法国的行政制度虽然“能达到最高度的简省、速度和效率”,但由于法国没有发达的市民社会,因而不能调节国家代表的普遍利益与社会不同等级的特殊利益,只有“中间等级”才能胜任既有效率、又能调节不同利益的行政工作。黑格尔说:“全体民众的高度智慧和法律意识就集中在这一等级中”[1]310,314。
中间等级成员不依赖私有财产为生,因而不是市民社会的私人;但他们也不能“仅仅为了生计从担任职务”,而要以知识和才能为国家服务。黑格尔说:“官吏的态度和修养”是法律和政府接触到公民个体和行政效力的关键点,“公民的满意和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计划的实施或削弱破坏要求,都依存于这一点”。为了保障公务员的素质,除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还要有市民同业公会依据自己权利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1]312-314。尤为重要的是,
国家的意识和最高的修养都表现在国家官吏所隶属的中间等级中。因此中间等级也是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没有中间等级的国家,因而还停留在低级阶段,例如在俄国[1]315。
在“立法权”部分,黑格尔设计的等级议会,除了包括产业等级和农业等级等拥有财产等级的代表外,还应有政府官员的代表,即中间等级的代表。黑格尔比较英法两国议会制度,法国制宪会议把政府成员排除在外,黑格尔认为是错误的,而英国正确地规定内阁大臣必须是国会议员[1]318。黑格尔反对把议会抽象地当作人民代表的组合。他说:
因为人民这个词表示国家成员的特殊部分,所以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1]319。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作为国家特殊部分的人民指他所反感的平庸的群众甚至“暴民”。黑格尔当然承认他们的权利,但要求群众的权利只有在等级中、因而归根到底在国家制度中才能实现。黑格尔说:“专制国家只有君主和人民”,而合理的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关系”;
相反地,如果不存在这种手段的话,那么群众的呼声总是粗暴的。因此,专制国家的暴君总是姑息人民而拿他周围的人来出气。同样,专制国家的人民只缴纳少数捐税,而在一个宪政国家,由于人民自己的意识,捐税反而增多了。没有一个国家,其人民应缴纳的捐税有像英国那样多的[1]332。
黑格尔法哲学遭到来自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的批判,被视作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辩护状,甚至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准备。我们引用文本证据说明的事实恰恰相反。黑格尔作为法国革命时代的产儿,总结了英法德等国的启蒙成果,他立足于当时德国现实所设计的合理国家制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ane Seiler (trans.).Hegel: The Letters[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
[4] 张世英.黑格尔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827.
[5]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黑格尔政治著作选[M].薛华,译.台湾谷风出版社,1988.
[7][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9.
[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1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40.
“Owl of Minerva” and “Eagle of Gaul”——Hegel and His Age
ZHAO Dun-hua
(Institute of Foreign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ain that Hegel was a completely sympathiz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his youth,w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Napoleon in his middle age and was a repudiate and reflector of the time spirit in his old age by exploring the texts published during his life time and after his death. Being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 in his whole life,Hegel understood the re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stitution gradually and deeply. Therefore,to regard Hegel as a defender of the German autocracy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
Hegel;Letters;Philosophical Method of History;Philosophy;Modern States
2015-03-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056)。
赵敦华(1949-),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级教学名师。
B516.35
A
1001-6201(2015)03-0001-06
[责任编辑:秦卫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