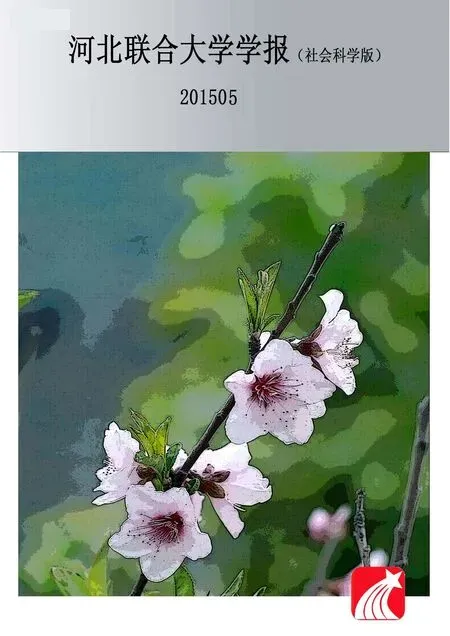莫里森《爱》中的原型探析
苏 娜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长治04601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她的主要作品在国内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其2003年《爱》的出版更进一步引起学者们对“爱”的深入探讨。《新闻周刊》中评论“这本小说像一颗致密的星辰,它精心动魄,又洗练完美,堪称莫里森巅峰时期的成熟之作”。批评家们通常把重点放到本小说的叙事手法、语言特征、文学伦理、社会性别及对作品主题寓意探讨等方面,而对《爱》中体现出的原型探讨却不多见。综观莫里森的作品及其创作历程,我们发现,莫里森的创作受到希腊神话与《圣经 旧约》的强烈影响,《爱》中更是如此。“神话以各种形式存在于黑人文化中。它能提供一种过渡,一种方法,以至于能看清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与避难所。”(Talor-Guthrine 113)莫里森将希腊神话式的人物与旧约中的英雄应用在其悲剧模式的作品中,用疯狂的爱,极度占有的爱与恐惧的爱去探索“爱”在《爱》中的本质。
一、人身监控——米诺斯的迷宫
丝克镇——一个黑人社区,经常出现“警头怪”——民防团——会吃掉那些不循规蹈矩的女人和小孩,是对黑人起居生活的一种人身监控。据桑德勒看,他从小就怕民防团,而民防团现在已经被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取代了。三十年代的警察局只有一名治安官,一名秘书,现在有了四辆巡逻车和八名拿着对讲机的警官负责维护治安。由此可见,白人对黑人的人身监控从民防团到警察再到治安官,随着社会的进步愈来愈紧,黑人似乎身处一座白人国家机器制作的大型监狱之中,无法摆脱,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障碍就像迷宫,无法逾越。
莫纳克街一号对桑德勒来说就像“监狱”。当朱尼尔带着好奇心和不安感来到这座“监狱”中时,“这个房间太亮了,像百货商场。每盏灯——六盏灯?十盏?——都亮着,简直可以和枝形吊灯媲美。”(《爱》25)她觉得这两个女人生活在聚光灯下,被她们之间的黑暗分开,抑或相连。柯西家对这里居住的女人们来说是一种人身监禁。被黑暗的迷宫束缚——“仇恨”。“仇恨烧毁了一切,只剩下仇恨本身。(《爱》34)”因此在留心与克里斯汀心中的迷宫就是仇恨,只有放下仇恨才能收获爱。
柯西度假酒店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是“最美好的时光”的所在。人们谈论国家大事,商讨解决方法。这个地方给予人们鼓励,让人们相信这一切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人们心中存有希望,因为有像柯西这样的人:他的笑脸,他的拥抱,他的体贴,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的不安与骚动,换来了宁静、平和与希望。但当柯西死后,留心接管酒店,梅开始偷窃,女人们开始争吵,L辞去厨师的工作。一切变得混乱。柯西酒店成了女人们争夺柯西遗产的迷宫。人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大打出手,相互算计,将自己陷入柯西酒店的人身监控中。
桑德勒现在居住的社区是经政府批准改造的,有“太多的人造灯光,让月光黯然失色,规划者觉得如果路灯比别处多一倍,黑人就可以少做点坏事。即使月亮又圆又亮,桑德勒也觉得那不过像搜捕逃犯的人远远拿着的电筒。”(《爱》40)黑人社区也在白人的监控之中。
莫里森认为的迷宫即是一座监狱:不只是柯西家、莫纳克街一号、柯西酒店还有上滩鱼罐头厂,柯西酒店,百货商场,监狱,教堂,妓院,朱尼尔上的少管所,克里斯汀的学校等等,甚至整个黑人社区。这些场所无一不受到监视与管制,像米诺斯的迷宫——监狱,没有自由,像病人,囚犯,小学生,工人等。黑人整个民族就像米洛陶的迷宫,始终受到监视,监禁,以致产生像梅一样的疯子,留心和克里斯汀的仇恨,桑德勒的嫉妒,朱尼尔的叛逆等。莫里森通过对黑人所在社区的、生活住所及工作环境的描写暗指黑人内部的不团结,而仇恨心理终归不能走出为自己设置的迷宫与监狱。同时,莫里森的写法似乎像“边沁的全景式敞式监狱”,每一章节都在描述一个不同人物,不同的场所,而每一章节都有一个监视者,人物之间的相互监视,通过L的视角,形成了黑人民族内部一座无形的监狱。
二、精神监禁——帖瑞西士雌雄同体
“从遥远而无法记忆的时代,人类就在自己的神话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男人和女人是共存于同一躯体的。”这样一种心理直觉往往以神圣对称的形式,或以创造者身上具有雌雄同体性这一观念形式外射出来。即赫尔墨斯哲学(Hermetic philosophy)中所说的双性人,即那位“尽管显现为男性,却始终内在地携带着隐于体内的夏娃或妻子的homo Adamicus(亚当式的人)”。(《心理学与宗教》《荣格文集》332)
《爱》中所有女人的崇拜者柯西先生扮演着她们内心之中的“阿尼马斯”这样一个角色,即可以假定为女人身体内少量的男性基因的心理表象,所以显得可能,是因为“在男性的无意识中就找不到同样的形象。”(《心理学与宗教》《荣格文集》332)“阿尼马斯”即animosity是憎怨的意思,它会使正常人产生出“恼怒的絮叨和不可理喻的见解。”阿尼马斯本应是出现在梦中的一个虚无形象,但莫里森刻意将其真实化,成为每一个女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女人们的梦中唤醒阿尼马斯,并让其介入女人们的生活之中,给他们带来困扰,制造喋喋不休、繁琐的争执。
当朱尼尔、留心、克里斯汀、梅、维达和凌霄经历了各自人生中最不为人知,并极力想隐瞒压抑的经历后,她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柯西酒店,在柯西光环的照耀下,仅获得了片刻温暖,便被隐藏并潜伏在各自无意识中的非凡力量所控制。以朱尼尔的出现为导火索,立刻将潜伏的无意识浮出水面,出现在她们的个人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如此,当人们“群集在一起成为民众,那一直潜伏和沉睡在每个人身上的怪兽和魔鬼就会被释放出来。”(《心理学与宗教》《荣格文集》317)因此,这些沉睡已久的怪兽在柯西阳光的照拂与温暖下,伸展双手双腿,蠢蠢欲动,随时随地都会苏醒。蕴藏在柯西加女人们身上的本能中完全陌生的力量就会立刻被召唤出来,因此,科西家女人们陷入了肆无忌惮费尽心机的争执中。
柯西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女人中引发如此多的争执、困扰与梦幻,主要是因为女人们从自己的世界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们解决内心的痛苦与现实困扰的对象。因此她们全都寄希望于柯西,他帮助她们脱离肮脏的工作环境,给予生活费,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等等。因此柯西扮演着女人们内心中的无意识,通过移情现象外化成为“一种反思活动的戏剧性展示”。将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让人们故意谈论并大肆争论,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内在矛盾升华为外在矛盾,从而将其激化,成为了“灵与肉”的冲突:经过漫长岁月的相互折磨,留心与克里斯汀在废弃的柯西酒店大打出手,结果留心不慎摔下楼梯,此时克里斯汀与其和解,梦一般的柯西这时融入了两位的激烈冲突之中——“一种精神和世俗的气氛,这种气氛钝化了道德冲突的尖锐,在遗忘中淹没了所有的精神痛苦”(《心理学与宗教》《荣格文集》334)最终留心与克里斯汀释放了禁锢在无意识中的阿尼马斯即柯西,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恢复了正常人爱的能力。
相反,柯西的给予也是有目的性的,他娶留心,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为妻,即其身上的“阿尼玛”复苏。柯西试图用留心取代他在白人群中想要袖手旁观甚至表面耻笑的那个黑人小女孩,因此,无论是留心还是黑人小女孩都是柯西内心之中的“阿尼玛”,他试图去逃避自己无意识中的罪恶感,因此对留心说只想当她的“监护人”,只想抚摸她,等不及要看她长大。柯西对留心的愧疚之情不如说是在弥补当时他未能救黑人小孩的罪恶感,他面对留心其实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他一直想要逃避却无法逃避的情感需要。事实上,他十分害怕这些需要会使他陷入种种麻烦——例如陷入“婚姻,陷入其他种种责任如爱、献身、忠诚、信赖、感情上的依赖,对灵魂需要的顺从等等”。(《教义和自然象征》《荣格文集》344)而实际上,柯西也的确陷入了各种麻烦之中:与妻子留心婚姻不和,找情人、儿子早逝、儿媳发疯、孙女叛逆、与孙女的朋友结婚、陷入种族困惑等。这些使柯西烦闷不已,只能通过买酒、听喜欢的音乐借以慰藉。他的做法不但没有给自己的精神困扰找到出路,反而更加束缚了他的生活,加剧了他的困扰,给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牢笼,监禁并折磨着自己的精神与身体,与此同时,用自己的方式监禁了身边的女人们。因此无论是柯西还是其身边的女人们都患了“神经症”。要想摆脱精神的监禁,必须释放内心的“阿尼玛”与“阿尼马斯”。
三、拯救信仰——第二亚当
根据荣格,亚当第二是个灵性化了的人,即那个往往被等同于基督的人。最初的亚当是必有一死的肉体凡胎,因为他是用可以朽坏的四种元素做成的,第二个亚当是不朽的,因为他是由一种纯粹而不会朽坏的本质构成的。第二亚当从纯粹的元素中进入到永恒之中。凡由简单而纯粹之本质构成者均可永世不灭。
罗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罗门是“残酷的,危险的,放荡的”。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罗门成长为真正的罗门,破坏了新来的残酷而危险的罗门。真正的罗门唤醒了他内心的勇敢,由原来肉体驱使的罗门回归到有内心驱使的罗门,从这个角度看,罗门正如道成肉身的亚当第二,斡旋在柯西一家人与朱尼尔之间。
柯西死后,科西家的女人们便失去了信仰,从而转向柯西的遗留之物——钱、地契、房产、酒店所有权的争夺,以示对柯西的忠诚。而事实上,这种转变已从精神崇拜转向物质崇拜,本质已发生改变。信仰缺失从宗教上来看是一种罪恶,莫里森通过对身体的残缺来表现柯西家女人们信仰的缺失。莫里森并不像劳伦斯笔下的人物,在描述男性角色时,让其身体残缺到失去某一功能来表现现代文明对人们的摧残,莫里森笔下人物身体残缺表现非常微小,如朱尼尔被舅舅们追赶双脚被卡车轧得“面目全非”,或变成“畸形的脚”;留心手被“一滴滚烫的油从锅里飞出来”溅到手上,变得“像小孩一样小,又像翅膀一样弯曲,像鱼鳞一样”;克里斯汀手上始终带着被认为是偷来的十二枚戒指(每只手的三根手指上各戴了两枚),暗示着她三次从家中逃亡;梅一直戴着头盔保护自己,表示梅失去理智,成了疯子。由此得出,每个人都有缺陷,暗示着失去信仰的黑人民族生病了,需要治疗,因为“信仰死亡了,爱冰凉了,热忱消失了。”(Da Yong Kim.Puritan Sensibility in T.S.Eliot’s Poetry New York:Peter Lang,1994:128)莫里森以此表示,缺爱的黑人民族是畸形的,不理性的,无法自救的,而“爱”就是黑人民族的根本信仰。因此为了拯救本民族人民的精神荒原状态,莫里森用了罗门,一个年轻、勇敢、富有爱心的亚当第二的形象,与柯西年老体衰失去生活目标,失去爱的形象对比,希望年轻一代的罗门们能承担起拯救黑人民族缺乏家庭之爱、友谊之爱、更缺乏民族之爱的弊病,做黑人民族爱的象征。
《圣经 新约》叙述耶稣经常给人看病,确定了神子和人类的关系是一种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是病人,身体自然就有问题,人的病因在宗教意义上源自原罪。莫里森笔下的人物身体与精神或多或少呈现出病态征兆,而病态的身体经历了完整到残缺的过程,实质是从精神的单纯到受世污染之后的蜕变,其身心俱受折磨,莫里森又没将全部残缺不齐的身体抛弃,而是让朱尼尔畸形的脚受到罗门温馨的舔舐,留心鱼鳞般的手终将支撑不住而衰落到地上,克里斯汀与留心在死神的召唤下醒悟过来,莫里森给予人物复活的机会,只要爱能在她们之间如星星之火,那么整个迷惘中的黑人民族也就复活了,会最终得以拯救。
四、爱的回归
身体的监控,精神的监禁,信仰的回归到爱的回归,莫里森通过探索黑人民族进化史中黑人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艰辛历程,试图为黑人寻求出路,同时也提出黑人民族的信仰应当是爱。只有爱才能解救她们,他们于世俗生活中喋喋不休的争吵与无穷无尽的怨恨之中。爱存在于亲情、友情与爱情中,不是工具,不是自私的占有,不是牺牲品,不是欲望的满足。因此,莫里森借用L的叙事向黑人民族展示了自己的观点:爱经得起注视,只要你敢直视它。过去的爱是疯狂的,恐惧的,绝望的,无法收回的,但未来的爱却是恒久的,无法停止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 新约 格林多前书194)
[1]Da Yong Kim.Puritan Sensibility in T.S.Eliot’s Poetry.New York:Peter Lang,1994.
[2]Talor-Guthrine,Danille,ed.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Jackson,1994.
[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文集,第十一卷,心理学与宗教[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4]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5]刘立辉.变形的鱼王:艾略特<荒原>的身体叙述[J].外国文学研究,2009.
[6]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7]圣经·新约,格林多前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8]托尼·莫里森.爱[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9]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