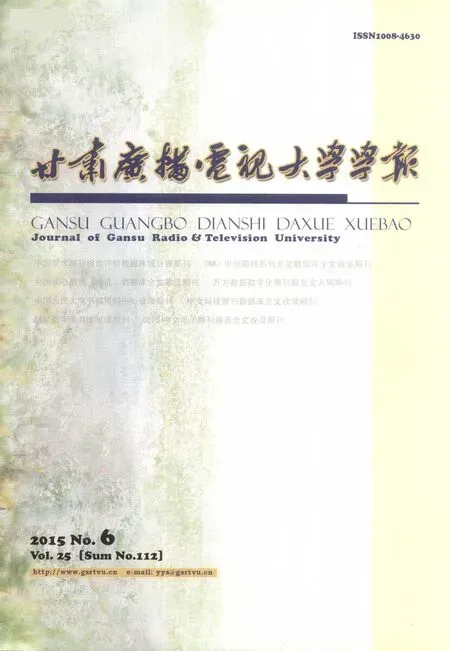略论赵壹及其思想
王德军(天水师范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略论赵壹及其思想
王德军
(天水师范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赵壹生活在东汉后期,此时正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汉代本是儒、道思想并存的社会,文人们一方面对儒家的德政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又非常愤世嫉俗,抨击社会弊端不遗余力。由于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与冲撞,赵壹具有儒、道兼综的思想特征,激愤与平和、慷慨与冲淡成为他人生矛盾的二重奏。赵壹在政治上亦是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赵壹;思想;儒道兼综
赵壹,东汉文学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擅长赋、颂、箴、诔、书、论等。原有文集,后佚。今存作品仅《穷鸟赋》、《刺世疾邪赋》、《非草书》以及《迅风赋》残文。关于赵壹的生平及思想还有许多疑问。
一
《后汉书》卷八十有赵壹简略的传。由此简略记载可知,赵壹生活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党祸不断的时代。他身长九尺,体貌魁梧,美须豪眉,望之甚伟。然恃才倨傲,不畏强暴,对地方恶势力十分愤恨,使他在家乡期间为乡党所排斥,屡屡得罪,几乎死于非命,多亏友人相救,才得以幸免。乃贻书谢恩,又作《穷鸟赋》以喻其事。
后来,赵壹进入政界。光和元年(178年),他以上计吏的身份入京师洛阳。当时接见的官员是三公之一的司徒袁逢。面对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同来的几百个计吏,一齐拜倒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只有赵壹仅拱拱手而已。袁逢感到意外,命令手下的人责问赵壹:“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1](以下未注出处者均见《后汉书》)赵壹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袁逢听后,知道赵壹非同寻常,忙整衣袖下堂来,“执其手,延至上坐”。接着,袁逢向他请教西北边疆问题,赵壹做了精彩的阐述。袁逢“大悦”,环顾在座的人说:“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从相府出来后,赵壹又去拜访大名士羊陟,不得见。乃日,羊陟尚未起床,赵壹便径直走进卧室,来到床前,说:“窃伏西洲,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于是放声大哭,致羊陟手下大惊。羊陟知道赵壹不是常人,忙起来和他谈话,“大奇之”。第二天,他亲自率领大队随从,登门拜访了赵壹。当时的地方官,个个车马壮丽,只有赵壹一辆“柴车草屏”,晚上露宿车旁。羊陟与赵壹言谈直至尽兴,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于是,羊陟与袁逢联手推荐赵壹,一时轰动京师。士大夫们都想一睹赵壹的风采。
而后,赵壹西返天水,路过陕西弘农县时,顺便拜访太守皇甫规,看门人未能为他立即通报,赵壹遂去不顾。看门人急了,赶忙告诉皇甫规。皇甫规听说是赵壹求见,大惊,“乃追书谢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更启乃知已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宁当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责……谨造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皇甫规的人终于赶上了赵壹,但赵壹没有回去,他只是给皇甫规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兄,昭其悬迟……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赵壹在一番客气之后,笔锋一转,以凌厉的笔法,向皇甫规发起声讨:“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 ……诚则顽薄,实识其趣。但关节疢动,膝炙坏溃,请俟他日,乃奉其情……”于是不顾而去。后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终其一生,再未出仕。卒于家。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赵壹在京城期间,先是拜访袁逢,之后又去拜访了大名士羊陟,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羊陟这样的人引荐,根本无法在京城立足。可见,赵壹虽然为人狂傲自负,但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他敢于与朝廷重臣分庭抗礼,虽是性格使然,但恐怕也有显示才华、吸引当权者注意的用心。按理,以出众的才华在京城慑服群臣、威震三公的赵壹,接下来步人政界,一展身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却从此销声匿迹,再未与封建政权发生联系。赵壹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疑问。那么,我们除了从他所处的时代寻找原因外,还可以从他存世不多的文章中窥探其思想。
二
《非草书》是赵壹所作的一篇杂论,收于唐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卷一,首篇。这是一篇非难草书的文章。
草书(今草)在东汉兴起,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出现的隶草、藁草与“趋急速”的实用化完全不同,已由实用进入到审美的境界,取得独立的艺术地位,并出现了崔瑗、杜度、崔寔、张芝、罗辉、赵袭等众多草书名家,草书已成为在士人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书法流派。当时在赵壹所处的西州,草书风行。从赵壹《非草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时人对草书的狂热心态: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这虽有文学的夸张,但基本事实还是可信的。人们为了追求草书艺术可以抛弃仕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大批士子也弃置经学而献身草书。因此,赵壹撰文,其目的是“惧其背经而趋俗”,“非所以弘道兴世”,“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晖)、赵(袭)、息梁(宣)、姜(诩)”。为西州的草书热泼凉水以降温。
首先,赵壹认为草书本非象形文字,“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大约只是在秦之末期,刑罚险峻,法网严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目的不过是“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而“非圣人之业也”。他恪守儒家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认为大篆才是仓颉、史籀等圣人所造,草书只是“删难省烦,损复为单”,“非常仪也”,更非圣人平治天下之事业。但如今却“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赵壹对此很不理解,很不满意。这也使他很惧怕。惧怕者何?“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其次,赵壹还认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又有多大作用?“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字之工拙,也无关宏旨,“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根据汉代的实际情况,说明擅长草书这一书体,既不在《尉律》选拔文吏的条件之内,也不能以此讲经解艺,更与征辟孝廉茂才和升迁考绩等一切正经大事无关,于政治无所损益。因此,不要“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志小而忽大。
赵壹所处的东汉,正是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活跃的时期。他对士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艺进行非难,显然是站在儒家卫道立场上的。在赵壹看来,对草书的耽迷是背经离俗,误入歧途。他要使文人学士重新皈依经学,就有道而正焉:
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 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2]?
建议将精力神思用于“兴至德之和睦,弘大伦之玄清”。这样,“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对赵壹而言,书法只是圣人的载道工具,而当书法独立于经学之外并直接对经学构成冲击时,便提出了批评。当然,他力倡书法对儒学的遵循,似乎在无意间开启了书法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强化了书法的文化品格。
《非草书》是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章。它显然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其目的即在于平息弥漫于整个士人阶层的习草热潮,归根结蒂还是坚持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观点。从中不难看出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背景下赵壹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和孤傲的性格。
三
《刺世疾邪赋》是赵壹另一存世名篇。
赵壹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后期最黑暗腐朽的时期。帝王昏庸无能,外戚与宦官相继成为政权的主宰,他们录用了大量的徒子徒孙,通过非法渠道进入政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贪得无厌、打击异己。成千上万的正直官僚、知识分子、太学生在“党锢之祸”中被屠杀,酿成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冤案。真正的人才仕进之途被彻底堵死了,社会千疮百孔。
《刺世疾邪赋》对这种丑恶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踽名势,抚拍豪强。僵蹇反俗,立致咎殃……邪夫显进,直士幽藏。”[3]434-435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那个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社会现实,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痛心地指出,世风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3]434-435。皇帝昏庸腐朽,外戚、宦官为所欲为,“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3]434-435。在这种黑暗统治下,“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虽然“安危亡于旦夕”,仍然“肆嗜欲于目前”。这不等于是“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吗?显然,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日暮穷途、无可救药的地步了。面对丑恶的现实,作者感慨万分,他悲痛地说:“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表达了与当权者决不妥协的态度。作品篇末假托“秦客”、“鲁生”的两首小诗,尽情地表达了义愤: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藉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固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3]434-435
《刺世疾邪赋》是一首政治抒情赋,题目本身如刀似枪,内容更是针针见血。它一反汉赋 “体物写志”、“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僵死特点,转而变为笔势凌厉、措辞尖锐,意气风发、淋漓尽致的风格。并以它独有的思想风采,成为古代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与《非草书》站在儒家卫道士立场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壹的这篇《刺世疾邪赋》一反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全然不顾儒家所谓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批评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思想之鲜明、气势之凛然,在文学史上独标一格。甚至在整个封建时代,就对专制统治认识的深刻程度,揭露的尖锐程度而言,赵壹的抨击力度也是少有人能够超越的。这一点颇有老庄愤世嫉俗的一面。老子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4]326,庄子抨击世俗,更是不遗余力。道家虽然主张清静恬淡,胸中却怀着济世利物的主见。而且自命甚高,又不愿与世同其波流,因而欲进取而无门径,多被拒之于庙堂之外,即使进了庙堂也被挤在一边,不能发挥才智。这时他们的逆反心理便被激发起来,变而成为当权者的对立面。由于他们洞悉世情,深知各种流弊之所由,因而揭露世态、鞭挞时弊往往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赵壹有在京城慑服群臣、威震三公的出众才华,所以他对自己怀才不遇、不得升迁的尴尬,能够一语中的:“佞谄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指出统治者道德沦丧、忠奸倒置,社会正气已荡然无存的现实。在开篇,历数五帝、三王、春秋、战国、秦、汉每况愈下,这种历史退步论,旨在抨击现实之“怨酷”。而这与老庄借上古“至德之世”来表达对现实的愤世嫉俗之情何其相似。
赵壹的愤怒有如瀑布之倾泻,而其可贵之处却在于激愤之余的冷静思索。在尖锐激烈中最见深度,他所指出的世风败坏之原因就在于“执政之匪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这显然是对“温柔敦厚”传统的大胆超越。赵壹才华之超拔,思想之深刻,批判之凌厉,文风之恣肆,都有庄子之风。
老子以愚拙自处,以自隐无名为务,不求闻达。庄子辞卿相之位而曳尾涂中,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这些都成了后世许多文人师法的典范。封建时代的文人读了书,都想在官场上施展身手,以实现理想。而一旦沉屈,便会消沉起来,直到看穿看透之时,才会与之决绝。很多人都走过由士子到官场,又由官场转而退避山林田园的路子。赵壹最初也是进都入京,本想建功立业,施展才华,事实上他也得到羊陟与袁逢的联手推荐,一时轰动京都。然而,为什么他又不顾而去了呢?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其实,答案是可以找到的。在赋中,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生活择抉,宣称“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不与当权者妥协,决心为自己认定的真理而献身。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从京城回到家乡后,公府十次征聘,他都断然拒绝。这足以证明他的不同流俗、洁身自好和对现实的厌恶。至于赋中的“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 则表示了他对儒家的德政、法家的赏罚的否定,而向往“无为而治”的尧舜时代,显然接近于道家的政治理想。而在篇中揭露世态,也多取法于《庄子》。赋中“舐痔结驷”[5]828、“咳唾自成珠”[5]410等,语出《庄子》之《列御寇》和《秋水》,“被褐怀金玉”[4]326语出《老子》第七十章,以此可看出他受老庄影响之深。
四
汉代本是儒、道思想并存的社会。汉初,黄老思想是治国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失势,接着黄老思想便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它与儒家合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使得文人们对儒家的德政充满期待,故对现实政治颇多建设性意见,《非草书》便是典型;另一方面它又与庄子思想合流作为儒学的异端而存在,当社会处于衰乱、江河日下的时候,文人们也同庄子一样,非常愤世嫉俗,抨击社会弊端不遗余力,而且特别尖酸辛辣。这种特殊风格在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就是其代表。
总之,正如许多乱世中的仕宦文人一样,赵壹具有儒、道兼综的思想特征。正如陶渊明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飘逸,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6],由于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与冲撞,使得赵壹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境界。激愤与平和,慷慨与冲淡成为他人生矛盾的二重奏。青壮年时猛志逸四海的赵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境,于是他在诗文中做了激切沉痛、针针见血的“刺世疾邪”。这既是时代情结的反映,也是赵壹理想世界与现实相冲突的结果。于是他由刺世转而与世道决绝,不顾而去,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终其一生,再未出仕。回到西州老家的赵壹,虽无历史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想,他的心灵一定是与鸡鸣狗吠、墟烟远村的田园风光相契合了。“逸鹤任风,闲鸥忘海”,碧空白云,舒卷自如,濠梁观鱼,曳尾涂中。什么“魏阙之下”、“庙堂之高”,对于此时的他,不过是“鸱之腐鼠”罢了。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770-772.
[2]叶郎.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秦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10-511.
[3]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70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04.
[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5-11-10
王德军(1964-),男,山西汾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I206.2
A
1008-4630(2015)06-002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