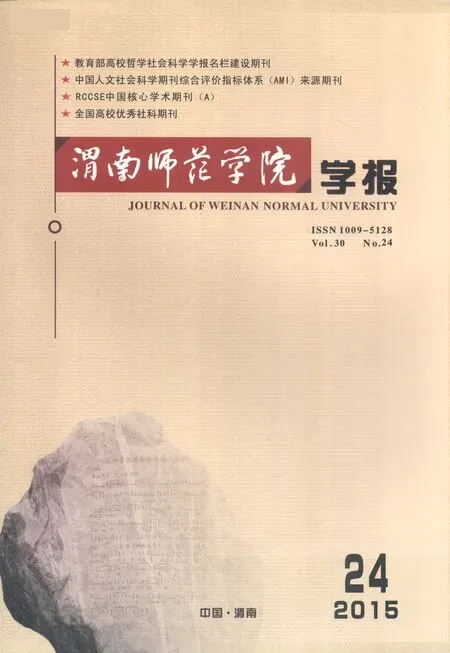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原型探究
苏 焕 莉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原型探究
苏 焕 莉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中最受公众欢迎的田园派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位用“原型”写作的诗人。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利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出现的各种原型意象进行阐释,通过原型理论对弗罗斯特的田园诗歌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弗罗斯特诗歌与原型之间的关系,以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人类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力量。
弗罗斯特;荣格;原型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是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中最受公众欢迎的田园派诗人,虽然他成名较晚,但其一生著述颇丰,共出版10本诗集,晚年还写过2部假面戏剧,曾4次荣获普利策诗歌奖,被称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民族诗人。在美国的现代诗歌史上,弗罗斯特堪称一位“原型写作”的诗人。本文拟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利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对弗罗斯特诗歌中出现的各种原型意象进行阐释,通过原型理论对弗罗斯特的田园诗歌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弗罗斯特诗歌与原型之间的关系,以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人类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力量。
一、原型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原型”是一种原始经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更深层结构。荣格的原型理论就是集体无意识理论,集体无意识是构成原型的基础。荣格曾说过:“人的无意识同样容纳着所有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行为模式,所以每一个婴儿一生下来就潜在地具有一整套适应环境的机制。这种本能的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始终存在和活跃于人的意识生活中,如果把这种无意识人格化,则应该设想为集体的人,这样既结合了两性的特征,又超越了青年和老年,诞生和死亡,并掌握了人类一二百万年的经验,因此几乎是永恒的。”[1]25因此,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遗存。荣格认为,“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的虚像(Virtual image),已经先天被他具备了。”[2]111由此可见,原型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用海岛作比喻的话,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面下由于潮汐运动显露出来的就是个人无意识,而隐藏在深海之下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荣格被认为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他在《心理学与文学》一书中提到: “原型的影响激励着我们(无论它采取直接经验的形式,还是通过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现),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3]86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其著作《金枝》中阐述了人类很多古老的仪式和习俗,将诞生、发育、死亡与复生这些生命的循环加以描述,成为原型象征的母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甚至将《金枝》作为神话——原型批评的奠基之作。
二、弗罗斯特“原型写作”的原因
弗罗斯特于1874年出生于西海岸的旧金山,是一位以描写新英格兰地区出名的乡土诗人。他的一生颠沛流离,直到近40岁的时候才迎来了事业的转折期。弗罗斯特所处的时代背景从现代主义跨越到后现代主义,期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席卷全美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喧嚣与浮动并存,理想与堕落并行。与此同时,弗罗斯特在成长中也经历了生存与死亡的多重考验。他的父母都是新英格兰人,家庭生活并不富裕,11岁时,父亲因肺病去世,几年后,妹妹又得了伤寒病,弗罗斯特只好退学,挣钱养家。他当过教师,做过各种杂活,在空闲的时间里,一边专心创作,一边研读莎士比亚。弗罗斯特热爱大自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农场住过几年,做着农夫的工作,可是他并不是称职的农夫,他一边耕种,一边写诗,微薄的收入加之此时诗作也默默无闻,身心俱疲之下,他带着全家去了英国,在英国安顿下来,一战爆发后又带着全家返回美国。弗罗斯特丰富的人生体验,使他的诗歌内容深刻,充满智慧。弗罗斯特的诗集《一个男孩子的意愿》《波士顿以北》《山间》《新罕布什尔》《西流的小溪》《山外青山》《见证树》《理智的假面具》《慈悲的假面具》《绣线菊》《林间空地》和大自然息息相关,将自然与人类融为一体,以自然为载体来探索人生的哲理。诗人热爱大自然,加之有农场生活的切身体验,他早期的生活经历正是他用“原型”写作的重要基础。弗罗斯特的诗歌分为短篇的抒情诗和长篇的叙事诗。短篇的抒情诗将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赋予深切的情感,在诗歌中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怀旧情感,批判了现代的城市文明。如《摘罢苹果》(AfterApple-Picking)、《白桦树》(Birches)、《火与冰》(FireandIce)等。长篇的叙事诗多以对话体出现,通常以描述邻里之间的关系为主,如《雇工之死》(TheDeathoftheHiredMan)、《家葬》(HomeBurial)等。弗罗斯特复杂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显现出原型的特征。同时他对城市主题的诗歌也充满了谴责和讽刺。由于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战争的侵袭、 城市文明的加快、人际关系的疏离等都使诗人的精神遭受现实的无情冲击,诗人的情感借助自然元素的原型倾泻而出。“原型”中涉及大自然中的各种元素,如土地、树木、黑夜、白雪等等,经过长期的传承,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通过人类的无意识进化心理,集聚了人类的原始经验,逐渐形成原始的“原型”意象。由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积累,使这些原型的意象成为真实的象征。
三、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原型研究
荣格认为:“艺术家不是要观察和深入生活,反倒是要从现实生活中退缩回来,努力发掘自己的内心,从而沿着精神发展的方向,返回到其最初的发源地、人类灵魂的故乡——集体无意识,只有从这儿, 艺术家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艺术灵感,获得创作冲动和激情,也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3]20弗罗斯特在诗歌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情感,他总是借助大自然中的一些意象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并从大自然的元素中体会生命的原始情结。诗人常常将林子、路、草、镰刀这些自然界的元素作为诗歌的主体,因为这些元素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发展和死亡。在他最著名的诗歌《一条未走的路》(TheRoadNotTaken)中,“两条路岔开在黄叶秋林,遗憾我不可能同时都走,遗憾我只是孤身一人……”《雪夜林中停留》(StoppingbyWoodsonaSnowyEvening) “这是谁家的树林我想我知道,尽管他家住在村子里,他看不见我在这儿停住并观瞧,他的林中雪栖树枝落满地……”[4]200《刈草》(Mowing)“林子边上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声音,那是我的长镰刀在对着大地低语。它在低语些什么?我自己也不很清楚;也许是说些关于太阳很热吧,也许,是说些关于缺少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它只低语而不大声说话。”[5]83他钟情于乡村风物,笔触选择描写田园生活,无论是他诗歌中的大地,还是一条小路,或者只是一堆柴草,这些对于人类原始社会的生存都有着血肉关系。而这些自然元素组成了一个乡村小镇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是永恒的、不朽的,它折射出人类心灵中最深邃和最广阔的东西,也反衬出一种悠远的历史感。而树林、大地、白雪、小溪、池塘这样的自然物质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就像有一股暗流将诗人的意志控制,这样的暗流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诗人创作的时候总是受到这样一股原始力量的召唤,在民间生活中寻找原型的主题。其中 “树木”原型总是在诗人笔下反复出现,《一条未走的路》中黄色的树林、《摘苹果之后》中的果树、《雪夜林畔》中的树林,《见证树》《白桦树》《圣诞树》《我窗前的树》等树木的种类也各式各样,有果树、桑树、白桦树、樱桃树等等。诗人对树木的热爱是因为树木对人类有特殊的意义。人类在远古的丛林中生活,树木是生命之本。《金枝》中也曾着重刻画人类对树木的崇拜,人类有许多神圣的仪式是在大树下进行,这种对树木的崇拜经过代代积累,成为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力量,树木与人类的关系密切,诗人在其诗歌中反复植入树木,不仅表达了诗人的直观感受,更是传达一种悠远的历史气息。
诗歌中也明显反映出诗人对现代城市文明生活缺乏适应能力,远离了城市文明,诗人沉溺于内心生活,返回集体无意识中寻找能够满足他精神需要的东西。如名作《一条未走的路》,黄色的林子中有两条路,我该走哪一条呢?诗人内心的情感在沉淀、发酵,黄色的林子寓意着秋天,在秋天,诗人在岔路口思索人生,这种情境唤醒了诗人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人类在面临困境时可作出的种种选择,同时诗人似乎也在抱怨无法作出更多更好的选择。“很久很久以后在某处,我会叹息着把这事情讲:两条路岔开在一林,我未踟蹰——选择了一条人们较少走的路,而这选择竟决定了人间与天上......”[4]200人类从诞生到发展到死亡这样一种类型的圆圈意象是人类的梦与幻想的基本模式,是原型的主题之一,生命的能量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无限循环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演绎了生命能量的一种循环,人类诞生于大地,在大地的各种环境中艰难抉择,生命终结时回首往事,诗歌中表现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仿佛让我们走入了一个原型的世界。
弗罗斯特主张“诗歌以欢欣开始,以智慧结束”。[6]126他的诗歌创作来源于大自然,除了描写这些自然物质外,诗人的笔下还出现了一批劳动者的形象。如《规矩》中的收草工,《割草》中的割草工,《熄灭吧,熄灭——》中的拉锯少年,《雇工之死》中的赛拉斯,有《摘苹果之后》中的老农,《收落叶》《修墙》《泥泞时候的两个流浪者》中的体力劳动者等等。追溯人类经验,这群劳动者仿佛从远古的丛林中走出,依靠自身的体力劳动,演绎着生命的恒远流长。这些劳动者就是“原型”的本身,人类的劳动从诞生之时就开始了,为了生存,无论是远古的丛林还是现代的都市,这些劳动者体现着人类从懵懂走向文明。《创世纪》中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7]7劳动者是乡村生活中的主体,从远古到当今,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开始。真实是劳动所知道的最甜美的梦。[5]83诗人在诗歌中唤醒了人类对劳动者的最原始的情结。
弗罗斯特对乡村生活的感情和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奠定了他原型写作的基础,而他对乡村生活的厚爱,使他偏爱于乡村题材,诗歌中描绘的乡村画面,大地、树木、农舍、河流还有劳动者,他笔下的现实世界完全是经过了诗人浪漫主义情怀的渲染,将诗人现实的情感经过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使诗人更深刻地思索人生,思考集体无意识原型。诗人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现代喧嚣的生活产生反感,内心渴望回归,寻找真正的自我,诗人向往最初的原始状态,古老的原始村庄在诗人的脑海中形成一副和谐美好的画面,人类最初的生活场景就是诗人笔下构筑的乡村世界,经过长期的文化沉积,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象征着人类向自然本性的回归,不能不说诗人的创作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控制。原型具有无穷的生命力,集体无意识的本能使诗人对原型写作情有独钟, 他诗歌中出现了各种原型意象。荣格强调,“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享有绝对的创作自由,在创作过程中,无论自觉与否,始终不免要受到各种制约。”[3]21荣格所说的制约其实就是无意识原型的制约,在弗罗斯特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原型的象征世界,大地、河流、树木、小草、小木屋等等这些诗人构建的象征世界中有着强烈的循环往复的心理暗示,弗雷泽说过:“大地外表上经历一年一度的巨大变化强烈铭刻在世世代代的人类心中,并激发人们去思索:如此宏大如此神奇的变化出于什么原因呢?”[2]429大自然的这些普通景物的变化,牧场、落叶、小鸟等在人类的心理中有了强烈的象征模式,对于生命来讲,它暗合了人类集体的经历和记忆,是人生集体的缩影,人生既是空幻的也是真实的,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象征描写,来展现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形态。从摘苹果的老人、补墙的好邻居、勤劳的顾工塞拉斯、家葬中的小夫妻、可怜的拉锯少年到趴在万能花上的蜘蛛、能打秋千的白桦树、桌布上的小蚂蚁、树林里小路、下雪的夜晚等等,这些场景中有些是劳动的画面,有些是夫妻间的闲谈和争吵,有些是乡邻之间的对话,有些是大自然中静谧的景物,还有些是人生哲理的总结,无论哪种场景在弗罗斯特的笔下总是带有原型的思考,在人类的潜意识中不断体现,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形态,这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段原始的记忆,人类在这样的集体中生存和一代代繁衍。
四、结语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生给诗坛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他的诗歌跨越了时空,他笔下的世界是人类从诞生到成年的一段集体的记忆,诗人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山山水水,而是表达一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诗人用丰富的想象构筑成理想的幸福乐园,用典型的原始意象传达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无论时空如何转换,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无法更改,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之一,他在诗歌中用一种人类历史的情感去表达一种追本溯源的历史情怀,以便读者更好地去了解他的诗歌价值。
[1] [瑞士]荣格.荣格文集[M].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2]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李正栓,陈岩.美国诗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张曙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 金莉,秦亚青.美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7] 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7.
【责任编辑 贺 晴】
An Archetypal Study of 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
SU Huan-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Robert Frost is the most popular pastoral poet in American modern poetry, as well a poet who used archetypal criticism to write poem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some various archetypal images in Robert Frost’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with Carl Jung’s theory, and reinterprets Frost’s pastoral poetry through archetypal criticism,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ost’s poetry and archetype, so that readers can deeply feel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of the human hearts.
Robert Frost; Carl Jung; archetype
I712
A
1009-5128(2015)24-0058-04
2015-06-01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在高中外语教师专业成长中的应用研究(SGH140764);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专项项目:美国现代派诗歌研究(11YKZ049)
苏焕莉(1978—),女,陕西澄城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