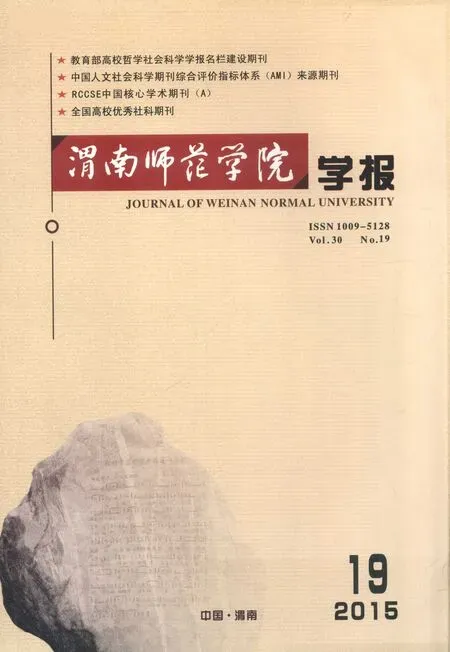从《左传》《史记》看楚庄王形象演变的文化意蕴
张 佳 玉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左传》《史记》看楚庄王形象演变的文化意蕴
张 佳 玉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楚庄王是春秋时期的一位贤明君主,经历不同史学家的记录,其形象逐渐发生变化,《左传》中他是“礼”的模范,《史记》中他则是“义”的楷模。其形象由“重礼”到“尚义”的演变,一方面与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价值取向有关,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时代主流文化的变迁,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人们精神文化中的不足,而这正是典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楚庄王;《史记》;《左传》;礼;义
王立群先生的《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提出历史四层次说:“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1]其中“记录的历史”指“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1],比如《左传》和《史记》。但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并非百分百可靠,不能真正再现历史全貌,而且历史事件的本身以及历史文献又太复杂,史学家在写历史时必然有所选择,“选择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1]。因此,不同历史学家手中“记录的历史”便存在一些差异,正如《史记》和《左传》中的楚庄王形象。
一、《左传》记录中的楚庄王:明礼重视德
楚庄王熊侣是春秋五霸之一,是楚国最有作为的君主,楚国在其统治下不断强大,最终打败晋国,称霸中原。楚庄王的事迹在《左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见于鲁文公十四年到鲁成公二年。《左传》中楚庄王最突出的特点是遵礼重德,在春秋这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始终能遵从“礼”的要求,符合《左传》作者的政治观念。
宣公十一年冬,陈国夏徵舒杀其君发动叛乱,楚国作为盟国率领诸侯诛杀夏徵舒,平定陈国内乱。楚庄王非常得意,认为自己站在“礼”的一方,因此当申叔时归国后不称颂其功绩时,楚庄王非常不高兴,甚至派人去责让申叔时,“夏徵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2]464楚庄王沾沾自喜时,申叔时泼了他一头冷水,指出他的行为无异于“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名义上讨伐陈国夏氏之罪,最后却贪图陈国之地,趁机占有并将其降为自己的一个县,这比夏徵舒的行为更恶劣。楚庄王听后十分诧异,“善哉!吾未之闻也”。当时楚处于蛮夷之地,虽自称黄帝之后,受文王封地,文化却与中原文化存在很大差别。楚成王时期虽已和中原各国有所接触,然至庄王时,对中原文化吸收和接受的程度总体仍不高。楚庄王能听从申叔时的意见依“礼”让出已到手的土地,复封陈,并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符合周礼。这对于一直轻视楚国不懂礼的中原诸侯而言,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楚为蛮夷,尚且尊礼,而一直以尊礼自居的中原诸侯却不断做出违礼的事情,《左传》作者十分痛心,因此详细记录此事,称其有“礼”,一方面赞扬楚庄王重礼,一方面劝诫诸侯大夫需尊礼重礼。
楚庄王不仅对“礼”非常看重,也很注重“德”,突出地体现在晋楚邲之战前后。宣公十二年,晋楚在邲交战,楚国获得全面胜利,这是楚国分割晋国霸权,称霸中原的重要转折点。邲之战前,楚国因郑国背叛盟约贰于晋,因而出兵郑国,郑伯肉袒牵羊请罪,左右之人皆认为应趁机灭亡郑国,庄王却力排众议赦免郑国,理由是“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2]468郑伯身上的谦恭、信义、民本思想是他看重和赞扬的,因此释放了郑伯,并与郑国重新订下盟誓,这一举措赢得了郑国的诚心服从。
“邲之战”结束后,大臣潘党建议楚庄王用晋国士兵的尸首作“京观”,以显军威、明战功、示子孙。他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提出“止戈为武”的理念。何为武?止戈即为武,楚庄王认为真正的“武”是不使用武器(武力)而能到达“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他强调化干戈为玉帛,以德服人,反对乘人之危肆意动用武力,以武力威胁诸侯,这样自己本身就是强暴,何谈禁止暴乱,使人民安居乐业。当然,他的“武德”观并不是完全放弃使用武力,真正的“武”应该是用在伐不敬、诛乱首的地方,并且当适可而止,不做大面积的屠杀。因此,在对晋之战中,他并未继续对晋国用兵,选择罢兵归国。
楚庄王一生的重要事迹当然不只这些,这只是《左传》作者大力描写和着重突出的,里面蕴含着作者比较鲜明的思想和评价,可以发现作者极力强调、着重突出的都是庄王明礼重德的一面。虽然楚庄王也有违礼的行为,如楚庄王问鼎一事,但春秋时期哪个诸侯国君没有做过,作者虽有记录,却没有给予十分明确的有关“礼”或“非礼”的评价。当然不否认这是曲笔,但亦可从中看出《左传》作者对楚庄王这一举动并不是非常反感,因为楚庄王最后还是听从了王孙满的话退兵了,并不十分过分。
二、《史记》记录中的楚庄王:崇义不贪利
与《左传》旨在弘扬“礼”不同,司马迁在塑造庄王形象时更关注其内在的品质“义”。“义”是一种传统美德,常与“利”相对,指为了别人可以放弃或者让出自身利益。如吴太伯,为了能让周文王姬昌登上王位,与其弟仲庸让位三弟季历,出逃至荊蛮。他们为了本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义,毅然放弃自身利益,受到司马迁的大力推崇,将他们列入世家,并列为第一。楚庄王身上同样闪耀着这一光辉,这正是司马迁作《楚世家》的主旨,即“嘉庄王之义”[3]3988。
围绕这一主旨,司马迁书写楚庄王主要事迹时并未照搬《左传》材料,而是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认知对《左传》原有史料进行适当删减、改动,用聚焦的叙述方式,不断聚焦庄王之“义”,以便更加突显人物传记的中心。以楚庄王十六年复陈一事为例,司马迁保留了《左传》中楚庄王占陈又复陈的基本事实,只将申叔时的话做了细微修改,把“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2]464,提炼为“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3]2041,明确指出楚庄王县陈之举是贪利不义的,如果放任,楚王将失义于天下,不可能成为天下霸主,楚庄王听后马上恢复陈国。孔子读到这一段历史时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非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4]44(《孔子家语·好生》)《陈杞世家》里也引用了这句话。在孔子看来,楚庄王把义看得很重,将千乘之国看得很轻,因此赞扬他。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谏言,不可能表现出楚庄王的道义;没有楚庄王的贤明重义,他不可能接受申叔时的谏言。楚庄王能把国家间的“义”看得这么重,放弃既得利益,在那个动乱纷争,大国兼并盛行的时代里,确实值得赞扬,不失其春秋五霸的美誉。
楚庄王重“义”并不意味排斥“利”,“利”与“义”亦不是绝对地对立。《周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人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5]9“利”,义之和。“义者,宜也 ”(《中庸》);“义者,正也” (《墨子·天志下》);“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所谓“义”,指人的行为要合于仁的原则,礼的规定。换言之,凡是合于仁的原则规定的利,就是真正的“利”。在义利问题上,先贤所讲的“义”,本身就包含了正当适宜的利益因素,合情合理的利就是义,公利公益更是大义。楚庄王在争霸道路上坚持不利人之机、安人之利、以为己荣,不肆意兼并、奴役小国,始终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2]475为宗旨,以期恢复礼乐之传统,使天下无战事,人民皆安乐。在对郑、宋的问题上,楚庄王也没有肆意采用暴力征伐,灭其国,据其地,而是以“义”感之,使之成为同盟。楚庄王十七年,面对郑襄公的献地投诚,他力排众议,拒绝接受郑国的土地和人民,保留郑国原有社稷。他认为此次围郑的目的是为了伐不服,“今已服,尚何求乎?”[3]2122(《郑世家》)土地之利并不是他的目的,而且他认为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3]2041一个重视人民的国君必是有为之君,必能使其子民生活安乐、国家昌盛,何苦灭其社稷,使百姓流离失所!楚庄王以义为重,不贪图他国、他人之利益,而且非常重视黎民百姓。在后来的对宋之战中,感于华元之诚、百姓之苦,罢兵而去。
三、楚庄王形象演变的文化意蕴
楚庄王是春秋时期一位贤能的君主,他的形象在《史记》和《左传》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左传》关注外在的“礼”,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雄才大略且明礼重德的君主,他奉“礼”而治,是一个标准的霸主形象;司马迁则融合自身认知,对楚庄王进行重新定位,更关注其内在的品质“义”,强调其凭“义”而为。为什么两者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原因在于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本身存在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反过来说,偶像的树立和彰扬,正是由于它特别缺乏的缘故,如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6]134《史记》和《左传》对楚庄王形象关注点的不同,表面上是司马迁个人价值判断、思想观念等造成的,实际上恰是时代主流文化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变化在文学中的投射。
(一)“礼”的僵化
“礼”,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包含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属性。政治制度的“礼”,维护封建统治,强调“名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道德的“礼”,是人们行为的标准和要求。“礼”在西周社会高度发达,有严密的体系,从大处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入,利后嗣”[2]43,从细微处看,揖让、周旋都属于“礼”的范畴。至春秋时,周王室威信扫地,政由霸主出,“礼”的贯彻实施毫无保障,愈来愈被歪曲、被遗弃,礼坏乐崩成为时代主题。在此情况下,《左传》作者感于时代的动荡、诸侯的混战、制度的混乱,思慕西周和平稳定,天下共主的繁荣景象,认定若能恢复西周礼乐制度,每个人皆按“礼”的要求行事,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天下便能恢复和平安定的局面。因此,《左传》作者极为渴望恢复礼乐制度,笔下的人物言必称“礼”,凡合乎“礼”之规范的,便会得到君子的褒奖,而违“礼”的举动,则受到谴责,甚至亡国败家丧身,以此警醒世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礼乐制度”最终被时代丢弃,成为明日黄花,并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原有礼制经历春秋战国以及秦的破坏多已消亡。汉武帝时,重新组织学者建立了新的礼仪制度。董仲舒又兼收阴阳五行、道家等思想提出“德主刑辅”“阳德阴刑”的思想,将礼与法融合。这一举动促进了礼的法化,即用礼来解释法,凡合礼的即合法,凡礼所不认同的就是违法,通过法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礼的全面实行。一切行为规范都被政治化、法律化,成为不可破的硬性规定,必须遵守。“礼”虽再次取得了支配人们生活的权力,却失去了原有之义。变异的“礼”成为控制百姓生活和思维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并且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们像对原始宗教一样盲目崇拜它。“礼”不断被功利化、虚伪化,带着“礼”的面具做违礼事情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正是史公最厌恶的一点。他认为现实中真正依礼行事的人几乎没有,因而《史记》中对“礼”的强调便淡了很多。
(二)“义”的匮乏
“礼”虽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但揭开其华丽的外衣,内在却已腐朽不堪。物欲横行,人们都已被“利”腐化,“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追名逐利成为每个人行动的最终原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3]3924。“利”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应有的温暖和关怀,儒家倡导的仁义思想反而成为追名逐利者的遮羞布,极具讽刺意味。因而,楚庄王能够因申叔时一言而放弃县城,而且能体恤百姓疾苦释郑释宋,在对外战争问题上从不肆意贪图他国土地,凌虐他国人民,始终坚持仁义,在武力征伐、兼并盛行的时代极为珍贵。楚庄王对“义”的坚持在当今时代同样具有榜样意义。
“利”的肆虐扭曲了人性,丑陋不堪,司马迁重新塑造楚庄王形象,正是源于对追名逐利的社会现状的批判。《孟子苟卿列传论赞》云:“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3]2833黄履翁评论道:“昔太史公读孟子书,至利国之对而为之废卷太息流涕而言之。彼盖有感当时功利之徒,而深信孟子塞源之论也。”[7]528司马迁对于孟子的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应,除了作为史家的职业责任感外,更多的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感触。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为了获得汗血宝马而发动数十万军队,以致“天下骚动”,这都是司马迁亲身经历的。然而,最为惨痛的莫过于“李陵之祸”。“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乃至有“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8]2729,司马迁痛恨这些小人只会锦上添花或者落井下石,只有他为李陵仗义执言,却触犯了皇帝,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8]2730,最终惨遭酷刑。司马迁对世态炎凉、逐利弃义的体会不可谓不深。惨痛的个人遭遇使司马迁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对楚庄王形象的塑造正是源于如斯现状,因而更加突出“义”,为的就是弘扬这一传统思想,重申传统文化中的“崇让”精神,正如尧舜禹禅权,吴太伯禅国,宋襄公始终恪守仁义。
楚庄王在《史记》和《左传》中都被树立成模范的君主形象,前者是能因“义”而弃千盛之国的君主,后者是重“礼”的模范霸主,两者间的些微差异反映的不只是史学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更折射出了两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意识的变迁以及当时人们精神文化方面的缺失。因为,偶像的存在,正是为了弥补现实的不足,犹如现在对所谓的好人好事的表扬,正是由于这些事迹极其稀罕的缘故。另外,史学家本身的使命是使人能从历史事迹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达到明得失、知兴衰的目的。故而,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史记》和《左传》在树立楚庄王形象时,很自然地融入了当时社会普遍所需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楚庄王形象的演变,正是春秋到汉代文化变迁的一个佐证。
[1] 王立群.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1,(6):147-154.
[2]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三国]王肃.孔子家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33.
[5]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宋]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M]//四库类书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朱正平】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Image Evolution of the King Zhuang of Chu Based on Zuo Zhua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ZHANG Jia-Yu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King Zhuang of Chu was a great empero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xperienced the different records by different historians, his image had been changed. In the book of Zuo Zhuan, he is a model of “propriety”, but in Historical Records, he is a model of “righteousness”. The evolution of his image has two reasons. On the one hand, it’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 the culture of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flected the reality in people’s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society, which was the cause of the model.
King Zhuang of Chu; Historical Records; Zuo Zhuan; propriety; righteousness
K234
A
1009-5128(2015)19-0072-04
2015-04-15
张佳玉(1990—),女,河南新乡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