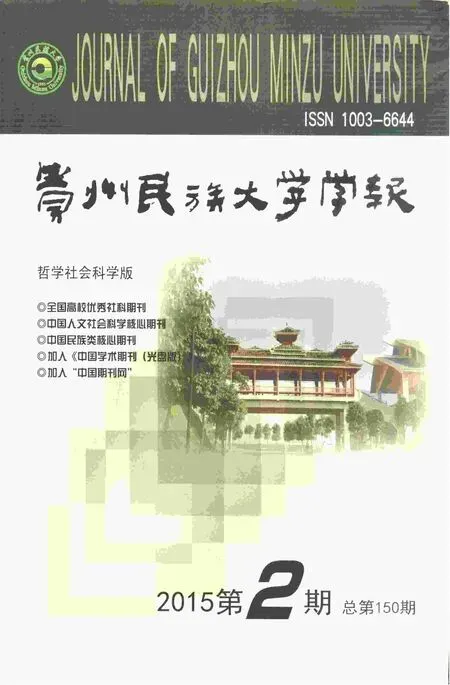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范式探析①
吴献举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成就世界瞩目。但与此不相称的是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外民众眼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和改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内部及外部公众对该国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国家形象优劣不仅会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影响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这一课题,不仅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且也成了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在众多研究中,总体的研究趋向呈现实践性导向,即重视具体事件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如全球性事件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譬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媒体产业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如电影、纪录片等;具体行业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如出口产品质量问题等。[1]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理论厚度不够,要么找一两个国外媒体分析一下有关涉及中国的报道(媒介中的国家形象),要么简要分析国家形象建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等。这些分析由于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学理性不足。国家形象研究涉及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因此,研究国家形象问题,除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外,还应借鉴国际关系研究的有关成果。
目前,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有三个大的理论流派:结构现实主义、自由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相应地,国家形象研究也有三种理论范式: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和建构主义理论范式。“范式”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特定科学的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代表该研究者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价值、信念、技术等构成的整体”[2]P378。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从事国家形象研究的研究者所应遵从的世界观与行为方式,它是国家形象形成、发展、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研究者在不同的理论范式指导下就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形象观,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会迥然不同。
一、现实主义理论范式
现实主义理论曾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达40年之久,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流派。在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摩根索构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而沃尔则兹完善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卡尔把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想主义,一类是现实主义。这样的分类,引发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的理论大辩论,即卡尔的现实主义理论挑战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理论论战。卡尔在批判理想主义理论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道德的虚幻性、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根本冲突性。摩根索在代表作《国家间政治:权力的斗争与和平》中提出了“以权力定义利益”等现实主义六原则,形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基本构架。[3]P4-37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权力,他将国家的所有行为动机归结为一点: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为此,他提出了为维护或增加权力而显示它所拥有的权力的“威望政策”。他认为,炫耀武力是一个国家使自身拥有的实力给别国以最突出印象的最重要手段。可见,摩根索理论中的国家威望或者说国家形象,就是被他国所认可(意识到)的军事优势,或者说是他国心目中的“实力名声”。沃尔兹的理论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权力,沃尔兹认为,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即国家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了权力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在无政府条件下为权力的斗争。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家的硬权力密切相关。国家的硬权力越强,对世界的影响力就越大,国际地位就越高,国家形象也就越好。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理查德·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就是以现实主义为重要理论依据的。他认为,要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国家形象理论,首先外交决策者要强调相对国力的重要性,因为相对国力限制了国家实施外交决策的范围,从外交谈判到全面战争,强国在外交决策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弱国的选择余地则较小。其次要判断对象国对本国构成的是威胁还是提供了机遇,这也与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相吻合。[4]
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思考和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物质因素是其他各项社会力量发展的基础,但是这种理论范式片面的强调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忽视了非物质性因素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在实践中所形成国家形象认知未必都是正面的。如现实主义理论主张用“冲突”和“竞争”的视角来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开始对我国持有戒备心理,认为国强必霸;也有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威胁其地位和利益,开始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可见,中国国家形象非但没有因为国力的提升而改善,反而有恶化的倾向。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其以炫耀武力为特征的“威望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建设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政策如果不能被其他国家正确理解,就会造成负面效果,有损国家形象,影响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根据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认识国家形象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硬权力的提升,而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缺乏影响力和吸引力,这种权力的提升往往会引起他国的误读,不利于国家形象的改善。
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
自由主义根植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之中,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其理论渊源是洛克的权利政治与个人主义理念、格劳秀斯国际社会与法制思想、康德世界永久和平理论以及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等等。[5]P54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是在学理上与现实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概念,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后,基欧汉对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并在1984出版了著作《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他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与财富分配对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层次理论—国际制度理论。[6]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在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它与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区别是对国际关系的本质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是国家为权力而展开的斗争;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是各国际关系主体为秩序而进行的努力。[7]P94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各国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国际合作往往难以达成。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因为国际制度可以减少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对国家行为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制约着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其是否遵守国际制度有关,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形象就好,反之则国家形象就差。罗伯特·基欧汉在论述遵守国际制度的问题时,重点强调了政府的声誉因素。“他认为,政府的声誉是说服其他国家与其达成协议的重要资产。国际制度通过提供衡量国家表现的行为标准,并将这些标准与特定议题联系在一起,提供公开讨论的论坛,而且还常常借助国际组织作出评价来评估国家声誉。”[8]P115如朝鲜被美国称为“流氓国家”,其屡屡无视和挑战国际秩序,肆意违反国际协议,如屡屡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及撕毁停战协定等。此外,叙利亚、伊朗、古巴等所谓“无赖国家”,也大多是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破坏者。
但是,二战后的国际制度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在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创建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被剥夺了国际制度制定的参与权。国际制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为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性霸权体系而制定的。因此,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主张的以国家是否遵守这种制度来判断其形象好坏的做法,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西方立场和意识形态偏向。
此外,自由主义理论范式也强调了软权力对国家形象形成的作用。“软权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软权力又被称为说服性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的,指使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的能力。而硬权力又称为强制性权力主要指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从而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硬权力可依赖劝诱(胡萝卜)和威胁(大棒)的方式达到目的;软权力则通过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性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来吸引他人,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9]P6用一句话来说,软权力就是吸引力和影响力。具体来讲,软权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等几个方面。[10]
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国家的软权力,如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等与他国对该国的国家形象认知有很大的关联性。自由主义按民主的标准将国家分为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两种类型。民主国家以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代表,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样本建立起来的,与他们相似的政治制度往往被视为民主制度,获得较高的认同;反之,则被视为专制独裁国家,被所谓的民主国家所诟病,“民主国家”对他们往往带有敌意或偏见。这种根植于意识形态的敌意或偏见,影响着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强化了彼此的不信任感,是地区不稳定的动因。
但是,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却提供了认识、研究国家形象的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对国家形象认识的不足。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的增强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固然重要,但光有物质实力的增强是不够的,还应注重提高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对于今天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建构主义理论范式
建构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对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发展起来的,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理论范式之一,与自由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共同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三驾马车”。与现实主义重点关注权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不同,建构主义把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建构主义发展到今天,出现诸多流派,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尼古拉斯·奥努弗、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目前,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所提出的理论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理论中体系最为完整的。温特认为,国际政治学者在借鉴不同社会理论的过程中,越来越普遍的接受了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11]P1。第一条基本原则体现了建构主义解释世界的理念主义理论,强调共有观念,这与新现实主义重视物质能力的分配不同。第二条基本原则表达了整体主义的研究方式,强调整体对个体的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就体现在国际制度、国际文化对国家的作用等。温特强调,国际体系文化(或称为共有知识、共有期望、共有观念等)不仅影响着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通过国家的互动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身份和利益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身份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的,而国际体系文化则是通过国家的互动形成的。国家的身份与国家利益和行为密切相关: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又决定行为。温特认为,国家共有四种利益,即生存、独立、经济财富、集体自尊。“所谓集体自尊就是指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要”。[12]P230温特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集体自尊,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集体自我形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3]P231,这部分地取决于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自我形象是通过他者才能认识的。国家之间互动的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自我形象,相互蔑视和侮辱会产生负面的自我形象,而相互尊重与合作则产生正面的自我形象。[14]P231可见,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建构主义理论也认为国家形象属于国家利益范畴。不过,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不是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国家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身份或认同界定的。
可见,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家的身份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各国在国际社会互动中,通过观念共享,凭借观念结构或结构化的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因而是“社会性共有知识”、“共享观念”、“共同知识”或“主体间共识”的建构物。[15]P142-158也就是说,相关国家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界定了国家的彼此身份,也决定了彼此的形象认知。因而,国家之间共有或共享的知识(观念)的性质造就了国家之间相互身份认同的性质,也决定了彼此所认知的国家形象的性质。国家之间共有的知识是友好、合作型的还是冲突、对抗型的,决定了双方是朋友、伙伴关系还是对手、敌人关系。如美国与朝鲜共同持有一种敌对观念,这种共有观念塑造了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敌人身份;而美国与韩国共同持有一种友好观念,这种共同观念塑造了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盟友或朋友身份。可见,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形象不是“自然物”或“自在物”,而是体现为一种国际社会关系,是一种在国际社会内与对象国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承认、认同的关系,脱离他国或国际社会的承认、认同,就形不成一国的国家形象。[16]P25因此,国家形象不是靠一个国家单方面自我设计、定位出来的,而是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形成共同观念,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换言之,国家形象是国家特征的自我设计、定位与其他国际主体的社会承认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后者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建构主义为我们研究国家形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开辟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开拓了视界:我们不但要重视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等软权力的建设,而且要加强与他国的交往互动,增强彼此的了解和认同,这就要在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国际传播等方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
四、余论
综上所述,在国家形象研究方面,三种理论范式各具特点:现实主义看重经济、军事等物质性的硬权力的作用,自由主义更强调国际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影响;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形象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交往互动过程中彼此建构的。可见,国家形象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研究课题,研究者所遵循的理论范式不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也会有所差别。因此,探讨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范式,不但可以更好的理解、运用相关的理论背景,增加研究的理论深度,而且对国家形象建设实践具有更好的指导意义;如果回避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范式,笼统的谈论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误区,对国家形象的建设实践的指导也缺乏针对性。
但是,国家形象建设是系统工程,每种理论范式都有其局限性,单独依靠一种理论很难改善一个国家的形象。约瑟夫·奈也认识到这一点,2006年,他发表了《重新思考软权力》,称单独依靠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错误的,提出了将软权力和硬权力巧妙结合而构成“巧权力”的国家战略观,并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以推动将巧权力落实到外交政策中,来维护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我们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上要借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主张,不断提高我国的硬权力和软权力,并综合运用在对外交往中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同时,我国应加强与他国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他国的理解和认同,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1]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基于文化、利益、媒体三重透镜偏曲下的影像投射[J].国际新闻界,2013,(2)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的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Richard K.Herrmann,James Voss,Tonya Schooler&Joseph Ciarrochi.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7,41,(3).
[5][7]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J].美国研究,2002,(4).
[8]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M].苏长河,信强,何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9]约瑟夫·奈著.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J].美国研究,2005,(1).
[11][12][13][14][15]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