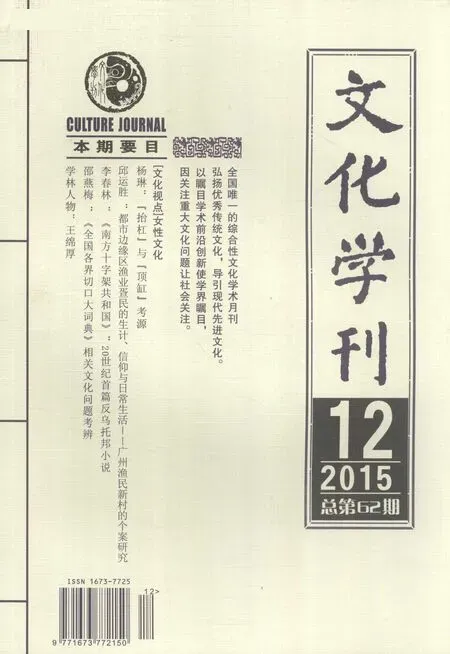《女勇士》中“割舌筋”的隐喻解析
赵 越 马春丽
(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一、汤亭亭与身体修辞
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是近年来美国大学校园中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在享有众多读者的同时,作者与其作品也受到了批评家的质疑与批判。批评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汤亭亭是否真实呈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能代表华裔女性以及被界定为自传的真实性。陈耀光指出,汤亭亭错误地解读广东话里“鬼”的含义,作品是完全基于她个体的经历而呈现出扭曲的中国文化。甚至他对出版社把此书定义为非小说而感到失望,这完全贬低了华裔在美的经历与生活。[1]Benjamin R. Tong 认为,汤亭亭故意展现错误的中国文化,是为了适应白人阅读喜好,以便获得更大的图书销售量。[2]
这样的批评从文本层面讲,的确直指作品的真实性,也使得在深入解析作品时面临诸多问题。然而,对于这部集合女性的、非主流文化的、少数族裔的作品,如果不把文本解读置于社会、历史、身体的大背景下,就无法有效揭示作品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和作者的意图。
本文主要探讨“割舌筋”这一身体修辞隐喻功能。母亲说:“割了以后,您的舌头就活泛了,能说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说截然不同的语言,能发出任何一个音。你的舌筋太紧了,说不了那些不同的外国话,所以我就把它割了。”[3]割舌筋体现了语言与身体、精神世界与身体在特定范式社会中的关系。从身体叙述讲,作者通过身体隐喻的力量激活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二、“割舌”的沉默隐喻
“割舌”作为华裔在美国社会中沉默的隐喻呈现。《女勇士》中呈现出种族化的身体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Cassuto 认为,与其他可见的种族标记不同,舌头通常不受外界观察者的注意,拒绝被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载体,却同外在世界一起把说话人标记为他者。[4]舌头这个隐蔽的语言载体,与语言的关系被突显出来。具有华裔标记的身体,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了文化的、意识的冲突。King-Kok Cheung 认为,华裔女性被种族和主流社会双重边缘化,由于性别、种族、话语权力的压迫而导致语言限制或语言障碍。[5]
“无名姑姑”因通奸产子而自杀,仿佛被“割舌”的她没有申辩和控诉,沉默死去。“西宫门外”的月兰从中国来到美国,看到已婚的丈夫,沉默直至疯掉。汤亭亭认为,沉默意味着死去和疯癫,是华裔对沉默的恐惧,对生存的担忧。种族歧视和排华法案的政策加剧了沉默。汤亭亭在步入美国社会之初就开始沉默。“第一次进幼儿园,不得不讲英语时,我就沉默了。”即使是最简单的问候或“问问公共汽车司机去的方向”“我的话仍然羞于出口。”[6]华裔在掌握和运用语言的同时,似乎又在怀疑和抗拒这种适应范式的方式。对华裔来说,种族化的身体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训。即使“我”努力地说出了,仍然会被美国人问道:“你说什么?”或者“大声点”。在范式社会中,对其他种族的接受也受制于身体符号。“我”不知道美国人从不用茶盘喝水,当我用茶盘将水喝光时,美国人都在笑。学校活动时,因为声音太小,父母不允许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只有华人学生留在教室里。中美文化与行为的差异和冲突,投射在语言问题上,汤亭亭领悟到:“我沉默是因为我们是华人”。[7]汤亭亭对华裔沉默的描述,呈现出种族与文化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Cheng 认为,外在身体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系,是种族主体的社会认知与种族焦虑的体现。[8]如同“割舌”一样,华裔在遇到种族与文化冲突时保持沉默,沉默是焦虑的载体,抗拒的体现,也是自我防御的手段。
三、“割舌”的华裔文化与种族身份隐喻
“割舌”作为华裔努力摆脱中国文化束缚,探寻生存空间的隐喻体现。同时也是华裔认识到在语言习得背后蕴含着社会范式与文化规训。在汤亭亭父母移民美国时,美国已开始规范强制使用英语作为公共场所用语。如果不能掌握英文,就被视为下等人。作品中的母亲期待“割舌”能创造出一个“活泛”,说“好听的话”的华裔女孩,这激发了汤亭亭敏感的自我意识觉醒,用沉默反叛对身体进行的暴力改制,她诉求专属于华裔的自由的“舌头”。在《女勇士》中,割舌学语的情节是汤亭亭虚构的,却把语言与身体的问题浓墨重彩地彰显出来。华裔受到语言的压迫,诉诸改制身体,使身体承载了精神诉求。
对华裔来说,掌握英语是关乎生存的问题,这令他们感到担忧和焦虑。“我”曾暴力地迫使一个“不爱说话的”华裔女孩讲英语,“我”与“她”的冲突与对话,正是华裔在精神世界的冲突体现。母亲把“割舌筋”与语言掌握的关系,变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身体作为精神世界的载体,割舌被寄予愿望:“母亲”相信割舌能说各种语言,能说出符合美国社会标准的话,华裔群体能在美国社会生存下来。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在试图颠覆传统的种种压迫。母亲勇兰是新女性的代表,她能言善辩,从事医生职业;花木兰以女性的力量挑战父权社会;“无名姑姑”成为复仇鬼;汤亭亭用语言找回话语权力,蔡琰故事更加强调回归中国文化,但在《女勇士》中,汤亭亭戏剧化地改写成蔡琰与匈奴人融合。蔡琰的歌曲唱的是中国和亲人,歌词是汉语,有时也有匈奴语,重要的是“野蛮人听得懂里面的伤感和怨愤”。表明了汤亭亭把中国元素与美国生活体验融合,通过异于两种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冲突与挣扎,都谱写成了一首蔡琰的歌曲。语言的障碍使华裔第二代移民意识到,华裔必须改变,寻找自己的身份与文化空间。割舌被赋予了隐喻的功能,华裔在精神世界中努力地“割舍”和“改制”着身体上的性、种族、文化的烙印。为了能适应美国生活,汤亭亭重塑过去的记忆,她强调的身份不是美国人、中国人,而是特指华裔美国人,可见,她的“割舌”蜕变,从沉默到把文字作为武器,从受压迫到成为英雄的女勇士。
四、结语
有评论者说,“割舌”是汤亭亭在东方话语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与华裔人群野蛮、暴力的理解,但汤亭亭以此虚构情节,表现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身体与语言的关系。从隐喻的角度诠释“割舌”,体现了语言的种族化和语言的等级化对少数族裔的影响。汤亭亭探索着现实社会与精神世界、身体与语言的关系。从“割舌”这个情节看,这些关系摈除了简单的因果逻辑,影响更加深入。华裔女性经历的从沉默到言说的艰苦历程,逐渐突破种族、性别及语言的屏障,摆脱父权压制与传统束缚。
[1]Nishme,LeiLani. EngenDecing Genre:GenDec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Men and The Woman Warrior[J].MELUS,1995,(20):67-82.
[2]Tong,Benjamin R. Critics of Admirer Sees Dumb Racist[J].The San Francisco Journal,1977,(11):77.
[3][6][7]汤亭亭. 女勇士[M]. 李剑波,陆承毅,译.张子清,校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48.149.150.
[4][8]Cassuto,Leonard. The Inhuman Race:The Racial Grotesqu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M].New York:Columbia UP,1997.67-75.53.
[5]Cheung,King- Kok.“Don't Tell”:Imposed Silences in The Color Purple and The Woman Warrior[J].PMLA,1998,(2):16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