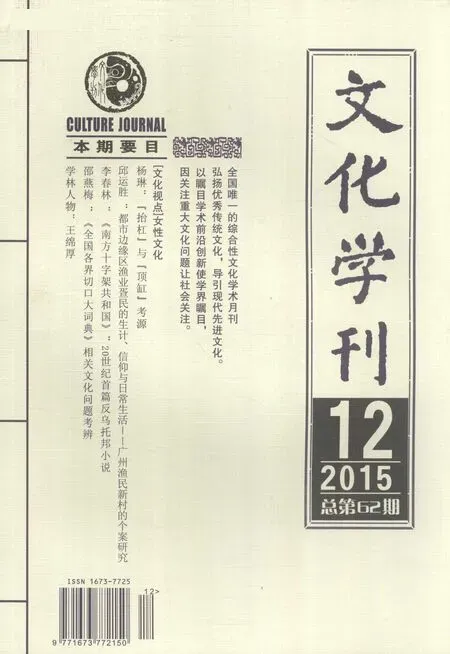都市边缘区渔业疍民的生计、信仰与日常生活——广州渔民新村的个案研究
邱运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引言
疍民是一个古老的水上族群,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沿海及各大水系沿岸。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岭南疍民研究始于20 世纪20 年代。钟敬文于1926 年撰写《中国疍民文学一脔》一文,并出版民歌集《疍歌》。[1]罗香林写于1940 年的《蜑民源流考》从蛇或龙图腾、生计方式、地理分布、蜑称词源等方面论证蜑民源出于古代越族。[2]陈序经的专著《疍民的研究》,对疍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3]伍锐麟基于其在广州珠江南岸、三水河口的田野调查,写就数篇研究报告。[4]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何格恩、黄云波、谢云声等人的研究著述问世。[5]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疍民调查和民族识别,对珠江口、西江、粤东、北江以及沙田区的农业疍民进行了全面调查,成果后经整理出版。[6]有关机构综合调查的成果认为,疍民“民族特征逐渐消失,民族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自我意识淡薄”,不应识别为少数民族。[7]此后,中国内地的疍民研究趋弱。外国学者如华德英(Barbara E. Ward)等人则以香港疍民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8]
新时期以来,随着地方文化的复兴,学界对疍民的研究有所加强。系统性的专著如张寿祺《蛋家人》[9]、体质人类学研究如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10]。论文则主要涉及疍民历史源流[11]、族称族属[12]、明清时期的疍民生活习俗和地缘关系[13]及沙田疍民与地方大族的经济、权力关系演变[14]等,也有学者从“他者”身份建构的角度再行审视历史上的“疍民歧视”现象[15],或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用于疍民研究[16]。对比不同时期的研究,除少部分专著以外,近年多数研究集中于历史上的疍民问题或族群互动,田野个案考察则不甚多见,然而,在南海、粤西、珠江、西江等沿岸水域,尚有规模不一的从事渔业生计方式的疍民零星分布,并且正在经历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急剧变迁。这些仅存的水上疍民族群不可忽视,亟待田野调查的深入。
一、上岸的浮生:珠三角疍民及其陆上定居的历程
历代文献常将疍民称为蜑、蜒、蛋、龙户、游艇子、白水郎等。《太平寰宇记》将疍民的来源记为“卢亭”,为晋末卢循之后。[17]据《岭表录异》记述卢停者:“卢循背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18]“卢亭”是所见文献中较早关于疍民族源的确切记载。清代文献则将疍民源流追溯至更远,如《粤中见闻》称:“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土,与鱼鳖同处。蛋,即丛薄中之逸民也”。[19]当代学者张寿祺、黄新美等从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研究得出结论,“南越族群”先民是疍民最初的来源,后与历代投奔江海的陆上族群长期融合,构成历史上珠江口的疍民族群。[20]这是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主流观点。古代岭南疍民传统的生计方式主要包括捕鱼、采珠、取蚝、运输、伐木、农耕等多种类型。《桂海虞衡志》记载:“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21]《岭外代答》中说:“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22]历史上,疍民所赖以为生的职业异常艰辛,尤其以采珠风险为大,“葬于鼋鼉蛟龙之腹者,比比有焉”。[23]《粤东见闻录》尝言:“男女朝夕踞蹐舟中,衣不蔽体。春夏水涨鱼多,可供一饱,率就客舟换米及盐。常日贫乏不能自存。土人不与婚姻,亦不与陆居。蠹豪又索作以困之。海滨贫民,此为最苦。”[24]古代疍民既要应对朝不保夕的生存压力,又要忍受陆上居民的勒索歧视,生计艰难,可见一斑。疍民上岸定居的历程,始于雍正七年(1729 年)。清廷颁布谕令:“凡无力之疍户,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至意。”[25]成为编户齐民的疍民,得准上岸居住,但受到的外来歧视并未真正得以消解。《广东新语》有云:“每岁计户稽船,征其鱼课,亦皆以民视之矣。诸蛋亦渐知书,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26]上岸居住的疍民不少从事沙田耕作,但是生存境况依然困窘。“他们多数是一无所有的雇农……他们主要为地主‘耕青’。所谓‘耕青’就是每年在秋冬二季农忙时节,向地主包种或包割,包种从插秧、除草直到禾熟才把田交回田主。”[27]清代华南地区与海外的商业贸易空前繁盛,分布于珠江口的疍民多从事船舶运输,与西方人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美国人亨特(Willian C.Hunter)记录了1825 年广州珠江河道上的情形: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还有一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所出售的日用品的艇等;另还有算命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28]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安排水上的疍民上岸居住,在消除陆上居民对疍民的歧视问题上也做了努力,疍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1951 年,当时的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颁布了《关于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处理办法》。文件显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称谓,由各省、市人民政府制定有关机关加以调查,如发现有歧视蔑视少数民族的称谓,应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协商,改用适当的称谓,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定,公布通行。”[29]由此,“蜑”、“蜒”、“蛋”等族称都不再使用,改称“水上居民”或“疍民”。1954 年6 月30 日,周恩来访问缅甸回国,途径广州,到黄沙、白鹅潭、沙面等沿江一带了解当时水上居民的生活情况,并指示省市各级政府拨出专款,为水上居民兴建住宅区和新村,让他们上岸定居。[30]随后,广州出台了《珠江区水上居民专业安置计划》。1958 年和1959 年,广州市政府两次拨款共220 万元,1960 年,中央拨款1200 万元,在山村、基立村、荔湾涌、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素社、石冲口、科甲村、如意坊、马涌、东望、猎德、墩头基等十几个地点建立新村,居住面积达28 万平方米,安置了大批疍民。[31]据有关学者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 年,政府共为广州水上居民兴建住宅20 处,建筑面积177694 平方米,9474户40205 多人上岸定居,上岸定居人数占广州水上居民总数的70%,人均4 平方米,基本上解决了广州水上居民上岸定居问题。[32]疍民上岸定居是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各处疍民上岸的时间及上岸后居住的区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何国强在《伍锐麟的社会学调查》一文中指出了疍民上岸后发展并不均衡的现象:“现在居于城市中心的新港东路、五羊新城、如意坊一带,都是上岸较早的疍民的聚居点。这些人已繁衍了两代,他们的都市化时间较长,完全适应了陆地环境。而九沙围等城市边缘地带的渔民新村则情形不同,那里的疍民,上岸较迟,规模也不大,政府对他们的投入有限,引导他们转产、转业的力度不够,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边缘群体。”[33]本文的调查对象广州渔民新村即是上岸时间较晚,有了固定房屋后,继续从事渔业生产的疍民村落。
二、从内河到沿海:渔民新村及其生计方式
渔民新村位于广州市东南部四面环水、地域狭长的琶洲岛最东端。至2013 年,全村有人口976 人,240 余户,拥有从事渔业生产的渔船149 艘,渔业捕捞从业者224 人。渔民新村成立于1966 年。据村中一位退休干部讲述,新村村民是由从各地集中上岸的水上居民组成的,例如人口数量较多的梁姓家族是从如今的天河区车陂迁来新村,被称为“车陂梁”,而彭姓家族则是一百多年前从黄埔区矛岗村迁来黄埔古港。渔民新村人数较多的大姓主要有:梁、陈、彭、吴、黄、邓等姓氏。1966 年,上岸的疍民被组织为渔业人民公社,隶属于白云区渔业联社。渔业联社由新洲、芳村、沥滘等多个渔业社组成,相当于一个镇的建制。1985 年,开始私人承包渔船作业。2014 年,渔民新村仍有渔业生产从业者224 人,其中出生于1950-1960 年代的人占了绝大部分,1970 年代出生的人只有少数几位。如今渔民新村面临较为尴尬的处境是,渔业社与行政村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行政上隶属于白云区,社区管理服务却由其所在地海珠区琶洲街道广渔社区提供。这导致一些公共资源无法及时覆盖到所有村民,村民大有“被社会遗忘”的感叹。
自1966 年组建渔民新村以来,当地渔民最初进行捕鱼作业的地方就在村子南面的珠江水面。当时的琶洲岛附近水网密布,黄埔涌、马涌、沙涌、上涌等河涌互相勾连,渔船往来便捷,小涌里的水干净清澈,鱼虾产量可观。渔民们通常趁每天涨潮、退潮的时候捕鱼。人们捕获的鱼类主要包括:凤尾鱼、狮子鱼、鳗鱼、花鱼、白甲鱼、蚬等品种。实行家庭承包渔船单独经营后,渔业产量实现了增产,而此时珠江水体却面临被污染,水质迅速下降,到了上世纪90 年代,珠江内河捕捞业急剧萎缩。渔民新村的渔民开始了到珠江口沿海地区进行捕捞作业的进程。渔民沿海捕捞作业的地点主要选择在珠江口的珠海万山岛、蕉门、东莞虎门等水域。由于距离较远,渔民们出海一次通常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远海作业使得渔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在船上渡过。渔民捕获的鱼虾,基本上是在当地出产、当地销售。在2008 年实行休渔政策之后,渔民们无论是在水上还是在陆上,生活的时间节点便都围绕着开渔、休渔的渔政政令来进行着人为的调节。每年的五月、六月、七月三个月的时间为休渔期,这一时期为鱼虾的繁育期,是禁止捕捞作业的。在休渔期间,村民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修理渔船、修补渔网,一些礼仪、庆贺的活动也被人们安排在了休渔期举行。
三、变迁之神:民间信仰的演变与建构
在渔民新村上岸疍民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中,与其渔业生计方式关系致为密切的水神、海神等神灵,日常受到人们的崇敬和供奉最为频繁。人们相信,求助于水上神灵的超自然力量不仅可以保障鱼虾捕捞取得令人满意的丰厚回报,而且有望在天气复杂多变的水上作业环境中,保全人员和渔船的平安无虞。每当出海捕鱼之前,渔民们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的渔船上进行拜神、祝祷的简短仪式。祭祀水神需要准备的供品有整鸡、水果、糕饼、香烛、纸质金银元宝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渔民新村的地界上,水神、海神并未形成特定的偶像形象和祭祀设施,与神灵的沟通,也无需专门的神媒人员的参与、协助,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中的神灵。
或许由于近年来,渔民捕捞作业的空间范围已经由内河向沿海拓展,因此人们更加看重对海神的敬奉。新村渔民会有组织地如期参加每年三月份在黄埔区庙头村南海神庙举行的“波罗诞”庙会,以求得海神庇佑,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各地的疍民最初被安排上岸,聚居于渔民新村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曾被严厉禁止,因而在村中,笔者并未发现年代久远的寺庙。在村子东侧进村的入口处,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土地庙。土地庙修建于1997 年,位于村口的一颗古树之下,是由热心村民自筹资金兴建的简易宗教设施。土地庙采取的是二进格局,前庭预留有一定的空间供人叩拜。门楣之上贴有五张福字样的条幅,内庭则设有土地公、土地婆和观世音菩萨的石刻雕像。渔民祭祀土地神的时间通常为出海打渔之前、收获返程之后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出海前的祈求与愿望实现后的酬神、还愿同等重要。土地神是传统农业社会保境安民的社区神灵,其力量统摄的范围是以社区的边界为界限的,负责护佑人们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山林等。上岸定居的疍民,在陆地上有了固定的栖身之所,像其他耕作于土地的农业村落一样,渔民们逐渐有了保护本乡本土的意识,因而土地神的崇拜得以产生。然而,上岸疍民并未彻底脱离渔业捕捞的传统生计方式,于是,原本管控土地的陆上神灵土地神,被纳入到了渔民们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中,成为水陆共管的神灵。农耕文化所崇拜的土地神被疍家人赋予了庇护江海渔船的角色,可谓是人们上岸定居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在其精神世界的反映。
四、当下上岸疍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当下,上岸定居的疍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地理空间已经经历了从水上到岸上的迁移,人们生产、生活的时间节律也相应地有了休渔期与捕鱼期的调整和变化。伴随着都市周边区域的开发和建设,水产养殖业、商品交易市场、物资供应条件都发了显著的变化。渔民新村疍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呈现出了许多城市居民的消费特点。按照一般常识性的看法,渔民对于鱼虾贝类等水产品的需求,通过“自产自销”的方式便能得到满足,事实却并非如此。调查显示,如今身处市区的渔民早已卷入了消费品供需市场。除了出海打渔的人员以外,生活在岸上的渔民对水产品的消费,也必须通过在农贸市场购买水产养殖户生产的水产品。渔民新村南面朝向珠江水域,用他们的话说便是,“家门口就能捕鱼”,但是,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珠江河道水质因受污染已经日益恶化。对于家门口就可以捕获的鱼虾,人们形容为“不好吃、口感差”,还比不上池塘喂饲料养殖的水产味道好。渔民们还能记得,20 世纪80 年代珠江水里的虾一旦被捉到,能够立即去壳生吃,十分可口。
同样受益于市场供给,渔民的日常饮食结构也变得与城市居民几无差异。在营养成分蛋白质的获取方面,人们过去主要是从鱼虾等水生动物性食物中摄入,如今随着物质供应的日益多样化、快捷化,食物中家畜、家禽的构成比率几乎与水产品相当,成为人们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由于渔民们仍维持着渔业生计方式,特别是远海捕捞作业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大可能有条件和时间像一般农村家庭一样饲养家畜、家禽,因此笔者行走在村子内,从未见过有村民家中饲养了猪、鸡、鸭、鹅等动物。渔民们对于鸡的需求,在平日饮食以及祭祀水神、海神时,都是不可或缺的物品。目前,这些食物的获得唯有通过市场渠道才能实现。由于没有土地,因此渔民们对于水果、蔬菜的消费则更加需要依靠市场的供应。得益于日益便捷的交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流通市场的联系已经愈发密切。
五、结 语
渔民新村上岸疍民传统的渔业生计方式至今仍得以维系,但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其一,渔业生计方式由珠江内河捕捞延伸至珠江入海口沿海地带作业,赖以为生的水域地理空间发生了变化;其二,国家制度层面上于2008 年开始执行的休渔政策,使上岸疍民的生产劳作、闲暇休憩、社交互动的时间节律有了相应的调整与适应。其三,作为广州市区最后一批渔村,渔民新村被裹挟在广州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渔业生计方式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已经丧失殆尽,正在迅速走向衰落。在民间信仰方面,上岸疍民水神、海神崇拜依然存在,而土地神崇拜逐渐演变为兼有保护陆上定居村落社区一方平安和庇佑水上捕捞作业顺利进行的双重功能,陆地神灵被建构出水神的角色。上岸后,当地疍民的日常消费结构、饮食结构有了显著改变。如果将上岸疍民如今的生计、信仰及生活实践视为一个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动态的视角去观察,那么疍民过去的水上生活史呼应着当下的实践,而与遭遇都市化的过程依旧在持续。
[1]钟敬文.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3)·疍歌[M]. 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1970.83-97.
[2]罗香林. 百越源流与文化[M]. 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223-255.
[3]陈序经. 疍民的研究[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4]伍锐麟. 民国广州的疍民、人力车夫和村落:伍锐麟社会学调查报告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5]詹坚固. 20 世纪以来疍民研究述评[A]林有能等.疍民文化研究(二)[C].香港:香港出版社,2014.1-15.
[6]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广东疍民社会调查[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7]黄光学. 中国的民族识别[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287-291.
[8][英]华德英. 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M]. 冯承聪,等,译. 香港: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
[9]张寿祺. 蛋家人[M]. 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1.
[10]黄新美. 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1]吴建新. 广东疍民历史源流初析[J]. 岭南文史,1985,(1).
[12]詹坚固. 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J]民族研究,2012,(1).
[13]叶显恩. 明清广东蛋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
[14]萧凤霞,刘志伟.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3).
[15]何家祥. 农耕他者的制造——重新审视广东“疍民歧视”[J]. 思想战线,2005,(5).
[16]陈光良. 岭南疍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1,(2).
[17][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M]. 王文楚,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2030.
[18][唐]刘恂. 岭表录异[C]//历代岭南笔记八种. 鲁迅,杨伟群,点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53.
[19][清]范端昂. 粤中见闻[M]. 汤志岳,点校、注释.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232.
[20]黄新美. 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22-123.
[21][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C]//范成大笔记六种. 北京:中华书局,2002.160.
[22][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15-116.
[23][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李梦生,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268-6269.
[24][清]张渠. 粤东见闻录[M]. 程明,校点.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59.
[25]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 清实录广东史料[M].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314.
[26][清]屈大均. 广东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85-486.
[27]谭棣华.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121.
[28][美]威廉·C·亨特. 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M]. 冯树铁,译. 骆幼玲,等,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10-11
[29]政务院. 关于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处理办法[J]. 文物参考资料,1951,(6).
[30]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市志·卷一:大事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366.
[31][33]何国强. 伍锐麟的社会学调查(序)[C]//伍锐麟. 民国广州的疍民、人力车夫和村落:伍锐麟社会学调查报告集.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36.
[32]詹坚固.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