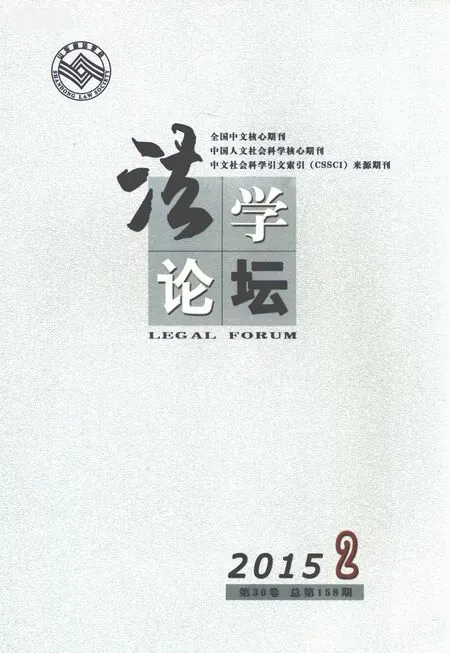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
——《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刘 远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学术视点】
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
——《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刘 远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司法逻辑是一种客观逻辑,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对此要在刑法自身结构中的自生性(内部性)与建构性(外部性)的矛盾中理解。《刑法》第1条乃是这种精神之总成,其中“结合”与“为了”之表述体现此精神尤为明显。在司法逻辑中,控方以《刑法》第2条为总依据的追诉偏好刑法的外部性,而辩方所偏好的则是刑法的内部性。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是理解《刑法》第3至5条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
司法逻辑精神;刑法的外部性;刑法的内部性;语境论;无知论
一、问题、理念与方法
当下,去行政化、审判中心化、庭审实质化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定罪量刑本属司法活动,但长久以来却被高度行政化地运作,所以在现实中刑法很大程度上成了行政法。例如,很多案件的实体处理实际上常被控方主导,于是刑法在其中主要是作为刑事执法所执之法而起作用的,而刑事执法显属于行政活动。再如,法定犯的事实认定和规范评价经常是行政机关主导的,在这里刑法同样实质上被行政法化了。假药的认定、醉酒驾驶的认定等就是适例。又如,行政执法对于当事人来讲常常是不由分说的,而在定罪量刑中也往往出现法官排斥辩护的情况。
然而,刑法作为典型的司法法,其精神终归是公正而不是严格,虽然严格执法是公正司法的必要前提和必经阶段,但严格执法本身不等于公正司法。刑事司法有一个特殊之处,即控方在公诉制度下不仅是控方,还是刑事执法者,其所执之法,当然是刑法,但只是其单方面理解中的刑法,这种单方面理解的可修改性要比执法者对行政法的单方面理解大得多,这是司法法的一个显著特性。例如,控方对何为卖淫(如女性提供性交之外的有偿性服务是否卖淫)、强奸(如婚内强制性行为是否强奸)的单方面理解就常常如此。因此,若以严格执法代替公正司法,必将毁灭司法公正。“法的精神”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具体到刑法和行政法,两者的精神显著不同,因为刑法的精神是在司法逻辑中实现刑事公正的精神,即司法逻辑精神,而非行政逻辑精神。
一谈到逻辑,人们常常理解为主观逻辑,即推理的规则,但是,我们也能够把逻辑理解为客观逻辑。*这里借用了黑格尔关于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区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概念的发展处于自在的(即潜在的、尚未展开的)阶段时,黑格尔称它为客观逻辑;当概念进入自为的发展阶段时,称之为主观逻辑。参见张懋泽编著:《〈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作为客观逻辑,“逻辑”一词指向的不是主体自身的思维进程,而是主体之间的行动结构及其客观进程。在这种客观逻辑的意义上,可以说执法和司法各有其逻辑,正如市场有市场的逻辑*例如张维迎说,“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建立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完善已存在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有时候,甚至“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改革过程将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进行。”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2、244页。、改革有改革的逻辑*参见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制度有制度的逻辑*例如海尔布隆纳论述“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时候,其逻辑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模式”,是社会制度“生命历程”中和制度构造过程中发生的运动及变更。参见[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6-7、11页。一样。因此,所谓司法逻辑,讲的不是法官关起门来如何进行法律推理,而是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特别是在法庭上)就定罪量刑进行相互行动的客观结构及其进程。司法逻辑的基本表现,就是先有追诉后有辩护,控辩双方按照程序进行的博弈是法官获取案件真相和实现司法正义的基本途径。刑法是司法法,故《刑法》以司法逻辑架构,这意味着《刑法》是司法过程中控、辩、审共同依据并受其规制的法律文本。
既然司法逻辑是客观逻辑,那么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就是客观精神。如果按照蔡枢衡的说法,即哲学性、规范性和现象性(事实性)是刑法一体之三面,*参见蔡枢衡:《刑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那么这种客观精神指涉的则主要是刑法的现象性与哲学性这两面。因此,要理解这种客观精神,就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哲学、法哲学为基点。哈耶克为我们建立了这种基点。他深刻指出,社会整体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产物,与纯自然秩序相比,所不同的只是构成社会秩序的每个分子都是有着自身目的和预期的行动着的人,由此社会秩序比自然秩序更为复杂和独特。*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现代科学和哲学对此早予以肯定。*参见刘远:《刑事法哲学初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对于超过面对面规模的开放社会,政府既是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产物,也是其得以维持和改进所不可或缺的。但随着政府政治整合功能的日益增强,其组织性的建构理性也急剧扩张,常常出现以人造社会秩序取代自生社会秩序的企图或趋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威胁乃至毁灭社会的企图或趋势加以警惕。根据哈耶克的识见,刑法在整体性质上乃是自生自发的正当行为规则,*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12页。其经由与社会整体自生自发秩序的互动而演进。然而,刑法在亚层次上又必有一定的人为建构性,这体现为立法机关对刑法的更改或修正(而不是创造性的制定)。*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相对于私法和刑法这些整体上自生自发性的内部规则,行政法是立法建构的外部规则(组织规则)。随着20世纪以来立法主义的普遍盛行和公法至上的盲目扩张,私法和刑法的自生自发性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有沦为全权性政制的工具之虞。外部规则和组织秩序只有限于一定范围才属于社会整体自生秩序,才不会变成与自生秩序相对立的、干预和破坏社会正常机能的全权性工具。*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由此,如何处理好刑法自身结构中整体上的自生性(内部性)与亚层次上的建构性(外部性)之间的矛盾,亦即蔡枢衡所说的规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参见蔡枢衡:《刑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乃刑法哲学基本问题之一。
谁也不会否认,《刑法》第1至5条集中体现了刑法的精神,但它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则见仁见智。本文把这五条所蕴含的刑法精神定位于一种司法逻辑精神,并把它放在上述框架中加以理解。因此要看到,在公诉制度下,控方作为广义政府的一部分,承担着追诉犯罪的组织化职责,其追诉立场、组织特性以及实现秩序预期最大化的执法逻辑,必偏向于刑法的建构性或外部性,或者说会使刑法规范由内部规则向外部规则转化;而辩方中的当事人,是作为孤立个人即社会行动者被控方追诉的,其所固有的辩护立场、个人特性以及实现个人预期最大化的行为逻辑,映现出的只能是刑法的自生性或内部性。法官的功能正是在适用刑法中实现刑法自生性与建构性的适度统一,这种适度统一是以控辩双方对刑法解释的构成性作用得以发挥为条件的。
二、《刑法》第1条:精神之总成
如果不以司法逻辑的眼光去看,《刑法》第1条就会被第2条架空而只剩下形式意义,这正是传统理解模式之弊。即第2条被认为对第1条宣示的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进行了具体化,而第1条所谓立法根据(其一为法律根据即“根据宪法”,其二为实践根据即“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更是被忽视至极。这样,第1条似乎仅仅是《刑法》的开场白。究其实质,这种理解的背后是执法逻辑。不以司法逻辑理解刑法,必以执法逻辑理解刑法,只要以司法逻辑的眼光去看,第1条就蔚为大观。*笔者曾专文探讨,兹不赘述。参见刘远:《刑法概念的司法逻辑建构——〈刑法〉第1条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
概言之,第1条乃是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之总成。所谓“结合”和“为了”这两个短语尤能体现此点。造就刑法规范的具体因素不可胜数,但直接说来,可以说刑法规范是两种基因相结合的结果,亦即自上而下自觉的权力意志(刑法政策)与自下而上自发的公共意见(刑法生活)相结合的直接结果;*伯尔曼、博登海默等许多学者都对此作过精辟论述。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4页;[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因为,万象虽“多”而皆有对,可名为“两”,即“阴”与“阳”,*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6页。而上述两种基因谁为阴、谁为阳不言自明。需要强调,在这种“结合”中,所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字面上包括我国官方的刑事政策经验和现实诉求,也包括我国民间的刑事生活经验和现实需求,但逻辑上前者已为立法政策所吸收,所以该短语所表征的只是后者,它可以被术语化为“社会刑事生活经验及需求”,或简称为“刑法生活”。*刑法生活就是这种民间生活经验的来源、载体。它是所有追求各自生活目标的行动个体在相关行动领域复杂互动,使其刑法需求和情感自发形成集中化趋势或使这种趋势得以维持、演化的社会过程。换言之,相关社会成员关于刑事谴责和惩罚的公共意见的自发形成、修改过程就是刑法生活过程。广大市场主体经由复杂的互动自发形成关于刑事谴责和惩罚某些市场行为的趋同需求的过程是刑法生活过程,广大普通百姓关于死刑适用度的潜移默化的观念转变过程也是刑法生活过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哈耶克所言,在早期文明中,“立法者”可以努力祛除他认为法律中所存在的讹误,也可以努力使法律恢复其原始的纯正,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制定新的法律。然而,所有生成于阐明规则过程中的法律,都可能在自生自发过程中陷入困境,甚至成为恶法,而这是仅凭自生自发力量所不能摆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由立法者进行修正。立法修正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法律发展的司法过程必定是渐进的,很可能跟不上时代脚步,只有立法途径才能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再者,法官有可能认为另一项规则会更好,但在该项规则被人们广泛知道之前就由法官加以适用,可能造成明显的不公正,而如果由立法者以修订法律的方式加以事先公布,就不存在这种不公正。当人们认识到某些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接受的规则依照更为一般的正义原则乃是不公正的时候,所需要加以修正的很可能不只是个别规则,这项任务只有立法者才能完成。然而,哈耶克指出,立法者的“意志”必须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见”为基础和界限。这种意见是有关立法者被授予的只是规定何者是确当的权力的意见,它所关注的并不是立法决策的特定内容,而只是任何正当行为规则都必须具备的一般属性。这种意见的力量,只是一种拒绝给予支持的否定性力量,而这种支持则是立法权所最终依凭的基础。在一个所有的权力都以意见为基础的自由社会里,这种终极性权力并不直接决定任何事情,但却能够经由界定肯定性权力的实施方式而对所有的肯定性权力进行控制。*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42页。著名的许霆案正好是一个例子,因为公众对于究竟该如何处理许霆是不能给出几乎一致的肯定答案的,但他们对于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却可以给予几乎一致的否定意见。可见,虽有政策基因或人为制定,但刑法主要是“长”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长出来的法律,哈耶克称之为司法法律;造出来的法律,则称之为政治法律。行政法属于后者,刑法属于前者。哈耶克由此强调刑法的自生性,*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12、 213页。亦即刑法生活对刑法的基础性地位和控制性作用。如果夸大处于抉择性地位和发挥调节性作用的刑法政策对刑法的构成性意义,把刑法看作主要是造出来的,就必然造就“恶法”。
“为了”,则宣明了刑法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必须从双向来理解,即惩罚犯罪以保护法益和规制权力以保障人权是刑法的目的。法益之保护,发动于刑事追诉;人权之保障,依赖于刑事辩护。这两方面对立于刑事司法过程,统一于刑事司法结论。因此,对于《刑法》规定的每个罪,都不能只认为其立法目的仅在保护法益,也应承认保障相关行动自由亦是其立法目的。
可能有人会问,这种理解符合立法者的意图吗?这涉及如何看待立法者问题和语言问题。就立法者这一概念而言,我们能否像利科尔所说的那样,认为文本一旦产生,作者就死了?*参见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撇开立法者而仅仅探寻法律的客观意思,可能只是一种错误理解立法者概念而导致的万不得已的策略。而如果把立法者理解为一个由某些特定个人所组成的具体人群,那么立法者显然会退休和死去;一旦这些立法者不复存在,我们在理解《刑法》时的选择就很难判断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问题是,我们不应当把立法者看作是那样一个具体人群,而应当在观念意义上理解“立法者”。就是说,立法者是一个在特定国家中其职位届届相传、其追求不断发展的政治组织体,立法者会适应时代变迁而刷新自己的法律观。当过去的法律文义(无论当时是基于什么意思)还能满足现实需要,还能被赋予新含义,立法者是不会加以修改的。既然立法者没有修改也没有准备修改法律文本,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立法者现在对这个文本会怎样理解。
就语言来说,应当摈弃图像论。图像论的语言观认为每一字词都是一种事物的名称,而句子是这些名称的组合。它相信语词具有超越情境的固定的意义。它一劳永逸地给出一个词的意义,从而在任何时候语词的意义不与语境相关。这个图像是由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观念带入日常语言的。*参见邱文元:《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明晰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6页。边沁就认为语言完全是对实在的指称,并且是清晰可辨的。这种语言观导致他提议英国起草法典,它将在立法者与法官和公民之间建立一种不会有曲解的交流渠道,从而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机械化,而这个任务低层文官就可以胜任。*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转向了语境论,主张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的用途,*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11页。语词的使用由日常生活的情境所决定,因此要达到语言的明晰性,就必须进入到使用这种语言的文化情境中。*参见邱文元:《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明晰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维特根斯坦提倡语用研究,哈贝马斯进而认为,一种只涉及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关系的“独白式”语用学是不够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还需要一种相互性或交往性的语用学,即“普遍语用学”。他断言普遍语用学是一种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功能,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达到理解一致的学问。*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跟图像论相比,语境论是一种好的语言观。
因此,不管立法者当时试图在第1条中表述什么样的刑法观,只要其所使用的语言能够容纳语境变化带来的新内涵,我们就应该在新语境下作出新理解。相比1997年《刑法》写定第1条之时,语境的根本变化就是2004年人权入宪。同一个文句,在不同语境下当然有不同意思和意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孟子原本是专就《尚书》讲的,但后来“书”泛指书本知识。*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法律解释问题》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杨朱在先秦礼崩乐坏语境下提出“损一豪利天下,不与也”从而张扬“贵生”的进步思想,*参见:《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5、18页。随着语境变化,“一毛不拔”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在人权语境下,“为了惩罚犯罪”是刑法的传统价值,刑法通过惩罚犯罪以保护法益,而法益的种类和范围在《刑法》第2条有具体的表述;“保护人民”则是一个应当与惩罚犯罪相区别的现代价值,这就是保护人民免受违法的追诉和裁判,《刑法》第3条至第5条集中作了表达。这也就是李斯特提出、为后世高度赞同的“自由大宪章”思想。*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在逻辑上,公权力的错用和滥用,包括违法的追诉或裁判,本身未必构成犯罪,即便构成犯罪也不能等到它构成犯罪才去保护人民,所以新解并未违反形式逻辑。
三、《刑法》第2条:刑法的外部性
在司法逻辑的理解中,《刑法》第2条的要义是惩罚犯罪以保护法益乃刑法的任务。刑法的任务由控方积极承担。*参见刘远:《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解读》,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如上所述,刑法的精神是在司法逻辑中展现的,而司法逻辑的起点就是追诉。不始于追诉之正,不经由辩护之反,无以实现裁判之合。在公诉为主的刑事追诉制度下,控方的立场、视角、逻辑、表达是怎样的?这是理解第2条及其与第1条关系的关键。
在公诉中,控方主要由警察和检察官组成。到90年代初,公安机关不是司法机关而是行政机关的公论已经形成。随后,在司法机关概念和司法权本质的普遍追问中,检察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宪法没有提供答案)的问题也被提出。本文认为,把行政权和司法权对立起来不符合辩证法,毋宁把两者看作一个权力连续体的两极,其间存在着若干有意义的过渡环节。以此分析模式看,相比于其他行政权,警察权无疑具有明显的司法权因素,或者说更靠近司法权一极,这使得在实现刑事公正的道路上,警察权较之其他行政权更为可靠。但是,警察权并不因为包含司法权因素而不再是行政权,正如阳中有阴而仍为阳。同理,相比于警察权,检察权更靠近司法权一极,所以在实现刑事公正的道路上检察权较之警察权更为可靠。但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检察权在上述权力连续体上是否超过了临界点而成为司法权,则取决于一国的司法体制。从我国的传统和现实及改革需要出发,判定检察权是司法权是实事求是的。仅就改革而言,把检察权定位于行政权,不利于渐进式司法改革。同样,相比于检察权,审判权更靠近司法权一极(假定纯粹的司法权只是一种观念)。人们对审判权的公正性并非没有怀疑,但在现实中,还有哪种权力比审判权更有资格被称为司法权呢?因此,检察权相对于警察权是司法权,但相对于审判权只是中立性和公正性次一级的司法权。这既是司法架构的前提,也是理解控方的关键。
美国学者指出,法律的自由形象与秩序形象之间的冲突是相当普遍的,而“由运用法律同‘犯罪人’做斗争的官员们来体现的”是法律的秩序形象。每一次刑事追诉都要跨越危险的地界,被怀疑有罪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因此,若不检视犯罪控制的社会历史学和政治学,关于刑法的讨论将是不完整的。可是,实证主义和法律文本主义排除了任何可以获得批判性见解的外部观察点,职业法律教育也就无法提供分析法律文本主义的心理和社会现象的基础。*参见[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法律过程导论》,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6、312、314、313、598页。因此,揭示出控方作为权力组织的秩序视角,对刑法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控方的追诉立场、秩序视角与其整体主义或结果主义的行动逻辑以及始于法益并终于构成要件的表达方式是相适应的,*参见刘远:《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建构探析》,载《法学》2014年第10期。假设此种本性能够改弦更张(这种客观逻辑现象无关乎对构成控方的任何个人的评价),辩护制度、公诉转自诉制度等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而这种假设显然不能成立。试看以下两种追诉现象便见分晓:
其一,以某种行为侵犯外部秩序为动因而追诉,对行为人的个人自由形成压力。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所谓法定犯的追诉上。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该罪侵犯的法益被认为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金融管理秩序表征的仅仅是金融秩序的外部性。因为,“金融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市场化的自然生成”,*参见周德文:《温州金融改革最应该改的是什么》,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编《中国经济迫切十问》,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但自然生成的金融市场离不开金融管理,因此金融秩序由金融交易和金融管理两个方面的活动整合而成,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统一;在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金融交易活动在金融秩序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目前正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方向发展。金融交易秩序是一种内部的抽象秩序,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到,也不可能经由直觉而认知到这种秩序,而只能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而金融管理秩序是一种外部的具体秩序。经济学家看重金融交易秩序,政府官员看重金融管理秩序。在民间融资问题上,一派是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严惩派”,主张严厉惩罚,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派是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松绑派”,主张民间融资罪轻乃至无罪。控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追诉,就是以行为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为动因的,而作为金融交易者的被告,不可能具有金融管理秩序的立场和视角,金融管理秩序无法成为其辩护之词。其能用来抗辩的,只能是金融自由概念。在许多民间融资案件中,报案的往往不是集资群众,而是当地的国有金融机构,当地国有金融机构之所以报案,往往是基于认为融资者分流了银行储蓄,损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所谓“受害群众”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人,对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并不领情,对司法机关的介入持观望态度,不愿出面登记债权。控方偏好刑法的秩序形象,在此表现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津津乐道;辩方偏好刑法的自由形象,在此表现为对金融自由的吁求。控方着眼于金融管理秩序,辩方着眼于金融自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金融管理秩序与金融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性判断,则是法官的职责。法官眼中的金融管理秩序,是与金融自由相依存、相统一的概念,当然不同于控方眼中那种与金融自由相分离、相割裂的金融管理秩序。当下,法院应当通过对金融交易活动的公正刑法评价,为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提供保障和动力,尤其是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无罪裁判,对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倒逼效应。而控方那种不考虑或不充分考虑金融自由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不能寄望其改变的。
其二,以某种行为不侵犯外部秩序为理由而宽纵,对个人自由被侵犯熟视无睹。
这种现象反倒主要是发生在某些自然犯的追诉上。以非法拘禁罪为例,前几年引爆舆论的“黑监狱”*所谓“黑监狱”,是被截访的进京上访者们对那些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帮地方政府关押、押送上访者,从中收取佣金的保安公司所设立的非法关押场所的称谓。这一称谓先是通过媒体不胫而走,后得到公安机关的承认。事件,曾迟迟不能成案。可以说,“黑监狱”是在愈演愈烈、纸里包不住火的情况下才被查处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黑监狱”未及时成案的原因呢?这就要分析控方的法益判断。
何谓法益,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罗克辛说,犯罪概念和法益理论一直是刑法理论中最不精确的基础问题。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但罗克辛此点说得很对,即法益是一个先于实在刑法的概念,但并不先于宪法。把法益概念限定在刑法意义上并不妥当。日本学者関哲夫认为,法益概念是作为社会的实在概念的“利益”与作为法的评价概念的“法的要保护性”相结合的产物。申言之,法益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之中必须由刑罚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 存在。这个法益概念,正如是由“法”和“利益”这两个词汇的记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由利益的要素和法的要保护性要素相结合的复合概念。法的要保护性的要素是与法益的性质相关的属性要素,是指其得到了值得刑罚保护的评价。这个法的要保护性的要素,是刑事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的衡量而进行的法的价值判断的产物。参见[日]関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王充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显然,将法益概念局限于刑法意义上,就使法益概念失去了作为刑法与其上位法、前位法之间纽带的功能。在此种棘手的“问题概念”支配下,控方会如何评价“黑监狱”行为的法益侵害呢?这包括以下几个子问题:其一,稳定是不是法益?虽然《宪法》没有予以直接的字面表述,但从其序言精神和条文规定中推论,没有理由认为稳定不是法益,只不过刑法学并不抽象谈论稳定,稳定是被具体化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等法益的。其二,稳定与人身自由孰轻孰重?罗克辛是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来定义法益的。*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学说)未必认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一定轻于个人法益。*参见[日]関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王充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行为去权衡不同法益之间的轻重,无异于缘木求鱼。其三,在对待上访中维护稳定与保障自由孰轻孰重?截访是某些地方政府一种价值判断的结果,亦即当维护稳定的需要与保障人身自由的需要发生冲突、不可兼得的时候,舍后者而取前者。显然,如果不以行为本身为法律判断的逻辑起点,法益判断就没有正确的判断范围,而只有法官在借助辩护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参见刘远:《规范vs法益:基于〈刑法〉第13条的司法逻辑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控方自身是难以摆脱整体主义的、结果主义的法益思维的,这正是控方的客观局限性,也是需要法官在倾听辩护基础上进行裁决的客观原因。
四、《刑法》第3至5条:刑法的内部性
人们通常将第3、4、5条理解为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实这种逐条孤立解读的或简单罗列式的非结构性理解方式,无法整体性地把握其中的精神。尽管这3条分别从罪之有无、人之平等、刑之轻重作了规定,但如果在司法逻辑上整体性把握其精神,这3条应被看作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和强调。就是说,第3条是核心规定,第4、5条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因素的强调。因为,在法治史上,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法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法治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法治之首要条件”。哈耶克指出,“法治之法”是自由之治的法律体现,而这种“法”兼具一般性和平等性,如果不对那些综合起来方使法治成为可能的全部原则进行考察,就根本无法充分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0、261-268、426页。可见第4、5条是使罪刑法定变得真正可能的必要因素。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其否定句式表达以及在刑法文本中所包涵的否定性行为规范(即禁止规范)意味着,刑法要保障每一个人合法预期的最大化实现(私域)。根据哈耶克的分析,从具体的习惯到法律的转变过程,要比从命令到法律的转变过程能更好说明此点。他指出,正是伴随着个人智识的发展以及打破习惯上的行事方式的趋向,明确陈述或重新阐释各种规则并且逐渐把对行动范围的肯定性规定转变成基本上对行动范围的否定性限制,才具有了必要性;而这种否定性限制,以某人的行动不侵犯他人所拥有的得到同样承认的行动领域为标准。*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页。这种禁止规范具有抽象性,即具体目的非依附性(意指独立于任何具体目的的特性)和形式理性(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理性,而是法庭论辩时控辩双方在相互争执时为自己的论述提供依据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理性)。这种抽象性和否定性意味着,我们并不拥有评断正义的肯定性标准,所拥有的只是何者为不正义的否定性标准,因此非正义才是真正的基本概念。*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以及该书第二、三卷,同出版社同年版,第65页。同时,这种禁止规范具有客观性,即它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既包括在司法过程中被阐明的规则,也包括更多的尚未阐明的规则。就是说,不是先有社会而后人们制定规则,而是社会因自发性规则的存在而存在。哈耶克指出,罪刑法定之“法”,所指的不只是立法者所颁布的成文规则,也意指那些一经形诸文字约束力即刻会得到普遍认可的规则。*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这种禁止规范又具有正义性,这是因为正义或非正义始终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些行动,而所谓应当,反过来预设了对某些规则的承认,这些规则界定了一系列情势,某种特定的行为在其中是被禁止或被要求采取的。*有学者将哈耶克意义上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特性概括为抽象性、客观性、正义性。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由此,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对于禁止规范需要把握以下两点:首先,禁止规范的内部性。“内部性”一词意味着禁止规范是社会自生自发形成的,立法者和法官虽然可予以一定程度的阐明,但禁止规范并不因这种阐明而不再客观,何况阐明只是相对阐明,而且尚未阐明的禁止规范要大大多于阐明的禁止规范,承认社会复杂性和理性有限性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一点。就此来看,我国刑法的内部性是在增强的。因为1949年以来,主流刑法观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从政策工具主义向法律正义的转变。1950年的《刑法大纲草案》,不光允许类推适用法律,还允许“根据人民民主主义政策判罪”。1962年《刑法草案》第27次稿第1条在表述刑法任务之时还插有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严格区分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的原则制定的”。直到1978年恢复刑法典起草,才开始在刑法内容上强调“结合”,这无疑是对政策工具主义有限而有益的纠偏。*相关史料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283、310、339、436、464、497-498页。到1997年,《刑法》第1条大大强化和扩展了刑法的生活基础,刑法的内部性趋于增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草案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中一些不具有生活基础的条文设计在最后文本中得以被删除,更是明证。
其次,每个人对禁止规范的无知性。由于禁止规范不是立法者或法官创造的,而是社会进化过程的结果,所以人们对它们是无知的。但是,社会自生秩序却能够将每个人十分有限的分立的规范知识整合起来,使每个人仅凭有限的分立性规范知识就能够安全地生活并分享任何个人都对之必然无知的整体性规范知识带来的文明秩序(百姓平日里无需不断温习《刑法》即是明证)。*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要知道,自发生成的东西较之人为建构(设计)的东西要复杂得多,正如精英们有能力组织一个计划经济,但没有人能够规划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任何人有能力设计的,而是芸芸众生自发行为的结果,理解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参见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182、241、270页。当刑法只是政策工具的时候,刑法就纯粹是官方的制造品,此时只有官员能够解释它,因为最了解它的人当然是制造者,就像对一件电器的使用最好是以厂家的说明书为准。刑法的解释权很自然地被垄断于制造它的国家之手,此时不可能有什么辩护空间,*张维迎说:“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拿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因为那套高度政治化而疏离生活的概念和用语,只有用体制性“知识”才能解释,对于这样的刑法来说,政治正确等于法律正义。而当刑法被放归生活,以广阔深厚的本土刑法生活及其形成和演化的禁止规范为基础之后,刑法就不再是政治体系“造”出来的了,而主要是从社会中“长”出来的,此时官员(包括制定它的官员)比一般百姓对刑法的无知感更强烈,学者们也会深感越研究刑法越觉得自己无知。此时,法官或控方对《刑法》规定的到底是什么,还能像政策工具主义时代那样继续保持自信吗?由个别国家机关独享刑法解释权还具有合理性吗?说到底,官员说什么是什么的执法逻辑对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已无能为力了,它不得不让步于使以生活为背景的辩护得以显示效用的司法逻辑。
刑事司法是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情势下所实施的具体行为依据刑法应否以及如何定罪判刑这种性质的案件,在法官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当面争执,最后由法官进行裁判的活动。因此,司法逻辑是一种情境逻辑,即在特定案件的特定情境中对被控的具体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不得不推出他的结论,但却不是仅从明确的前提中推出结论,而是从一种‘情境逻辑’中推出结论;当然,这种情境逻辑乃是以现存的行动秩序所提出的要求为其基础的,而这种行动秩序既是非设计的结果,同时又是法官所必须视之为当然的所有规则的基础。”*[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在一般规则之下作为特例来判决,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几乎所有的法系都是如此。”*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法律过程导论》,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15、23页。“每一案件的处理是多么的有赖于特定的情境”,“任何案件都必须依赖其具体的情境决定”。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这是我们理解以《刑法》第3条为核心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基于内部论和无知论,可以发现司法逻辑是任何人对之必然处于无知状态的禁止规范的知识分享机制和规范演化机制。因为作为禁止规范的刑法规范整体上是社会自生的,而对禁止规范我们缺乏知识,其中包括我们对生活中的具体情势以及刑法规范与之结合的方式及其自发演化所处的无知状态,所以任何主体对特定行为的刑法评价(实乃刑法规范的具体应用)都具有可论辩性。*关于这种可论辩性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远:《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建构探析》,载《法学》2014年第10期。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意味着刑事辩护对刑法规范知识的分享和刑法规范的阐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法律形式主义是一种偏离公正的司法逻辑的司法观,应予以警惕。法律形式主义热衷于用抽象概念进行法律推理和适用法律,脱离生活实际和实践要求,*波斯纳说,形式主义有三点让霍姆斯很反感:首先是它的概念主义和科学主义;其次是它的僵化特点,它酷爱将案件当作一套没有时间维度的资料,并且从中得出的原则本身也与时间无关;再次是法律脱离生活,形式主义处理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美国形式主义者赖以发现法律原则之线索不是来自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实践,而是来自以往的司法决定,其中大多数甚至不是美国的而是英国的。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其最终后果“是法律的关切与司法的关怀之间不断增加的疏离”。*[美]彼得·德埃里科:《法律是形诸文字的恐怖》,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法律过程导论》,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原因何在?因为遵循同一律的形式思维在对待对象时取其同而弃其异。*参见苏富忠:《思维论》,香港中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页。就是说,法律形式主义并非不沾染经验,不过它看到的只是过去经验与现下经验的抽象同一而非现实差异。要知道,用于表述或阐明刑法的工具是语言,语言虽起于经验却具有超验性(见第一部分相关讨论),这造成刑法文本的形式性,所以刑法文本才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不须随时修改。但是《刑法》作为刑法规范的抽象形式,与刑法规范的具体内容是相对同一而非绝对同一,*参见蔡枢衡:《刑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法律形式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把这种相对同一关系当作了绝对同一关系,于是把形式直接当成了内容本身。行动中公正的刑法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因为形式终究只是内容的形式,*康德为形式主义作了哲学论证。康德认为,任何受经验制约或与经验有关的“实质的”原理,都不能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标准,只有形式——“成为普遍立法的形式本身”,才是道德律令的最高原理。这样,“立法形式”成了道德律令本身,它舍弃了所有“实质的”道德原理所具有的这样那样的经验性质和感官内容。然而,要求与一切经验的实质原理划清界限,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康德的道德律令一涉及具体社会现象或问题,就无可避免暗中输进了非纯粹形式的规定。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0-291、298页。抽象也终究只是对具体的抽象,没有生活内容和具体情势与之结合,禁止规范就停留在文本上。已阐明的规范必须不断与未来生活内容和具体情势相结合才能在自然演化中保持其抽象性、客观性和正义性。所以法律形式主义导致法律不公正,在刑事司法领域其直接受害者自然是辩方,因为辩护最亲近现实和具体。
当然,在向行动中的刑事正义转变中,《刑法》因语言表述的抽象性与具体案件的具体性之间的张力而产生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必然凸显出来。“无论是哪种形式主义进路,它都使律师或法官无须同经验实体纠缠不清”;“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是通过仅仅在形式层面分析法律来保证的,这一层面的分析只要求探讨法律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当法律的结果取决于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事实之际,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就受到了威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历史上,当法律的不确定性再也无法回避之后,有人就通过把法律文本看作一个“框架”来维护法律确定性命题。凯尔森在法律的完整性诉求与法律的不确定性现实之间寻找答案,试图通过声称一般性规范是一种“框架”以解决这一紧张。据此,在一般性规范框架内,存在着为立法者所制定认可的所有可能性。法院如果将那些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加以适用,则它即是在适用法律。以《刑法》为例,在法定量刑范围内选择的任何刑罚在法律上都有效,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任何刑罚都无效。但正如恩迪科特指出的,把边际区域看作一个界限明晰区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任何明晰的界限把边际情形和明晰情形分开。对一项表达来说,在该表达明确适用的情形、是否适用尚不确定的情形、明确不适用的情形三者之间,无论是试图划定一条还是两条明晰分界线,都不可能。所以,规范不是一种给法院提供的确定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界限明晰的框架。*参见[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78-100页。可见,追求法律形式的静态确定性纯属幻想。恩迪科特说,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但不确定性论断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论断,它毫不怀疑法律表述和法律实践之意义,而是认为在某些案件中但不是在所有案件中,模糊语言的运用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论断对各种边沁式“标准裁决观”——即认为法官的任务只是赋予当事人法律权利和义务以效力的司法理论及法律理论提出了意义重大的挑战。*参见[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总之,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离开司法逻辑去寻找刑法的确定性理据只是徒劳,而消极哀叹刑法的不确定性亦会导致司法沉沦。历史上,在法律形式主义发展到极端之时,反形式主义思潮便开始上升。德国在法律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两方面都是急先锋。*法治最早在德国被抽离了实质内容而变为一纯形式观念。一战后,法律实证主义获得了最有效、最具影响的形式,即凯尔森“纯粹法学”。它将国家和法律秩序等而视之,否定“基本自由”,使立法权不受任何限制,将法治国变成一个极端形式化概念。另一方面,德国带有强烈政治技术色彩的统一进程强化了德国人根据预先构想可以重构社会的信念,于是法律实证主义同历史主义(非指“历史学派”)、自由法学派、利益法理学派一起,在法治思潮走向衰微的趋势下,源出于德国,传播于各国,19世纪末影响日隆。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313、251-256页。在美国,法律形式主义破产后,法律现实主义声称法律就是法官对你的案件所作的决定,从而使法官的司法裁量权扩张到令法律职业界不安的程度。*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7页。应该看到,法律确定不确定这类命题本身,毋宁是图像论的表现。这一语言观建立在逻各斯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上,逻各斯主义相信现象之后隐藏着本质,本质超情境地决定着事物的各种性质。真理是超越一切普遍为真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东西只能是意见。因此,逻各斯主义把“自己的真理”看作超越的真理,就可以完全不听取别人的意见,无视他者的存在,直至认为“他人是我的地狱”。尼采是第一个向逻各斯主义提出质疑的现代思想家。之后,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个自苏格拉底以来从未被问及的问题,生活世界开始被关注。现象学把以往哲学视而不见的“在世界之中”作为自己的课题。既然逻各斯主义超越具有虚幻性,“我不可能超越他者,他者始终作为我自己出现”的必要条件,那么“自己的真理”是片面的,他人的意见有可取之处,故“兼听则明”。*参见邱文元:《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明晰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9、53页。可见,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The Study of Criminal Law’s Spirit of Judicial Logic——the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Law’s Anterior Five Articles
Author & unit:LIU Yuan( Law School,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Judicial logic is one kind of objective logics, and Criminal Law’s spirit of judicial logic is also objective, which dema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minal Law’s spontaneity (internal nature) and nature of construction (externality). The first article is the quintessence of this spirit, in which the statements such as “related with” and “in order to” are the distinct reflections. In judicial logic, the prosecuting party leans to Criminal Law’s externality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article, while the accused party prefers Criminal Law’s internal natu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hird to the fifth article’s judicial logic- statutory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Criminal Law is the internal theory’s ontology and ignorance’s epistemology. The key to achieve criminal justice is not Criminal Law’s clarity, but of releasing control of dogmatism, the theory of image and externality, meanwhile, of discovering the path to criminal justice’s judicial logic from inter-subjectivity, contextual theory and Criminal Law’s internal nature.
spirit of judicial logic; criminal Law’s externality; criminal Law’s internal nature; contextual theory; Ignorance’s epistemology
2014-12-19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建构问题研究”(12BFX055)的阶段性成果。
刘远(1971-),男,山东章丘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哲学、司法刑法学。
D924.1
A
1009-8003(2015)02-0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