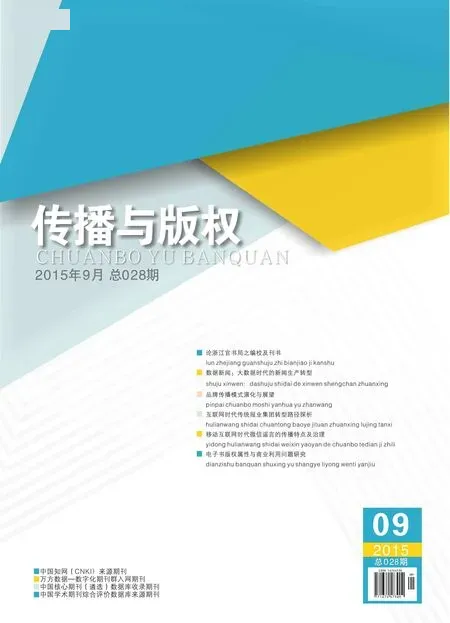论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从突发新闻的影响和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角度分析
张瑜婷 岳 廷
论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从突发新闻的影响和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角度分析
张瑜婷 岳 廷
主要选取突发新闻的影响和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两个角度,分别从媒体与美国社会的横向、时间维度的纵向来分析,探求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媒体;美国对华政策;突发新闻;负面报道
[作 者]张瑜婷、岳廷,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电视中心。
媒介,亦称传媒、媒体,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的公共机构。①约翰· 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杜,2004年。新闻传媒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技术手段来衡量,都是属于文化,②李敢、熊曙光:《论美国媒体及媒体外交》,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9卷第3期。其影响涉及方方面面,甚至是外交政策的制定。美国的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内政因素的影响。其中,舆论媒体以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既代表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在诘问中干预了政府决策。本文从突发新闻的影响和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两个角度,探求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一、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媒体与对华政策
2011年1月6日,CNN在网站首页的头条刊登了关于疑似中国研制出J-20的消息《New threat from China’s stealth jet ?》。很快,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分析:“标志着该国开发尖端军事技术的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美联社)”,“五角大楼错误地估计了北京发展军事新技术的速度(《航空周刊》网站)”,“中国在开发可能成为美国F-22战斗机对手的飞机(《华尔街日报》)”等。
在媒体报道J-20时,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美国的反应。据共同社报道,美国空军7日宣布,“将于下周晚些时候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嘉手纳基地临时部署15架最先进的F-22A‘猛禽’隐形战斗机”。美国空军表示,此次临时部署“是为了突出美国对于重要伙伴日本(的防务)的参与,展现确保整个太平洋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决心”。在这期间,媒体的对华报道起码起到了三个重要作用:提供信息、影响舆论、建议和监督政府决策③这符合《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作者从宏观上指出的“传播媒介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即决定公众议事日程、影响舆论等。。
“突发事件”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事件发生、发展的速度很快,出乎意料;二是事件难以应对,必须采取非常规方法来处理。④概念解释参考中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们选取的只是国际事件中涉及中美关系走向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于媒体在中美外交突发事件中影响力的问题,最早学界的看法是其作用极小,认为“事件发生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在受众中形成媒体的舆论影响”。但目前学者们却普遍认为:无论新闻是否会影响外交决策,突发性的新闻报道常常会迫使政策制定者迅速做出反应。
首先,新闻媒体提供和传递信息的功能在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尤其突出。首先,初期外交途径的信息往往不够全面,新闻媒体成为政府唯一的信息来源⑤徐海娜:《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3期。。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说:“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要多得多。”其次,“美国媒体很少介绍美中之间的政治关系”⑥语出《纽约时报》主编伯纳德·格维兹曼《美国媒体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而且美国媒体呈现多元化格局,难以形成统一的看法,公众舆论更难统一⑦王恩铭:《大众媒体与美国外交》,《国际观察》,1999年第2期。。因此,突发事件凭借仓促性、紧迫性的特征,新闻媒介的报道很容易成为受众眼中的“优势意见”,从而对反对意见产生压力而导致劣势意见的沉默、多数意见的螺旋扩展,进而影响舆论的诞生⑧正如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一样。。而舆论又对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二、美对华负面报道的内在逻辑
首先理清两点事实:一是美国人并不关心国际时事,这不只是对中国而言;二是CNN等美国媒体以负面新闻为主,因此首先要认识和区别这一因素的影响。
2005年5、6月份《时代》周刊题为《中国的新革命》的特刊中,包括《小世界中的大赌注》《沃尔玛王国》《赋予人民的权利》《他们同样出口污染》等多篇文章中,使用了大量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Repressive、infamous经常出现在中国人权的报道中,surge等词语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成“中国威胁论”的观念,这些具有隐喻和暗含的词语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印象”产生巨大影响,民众形成合意(即“舆论”)将影响美国政府制定新一轮的对华政策。
美国媒体一向标榜奉行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不承认新闻舆论导向作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没有意识形态特点和政治立场的新闻是不存在的。何英在《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2005年)中提出,按照奥克森伯格的分段方法,1979至1989年是美国对华赞美时期,而1989年至今是负面报道中国时期。在后一阶段,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基本上是揭露中国的所谓阴暗面,或反映中美之间的摩擦。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周刊等美国主要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1。①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34页。对华负面新闻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排华浪潮”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至1993年间,代表作是《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的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②吴霞:《是“强势威胁”还是“和平崛起”——分析美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发展”》,中国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156。。而这期间,美国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当年攻击中国人权和民主的重要由头;1995年台海危机前夕,《纽约时报》等呼吁李登辉访美的报道;2008年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西方媒体再次以“人权”来讨伐中国。
美国意识形态根植于“自由”的个人权利观和欧洲白人的价值观,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最大威胁。另外,企图把美国模式运用于世界的霸权主义理念,也与中国的反霸权传统格格不入,成为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所以,美国的深层文化基础和意识形态特点决定了其对华的基本战略,美国的媒体与政府在面对中国这一共同假想敌,双方立场是一致的。
三、结语
“媒体只是月亮,而非太阳,它只是反射太阳光。”③语出Nicholas ○.Berry《外交政策与新闻媒体》。一个国家的性格造就了其政府和媒体的灵魂,他们的观点时而对立,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媒体作为“风向标”或者“马后炮”④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身为“第四权力”永远不会与政治失去联系。本文以实例说明媒体提供信息、控制议事日程、影响舆论、监督政府的现实作用,也证明了媒体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决策的诞生。纵使目前从学术讨论的范畴看这一问题,角度不同,结论仍然有变数,但实际上,媒体与外交问题的背景和文化内涵其实是具有思考和研究价值的。
[1]李稻葵.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3]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4]Nicholas ○.Berry.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ess[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
[5]约翰· 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6]王恩铭.大众媒体与美国外交[J].国际观察,1999(2).
[7]徐海娜.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3).
[8]吴霞.是“强势威胁”还是“和平崛起”——分析美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发展”[EB/○L].http://www.ilf.cn/Theo/110223.html.
[9]李敢,熊曙光.论美国媒体及媒体外交[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