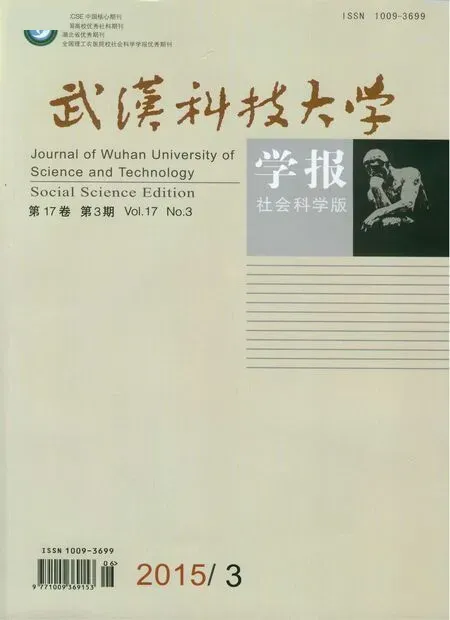空间批评的物质性维度——论本雅明的拱廊研究及其现代性内涵
杨有庆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自197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经历了所谓“空间转向”。空间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分支,已然成了当下人们审视和思考现代性、城市文化等问题的重要维度。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空间批评的先驱备受都市文化研究者的推崇,其对巴黎拱廊街的研究被视为都市文化批评的经典。《拱廊计划》研究从1927年开始,直到本雅明去世仍未完成,是其后期最主要的研究项目。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内,本雅明试图通过对拱廊街这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标本展开历史的、哲学的与文学的等多个层面的阐释,“从正面考察19世纪”[1]309,进而寻求人类乌托邦救赎的可能性,揭示历史的总体性趋势。因此,考察拱廊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缘何进入本雅明的研究视域,对理解其后期的思想尤为关键。本文试图从本雅明自身独特的城市体验、对超现实主义方法的扬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犹太神学的奇特糅合等层面出发,分析他是如何不断趋近拱廊这一城市空间标本并将其作为物质表征来阐释现代性的。
一、从柏林到巴黎的城市体验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认为,哲学取决于作为外部条件的真理事件,“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2]。所谓真理事件,就是人所遭遇的偶然性事件把人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状态中悬置出来,迫使人重新思考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现实。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化对本雅明来说正是这样的真理事件,尤其是柏林和巴黎这两座城市的变迁使他感受到现代人在城市中所经历的异化。
自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后,整个德国开始实施一种企图赶超英、法的现代化战略,德国在中欧崛起。到1900年前后,德国已经发展成为超过英、法的欧洲第一工业大国。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正值德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柏林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变的历史过程。
20世纪初,柏林的工业化和电气化发展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最具活力的城市。到1905年,柏林人口已经超过两百万,成为西欧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这一时期,柏林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许多铭刻着城市的过去与记忆的历史遗迹都湮没在纷繁的变迁中。本雅明的家在柏林的老西区,靠近著名的商业街“裤裆街”,从儿时起,本雅明就感知并认识了街道和整个城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柏林纪事》和《驼背小人: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本雅明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以空间为线索回忆了童年时代生活的柏林。在这两部关于童年的著作中,他利用打乱时空顺序的非连续性叙事方式描绘了20世纪初的柏林地图:动物园、老西区、街道、内阳台、屋后的庭院、祖母与姨妈的住宅、广场、公园、学校、农贸市场、火车站、滑冰场等。他在回忆的迷宫里寻找童年的记忆,以唤醒和救赎在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但目前已消失的1900年前后的柏林城市景观。
本雅明记忆中的柏林岁月,以某种隐晦的方式曲折地表现了当时城市化给人带来的冲击和空间体验。在《驼背小人: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的前言中,本雅明指出他是“在不可追回的社会发展必然进程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偶然经历中审视昔日的时光”[3]2。他企图通过这种审视“把握住那些包含着市民阶级子弟在大都市中所获得的经验”[3]3,通过对这些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的经验的展现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进一步揭示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所经历的异化。
在本雅明的童年记忆中,有轨电车的节奏编织着他的酣梦;那时间与空间各得其所的墓穴般的内阳台,那已经消失的西洋景艺术,那闪烁着英雄业绩的胜利纪念碑,都随着城市的重建消失在历史的瓦砾中;而作为现代生活的象征之一的电话机,那警报般的声音曾经使他心惊肉跳,带来某种类乎灾难的体验;时髦的骑自行车运动、外祖母家友善的门铃与温馨的房子、下雪的夜里依次亮起来的煤气灯以及名叫“弯街”的购物街等留下的美好记忆使他热血沸腾,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但同时,他发现了城市生活的另外一面,城市所造成的贫困、不幸与罪恶让他惊恐不已。这些童年时代对于城市的体验与兴趣伴随了本雅明终生,融入了他的思考和思想。
由于父母并非土生土长的柏林人,柏林对于本雅明来说始终缺乏某种家园般的归属感,但本雅明仍然把德国看作自己的故乡。1925年,他在法兰克福申请教授失败后,德国对他来说终于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温情,其后,他的兴趣和情感开始转向法国。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认为:“从1926年起巴黎在他心中获得了一个坚固的位置,他大多数时间在那里度过……他感觉自己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了,一有机会就回到那里去。”[4]就这样,本雅明在巴黎开始了“游手好闲”的生活,他说,“我直接把巴黎吸收进我的身心中……我感兴趣的是街道、公共交通、咖啡馆和报纸”,沿着开设着各种画廊的街道散步,“完全沉浸于巴黎生活的现象”[5]84。
对于巴黎的影响,本雅明说:“假如不是巴黎,我几乎无法将自己抛给最初城市生活的这些记忆湍流。”[6]202对他来说,认识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城市里迷路,就像在森林里迷路一样。当人在城市里迷路时,“标牌和街名、路人、房顶、亭子或酒吧一定会同游逛者说话,就像森林里脚下踩的吱吱响的树枝,像远处麻雀的惊叫,像一块空地突然而至的宁静,只有一朵荷花立在中间”[6]202。本雅明认为巴黎教会了他这种在城市里迷路的艺术,使他能够在墙壁、码头、艺术收藏与垃圾、广场、拱廊以及货亭等事物中发现现代性的独特语言。在他看来,巴黎是充满了奢侈品和时尚的“商品的洞穴”,人们的生活在商品的统治下成了某种“反讽的乌托邦”[7]89。他试图通过展示城市街道的迷宫将社会变迁和对于城市的无意识拼凑起来,使人们从现实的商品神话中觉醒。
汉娜·阿伦特认为,本雅明从柏林到巴黎的意义不是从一国到另一国那么简单,而是一次从20世纪返回19世纪的时间旅行[8]。在资产阶级商品废墟和垃圾中,本雅明重新发现了其文化影响了整个欧洲的“19世纪的巴黎”。他将19世纪的巴黎视为现代都市的典范、欧洲现代性的源头和发展迅速的“现代性之都”。他认为,对于游手好闲者来说,巴黎本身就是风景,形成了“辩证的两极:它作为风景向他敞开,同时又作为房间把他封闭起来。……令游手好闲者在城里闲逛时对既往的陶醉不仅在他眼前充实了感官印象,而且本身拥有丰富的抽象知识——关于已死的事实的知识,将其当作了经验过的和经历过的东西”[9]125。他惊奇地发现,在城市风景的迷醉中,现代人对城市生活带来的物质化和震惊无动于衷。现代人在城市中如梦游者一般,生活、欲望与记忆都被物质化了,但这种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却无人关注。因此,本雅明试图通过考察巴黎的物质性进程来揭示现代城市对人所造成的异化,将人们从对现实的无动于衷中唤醒,使其看清现代性所蕴含的风险与各种后果。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雅明将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城市的空间标本——拱廊上。拱廊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巴黎出现的一种商业街区建筑,它两边是店铺,两排店铺上面以玻璃拱顶连为一体。拱廊曾经充斥在19世纪的大都市,是店主们用来陈列商品和对公众开放的地方。当时一本《插图版巴黎向导》这样描写:“这些拱廊是奢侈的工业的一个新近发明,它们盖着玻璃棚,大理石镶嵌的走廊延伸到整个建筑群中,而这些建筑的主人们则联手从事这些企业。这些走廊从上面采光,两侧是最高雅的商店,所以,拱廊就是一座城市,一个世界的缩影,顾客可以在这里找到想要的一切。在突如其来的阵雨中,拱廊成了毫无准备的人们的避难之所,严格说来,为他们提供的是一条安全的人行通道——商人们也从中获益匪浅。”[9]124
自从1860年以来,拱廊不断被拆除,遭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到20世纪初,大多数拱廊已经被破坏了,人们也不再热衷于拱廊了。学者海默尔认为,正是这些过了它的黄金时期的拱廊,在它已经被取代而作为废墟之存在时“赋予本雅明后期著作以生命力”[10]112。
1925年本雅明在法兰克福谋职失败之后,兴趣开始转向法国,他对拱廊街的兴趣始于这一时期。1926年,他与一位热衷于法国都市文化的犹太人弗兰茨·黑塞尔合作翻译了普鲁斯特的作品。1927年,他们两人相约共同为一家杂志撰写一篇有关巴黎拱廊街的文章《一个辩证法的童话王国》。在写作过程中,本雅明搜集资料的范围不是仅限于拱廊街的话题,还包括了19世纪巴黎的各种景观,涵盖了巴黎一百年的现代性历史,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三年,直到1940年本雅明自杀前仍未完成,但他收集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1982年由罗尔夫·蒂德曼编辑出版的《拱廊计划》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著作,而是一千多页的资料、笔记、随笔和思想片段的汇编。
在本雅明看来,拱廊是现代性的某种具体而微的模型。随着工业的发展,玻璃被大量地用在建筑方面,巴黎即是个典型的玻璃城市。他认为,外部由无数玻璃镜子构成的拱廊像岩洞般辐射了整个巴黎,“在炫目的光中,在阴暗的角落里,过去变成了空间。古老的贸易在这些内部空间里幸存下来”[9]122。街道是集体的居所,这些玻璃拱廊扩大了街道的空间,打破了室内和室外的界限。在拱廊中街道展示为有家具的、为大众所熟悉的室内,这就使得方向更加难以辨认,使人更容易在城市里迷路。
本雅明认为,对于那些在城市里迷路的游手好闲者来说,“街道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街道引领穿过了一个消失的时代。它更加深邃,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不是私人的。……他识别出周围的一切;那不是来自他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过去,一个刚刚过去的青年时代,而是祖先或自己的童年”[9]128。拱廊街是过去时代的某种象征。因此,他试图将拱廊街这一历史“垃圾”作为19世纪巴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缩影,通过对其“原初历史”的解读来研究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以及对当下的影响。
二、超现实主义诗性实践的启迪与扬弃
1926年,本雅明访问莫斯科。这次考察的目的就像他在日记里所说,因为当时的德国“无依属的作家的地位遭到质疑,人们逐渐发现,作家(与最广义的知识分子一样)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在为一个阶级工作,并从这个阶级获得自己的代理资格。……人们很关心,在一个无产阶级成为雇主的国家里知识分子的遭遇怎么样”[5]91。但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他发现,知识分子在俄国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知识分子的各种组织中,最突出的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它支持专政的观念,甚至在精神创造的领域”[5]98。
莫斯科之行的失望、法兰克福求职的失利以及其后对普鲁斯特作品的翻译等因素都使他在情感和思想上日益疏离德国文化,开始亲近法国文化。在德国,他觉得完全脱离了他同时代的人,而在法国,路易·阿拉贡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强烈地吸引着他。
实际上,本雅明自超现实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对其十分感兴趣。布勒东在发表于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认为,超现实主义是通过把生活体验与感受用主观随意性的意象直接表现出来,使意识与无意识经验达到完美结合,最终使日常理性世界与梦幻世界共同构筑某种绝对的现实,即超现实。布勒东认为,只有通过一种不受任何理性控制的、“排除一切美学的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的自动记录”,才能以“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表达思维的真实过程[11]。超现实主义将梦作为体验来源的观点备受本雅明赞赏,他指出,“梦在世界结构里像一只龋齿,它会使个性松动。这种对自我的松动是通过沉醉来实现的,不过,这一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活生生的体验,它使人从沉醉中清醒过来”[12]193。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语言以一种富有魅力的断然方式进入梦幻世界”[5]140。在《驼背小人: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与《单行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关于梦幻与梦境的意象。他将梦幻意象当作经验和认识的来源,对他而言,梦是重新编织现实生活,使人从日常生活的平庸中清醒的神奇钥匙。
超现实主义试图打破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以揭示被日常理性所忽视的“另一种理性”,使人在超现实中重新感知和认识我们所生存世界的平庸之神奇。有学者指出,“本雅明的《单行道》则通过隐喻性的写作方式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13],即通过将一系列非连续性的碎片化意象不加修饰地直接展示出来,以表达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马赛克式的震惊体验。
本雅明在写于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之最后一景》中具体分析了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他指出:“从沉醉中获取革命的能量,这便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作品和活动的目标。”[12]199本雅明认为,超现实主义者通过日常事物的拼贴和并置编织的梦幻世界使人看到物之世界的贫乏,并从城市的超现实景观中发现了革命的能量。他们相信在看起来熟悉、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奇迹,只有造反才能揭开巴黎的面纱,使人们看到巴黎的超现实主义面目。正是从这个物之世界的客观偶然中,从日常生活的褶皱中出发,超现实主义通过拼贴来打破各种思维习惯的桎梏,以蒙太奇手法使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显现出奇特的魅力,进而消解了梦与醒、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所带来的对现实的否定,在经验和形象的领域,让人获得某种世俗启迪。哈贝马斯指出,在超现实主义“做秀的政治”或“诗意化的政治”等无意义行为中,本雅明发现了“诗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分裂被克服了”[14]。
在本雅明看来,对超现实主义的解读必须要与巴黎的城市景观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在作为现代性之都的巴黎,城市才完全以超现实主义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而超现实主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通过梦幻般的蒙太奇体验启发人们去重新认识城市之谜,发现那些藏匿于街道与建筑中的“辩证意象”和“世俗的启示”。
理查德·沃林认为,《超现实主义》一文应被看作是《拱廊计划》的绪论,“对于本雅明而言,超现实主义与无关紧要的客体、社会生活碎屑对应的救赎关系象征着一种诗性的实践模式,如果艺术想免于成为麻木不仁的东西,就必须采用这样的模式”[15]133。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也认为,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路易·阿拉贡的《巴黎农民》给了本雅明关键性的推动,促使他开始写作计划已久的关于巴黎拱廊的论文[5]137-138。
路易·阿拉贡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巴黎农民》创作于1924年,发表于1926年,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主人公在穿越歌剧院拱廊街时的一次观光。在这个拱廊街中他回忆了过去在许多酒吧和商店中的遭遇。在阿拉贡的描绘中,平庸的日常对象之上似乎笼罩着某种奇妙的光环,给人带来蒙太奇的审美感受。有研究者指出,“在他的文笔魅力之下,巴黎大剧院街上的那些小店铺隐藏着怎样含混不清的意义呀。在这些地方的混乱纷扰之中,他启开了没有锁紧的无限存在的大锁”[16]。阿拉贡在书中写道:“我们的城市充满了无以辨认的斯芬克斯,他们不会拦住路过的做梦人去问他们生与死的问题,除非他把他混乱的思考指向他们。但是假如这位贤人知道如何找到并询问这些无面目的怪物,他在那里发现的是自己的地狱……这些在大街上焕发光彩的、数量众多的、隐蔽着的拱廊,出于某个奇怪的原因,又被叫做过道……这些人类的水族馆已经被剥除了它们原初的生活,值得作为几个现代神话的储藏器进行思考。”[15]130
阿拉贡对拱廊的描绘以及他将拱廊作为“现代神话的储藏器进行思考”的思路,启发了一直对城市文化感兴趣的本雅明。本雅明在1935写给阿多诺的关于《拱廊计划》的信中也说:“我打开阿拉贡的书——《巴黎农民》,躺在床上,读两三页就得放下,因为心跳得厉害。这是一种警醒!多少年来,我已经没有这种阅读体验了,然而《拱廊计划》最初的框架正是缘自此时。”[17]351对本雅明来说,超现实主义使他发现了拱廊——巴黎这个被各种不断更新的时髦的商品构筑的现代性之都的文化标本。他将拱廊视为“商品资本的神庙”,认为可以藉此追溯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历史中被忽视的物质化进程,揭示其对现代城市人生存方式的影响。
虽然本雅明通过超现实主义获得了某种通往日常现实生活救赎之路的世俗启迪,但他对超现实主义却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的。“对他而言,跃入无意识的革命乌托邦的狂喜和超现实主义的狂喜好比是打开他自己世界的钥匙,为此,他探索了完全不同的、精确的、一丝不苟的表达形式”[15]134。他批评超现实主义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乐观主义使其很容易陷入审美自律之中,在日常事物被偶然性撕成碎片的意外惊喜中退缩到个人梦幻世界中,因而缺乏真正的历史性。对他而言,超现实主义犹如药引子,因为蒙太奇原则可能是某种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的方法,而通过蒙太奇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最细微之处发现总体性的存在。
本雅明的拱廊研究是受阿拉贡的启发才开启的,但在他看来,阿拉贡始终停留在梦幻的世界中,缺乏某种唤醒现实的乌托邦向往和力量,而他通过拱廊展开的研究是要“把神话消解到历史的空间中去”[1]310,通过唤醒19世纪的巴黎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秘密。研究者海默尔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本雅明在超现实主义中发现了一种理解日常的诗学,但是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的采用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另辟蹊径。……超现实主义拥有戳穿现代性的迷梦的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兑现。”[10]104超现实主义虽然完成了理解现代城市生活的诗学运作,但却沉迷于梦幻世界中,不能对城市生活产生的现代经验进行批判性探究,缺乏真正的历史性。本雅明则通过拱廊这一城市生活物质标本,运用超现实主义文学蒙太奇的方法爆破历史,探究物质实践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及其变化。
三、“政治的和神秘的”:废墟上的救赎批评
1915年,本雅明认识了格哈德·肖勒姆,他们两人具有相同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而且都对形而上学感兴趣,厌恶僵化的学校教育,坚持独立思考,这些共同点使他们开始了毕生的友谊。肖勒姆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来成为著名的犹太教学者,尤其是他对犹太教卡巴拉传统的非主流阐释,更是影响巨大。有研究者指出,正是肖勒姆引起了本雅明对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迷恋以及对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18]。肖勒姆使本雅明发现了认识现实的另外一个维度——神学,特别是犹太教神学的末世观念与弥赛亚思想对本雅明的写作和思想产生了终生的影响。本雅明曾坦言:“我的思想与神学的联系就如同吸墨纸与墨水的联系,它浸透了神学。如果你只根据吸墨纸去判断,那么所写的一切都不存在了。”[1]326
但本雅明所谓的“神学”以及弥赛亚情结与作为宗教的犹太宗教及其宗教实践无关,而是“一种综合了神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历史哲学,目的是在一个充满了动荡、危机与矛盾的现代世界思考真理和救赎问题”[19]375。本雅明这种具有神学内核的历史哲学源于肖勒姆对犹太教卡巴拉传统的非主流解释。“卡巴拉”为希伯来语kabbala的音译,意思是“传统”,最初是《塔木德》的一部分,后来用来指称一种口传的律法,被理解为对《圣经·旧约》的一种带有实践性和经验性的晦涩的阐释传统。
肖勒姆对卡巴拉的阐释与传统的实践性阐释不同,他将它理解为“一种玄妙和思辨的哲学,而不是宗教现象,终极目标是在世俗的世界中思考永恒真理问题,或用肖勒姆的研究者戴伊尔的话说‘是勾勒神的世界的地图……可用作地图,指导一个人走完一个旅程’。也就是说,肖勒姆的卡巴拉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历史总体性的宏大叙事”[19]377。本雅明接受的犹太教神学正是这种与实践性无关而侧重玄思的宗教思想,与他早期醉心的形而上学传统一脉相承。
1919年,本雅明结识了恩斯特·布洛赫。布洛赫从犹太教哲学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革命和宗教结合起来,认为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源于弥赛亚冲动。1924年,本雅明与布洛赫一起在西西里度假时结识了苏联女导演阿西亚·拉西斯,对拉西斯一见钟情,这次邂逅对本雅明转向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后来,在布洛赫与拉西斯的思想熏陶下,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与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并于1929年在拉西斯的介绍下认识布莱希特。从此,本雅明在情感上和思想上趋向了马克思主义。
但本雅明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对犹太神秘宗教思想的兴趣。他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力图创造一种可以同时包容这两者的独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两面性造成了本雅明思想的另类和复杂,也使得他的思想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将之称为“救赎批评”,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那个充满永存不朽的过去”[14]412。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比作穿着土耳其盛装、叼着水烟筒端坐在桌边移动棋子的牵线木偶,而犹太神学则是躲在暗处通过线绳操纵木偶的棋艺高超的驼背侏儒。他在批评卡夫卡的文章里指出,卡夫卡“同时把握着两个目标,即政治的和神秘的”[7]65。其实这也是他本人思想的目标,试图将政治与救赎合为一体是本雅明著作中一个相反相成但又贯穿始终的主题和目的。他的最终目的不是神学,而是现实政治,他试图通过神学的维度来实现对历史总体性的弥赛亚主义救赎。
在本雅明看来,历史并非在同质的时间中不断进步的过程。他将同质化的历史时间与由弥赛亚式时间碎片构成的当下对立起来,进而把历史划分为历史时间与弥赛亚时间两种类型。他认为,整个历史是由历史时间和弥赛亚时间的辩证关系构成。受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本雅明相信历史具有终结性质,而救赎的观念则是一种“在概念的风帆上的终极之风”[1]328。学者刘北成指出,“这种终结不是‘进步’的完成,而是对‘进步’的否定,是对‘现在’时间中被排斥的异质因素的肯定。”[5]28-29
本雅明认为,那种进化论的历史观念,其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假象,以掩盖历史事件中的革命契机。这种历史观缺乏批判性,将现实当作目前可见的既成之物来看待,“漏掉了那些传统断裂的地方——漏掉断裂之处所留下的奇峰险崖,而这些却提供了翻越过去的立足点”[1]330。在本雅明看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连续性把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原理,可以发现同质的经济史、法律史与文学史等都是不存在的,历史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语言文本,并且过去的各个不同的时代被当下的史学家触及的深浅程度也有差别。
因此,本雅明认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把一个时代从物化的历史‘连续性’中爆破出来,但同时它也炸开一个时代的同质性,将废墟——即当下——介入进去”[1]330。他相信,辩证法的特征就在于对新对象使用新方法,而进步的观念只有在时间被打断时才会如同黎明的清爽般第一次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就在于对历史连续性的爆破,因为历史对象不能被锁定在时间的流逝中,亘古以来的历史叙事都是挑选对象然后“嵌入历史的连续体中去”,这就掩盖了历史的各种力量与利益关系。只有将历史对象从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出来,才能发现其中历史冲突的形式和内在蕴涵,实现真正批判现实的功能。
本雅明指出:“唯物主义的史学方法并不是任意选择对象,它不是把自己牢牢拴在对象上,而是将对象从连续的序列中松动出来。”[1]332本雅明将对现状的否定、历史的总体性与弥赛亚主义结合起来,从弥赛亚主义的角度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救赎。在他看来,弥赛亚的具体化就是重构一个充满了突爆、断裂和骚动不安等潜在革命能量的历史,并藉此打开一个救赎的空间,寻求整个人类的回归之路。
本雅明所划分的世俗的历史与弥赛亚救赎,表面看起来是相反的两种历史观念,前者追求世俗的利益和进步,后者则否定世俗中的历史秩序,但它们却经常相反相成,对本雅明来说,总是在否定与批判的同时力图指向终极旨归——救赎。在他看来,“历史的进程越是加速,救赎越是迫切,救赎就是寻求打断这个盲目的进程,修复破碎的总体性”[19]381。正是从这种通过救赎来修复破碎的总体性的理论目的出发,本雅明始终关注巴黎拱廊这一19世纪资本主义标本,试图通过对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过时商品的分析,以爆破物化历史的连续性来揭示历史的总体性,寻求人类解放的乌托邦。
总之,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的规模与数量急剧增加,城市越来越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活动空间,城市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本雅明在其独特的城市体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以及一种糅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多种立场的融合下,发现了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的物质性向度所蕴含的巨大意义。通过研究19世纪巴黎城市的缩影——拱廊这一城市标本的“原初历史”与历史变迁,揭示巴黎现代性的物质进程,修复破碎的总体性,进而实现对历史总体性的救赎与回归。本雅明的思想虽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拱廊研究中对物质性过程的强调和唯物主义方法的运用对当下探讨城市化与现代性问题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之N:知识论,进步论[M]∥汪民安.生产(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彼得·霍尔沃德.一种新的主体哲学[M]∥汪民安.生产(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1.
[3]瓦尔特·本雅明.驼背小人: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M].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M].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30.
[5]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M].潘小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7]杨小滨.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8]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M]//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9.
[9]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导论[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M]//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67-68.
[12]陈永国.本雅明文选[M].贾顺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王才勇.译者前言[M]//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
[14]尤金·哈贝马斯.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M]∥西奥多·阿多诺,雅克·德里达.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31.
[15]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M].吴勇立,张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6]伊沃纳·杜布莱西斯.超现实主义[M].老高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45.
[17]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关于《拱廊计划》的通信[M]∥汪民安.生产(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8]居伊·珀蒂德芒热.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M].刘成富,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49.
[19]郭军.卡巴拉传统中的阐释学[M]∥汪民安.生产(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