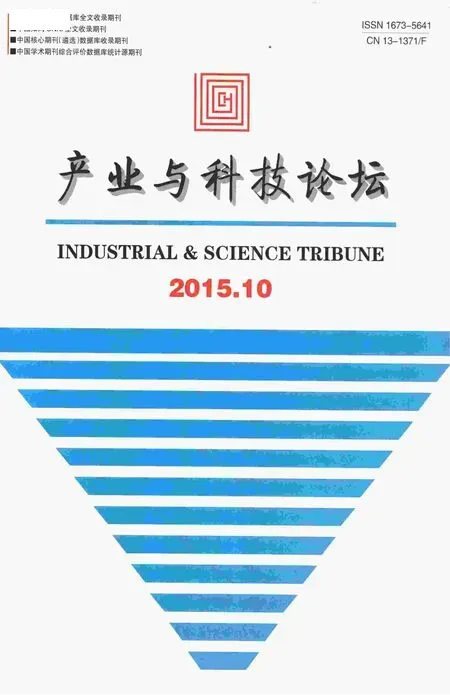网络流行语在外国影视翻译中的应用
□张 璐
随着电影文化的流行,很多国内观众对欧美影视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观看美剧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欧美影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可是能够完全听懂英文影视作品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对于这些影片的翻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大部分观众一般只能观看译制片或带字幕翻的原版片,而后者由于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声响效果,得到了更多观众的青睐。作为一个和电影同时诞生的专业行业,字幕翻译正吸引着来自学术界的更多关注。通过研究近几年的影视字幕翻译,可以发现网络流行语开始出现在字幕翻译中,并逐渐形成了翻译“本土化”的趋势。因此,如何在保证字幕翻译的品质,在遵循传统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前提下,正确使用网络流行语,是当前影视字幕翻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网络流行语概述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一诞生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神速。目前正在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版本是“浮云水版”。网络语言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图片,起初主要是网虫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的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特定语言了。网络上冒出的新词汇主要取决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如果那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人们就可以接受。
二、字幕翻译的特点
与配音和画外音翻译相比,字幕翻译保留了原有的音轨,对语言学习有积极作用。但是字幕翻译也有可能影响画面的完整性,同时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注意画面、音轨和字幕。而字幕制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制,翻译者往往需要压缩文本,减少信息量,如果观众对于源语言不是很熟悉,就会引起对情节的不理解或曲解。在外国影视作品刚进入中国时,配音是主要翻译方式,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外语普遍不熟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开放,中国人经历了第一波美剧热潮,以《老友记》和《成长的烦恼》为代表,当时仍旧以配音为主,但发行的光盘中往往是字幕翻译。而当以《越狱》、《迷失》为代表的第二波美剧热潮在2004年来临时,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众多英语学习者和爱好者,字幕翻译开始取代配音翻译成为影视翻译的主要手段。
字幕翻译的主要限制因素包括:在翻译语言、文化和认知问题上的难点、口头语向书面语的转化、以及不同观众群体和时空限制。在这些因素中,时空限制即文本压缩给翻译者提出了不少难题。空间限制意味着每屏只能有两行字幕,每行不超过34 ~37 个字。翻译者还要根据电影节奏调节字幕,使字幕和画面、声音同步。在这种限制下,翻者需要删除不必要的信息,将文本压缩到合适的大小和长度。文本压缩意味着要将原信息量至少压缩三分之一,尤其是演员语速较快、多人对话时,或者导演希望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上时。文本压缩往往通过对句型的简化实现,包括重新组织、总结和改编。字幕的这些限制因素不仅仅对翻译者提出较高要求,同时也会让特定的观众群体感到难以理解。儿童观众一般都适合观看配音的影视作品,因为他们对母语更加熟悉。对源语言完全没有了解的观众一般也不适合观看字幕翻译的作品。而对源语言有一定了解或正在学习过程中的观众能在字幕的帮助下更好地欣赏原声作品。
三、网络流行语在字幕翻译中应用的策略
(一)字幕翻译的“归化”选择。翻译的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是“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二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第一种方法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是“naturalizing”(归化)。这两个概念后来被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采纳,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正式提出。韦努蒂认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即要求译者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区分的。
就影视字幕翻译而言,由于每部影片的台词中都会包含一定的、不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文化信息,译者必然会遇到“异化”和“归化”的选择。“异化”有助于向观众引入新事物,帮助观众了解英美文化;而通过使用目的语受众普遍接受的表达方式,“归化”后的语言更地道,易于理解。某种意义上来讲,字幕翻译中的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正是“归化”的体现。鉴于字幕翻译的特殊性,为了便于观众迅速理解,对于文化背景深奥或某些难以理解的习语俚语,就字面直译,观众很难理解其信息,“归化”显得更为合适,因此恰当利用网络热词的“归化”值得尝试。早在2006 上映的《加菲猫2》中,就根据片中角色特征,把“非常”翻译成“灰常”;接着,在《功夫熊猫2》中熊猫阿宝说:“把神马都当作浮云。”这些网络热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大银幕上,带给观众全新而陌生的审美体验,而这些接地气的“归化”字幕翻译也由此逐渐被观众所接受。
在《里约大冒险》中“But just for argument sake,what are you doing?”字幕翻译为“弱弱地问一句,那你想要干什么?”,如果按照原文“But just for argument sake”的说法,译者很难将影片所表达的意思传递给观众。而“弱弱地问一句”这句最新兴起的网络用语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体现了当时角色当时尴尬的表情,更很好地刻画了角色胆小羞怯的性格,让观众也觉得亲切,而且也符合影片整体的轻松幽默特点。“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字幕翻译为“我是来打酱油的”。这句经典的台词出现在猴鸟大战的场景中,一只小鸟怕惹祸上身便说了这句话。原文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那该如何处理呢?根据当时的画面场景以及故事的发展,“打酱油”既表达了“与自己无关,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十分切合原文想表达的意思,而且符合其搞笑风格。同样的,“I know i’m not pretty birdie,but I used to be a quite a looker,a star”字幕翻译为“别看我现在长的很纠结,但是我以前却是个英俊潇洒的大明星”,相比翻译成“我知道我不是一只漂亮的鸟儿”,网络流行语的恰当使用更加容易打动观众。此外,现在比较流行的美剧里面也出现不少“归化”翻译:比如在《神盾局》第二季中男主角Grant Ward 说了一句“I am a meat and potatoes guy”,字幕翻译为“我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男人”,“接地气“的翻译不仅充分表达了主角当时调侃的语境,而且也很容易让观众快速接受。
不过,并不是所以的“归化”翻译都会得到人们的接受,比如当《黑衣人3》和其后上映的《马达加斯加3》也来赶这个时髦时,却引来观众的热议:“接地气”和“发挥过度”的言论各执一词。本文作者认为部分“归化”翻译并未能很好的表达原文的韵味。例如在《黑衣人3》中“I think I just saw a tooth in that thing,or claw,a hoof”字幕翻译为“我真的怀疑他们用的是地沟油,瘦肉精”,就把原文隐藏的外星生物入侵的含义完全忽略了;而探员k 说的“I keep emotion out if it”被翻译为“这叫老当益壮”,完全没有体现探员k 自认面瘫的自嘲,脱离了影片原来的内容及幽默感。
(二)字幕翻译的基本原则。字幕翻译者在翻译中必须遵守一些规则。一是通顺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影视翻译中,“信、达、雅”三项原则恐怕以“达”最为重要。为了“达”(通顺),有时不得不略微牺牲一点“信”(忠实)。影视翻译内容不是科技论文,不是法律文书,也不是商业合同,不必要求其绝对忠实于原文。如果使用一般的语言就能够完整得体地传递信息,那就没有必要为了取悦观众或造成戏剧化效果而使用不那么准确或不必要的网络流行语。翻译不是个人才艺秀,它是一项面对各种观众群体的服务,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外国影片。在不违背这一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地运用网络流行语,不仅可以传达影视作品的幽默,更能很好地服务于对象群体,使观众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捧腹大笑。二是关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网络流行词并在合适的语境中使用:多加谨慎,三思而用。网络流行语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是把双刃剑,用得好能收到满堂彩,反之则弄巧成拙。规则很简单:选择只有那些历经过时间考验,为大多数观众所知的词。至于那些“新”词或意义不明的词语,最好不要在字幕中使用。尤其对于业余字幕翻译者来说,尽管他们的创意和才华值得表扬,但有时候传统的方法也有它的妙处。如果把强烈的个人风格放到一边,业余翻译者们应该意识到字幕翻译的最终目标,即用简单准确的汉语将一部外国影视剧呈献给观众。如果在某些场合网络流行语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不应该使用。
四、结语
总体而言,“忠实”、“通顺”是衡量任何形式翻译的基本标杆,由于受影视其本身艺术形式限制,在不违背原片信息、妨碍观众观影体验的前提下,字幕翻译为追求通顺简洁,偶尔跳过“忠实”,进行再创做无可厚非。作为商业大片,与流行文化的结合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便是成功。有理有据地巧妙运用,让本土化的流行语为影片服务、为观众服务才是在字幕翻译中借用流行语的根本准则。
[1]钱绍唱.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2000
[2]赵速梅.论影视作品字幕翻译的两个不同层面——影视作品文本翻译与字幕翻译的不完全重合关系[J].外语学刊,2008
[3]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Routledg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