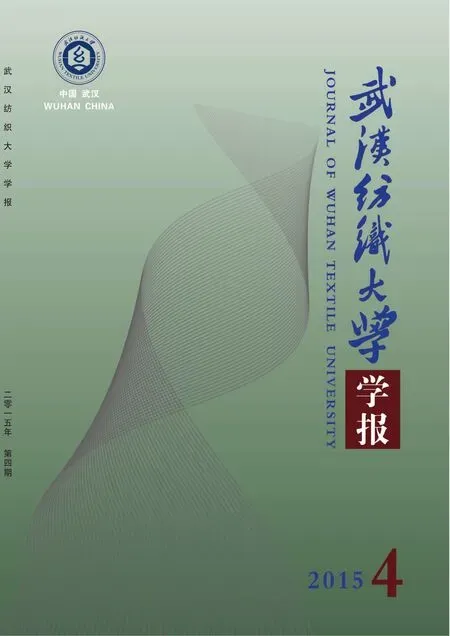农村人际关系的结构性要素及其变迁
熊 峰,余 盼
农村人际关系的结构性要素及其变迁
熊峰,余盼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农村人际关系结构发生重组,致使重视伦理、强调血缘、轻视利益的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形成利益日益凸显、血缘意识淡化、伦理约束弱化的趋势。但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本质和“人情”规则没有根本变化,仍是制约农村人际交往的结构规范。
血缘;伦理;利益;人情规则
人际关系是个体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联系,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构模式。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人际关系模式寓于社会结构中,体现整个社会结构的普遍要求,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人际关系相应的变迁。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历经分化重组,人际交往的社会环境随之变化,农村人际之间关系结构的变迁正是这一过程的深刻写照与真实反映。
一、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构成要素
首先,血缘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基础性要素。关于中国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研究很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揭示了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结构是根据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来确定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费孝通所举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例子,表明造成这种亲疏远近的中心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地缘只是血缘的投影,在二者之中,血缘更为根本和重要。在传统农村社会,“己”是被“家族和血缘”包裹着的,是从属于家庭和血缘的个体,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可能。尽管“己”是人际关系结构中的最小社会实体,但是“己”没有独立的权力和地位,根本无法割裂血缘的纽带而独来独往,因而传统人际关系的意义单位不是个人而在于“家”,人际交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庭、家族、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关系,家族、血缘思维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思维定势。传统乡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安土重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际关系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固定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范围内。“血缘远近决定并固定了关系的远近,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1]因而以血缘为核心的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具有“远近差序”、“内外有别”的封闭性和壁垒性特征。可见,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模式起源于血缘关系,其实质是先赋性关系,是家庭、家族、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凝固的产物。
其次,儒家伦理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规范性要素。血缘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先天性,而是与之相印合的文化内涵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儒家文化赋予血缘关系一种符号内涵,在定位上转化为一种差序性的伦理关系。传统儒家伦理认为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五伦关系结构中,即父子、夫妻、兄弟、君臣及朋友。这五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三种家庭关系,其代表儒家所强调的“亲亲为大”。尽管儒家伦理道德要求“仁者,爱人”,可以将“亲亲”之爱推至一切关系,但“亲亲”才为人道之始,血缘伦常才是人际关系的核心。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儒家伦理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平等的爱每一个人,因此,儒家伦理的“爱”是一种“等差之爱”、“差序之爱”。儒家伦理所讲的“伦”,指的也正是处理个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各种伦理关系就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是一种“伦理本位”,“中国人处处以他人为重,这种种关系即种种伦理。”[2]“伦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如尊卑、贵贱、上下、长幼、亲疏等;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应建立的关系的种类,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3]可见,儒家伦理使人们在实践中承认一切由于先赋性身份地位所造成“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差序性关系,同时也规定了人与人关系网络中尊卑上下的等级纲纪。从这个角度看,伦理文化造就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在定位上以道德伦理为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在日常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差序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显现“伦理本位”的道德烙印。伦理内在于农村人际关系结构之中,构成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要素。
最后,利益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中的隐含性要素。传统人际关系通过日常交往来维系,乡土社会的日常交往受制于亲密的血缘关系和制度化的伦理道德,表现一种礼尚往来、表达情意的人情互惠。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情关系除了相互支持的实际意义外,更本质的是“表现互惠”的符号意义,更加强调血缘情感和伦理义务而不重视利益得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结构中完全没有利益因素,如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所举的邻居跑到大老远的街市上算清,而不在门前算清的例子,就说明传统农村人际关系中本身存在利益交换关系,既包含利益也包含人情,二者混合不清很难分开,但是到一个“无情”的场合将人情“冻结”就可以当面算清。俗语所云“财上分明大丈夫”,正是对利益交换的充分肯定,而“亲兄弟,明算账”更是将利益交换的原则直接带入亲情关系中。可见,“亲情中也渗透了交换的因素,亲属、熟人之间的交往也要衡量回报的大小”,但是传统人际交往必须“在利益和亲情之间进行权衡:获利尽可能不破坏亲情关系......,交换关系蒙上一层亲情的面纱。”[4]因此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乡土环境中,对于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利益因素既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完全忽视。因此,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训下,农村传统人际关系不是基于经济理性而是基于“伦理规定”的社会事实,以一种人情互惠的状态呈现,但这不表明人们不再想利,传统人际关系中完全没有利益因素的渗透。尽管利益在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不凸显,但也是其构成中不容忽视的成分。
综上所述,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主要体现为血缘、地缘、伦理、人情等,并以血缘和伦理为基础,利益的成分受制于伦理和血缘关系而不凸显,更多地以一种互惠性的人情方式表现。血缘和伦理展现了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横向的亲疏关系和纵向的等级关系,呈现一种多维、立体的关系网络模式。血缘的先赋性和伦理的制度化使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固定性和封闭性,呈现一种“内外有别”的状态。
二、社会变迁中农村人际关系要素内涵的变动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按照严格的亲亲、尊尊、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间的等级秩序为主要原则,以血缘为基础、宗法为主导的封闭而固定的存在。传统社会以宗法伦理为基础,强调等级的长幼关系和男主女从的尊卑关系是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核心,子女唯家长之命是从,族众唯族长之命是从,而女性在社会地位更加低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仅体现出传统礼治道德对血缘关系的制约,也反映出伦理等级关系的制度化与不平等。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从属于家庭或血缘,没有独立的权力和地位。近代以来,传统乡土社会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剧变。清末民初以来,国内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渗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发酵,产生了对平等自由身份的需求。西方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五四运动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等对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宗法思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及改造。在一些受民主思想的影响较大的农村地区,传统的等级道德观及宗法制度受到很大冲击,西方的近代民主、平等和独立的观念进一步传播,家长权、父权、夫权、族权开始削弱,家属间、父子、男女、夫妇间的依附关系开始松弛。“尊尊”“男女有别”的等级伦理关系开始弱化,人与人之间已不存在制度化的“尊卑上下”,个体之间关系在人格上趋于平等,削弱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对个人的约束力,势必引发传统血缘关系松弛、弱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广大偏远农村地区仍在封闭的“小天井”里沿历史的故道彷徨,传统社会的经济根基并未有动摇,传统血缘与地缘统一的聚居的组织形态没有变化,孕育家族血缘文化的社会环境未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从总体上看,尽管传统农村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渐进的、并不普遍的变化,但血缘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主要人际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系列运动更替使国家力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同志”普遍关系代替了朋友和亲属的个人关系,“同志”要求对社会上的所有人一视同仁,血缘亲疏的差序式关系被否定,在朋友之间、亲友之间、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变成了政治关系。“亲不亲,阶级分”,农民开始忠于自己的阶级派别、组织,在政治关系面前血缘关系变得软弱。政治身份取代血缘身份成为划分群体的标准,农村人际关系从血缘伦理关系到国家取向的政治契约关系演变。民国时期由于“国家权力未有延伸”而相对保持稳定的乡村地区,也逐步被纳入国家政治范畴之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开始由道德主导向政治主导嬗变。国家运用政治和行政权力,以政治运动为武器,取缔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族制度。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宗族制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各种形式的批斗会使农民从传统血缘、伦理关系中剥离出来,建立了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同志关系。同时,计划控制成为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和权力,失去了资源分配功能、“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利益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是来自这里的时候,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5]这种政治色彩甚浓的社会运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统伦理中的尊卑长幼之分向阶级色彩浓厚的“平等”社员同志式关系转变,进一步分化了家族伦理对家族关系的整合功能,家族权威的合法性遭到颠覆,势必会给以血缘为基础的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巨大冲击。但是一些地方“瞒产私分”的现象表明集体性组织的表象下,农村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仍以隐性方式存在,影响着农民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形式,促使家庭部分生产资料和全部生活资料所有权的回归,家庭利益的主体性日益显现。家庭主体性的回归意味着传统社会的“亲亲之义”和血缘意识在人际关系的构建中又重新发挥作用。但这种血缘意识在家族层面由于缺乏公共财产基础和宗族权威合法性而日渐淡化,人们日常生活中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同族的人只有“人情往来”时才会聚集在一起,传统中的建祠堂、修族谱等礼俗活动越来越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的房支、宗族、家族等外围血亲联结日益松散。但“农村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密依赖感大大增强,家庭内核关系更加稳固,家庭之外的外围关系不断更新,呈现‘内紧外松’的状态”[6],更加强调家庭本位模式。传统农村血缘关系的封闭性和固定性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拟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也可以加入到人际关系网络中来。“这种拟亲缘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感情+利益’的关系”。[7]这意味着传统只以血缘亲疏决定关系远近的标准发生变化,利益成为决定人际关系远近的实质。市场化所带来的功利性价值观及人口流动,当人们不再受制于土地,传统道德约束机制日益失范,传统“重义轻利”的社会关系向功利化方向显现,人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物化”,“资源互换”成为“人情互惠”的首要意义,血缘认同、情感成分越来越淡化。尽管人情关系中利益成分日益增强,传统道德随着社会变迁成为一种“虚礼”,但“‘攀关系、讲交情’的盛行不衰又说明利益联系必须披上‘亲情’的外衣才能让人们在心理上感觉更加可靠”[4],“人情”仍然以一种“礼尚往来”的面相来约束着人际关系的发展。正如有调查显示,村民最痛恨的人际行为中,“见利忘义”成为选择比例最高的一项,但在现实中,人们却没有表现“视利为污秽”,无不在竞相逐利。[8]因此,市场化的“经济理性”与传统的“血缘人情”成为农村社会转型中两种重要的人际交往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以来,农村人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拟血缘关系的加入使血缘关系的范围逐渐扩展,标志着农村人际关系中的工具性因素日渐凸显,逐渐呈现一种实效性互惠的状态。传统人际关系受伦理制约表现着一种不凸显利益的人情关系,但随着政治改革、经济转型、文化变迁道德伦理的制约力逐渐弱化,农村人际关系愈发理性化、功利化,利益元素愈发明显。但是传统人情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并不是一种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呈现一种双元并存的状态,都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性元素和结点。
三、讨论与结论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理性化特征。理性化又包括以工具为导向的形式理性化和以价值为导向的实质理性化。实质理性化以契约和制度为基础,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用契约来概括,并形成了公平正义的普遍性观念。而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实质是一种形式理性化,逻辑思维是私利性的,它总是将私人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关系都是私人性的,具有特殊主义的特征。帕森斯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一对模式变项来描述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特征,特殊主义取向的属于传统人际关系的特征,而普遍主义取向则属于现代人际关系的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以血缘和人情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熟悉和陌生的内外之分;而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以理性为基础,按照契约来确定信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内外之分。在当代中国,契约理性并没有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私人性关系仍然是农村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家族式乡镇企业、村官家族式腐败、日常人情往来的大量存在表明农村人际交往的图式仍然是以人情和关系为基础,尽管村民不再受宗法伦理和家族血缘的制度化约束,但家庭血缘关系成为人际关系结构中更加坚固的内核,当代农村的个体仍然无法摆脱家庭血缘的包裹,是一种“家我”。同时,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个体很难做到“不求人”而独立生存,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与搞好人际关系获取自身利益。个体不仅仅是“家我”,而且是一种关系体,是处于种种社会人情关系中的个体。可见,尽管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要素以利益为核心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但人际关系结构中特殊取向的结构图式并未有发生彻底变化。正如吉登斯所言的那种“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是那些日常活动过程中不断被运用的程式化的东西。”而在中国社会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正是费老所说的“意会”规则,即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不言而喻的某种境界。“招呼”、“知会”、“告知”等不仅成为人们交往、交流的规则,而且还在不断维持着“意会”基础上的关系差序再生产。这种人际关系中“亲疏远近”和“内外有别”的人情差序已经成为村民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倾向和文化结构。尽管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的利益成分日渐凸显,但其差序本质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亲疏远近”和“内外有别”的差序关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人际交往中的人情规范并没有彻底变化。差序关系结构及其衍化的默契规则,已经世代传承并积淀于人们的行为习惯中,同时,这种行为倾向和意识系统又反过来支撑着人际关系结构在过往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中能动地建构及再生产。因此,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式过程,传统人际关系结构特质在转型中与现代化发展相融合,形成一种双元特质的结构模式。
[1]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社会学研究,2003,(01):21-29.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80-93.
[3] 潘光旦.政学刍议[M].上海:观察社,1948.113.
[4] 何君安,刘文瑞.权力、利益、亲情的冲突与嵌合:再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青海社会科学,2013,(03):111-116.
[5]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05):22-32.
[6] 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9,(01):64-95.
[7] 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01):8-13.
[8] 乐国安.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50.
The Structural Factors of the Countrysid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ir Changes
XIONG Feng, YU P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e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structures are recombined, so the blood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onstraint of the countrysid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tends to weakening, and interests component of it gradually are prominent. However, the nature of differential and the rules of “renqing” of the countrysid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on’t change fundamentally, which still is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lood; ethical; interest; “renqing” rules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yfc100334).
C912.82
A
2095-414X(2015)04-0084-04
熊峰(199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与人口学.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