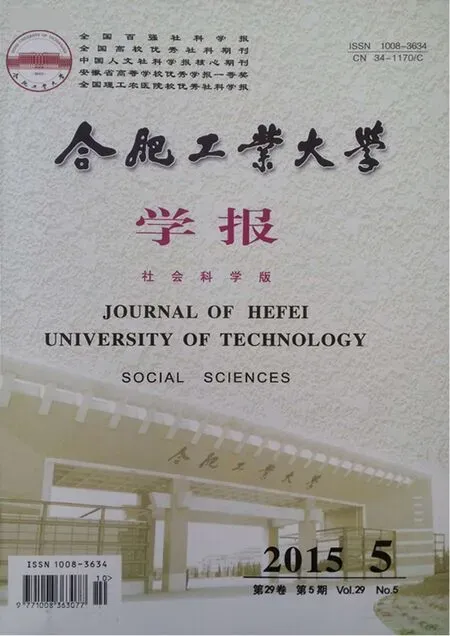《史记》感生神话矛盾性论析
刘书惠,李广龙
(1.黑龙江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22;2.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3.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史记》载有多种类型的神话,其中,始祖母感应于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而妊娠生子的感生神话很有代表性。这类神话展现了人们追根溯源的心理、神化祖先的主观意图,以及对圣王形象的美好设想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向往。《史记》中的感生神话不但含有上述意蕴,更因时代要求与延续传统的冲突、史学精神与神话思维的冲突、今文尚义与古文尚实的经学冲突、天命思想与道德观念的冲突等,而展现出强烈的矛盾色彩,立体地突显了司马迁神话思想的内在矛盾。
一、渊源有自和因时造作
《史记》中的感生神话来源有二:其一,源于前代典籍的记载,司马迁或整理完善,或解释扩充,而原神话情节主体不变。如“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殷本纪》)本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及《楚辞》“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再如“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周本纪》)则初载《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叙事要素、情节发展等方面几无所差,《史记》不过是增加细节并加以解说罢了。
《史记》以经典记载为原型叙述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展现了司马迁对史料的审慎选择,实践了“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及“折衷于夫子”(《孔子世家》)主张。同时,也展现了太史公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族群源起的深沉思考。《殷本纪》沿用简狄吞食鸟蛋而生契的感生神话,肯定了东夷商人与鸟图腾的密切关系。《秦本纪》仿照前者,将秦人的源起亦归之于“玄鸟遗卵”。“这篇《秦本纪》开宗明义的世系补叙,乃神话插曲,好像是开暴秦的玩笑,实则分析其民族本质。”[1]姜嫄践巨人迹而有孕,孙作云解释“巨人迹”说:“大人之迹即熊迹,周民族乃以熊为图腾者。”[2]司马迁的这一记录,又是对周之源起的说明。
其二,根据时代的需求而自行创作的感生神话。《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高祖本纪》云:“其先刘媼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秦始祖大业与汉高祖刘邦的感生神话都是在《史记》中首次出现。秦之始祖大业的感生神话,很明显是受到了殷契感生神话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对后者的仿作。作为秦之推翻者和继任者的汉朝开国帝王,刘邦的感生神话里并没有出现“感鸟”、“杀鸟”的情节或任何与鸟有关的因素,而是因龙感生,其造作的痕迹更为明显。自秦始,龙由神异之物转而为帝王象征,这种帝王身份与神秘形象的内在联系直接影响了刘邦感生神话的创造。“在刘邦时代,民间还有上古龙图腾崇拜的残余影响,还有乘龙可以上下于天的神秘传说,还有周代礼制以龙为装饰,龙象征王数的政治神学观念的存在。”[3]于是,《高祖本纪》中刘邦被说成是受神龙感应而生的龙子。同篇又载根据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五色方位帝的观念而制造的二龙相争神话:“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高祖为南方楚人,属赤帝;秦为西方,属白帝。白蛇死,无疑是刘邦以赤帝子身份改朝换代的政治隐喻。
刘邦的感生神话无从找寻经典的依据,司马迁只得根据当世盛传于世的材料加以改造整合以适应探古记源的需要。太史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来自于民间的刘邦与上古帝系的丝毫联系,无法再像秦始祖感生神话那样替换因素而继承情节,只能另寻与秦相关的衔接点,于是,由秦开始的尊龙为帝王象的象征意义发挥了作用,感生物的焦点由族群图腾转为帝王象征,因此便有了刘媪感龙生刘邦的故事。《史记》中的感生神话在追溯族源之外,又有了形似追根溯源实为后起造作的谱系新编。
《史记》新造作的感生神话体现了时代与文化的新需求。汉朝新立,统治者需要从各个层面证实自身获致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神化出身、建立起与天帝的神系血缘关联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制造感生神话便是这种有效方式的直接实践,是君权神授论的关键依据。尽管秉笔直书为史家精魂,但司马迁作为汉朝统治阶层的一分子本就有崇神其祖、美化其王的主观意愿,再加上统治者对这一问题极为敏感,受时代精神和局势变化的影响与约束,《史记》总需在始祖和帝王降生方面多费些笔墨,创造出一些新的感生神话来。这里面包含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虚构,也有无法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的困惑。
二、圣人无父与身份承袭
远古感生神话,往往只记其母不记其父,也就是所谓的“圣人无父”。这是建立与神之关联的需要,也是“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的社会现实在神话中的曲折反映。《史记》所记感生神话亦有无父感生的特征。“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生鬼神异类,有是理乎?”[4]正是对这一情况的质疑。但司马迁又说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次妃”、后稷之母姜嫄的身份为“帝喾元妃”,《三代世表》又言“高辛生契,契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契与后稷据此又有了直接的父系血缘身份。《三代世表》直接将这种矛盾表现出来:“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媼”,其为人子的身份再明晰不过了。但《高祖本纪》又说刘邦是其母感龙而生,反又突显了其神圣的出生。因此,《史记》所载的感生神话,一方面极力宣扬始祖的神圣身份,强调他们作为天之子的高贵出身;另一方面,或是为感生主人公加上一个血缘上的父亲,或为受感而孕的母亲安排一个婚内身份,交代出比较明确的承继关系,始终存在着始祖感生、圣人无父与父母明确、身份承袭的矛盾。
《史记》中这类无父感生与确认承袭身份的矛盾,是汉代今古文之争在神话学上的反映,也是太史公阙疑和实录精神的展现。汉代古文经学主质尚实,不惑虚妄;今文经学则倡天人感应,强调受命更化。“两汉经说于‘感生’主题基本上可归为两类,如今文经学家主张‘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经学家则主张‘圣人有父,父皆同祖’。”[5]例如,《诗经·大雅·生民》:“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佚文:“《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6]随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逐渐融合,“有父”与“无父”观点的绝对对立亦被打破。东汉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的郑玄说:“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娀简吞釔子生契,是圣人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虫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多怪?”[6]《史记》则远在郑玄之前的今文经学大昌之际就积极尝试融合今古文之说,是兼综今古以叙神话的时代先锋。《仲尼弟子论传》论赞云:“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司马迁认为古文所记“近是”于历史事实,典雅可信。《史记》遂存“有父”之说,承认“人子”的身份。与此同时,司马迁曾受业于董仲舒,受今文经学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十分关注人神之间的交互关系,《史记》遂又记录了“无父”之说,强调了“天子”的神圣。
《史记》所录感生神话所表现出的无父感生与身份承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司马迁的疑则传疑的实录精神。《史记·三代世表》通过“张夫子”与“褚先生”之间的问答解释感生主人公“人子”与“天子”的身份二重性及血缘关系的矛盾性说:“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元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司马迁一方面对汉代的感生神话做如实记载,另一方面又凭借敏锐的历史触觉,对感生现象有所怀疑。在《史记》的书写体系中“神话的历史化”(契、稷之母的婚内身份)和“历史的神话化”(刘邦母感神龙妊娠)的神话的双向演化过程被清晰地展现出来,神话在汉代的流变得到了生动演示。
三、天降大命与君权德授
汉时人们虽然早已不像先秦时期那样奉神信鬼,但对“天”的敬畏和信仰却未曾淡去,特别是董仲舒融合阴阳五行建立起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后,“王者天授”被接受认同。董仲舒按照现实的君权面貌与自己的设想,塑造了上天神权的最高主宰——天帝,反过来又让这个最高主宰对人世发号施令,并以此神化君权,加强天子的统治权威。一个王朝的兴起、一位帝王的诞生,仍要听凭“天”的示意。“天帝”作为“天”的具象化存在,直接决定了天命授予何人,谁有资格成为“天子”。正如《为人者天》所云:“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天人感应学说与天命盛行之风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很大,使其对天降大命、感天而生有了更为深刻的看法。“在司马迁眼中,‘天’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之‘天’,强调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承天受命’之‘天’,即天帝或上帝及神主宰着世间的一切,神(天)的意志不可逆转,一切由天命来决定;三是义理之‘天’,认为‘天’是有‘德’的,必须恭敬于天,强调‘德’与‘天’的同一性,借‘天’发挥道德的威力或力量。”[7]对“自然之天”的认知,让司马迁关注人事并注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求“通古今之变”;对“承天受命”的接受,又促使司马迁的书写了一些奇异的感生神话,看似无稽的情节却承载着太史公对人神交通的认知;对“义理之天”的恭敬,又使司马迁把“德”与天命融为一体,天被视为道德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天命所降,不仅依凭的是受命者的神系血缘,更要看受命者是否有德。《史记·三代世表》:“曰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所以在《史记》中并非简单的“君权神授”而是“天感德授”,即以感生情节证实君权的合法化,以德行的有无和大小进一步决定授命与否,再证实君权的合理化。司马迁所记感生神话不仅仅包括具体的感生情节,而且包含对有德之行的赞扬,和修德以承天命的强调。如《史记》在分别叙述了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后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殷本纪》)。“弃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周本纪》)。在《史记》的思想中,感生不过是受命的开端,能否真有资格顺承天命,还要看德行和功绩的有无。
《史记》感生神话的矛盾性,是对各类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的采用、协调与整合,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化传统与话语霸权的超越与挑战,而最终又归之于司马迁神话思想的内在悖论。史官源于巫祝,对神话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对神话的继承与改造是自动而自然的。文化衍化,人文精神与历史意识随之增强,对神话的批判与质疑也因之产生。司马迁正生活在神学与人学交相冲突的时代关结点上,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神话思想与历史观念杂糅在一起,两者间的斗争和融合启发了他对“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新理解和新认知。司马迁在以理性的精神梳理神话的同时,又以天命之说解释着时势的变迁。在信与不信之间、在继承与创造之间、在感悟式的直觉与论证式的解释之间,司马迁的矛盾心理投射到感生神话的记述中,创造出《史记》丰富而独具魅力的一类神话,并成为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这一双向互动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64-565.
[2]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C]//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34.
[3]王维堤.龙凤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8.
[4]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45.
[5]鲁瑞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感生神话内容析论——兼论其与两汉经说的关系[J].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6:303.
[6](西汉)毛 亨.毛诗正义[M].(东汉)郑 玄,笺,(唐)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49.
[7]张 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