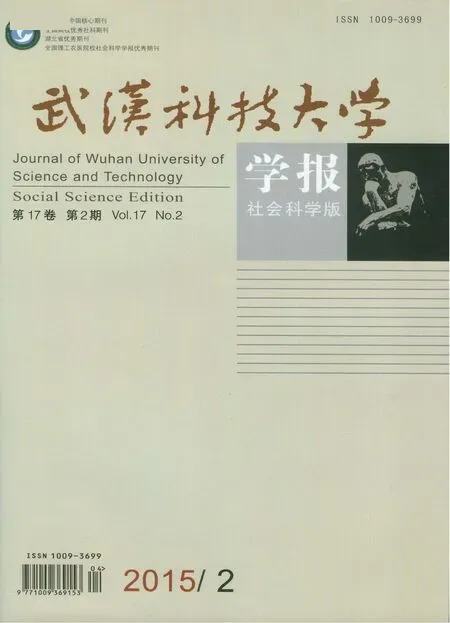从“分离”走向“和解”:黑格尔古希腊悲剧观中的“命运”思想
廖 璨 璨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从“分离”走向“和解”:黑格尔古希腊悲剧观中的“命运”思想
廖 璨 璨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古希腊悲剧中汲取营养并提出“命运”的观念。“命运”作为一种否定运动本身已经暗示了“分离”,其表现在伦理实体的美好个人全体性沦陷在否定的必然性之中,同时在更高层次上通过对命运的承认个体又能够扬弃分离而达到“和解”。黑格尔的这种“命运”观念与其历史观是一致的,并且在其早期神学著作中体现出了某种预示,这也是黑格尔哲学中神学性的体现。
黑格尔;命运;真理性;分离;和解;伦理
一、前言
在黑格尔的众多著作中,《精神现象学》一书尤为独特而晦涩。当我们试图对此书进行解读的时候,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解的进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换言之,《精神现象学》中对于辩证法的成功运用成为了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譬如其对于“主奴关系”的阐述便是运用辩证法的典范。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这句话时会发现,所谓“真正”一词其实是在暗示我们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另有一个“虚假”的诞生地。通过对体现其成熟体系的著作《哲学全书》中的《精神哲学》部分和《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精神现象学”仅仅作为《精神哲学》中“主观精神”的第二个环节出现,而这个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精神现象学》上卷内容的一个对应,下卷中的“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部分则对应在了“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中①在更具体的方面,黑格尔早期和成熟以后的思想也有一些出入,如对于“道德”和“伦理”的关系的看法,因此,在《精神现象学》中“客观精神”以及“绝对精神”与《精神哲学》中的各部分也并非完全对应,但是大体而言,其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哲学全书》中黑格尔的体系起点是“逻辑学”。如此,则我们顺着马克思的话可以认为,“逻辑学”在后来成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那个“虚假”的起点,而《精神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诞生地的本质则被隐藏于背后。
这个结论的重要就在于,其提示我们注意到该书《序言》和《导论》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两篇文章写作的不同时间和作用。《导论》实际上是对于上卷内容的一个概述,因此其所强调和突出的在于“意识”;而《序言》则明显不同,其完成于下卷成书之后,所论述的主题已经不局限于意识本身,而是对当代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批判和澄清。这里我们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引述黑格尔在《序言》中的那句名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要使之葬入于过去而着手于自己的改造。”[2]7这句话不仅启示了后文那个“新生儿的比喻”——成长着的精神需要一个质的飞跃来扬弃掉旧的世界结构,而且也表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尤其是下卷)的主题已经从意识进入到世界历史的领域。因此,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同,《精神现象学》并不是一种逻辑化的描述,而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乃是所谓“意识的经验科学”。经验的东西本来是一种世俗的东西,是一种堕落;按照基督教“道成肉身”的观点,神圣的道堕落于经验性而成为世俗的肉身。但是,当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堕落”时,世俗的生活就得到了拯救。
在此我们所要表明的是,《精神现象学》所确立的原则并不是开始于逻辑范畴,而是开始于意识形式,因此该书分析的起点是“感性确定性”。这个起点不断发展的规定性就在于当时的时代精神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故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我们不能被逻辑学这个“虚假”的起点所蒙蔽,而是要深入到其真正的起点,认识到其辩证法并不是单纯思辨的结果,而是黑格尔从历史的辩证演进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认识和分析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形态史发展的起点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个起点正是古希腊城邦社会(黑格尔认为亚洲等东方世界没有历史,真正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状态以及其中所必然蕴含的矛盾和冲突乃是分离的开始,这种分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上演,而黑格尔所注意到的正是其中所潜藏的一种必然性,这个必然性的原则及其发展和运动最终成为整个社会历史不断从分离经过扬弃而走向和解的源动力。
在《精神现象学》下卷论述古希腊城邦的“伦理”的部分中,黑格尔用不同于全书其他部分的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对这种“分离”以及“冲突”的必然性进行了揭示。黑格尔从古希腊的悲剧中敏锐而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必然性,并将其表达为一种“命运”的观念。本文将对黑格尔的“命运”所表达的内涵进行分析。
二、冲突及“分离”的必然性
《精神现象学》中“精神”这一章已经进入了“客观精神”的领地。黑格尔论述的起点是“伦理世界”,对应的世界历史时期是古希腊城邦时期,这一时期是精神真实的“再生”[3]209,选取这样一个论述的起点,显然是与黑格尔前述的理论相一致的。当理性达到了自身的真理性时,它就成了精神。此处所谓“真理性”,正是《序言》中“绝对即主体(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其表现的乃是一个从分离经过扬弃而达到和解的过程。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原始的或直接的单一性”并不是绝对的真理[2]11,它必须通过一种自身转化与自身的中介,在“重建自身的等同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思”[2]11中才能成为绝对的真理。换言之,真理首先表现为一个过程。
古希腊城邦正是这样一种预悬其终点为起点的社会形态[2]11。这是一个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形态,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它的公共生活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公民们把它看做最重要的事务。……城邦把最充分的自由和最深刻的公共生活统一起来”[4]42。这样的一种形态达到了自然和最高级的人类表现形式之间的最完美统一。
但是这种“和谐”仅仅只是理想的单纯的同一性,是蕴含着内在矛盾的、需要通过中介扬弃自身的、原始的直接性。因此,黑格尔以古希腊城邦作为客观精神部分论述的起点,不仅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城邦的和谐具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的张力,而这种否定性本身正是“实体即主体”命题真理性的体现。因为“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单纯的否定性”[2]11,它不须借助于别的东西,作为主体它只有一个否定性;且其并不意味着先有一个东西,然后才具有否定性,而是说这个主体就是否定性自身,其表现为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
古希腊城邦便具有这样一种规定性,因此黑格尔将其作为伦理实体的开始和目标,因为这个看似稳定和谐的伦理世界状态,在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的互生互成、互相规定之中,已经内在地蕴含了一种分离的必然性。
分离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在伦理本质与个体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义务或义务的分裂与情感的冲突,而是体现为伦理意识的冲突[5]21。对于个体性而言,其伦理意识需要一种决定,由于在此时其还只是一种直接性的表现,因此作为自在的存在,这种个体性的决定必然地只能表现为要么属于人的规律,要么属于神的规律,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特定的存在。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两种势力,其“在伦理王国中都是自在的,而现在它们在自我意识中都是自为的”[5]22,因此这种矛盾的实质乃是个体性的伦理意识与现实的冲突,是一种被知的东西与潜藏在背后的东西的对立,对立的结果就是分离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分离是伦理世界中具有单纯同一性的伦理实体所具有的否定性,是实体能够实现自身为主体的内在动力。因此,古希腊城邦的美好必然要堕落,这种统一必然将走向死亡,因为这是理性向着自我明晰的更高阶段发展的代价。
那么,在古希腊城邦生活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也就预示了伦理行为(Tat)中“罪”的必然性。由于在实体实现自己真理性而成为主体的过程中必须要产生行动,换言之,其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原始的同一性——理想的和谐状态将无法达到主体自身的真理性,必须通过行动(Tun)[5]24才能继续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而行动就必然蕴含了和谐的破坏,从而使得“和协一致就变成了悲惨命运的否定运动或永恒必然性”[5]20。在此,“命运”已经作为一种否定运动呈现出来,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种否定运动的必然性所带来的破坏仅仅是在一个阶段中所表现的,而当我们进入到历史的整体之中,会发现正是“命运”的全能和公正(对伦理实体中两种势力的吞噬)最终促成了绝对正义的完成。
三、命运:从分离到和解
黑格尔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汲取了营养,认为悲剧的表现主题正是这种伦理行为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本质的冲突,是伦理实体中相互独立的两种规律由于其意识所表现出的单一的决定性而导致的一种分离的必然性。因为自我意识其一方面表现为自我,这就决定了其真理性必然只能是一种直接性;另一方面作为自我意识又要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使其与自身的伦理规定性相违背,从而在行动的伦理意识和否定性现实之中构成了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中,伦理意识因为它的行动而造成了过失。在黑格尔看来,古希腊悲剧所要揭示的正是过失产生的必然性,换言之,当行动具有了现实性后过失就不可能是一种偶然。
因此,古希腊的悲剧在黑格尔这里具有了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进而言之,黑格尔将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作用在引起哀怜和恐惧而加以净化”这一命题,从一种情感的角度扭转成为一种内容原则的体现,即悲剧所引起的人的哀怜和恐惧的情感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而言,是基于一种“伦理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人的自由理性中的一种规定性。悲剧冲突的双方所依据的伦理原则乃是依据理性的自由而做出的,这种自由的获得正是我们在本文前面所分析的伦理世界本身内在具有的否定性所产生的分离,如查尔斯·泰勒所揭示的那样,黑格尔思想的关键体现在“分离对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4]103-104。
黑格尔后来在《美学》中对“悲剧性”的揭示十分清晰地体现了这种冲突的本质。“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思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6]286。而在黑格尔这里,悲剧的题旨乃是神性的东西。这种神性不同于单纯宗教意识中的那种神性,正如黑格尔的上帝其实乃是精神(Geist)而非传统有神论的上帝——其不能像创世纪之前的上帝那样完全独立于人而存在,其必须作为精神通过人而存在。同样地,悲剧中所体现的这种神性的最终落脚点不是在圣界,而是在尘世中的个别人的行动上体现出来,表现为一种人世现实中的伦理性的因素。
在这里,黑格尔主要是以索福克勒斯的两大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为基础——虽然其并没有在行文中直接说明——来对伦理行为中的冲突以及罪的必然性进行分析,这两个悲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在《俄狄浦斯王》中,黑格尔旨在强调的是伦理本质乃是两种规律的统一体,然而行动只能实现其中之一,从而在实现中另一种规律成为了一种否定物与行动方相对立,而作为统一体的这个真正的现实则隐藏在背后,正如俄狄浦斯王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弑父娶母,只有在伦理的自我意识的行动完成之后,这个隐藏的现实才从幕后走到台前进行审判,此时它才意识到自己乃是一分为二的东西,在行动之前意识的决定中所否定的那个方面此刻才显示出其与意识自身所具有的同一性。因此,这是一种无知的罪行。在这里所要体现的乃是一种支配人物的“悲怆情愫”(Pathos)①原文中的“思想感情”即是前面所提到的“悲怆情愫”,黑格尔均用“Pathos”表达。[5]218,其渗透在个体的整个存在并且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命运。
而在《安提戈涅》中,黑格尔所强调的则是一种更为完全的伦理意识——故意的罪行,其并不像前者所显示的那样是在一种现实被隐藏的情况下行动,而是伦理意识事先就已经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完成意味着现实与实体必然是统一的,因为行为者对于自己的过错是承认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承认——对对立面规律的承认,行为者自身就抛弃了他的现实而走向了毁灭。在这种承认中,黑格尔表达的是一种“伦理意境”,在这种“意境”(Gesinnung)中个体所获得的乃是“非现实”——当其承认相反规律的同时,其原来所决定从属的规律就不再是他的实体。
因此,悲剧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罪行。所谓“伦理”,其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犯罪或者过失。无论是无知的罪行还是故意的罪行,其必然产生伦理行为之间的冲突,从而两种伦理势力所依附的个体之间通过不断的相互运动(任何一种势力都不可能获取绝对的胜利,因为这两种势力对于伦理本质而言都是片面的,然而其又都是伦理本质这个统一体的体现)而最终同归于尽。此时,伦理实体的真正本质才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正是我们前面所言的“命运”的作用。命运,一方面作为一种否定运动使得两种势力在实现其伦理意识时互相消耗而至毁灭;另一方面,其又作为一种分离后转向下一阶段的和解方式而促成了“绝对正义”的完成。因此,黑格尔揭示出悲剧中这种伦理行为之间冲突的意义就在于,“悲剧的冲突导致这种分裂的解决。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6]287。换言之,只有通过“命运”,在伦理世界中的那种类似悲剧冲突所导致的分离才能最终获得和解。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从古希腊悲剧中得到灵感,揭示了“命运”在精神实现真理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分离到和解的必然性。当黑格尔在论述安提戈涅的罪行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其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原罪”学说的解释。原罪之所以成为一种“原始的”罪行,正在于其从原则上来讲构成了人犯罪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根本原因是:当人作为有限的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实体化时,其自身无法认识到“命运”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当其对“绝对”有了完全的认识——即当其自身与这种绝对精神达到历史中的同一时——才能走出任何一种片面的理解而达到自身的真理性。
此处“命运”的内涵让我们联想到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言的“理性的狡计”①“理性的狡计”在黑格尔看来是“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因此,“观念”自己是不受惩罚的,承担者是各人的热情。[3]30,在这种历史的过程中,人类无法自觉地意识到背后的精神所起的作用,对其的把握只有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精神之中才能获得解释,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其悲剧性就在于——在行为完成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俄狄浦斯王),或者即便知道这种角色,也只能是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其并没有认识到对立面其实正是与自己同一的存在(安提戈涅)。正如黑格尔在其晚年的成熟作品《法哲学原理》中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7]。当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时,或许其正是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受到的启发——较低层次的存在不完美地证明了潜存于事物中的必然性,而只有在更高层次的存在中才能获得对于之前历史事件背后所体现的命运必然性的认识。因此,“历史”在黑格尔这里表现为对于某种确定的人类命运的必然性的揭示,其背后精神的意图必须要经过悲剧性的冲突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解时才能获得揭示。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在悲剧的冲突中由于人们要通过决定而达到自身意识的单纯性,从而分离是不得不发生的——唯有如此人类才能不断地走向实现自身的道路;而其最终也必然要和解——因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是必然的,先前原始的同一性只有在此时才能获得其真理性。因此,历史在黑格尔这里表现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形态②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统一被失落和重建的过程,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基督教中与“三位一体”相呼应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阶段,从“道成肉身”到“原罪”到最后的拯救,正是这种从原始的单纯的同一性中分裂,经过扬弃而达到和解的过程。。
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黑格尔本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大神学家(当然,正如本文前面所言,黑格尔的“神”并不是排除了人的存在的神,恰恰相反,其正是以人的精神的实现作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精神现象学》中“命运”的观点在其早期神学著作中就有体现。《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一文中着重阐释的正是这种“命运”的观念,而且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命运”的看法很可能就是从此文直接继承过来的,并在其《美学》中通过对悲剧的阐释而达到成熟。在此文中,黑格尔认为犯法的人“不能逃脱惩罚,也不能逃脱他自己的行为”[8]324,“被了解为命运的惩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8]325,从而命运的惩罚是与法律无关的。命运作为惩罚,是一种否定运动的力量,但是其不像来自法律的惩罚,它是由精神的本质所决定着的。当分离必然发生之后,其并不是像法律那样对于生命的惩罚造成了对生命的永恒破坏[8]327;相反,在由命运所做出的惩罚中,对这种惩罚的承认能够在更高层次上恢复那个原始的统一,停止以分离的方式来行动,并不再把命运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强加于个体身上。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个体恢复了生命的单一性,“生命可以重新医治它的创伤,使分裂了的敌对的生命重新返回到它自身,并且可以扬弃犯罪行为的罪过,扬弃法律和惩罚”[8]326-327。因此命运作为否定的力量只是暂时地毁灭了自我意识,然而最终个体能够在生命中重新发现自己,在爱中同命运取得和解,逐渐地把它看做与自身是同一的①在黑格尔看来,此一过程中所体现的必然性与《圣经》中所言“谁想要保持生命,他将要丧失生命”(《马太福音》,第10章,第39节)具有某种契合。[8]322。命运作为历史背后的必然性力量体现在分离的必然性,但是通过对命运的承认,个体最终能够扬弃这种分离而达到统一。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4.
[8]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4-11-04
廖璨璨,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B504
A
1009-3699(2015)02-01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