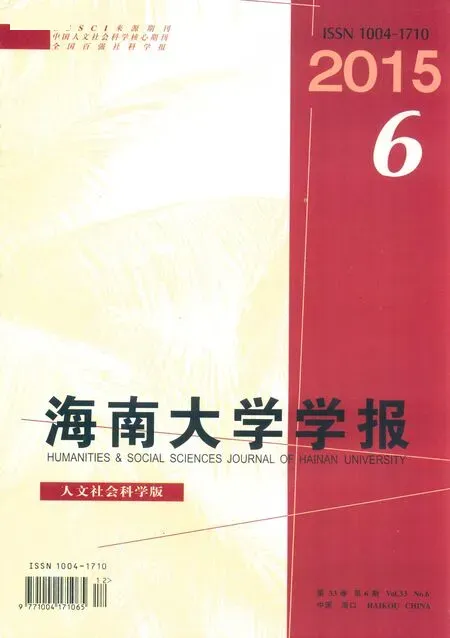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研究
——以双边渔业协定为视角
高婧如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研究
——以双边渔业协定为视角
高婧如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近年来南海渔权争夺异常激烈,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渔业合作机制。对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提供的三种合作模式,双边模式应是当下推进南海渔业合作最为可行的方式。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渔业协定中承载着合作的具体机制。文章从南海区域的双边渔业协定入手,分析现有合作机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为南海渔业合作提供有益参考。
南海;双边模式;渔业协定;合作机制
近年来我国南海渔权频受海上邻国侵扰。据统计:1989—1998年间共发生袭击、抓扣我国渔船事件92起,涉及渔船83艘,死伤渔民31人[1];2000—2008年间,仅海南、福建、广东、广西四省区就有530多艘渔船被邻国扣留,涉及渔民近6 000多名[2]。2014年5月12日,菲律宾司法部向巴拉望公主港地方法院起诉了在半月礁附近海域被抓捕的中国渔民。随着南海渔业争端的不断升级,传统的双边渔业协定在南海渔业合作问题上的适用性不足越来越明显,重新探讨对于南海行之有效的渔业合作机制是解决当下南海渔业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南海渔业问题肇始及解决路径的选择
南海渔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1)其根本原因是由于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设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导致新的海洋秩序诞生,原本一衣带水的南海诸国因新被赋予的“权力依据”而纷纷开始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拓展管辖水域范围,南海自此变成“六国七方”权利的角斗场[3]。《公约》作为上述问题的始作俑者,其注重的是设置新的海洋制度,而不是为这些纷争提供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4]。(2)美日等区外大国希望抓住一切机会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发展;南海一些国家也希望借助区外大国势力削弱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话语权,同时通过转嫁矛盾的方式稳定国内政局。(3)南海渔业资源丰富,但渔业活动缺乏秩序性和规划性,沿海国之间呈现竞争性的捕捞态势。陆架类渔业资源均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资源整体状况不容乐观。(4)目前南海渔业缺乏合作动力,虽然已存在不少渔业方面的合作协定及国际公约,但区域内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渔业纠纷不断。渔业既可以成为凝聚南海诸国的向心力,也可能成为间离南海诸国的离心力[5]。因此处理好南海渔业问题对稳定南海局势十分关键。
就目前南海渔业活动的基本状况来看,采取单边开发的路径显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争议海域内进行单边渔业活动,是造成目前渔业纠纷和渔业争端的主因。所以解决南海渔业问题的最佳路径依然应走合作之路。《公约》第123条就半闭海沿岸国家的渔业合作提供了三种参考模式:“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家……应该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由此可见《公约》鼓励相关国家间应当优先尝试通过直接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渔业合作。直接的方式包括双边和多边两种模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第三方区域组织参与的模式解决合作问题。如果采用双边模式进行合作,其优势在于:(1)能够充分考虑到双方的具体国情、资源的具体情况,更利于合作的顺利达成。(2)有较为明确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养护更具操作性。(3)双边模式的灵活性还在于,一旦在合作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正,从而为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阻力。但其缺点就在于对于鱼类这种移动性、共享性资源,无法做到统筹管理,所以在利用和养护的力度上还是只能止于部分海域。若采用多边机制,就目前南海局势来看,南海周边各国利害关系和诉求纠结,达成共识很难,而南海渔业秩序又亟待规整。南海目前尚无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区域组织,所以想要借助第三方解决南海渔业问题也欠缺条件。
此外,就中国对外渔业实践来看,双边模式一直是我国开展对外渔业合作的主要方式。经统计,1959年以来我国先后与30个国家以及东盟签署了双边渔业合作协定(包括涉及渔业合作项目的非专门性协定)。通过对先后有效的42部双边涉渔协定归类统计可以发现:(1)其中有8部是签署于《公约》生效之前,其余34部均签署于《公约》生效之后。(2)对外签约的国家中:非洲有6个(几内亚比绍、尼加拉瓜、毛里塔尼亚、塞舌尔、加蓬、也门);美洲有6个(智利、乌拉圭、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有6个(前苏联、希腊、英国、挪威、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大洋洲有3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澳大利亚),亚洲有8个(朝鲜、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巴林),此外还有马绍尔群岛。
因此,就目前南海渔业现状来看,采取双边渔业协定的合作模式仍是解决南海渔业问题的最优选择,在以双边合作为抓手的同时积极带动周边国家参与,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共识为目标,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南海区域性渔业合作机制,推动南海渔业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
二、南海双边渔业协定主要机制分析
在南海地区,2000年中国同越南签订了《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以下简称《中越渔业协定》),并于2004年达成该协定的《补充议定书》和《北部湾共同渔区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2001年中国同印尼签署了《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于同年12月19日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就利用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部分总可捕量的双边安排》,并于2004年进行修订(以下简称《中国印尼渔业安排》);2004年中国与菲律宾签署《中菲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2004年中国同马来西亚共进行了3次渔业合作谈判,并促成“中马渔业合作商务论坛”;此外,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将“农业”作为合作的重点领域;2009年我国广东省海洋渔业局与文莱渔业局达成了《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在这些法律文本中有一些逐渐成型的具体机制是近年来我国在南海双边渔业合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一) 适用海域划分制度
适用海域制度是渔业协定的必要条款,主要作用是划定渔业合作海域范围。目前的渔业协定对适用海域的划分方式有三种:一是经纬度标识法,主要用于1982年《公约》确立专属经济区制度之前签署的渔业协定中;二是直接使用“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的措辞,1982年之后的渔业协定几乎无一例外的使用了该类措辞;三是将上述两者混用的方法,多适用于两国存在争议海域的情况。目前的渔业协定对争议海域的划分存在以下类型:(1)“暂定措施水域”,为了实现对渔业资源的共同开发与管理,该水域适用船旗国管辖规则。即使发现对方渔船违规,也不能直接处理,而是先就事实提醒该国民及渔船注意,再通报另一方。(2)“过渡水域”,目的是为了照顾“传统捕鱼权”,规定在一定时限内逐步减少在对方该水域内捕鱼的渔船数量,以实现过渡。原则上在该水域的管理也适用船旗国管辖,但不同的是在该水域双方可采取联合乘船、勒令停船、登临检查等监督检查措施。此外,《中越渔业协定》规定过渡性安排结束后缔约双方相互享有“优先入渔权”。(3)“共同渔区”,是为了实现长期的渔业合作而划定的水域。在该水域双方共同制定渔业养护和管理措施。与“暂定措施水域”不同的是在检查监督的管辖方面适用的是“属地”原则,各方对进入己方一侧水域的双方国民和渔船不仅有监督检查权还有依照国内法进行处罚的权利。(4)“小型渔船缓冲区”,为了彼此能够谅解小型渔船*中国农业部《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6条(二):“海洋小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不满44.1千瓦(60马力)且船长不满12米。”无恶意地误入他国领海的行为。在该区域进行执法活动可以予以警告但行为上必须保持克制:不扣留、不逮捕、不处罚或使用武力。一切渔业活动争议交由渔委会负责解决,其他争议依据国内法解决。《中越渔业协定》虽然是在完成北部湾划界后签署的,但为了能够在敏感程度不同的海域内实现分级合作,就采用了经纬度标识的方法来标定“共同渔区”和“小型渔船缓冲区”这种特殊海域。这种海域划分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临时安排措施,在尚未完成海域划界国家间的渔业协定中尤为重要。
(二) 入渔制度
传统的渔业合作是对特定区域内的渔业资源的一种互换与重新分配的过程,入渔制度无疑是此种渔业协定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制定入渔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专属经济区资源状况、本国捕捞能力、传统渔业活动、相互入渔状况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因素。入渔制度的内容一般涉及以下方面:(1)入渔许可证的授予。沿海国通常是以颁发捕捞许可证的方式作为对“外国渔船”到本国专属经济区入渔的认可。对入渔船只通常采用“双许可制”,即既符合船旗国对于远洋渔船的要求,也满足沿海国对外国渔船的要求。通常情况下颁证以渔船为单位,即“一船一证”。《中国印尼渔业安排》第2条第2款中规定的“以渔场为单位颁证”的情形比较特殊,但实质上也是“一船一证”的情形。(2)对入渔船只、渔具的安排。协定一般从船籍、吨位、类型(捕鱼船、补给船、运输船)、装备、作业水域、作业期限、作业方式等方面对入渔船只进行规制。(3)对可捕鱼种的规定。协定大多会从可捕种群的鱼种、体长、数量、重量、性别等方面做相应规定。4.对渔获的规定。其中包括对渔获物(包括副渔获)的使用、转让、转运、卸下和加工等方面的规定。
(三) 渔业管理监督机制
渔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通常是由协定设立的专门委员会(通常称“渔委会”或“混委会”)来负责。渔委会的职权通常规定有以下几项:(1)代表双方进行协商的权利。协商内容主要涉及可捕鱼种、渔获配额、捕捞努力量投入、休渔禁渔期限等具体入渔制度,许可船只的违规处罚措施,争端的解决方式,渔业养护措施以及情报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等具体事宜。(2)向双方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利。渔委会对协商事项通常没有决定权,只能向双方政府提出建议,渔委会的一切建议须经双方代表一致同意方可落实。(3)维持海域作业秩序。这其中包括对许可船只作业时间、作业海域以及作业方式的监督和管理,审查船只捕捞日志,监督渔获量,防止违规捕鱼行为的发生以及针对严重违规行为的执法行为等。(4)对违规捕鱼行为的处罚。渔业协定往往赋予渔委会一定的处罚权,以及对一般渔业纠纷和海损事故处理的指导权。渔委会的运作机制通常是以年为单位由双方轮流举行一到两次定期会晤。2000年《中越渔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磋商机制,为及时解决渔业合作中的问题提供了更加灵活的交流平台。
(四) 渔业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捕捞习惯、捕捞要求不同以及对作业海域的生疏,很容易出现违反相关国家的渔业法规的行为。所以在渔业协定中规定具体的争端解决制度是防止渔业争端升级化、政治化、极端化的必要手段。常见的渔业争端根据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种:1.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如关于协定的解释和适用问题的争端、不满沿海国对其资源分配引发的争端。这类争端通常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得以解决。按照《公约》第297条第3款之规定,这类争端是不能提交导致有拘束力的裁判程序的,换言之,两国只能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2.国家与渔民之间因执法引发的争端。这种类型多数是因为渔民无证捕捞等侵渔行为而遭遇执法引发的争端,是目前渔业争端的主要形态。针对这类争端,尤其是执法国家的行为,《公约》和渔业协定一般规定:(1)迅速通知义务。《公约》73条第4款规定“在逮捕或扣留外国船只的情形下,沿海国应通过适当途径将其所采取的行动及随后所施加的任何处罚迅速通知船旗国”。至于通知的方式,《公约》并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而规定了“通知时限为4天”的1985年《中美渔业协定》,成为了42部双边渔业协定中将“迅速通知”时效化的唯一范例。(2)担保和迅速释放制度。根据《公约》第73条规定:“沿海国行使其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可采取为确保其依照本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被逮捕的船只及其船员,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迅速释放”之例外情形规定在《公约》73条第3款之下:“沿海国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反渔业法律和规章的处罚,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协议,不得包括监禁,或任何其他方式的体罚”。言外之意,《公约》是不反对两国协定中规定有关监禁或体罚内容的。(3)使用武力之克制规则。《公约》对“使用武力”的禁止主要适用在国家之间。国家对前来入渔的他国渔民使用武力的行为,原则上是禁止的。根据《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种群协定》)第22条1款(f)项规定:“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职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者除外,且应以必要程度为限。使用的武力不应超过根据情况为合理需要的程度”。3.两国渔民之间的争端,这类争端大多适用国际私法规则解决。
(五)渔业养护制度
该制度已成为渔业协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伊恩·布朗利教授在论及生物资源养护时认为:条约的目的总是结合对捕鱼的公平使用和公平限制的原则,维护渔业资源的最大可持续性产量[6]。因此,养护制度通常被吸收在入渔制度和管理制度中,表现为:(1)对捕捞量的控制。比如投入的渔船数、吨位、马力数、作业人数、作业时间、下网次数等。(2)对渔获量的限制。控制渔获量是对渔业产出量的限制措施。近年来随着世界对副渔获及意外渔获的重视,渔业协定中也出现了对副渔获的限制条款。所谓副渔获是指使用渔具对目标鱼种进行捕捞时所兼捕到的非目标种类渔获物。据统计全球每年大约有287×107t副渔获物,其中20×107t被抛弃[7]。对副渔获的控制在目前的协定中语焉不详,但是过多的意外渔获或副渔获会遭受沿海国的处罚是毋庸置疑的。《公约》、《种群协定》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鱼类的养护制度有详细规定,所以在多数渔业协定中并没有体现具体的养护规则。
(六)海难救助制度
由于渔业合作大多是在他国或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作业水域距离本国海岸较远,所以海难救助和紧急避险条款在规定较为详细的渔业协定中往往占有一席之地。《中越渔业协定》就以附件形式规定了“紧急避难”条款。回顾近年来较为激烈的渔业冲突,多数伴随着冲撞、截停、强登等野蛮执法行为,所以目前渔业活动的救助大多是比照适用有关海难救助及船舶碰撞方面的国际公约进行。
三、南海双边渔业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除了政治、经济等外因,渔业协定本身在界定渔业权利、规范渔业活动、缓解渔业纠纷等方面存在缺陷是导致南海渔业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双边渔业协定形成的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使之不能很好得适用到南海渔业实践之中。
(一) 争议海域划分制度未能体现实质公平
分析近年来几起典型的渔业冲突,不难发现在对争议海域进行划分时忽略了部分重要因素,比如两国的基本国情、渔业现状以及渔业实际需求量等问题,导致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实际上并不公平。中越渔业协定在划分“共同渔区”和“暂定措施水域”时沿用了中日、中韩渔业协定中的“中间线”原则。然而中国的渔民、渔船数量多,中国国民对鱼类资源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南海各邻国。据联合国水产农业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年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能达到50公斤[8]。《公约》第70条“地理不利国的权利”第3款之(d)项规定:地理不利国应有权参与开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有关协议条款应考虑到“有关各国人民的营养需要”。因此在谈判时应考虑并顾及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因素。另外,在进行争议海域划分时没有全面考虑到合作海域的资源分布状况的因素,刻板的对水域进行中线分割,在资源利用上采用这种“纯地理概念”的划分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渔业合作的对象是鱼类资源,所以还应结合资源量作为划分海域的依据。
(二)渔委会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渔委会作为协定设立的唯一执行机构,负责协定中诸多事务的实际操作。目前渔业协定的“渔委会”规则存在下述缺陷:(1)组织架构通常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是由双方政府各自任命1~2名委员组成。必要时方才设立专家组或工作组。(2)在规定渔委会的职权和任务时,渔业协定一般谨慎使用“协商”、“提出建议”、“指导”等措辞,并没有给予实际执行权,而是规定了磋商权和建议权,但协商的事宜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渔业活动。包括:协商可捕鱼种、渔获配额等入渔事项;协商有关维持作业秩序的管理事项;协商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状况和养护的事项;对渔业纠纷和海损事故的处理进行指导。(3)职能和人员架构的不匹配,导致实践中渔委会在渔业活动中的作用甚微。(4)渔业活动的各个环节涉及到丰富的专业知识,要想渔委会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期间需要做大量的科考与研究工作,不可能靠1~2人就能完成。(5)对于渔业纠纷的处理也是渔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现有渔业协定对渔委会的组织架构的规定来看,渔委会根本无法胜任。
(三)渔业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
目前大多数渔业纠纷都缘于他国执法者对我国渔民渔船进行扣押或逮捕等行为引发的。协定中对违规捕鱼的处罚程序已有规定,但执法程序条款不完善:(1)执法行为不够规范,比如,在很多情况下他国执法人员并没有发出停驶信号,而是径直截停或紧追上之后穿着便衣强行登船的,渔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反抗,不应以此作为抓扣渔民,甚至使用武力进行逮捕的理由之一。根据《公约》第111条规定沿海国“追逐只有在外国船舶视听所及的距离内发出视觉或听觉的停驶信号后,才可开始”,且“紧追权只可由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并经授权紧追的船舶或飞机行使”。(2)协定虽然明确规定了沿海国在抓扣渔民渔船后有迅速通知的义务,但是何为“迅速”却很少有协定给出具体的时限。纵观诸中外渔业协定中唯有1985年的《中美渔业协定》规定了必须在4天内将采取的行动及科处的处罚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政府。同样的时限模糊问题也存在于担保后的迅速释放制度中。(3)对于争端的解决,协定中缺少良好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导致一旦发生渔业纠纷,两国很难第一时间展开谈判、进行司法援助,而往往是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呼吁,这种方式对于渔民的迅速释放收效甚微。
(四)渔业养护被入渔制度所吸收
目前渔业协定中都存在专门的养护条款,但大多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用以明确入渔国的养护义务。但就具体该如何来参与沿海国的渔业养护活动规定得并不详细,缺乏操作性。目前协定中关于养护的义务实际上是被吸收在了入渔条款当中,将对入渔条件的限制视为对资源的一种保护。比如对捕捞船只与工具的限制、渔获量的限制、入渔时间的控制等。沿海国对入渔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是入渔国参与养护的最低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行为应当视为是违规甚至破坏性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目前沿海国对养护的规定相对谨慎,以避免为入渔国带来过重的负担,只要不对渔业及生态造成破坏,就尽量避免多余的责难。这种态度虽然是将合作放在首位,但长远来看对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及养护是不利的。
(五)渔业海难救助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守则》第8条第1款第6项规定:“各国应当独立地、与其他国家一起或与有关的国际组织一起安排把捕捞作业纳入海洋研究和救援系统”。渔业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渔船在协定海域发生故障、遭遇台风等恶劣天气、船员患有紧急性疾病等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海难救助制度应当作为渔业协定中的必要内容。目前渔业协定中对海难救助的规定尚不完备,对于救援投入的时间、遇险联络、避难场所、被救人员及船舶的救后安顿等具体事宜未作详细规定,一旦发生海难险情,救援效率必定不高,所以在渔业协定设立海难救助制度应为必要。
四、南海渔业合作机制之完善
(一)合作海域划分要适当顾忌基本国情及传统捕鱼权
适用海域划分制度对南海渔业合作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制度,直接关系着渔业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就南海诸国来说,除去与越南划定了北部湾海域界限外,我国与其他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均没有划分争议海域,与越南仍存在其他海域划分争端。对于仅涉及两国重叠海域的划分是可以参考《中越渔业协定》的划法,但是要顾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传统捕鱼权等问题。南海渔业合作的难点在于多国重叠海域,针对此类海域的合作方可以仿效中、菲、越三方关于南海协议区内石油资源储量联合考察的“三方协议”模式[9],即在中方与菲方率先签署了“南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基础上,越南也加入其中,扩大为中菲越三方协议。如果第三方愿意加入到已有的双边渔业合作框架之中,共同协商解决渔业问题,将是对南海渔业秩序更好的推进。三方划分合作水域应当进行区分,对于两国重叠区,由该当事双方进行对该海域内相关制度的商议;对于三方重叠水域,应当由三方共同商议该水域内的管理及养护事宜。对于存在争议的某些水域,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将其划出并隔离,在该区域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单方行为,可以考虑共同管理,但同时也要承当相应的养护义务。
(二)因国制宜灵活运用渔业对价制度
渔业对价制度的设立并非是协定的必要条款,渔业对价制度通常适用于进入相关国家水域入渔的交换条件而列明。尤其是在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渔业合作时,对价通常是以“技术换资源”的传统形式。比如: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海洋渔业协定》要求中方帮助毛里塔尼亚建造船只并保证船队的更新;2006年中国渔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与塞舌尔渔业局签订的《关于中国渔船在塞海域进行捕鱼的协定》规定中方在码头设施、冷库和冷柜集装箱转运设施建设,饵料生产,渔业资源加工等方面给予协助。但是随着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对价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降低。渔业对价形式正在趋于多样化。欧盟对ACP国家*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States,缩写ACP)。的“渔业补贴”模式是渔业对价制度中的一个亮点,对中国开展南海渔业合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南海其他国家的渔业资源相对充沛,而在渔业资金和技术方面存在较大需求,中国可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提供渔业补贴,打开他国市场。这种渔业补贴除了渔船建造等传统形式的补贴外,还有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贷款补贴、市场支持等多种形式[10]。这种补贴不仅可以补给对方国家相关部门,还可以补贴给企业甚至渔民。这种补贴对双方来说可选择性都比较大。就南海目前局势来看,这种自由度较大的对价形式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三)规范并细化入渔制度
入渔制度是渔业协定的主体部分。其内容一般情况下包括:(1)入渔许可证制度。对于入渔许可证的换发、变更、转让等细节事宜可以以专门附件的形式根据各国国内法要求作具体规定。(2)对入渔船只的要求。包括对船只的数量、规格、作业水域、作业天数、作业时间的要求。(3)对捕捞工具的要求。包括网具类型、网具大小、下网次数的要求。(4)对渔获配额的要求。包括比例要求、对副渔获/意外渔获的处理规定以及惩罚措施。入渔制度一定要细化、明确、可操作性强。如果国内法与协定规定有出入的地方,相关国家有责任对该项条款的适用进行明确解释,否则不得适用与协定条款冲突的国内法条款。入渔制度的完善是从源头上立下的规矩,对整个南海渔业秩序至关重要。
(四)增加渔委会机构设置
入渔制度需要依靠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的配合才能完成。渔委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协定的执行;渔委会应下设若干临时小组(争端处理小组、渔业科研小组、渔业救助小组等)负责对渔业活动中各部分内容有针对性地执行。渔委会运作机制、协调机制等内容可分别以附件形式加以规定;除了常设机构之外,可以通过建立“随船观察员制度”以完善对渔业活动的监管。通过委派渔业观察员的形式,完成对渔业活动及从业人员的记录、监督和检查工作。当然安装渔船监控系统[10](VMS)将是更为省时省力的一种监管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对渔船的全天候全方位实时监控,也便于一旦发生险情进行定位救援,同时也能够监控渔船的动态数据,提前预防违规行为的发生。
(五)规范渔业争端解决机制
渔业纠纷的发生原因可能由很多因素导致,但争端发生之后缺乏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是让整个南海渔业秩序至今处于混乱的重要原因。(1)争端对话机制。由渔委会下设的争端处理小组负责争端的沟通工作。一旦发生涉及渔业活动的纠纷,渔民首先联系己方渔委会,由争端处理小组负责争端双方的沟通与协调工作以及在第一时间通知渔民家属及所在公司,和在必要时联系国内当局的任务。(2)争端处理机制。根据争端的类型进行选择处理。涉及国家之间的争端,适用《公约》或其他国际法规定的争端解决办法;涉及渔民违规被捕引发的纠纷,应按照渔业协定规定的处理办法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应当适用相关的国内法包括海商法来解决。(3)规定明确的担保条款,包括担保方式及额度。(4)规定具体的迅速释放制度,明确释放条件及时间。(5)规定赔偿条款。给沿海国渔业资源造成损害的,应当履行赔偿责任,赔偿的数额由双方在完成对损害情况的评估之后协商确定。对于沿海国误抓误扣,以及超期羁押等行为规定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6)委派代理人制度。这个制度在《中美渔业协定》第9条第4款中有规定:该代理人主要负责在美国境内向中国渔船船主或经营者致送的任何诉讼文书有接受和答复的权限,该制度主要是为了方便下一步的诉讼活动而设立的。
(六)设置明确可操作的渔业养护制度
渔业养护制度应当成为渔业协定中的必备条款。当解决了规范入渔之后,相关国家获得了入渔配额,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养护责任。其中“养”的责任可能更多的会落在沿海国自己的身上,因为资源量的维护和增加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整个生物链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但“护”应是入渔国不可推卸的责任。“护”的责任分为“不作为”和“作为”两部分,所谓“不作为”义务是指入渔国应当严格按照沿海国制定的关于养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包括禁用破坏性的渔具和捕鱼方法、禁止随意处理副渔获及生活垃圾、禁止携带破坏水体及海洋生物的物品等,以防止对水体及生物种群的破坏。一旦入渔国船只违背沿海国的“不作为”规定将会受到相应惩罚,包括责令停止作业,驱逐出境;减少来年渔获配额;收回入渔许可;赔偿因养护不利造成的损失等惩罚措施。“作为”义务主要是指入渔国应当积极对进行渔业活动的水域进行留意观察,一旦水体或渔获物出现异常情况有责任向沿海国进行报告,并在适当时候配合沿海国的养护计划。
(七)加强不同形式的渔情交流机制
渔业协定中规定渔业情报交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该海域的生物资源状况,以便于对来年可捕量进行科学的评估以及对不适当的入渔标准和养护措施进行调整。该制度包括:(1)入渔国汇报制度。分为日常渔业活动的基本情况的汇报制度以及资源异常情况的随时汇报制度。(2)沿海国灾害气象预报制度。海洋环境多变,天气对于渔业活动和渔民安全至关重要。沿海国对于在自己水域进行作业的本国渔船和他国渔船都有险情预报的责任。(3)相关数据共享制度。包括海域水文数据、气象数据、水质环境数据、生物信息数据、渔业养护数据等与渔业活动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资料的共享。(4)交流制度。包括物的交流(设备,仪器,样品交换等);技术的交流(包括组织学术会议、讨论会和讲座等);人员的交流(科研技术人员、学者、官员等人员的交流与互访机制)。
(八)增加合作水域渔船互助机制
海难救助除了遵循海商法及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外,渔业协定中可以侧重于规定合作双方海上的互助与救助义务与途径。其中包括遇险渔船的呼救及通讯、沿海国及水域内其他渔船的接警反馈以及遇险渔船的寄泊(港口、要求、费用)等问题。海上互助主要指的是两国作业渔船在日常生活上给予对方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日用品的补给、油料的补充、不具倾覆危险的船舶及渔具损坏修复及其他提供海上便利的活动。该制度曾在1988年中国与前苏联签订的《渔业合作协定》第4条第1款有所体现,但在南海相关国家的渔业协定中并没有出现过。海上互助行为不仅可以帮助海上有需要的渔民渔船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同时也能够融洽两国渔民之间的关系。
以双边合作为契机的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对于规范南海诸国渔业活动、缓解频繁发生的渔业纠纷、增强南海区域向心力意义重大。双边渔业合作能够为下一步建立多边参与的南海区域渔业组织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曹云华,鞠海龙.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53.
[2] 于冬,金微.周边诸国频繁扣押中国渔民动机[EB/OL].[2014-01-06].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30/085818122131.shtml.
[3] Mark J Valenca. Regime-Building in East Asia: Recent Progress and Problem, Chirrop, MeDorman and Rolston edited, The Future if Ocean Regime-Building[M]. Leiden: Martinus Nijh off Publishers, 2009.
[4] 罗国强.多边路径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及其构建—兼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J].法学论坛,2010(4):93-99.
[5] Erik Franckx.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entrifugal or Centripetal Force? [J].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727-747.
[6] 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M].许安拓,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85.
[7] 唐衍力.副渔获物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及其减少方法的探讨[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3(2):211-218.
[8]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United Nations .National Aquaculture Sector Overview(China) [EB/OL]. [2014-09-19].http://www.fao.org/fishery/countrysector/naso_china/zh .
[9] 邹立刚,叶鑫欣.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法律机制构建略论[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59-63.
[10] 牛哲莉.论欧盟对ACP国家的渔业补贴—WTO视角[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117-122.
[11] 曹世娟,黄硕林,郭文路.我国渔业管理运用渔船监控系统的探讨[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2(1):89-93.
[责任编辑:王 怡]
A Study of Fishe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With the Bilateral Fisheries Agreements as a Perspective
GAO Jing-ru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fight for fishing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nse in recent years lies in the absence of an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fishery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reference to three modes of cooperation listed i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bilateral mode is supposed to be the most feasible to promote fisher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urrently. In China’s bilateral fisheries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contain the specific cooperative mechanisms. Starting from the bilateral fisheries agreement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the suggestions to perfect them in hope of providing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the fisher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bilateral mode; fisheries agre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2015-08-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海上维权执法权限和程序研究”(15BFX184) [作者简介] 高婧如(1987-),女,山东泰安人,海南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法学。
D 993.5;P 722.7
A
1004-1710(2015)06-0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