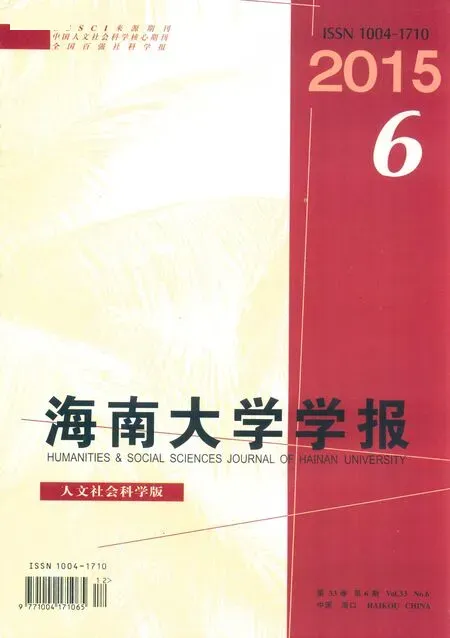中国家庭知识生产力的实证研究
陈永国,李建培,石慧君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既“美国虎妈”案例之后,关于“中国狼爸”教育方式的争论再次吸引众人的目光。受“棍棒底下出才子”的传统思想以及教育功利化趋势的影响,我国目前有不少家庭依旧采取专制的家庭教育方式。然而,严苛的管理方式、专制的教育模式,真的对孩子的学习、成长有利吗?家庭教育效果到底与哪些家庭因素有关呢?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是知识第一生产力,好家庭就是一所好学校。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家庭教育与人才培养,成为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因此,有必要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聚焦于家庭这个特殊的权力场,重点分析家庭的权力模式对子女知识生产力的影响,探索提升家庭知识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提高家庭的知识生产力、知识创新力,探索优良的家庭培养模式,对促进我国国民文化水平、创新能力的提高,对建设民主社会、知识型城乡、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生产力”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的,他强调知识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生产力最一般的定义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结晶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成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要素。”[1]也就是说,知识生产力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上的生产力。知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知识劳动、知识劳动者、知识劳动对象、知识劳动资料和知识劳动环境[2],其中知识劳动者是知识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知识生产力更加关注人力资源的“质”,而非“量”。对于知识生产力形成的条件,目前许多学者主要聚焦于个体或组织,从对象的个体层面,如年龄、性别、能力、毅力、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探讨对知识生产力的影响[3-7]。还有学者提到文化和组织因素,如组织和教师队伍的规模是组织知识生产力的关键因素[8-11]。Jordan等人对美国大学进行了研究,发现院系组织的规模与研究生产力之间存在正相关[10]。然而,Kyvik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规模与研究生产力之间没有显著关系[11]。由此看来,组织规模与组织知识生产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目前对知识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聚焦家庭环境对知识生产力的影响。那么,家庭知识生产力与哪些特征有关?对于家庭来说,知识生产力生成条件如何?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环境是人才成长在时空上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置性基础条件。作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单元,家庭权力、家庭氛围、家庭规模、家庭实力等方面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到底如何呢?
家庭权力就是一家庭成员改变其他家庭成员行为的能力。简单来说,家庭决策权就是谁在家里说了算的问题。家庭决策模式可分为不同的类型。G·Becker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出发,将家庭理性决策分为个人决策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两种[12]。梁开卷对家庭的二分决策模式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将决策权模式细分为个人决策、部分参与决策和全体参与决策[13]。Baumrind在大量的家庭观察、实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家庭决策模式:专制型、权威型(民主型)、宽容型和放任型[14]。方晓义、郑宇通过聚类分析将父母抚养方式分为平均型、矛盾型、放任型和积极型四种类型[15]。Hoddinott and Haddad发现,当母亲控制大部分家庭资源时,孩子做的更好[16]。Mouchiroud认为孩子的社会创造性与父母决策模式有关系[17]。当双亲采取民主开明的教养态度时,子女在创造力、知识生产力的表现比采取专制教养态度家庭的子女优秀[18-20],民主型的家庭模式则有利于孩子创造力、知识生产力的发展,而专制型和放任型容易使孩子养成依赖、服从的习惯,知识生产力、创造力水平低[21]。
有学者关注家庭氛围对知识生产力的影响。家庭氛围可根据不同的情绪感受分为平静型、和谐型、冲突型和离散型四种,许多研究发现,“和谐型”家庭的适应性较好[22],有利于孩子良好个性的形成。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有利于创造个性的良好发展[23],对孩子社会创造性、知识生产力有正向的预测作用[24][25]。也就是说,和谐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能够促进家庭知识生产力的提升。
家庭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其规模大小也有可能对家庭的知识生产力产生影响。家庭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其规模大小也有可能对家庭科技创新力产生影响。张珊明通过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家庭环境进行检测发现,独生子女的创新性低于非独生子女[26]。
家庭经济实力与家庭科技创新力、创造力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Venu Gopal Rao和Satyapal、Parsasirat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地位与家庭知识生产力、创造力紧密相关,家庭收入较高或父亲的职业为商人时,子女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水平更高[27,28]。国内部分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师保国和申继亮认为家庭经济地位对创造性有显著预测作用[29]。而仍有部分学者与此观点不一致,如万兴松等人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关系[30],吴晓颖也认为在家庭教育中,硬环境所起作用不大,尤其是家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31]。
综上可知,对于家庭知识生产力,以往的研究多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教养方式与子女成长进行研究,多基于外国情境,较少基于中国情境从政治社会学视角——权力角度进行分析;多从教养方式对子女的社会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较少直接对教养方式与知识生产力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多以描述性、质性分析为主,较少进行量化的实证研究;且家庭权力模式、家庭氛围、家庭规模、家庭经济实力等对家庭知识生产力的研究结论不一,有待进一步验证。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聚焦于社会学的家庭环境中的权力场,采用量化实证的分析方法,分析家庭环境中,家庭决策模式、家庭规模、家庭氛围、家庭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于家庭知识生产能力的影响,解释家庭决策模式等与知识生产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积极有效率的家庭决策模式,寻找提升家庭知识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水平、创新能力展开学理思考。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家庭决策权模式对知识生产力有何影响。对中国家庭来说,集权型抑或民主性型的家庭决策模式,知识生产力高低如何?(2)家庭氛围和谐美满与否对家庭知识生产能力如何?(3)家庭规模影响又如何?中国多是小家庭更有益于孩子成长吗?(4)经济实力在家庭教育中是基础性作用吗?家庭收入越高真有利于家庭知识生产吗?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笔者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大学生进行调查,第一,他们具有独立行为能力,能够方便回答调查问题;第二,学校是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便于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第三,可以通过询问大学层次类别来区别家庭知识生产力。对在校大学生所处的大学进行配额方便抽样。这样做,尽管样本代表性有所欠缺,不能用于各层次样本分布的总体推断,但不影响变量间关系的解释性说明。以学生的大学层次对家庭知识生产力进行操作化辨识测量,姑且认为:大学层次类别越高,家庭知识生产力越强,这符合家庭知识生产力概念属性逻辑,也符合经验观察,设计调查问卷,开展预调查后修改问卷正式收集调查资料,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回答上述问题。问卷调查的因变量为“知识生产力”,主要自变量为家庭决策模式、家庭氛围、家庭规模、家庭实力和性别偏好等,变量具体操作化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调研过程
通过控制学校的层次类型配额抽样,保证调研基本平均覆盖到各类学校。按照上述操作化设计,将全国高校分为七类:C9高校、非C9的985高校、非C9非985的211高校、非以上三类的一本高校、二本、大专、中专。按照方便抽样方法发放问卷。调研对象为这些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在预调查中,共发放了30份问卷,用于检验问卷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修改完善了问卷。在真实调查过程中,在七类不同的学校配额发放了300份问卷,回收到了297份,其中有效问卷279份。回收率99%,合格率93.9%,回收率和合格率都较高。收集到的数据在SPSS17.0中进行录入、处理和分析。
(三)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1.被调查大学生及其家庭基本特征。从性别来看,男性比例为48.7%,女性为51.3%;学校类型中,来自C9高校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4.7%,来自非C9的985高校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10.8%,来自非C9非985的211高校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11.8%,来自非以上3类的一本高校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35.1%,来自二本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28.7%,来自大专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7.5%,来自中专的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1.4%。家庭人均收入较平均,平均月收入多为3 000元以上(见表1)。由于是配额的非概率抽样,获得的分布比例虽不便进行规模推断,但不影响变量间关系的解释与验证。
2.被调查大学生主要家庭决策模式。从受访大学生填写的问卷中,笔者发现主要的家庭决策模式有两种,即民主决策模式(所有家庭成员在进行家庭决策时处于平等的地位)和集权决策模式(家庭成员在进行家庭决策时处于不平等地位或缺少发言权),其中,采用民主决策模式的家庭占62%,采用集权决策模式的家庭占38%。
3.学生主动/被动获取家庭决策权的情况。在所有受调查学生中,90%的学生具有家庭决策权。在这些学生中,有68%的学生家庭决策的权力来源是父母(长辈)从小就给予机会,有32%的学生是依靠以及主动争取而获得的家庭决策权。所有受调查的10%不具有家庭决策权的学生中,37%的学生主动提出过想要参与决策,63%的学生没有提出过想要参与决策的意愿。
4.学生提过建议也仍然不具备获得家庭决策权的原因。50%的人认为是因为父母能够给出最优决定,因此没有参与的必要,也就不具有参与决策的资格;40%的人认为因为父母觉得学生提出想要参与决策只是说着玩玩,没有当真,因此仍然不具备决策权;30%的人觉得父母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做决定大人来就可以。
5.学生想要参与决策的原因。32.6%的人表示在想要体现自己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更希望自己能参与做决策,34.5%的人表示在关系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更希望自己能参与做决策,32.9%的人表示在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出一个更好决定的情况下更希望自己能参与做决策。
三、结果与讨论
在279个来自不同类型高校的被调查者中,81.7%的被调查者的家庭采取民主决策模式和部分民主决策模式,但是依然有18.3%的家庭采取的是专制决策模式。因此,本文将综合利用列联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来验证家庭决策模式是否对科技创新能力有影响。
首先,利用孩子的自主性与决策模式考察问卷的建构效度。由卡方检验可知,不同的家庭决策权模式与孩子自主性之间有关(P=0.000),且 φ=0.331,在0.2~0.4之间,显著相关,符合设计,达到建构效度,说明问卷资料数据的质量达到要求。
其次,不考虑自变量综合作用的影响,只考虑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单独影响,为此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表2可知:(1)家庭人数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知识生产力大小的影响力不显著;(2)性别对知识生产力大小的影响非常显著,男性子女家庭的知识生产力水平明显比女性子女家庭的知识生产力水平要高;(3)家庭决策氛围对知识生产力大小的影响比较显著,满意度越高,家庭知识生产力越高;(4)家庭决策权模式对知识生产力大小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非集权模式家庭的知识生产力水平普遍比集权模式家庭的要高。

表2 各因素对知识生产力水平影响的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汇总
再次,为了更好地观察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新知识生产力的重新编码:1=知识生产力低,包括二本及以下高校;2=知识生产力高,包括二本以上高校。如此,进行家庭决策模式与新知识生产力变量交叉列联表如表3。由表3可知,在非集权模式的家庭中,部分民主部分集权模式的家庭的生产力水平要比民主模式的知识生产力水平高,这一结果值得注意。

表3 家庭决策模式* 新知识生产力交叉制表

表4 家庭决策模式*新知识生产力交叉制表的对称度量
进一步地,为了解释为何子女性别差异显著影响家庭知识生产力,进行了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考察家庭决策模式对知识生产力水平的具体影响。以性别为控制变量,做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的交叉表(见表5),控制性别后,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之间的Gamma相关系数值为0.428(其中男生组,γ1=0.601;女生组,γ2=0.282)(见表 4)。

表5 控制性别后家庭决策模式与新知识生产力的关系
未控制性别变量前,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的Gamma相关系数为0.460,而控制性别变量之后,不考虑性别影响时,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28,其中男生的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的Gamma系数为0.601,远远大于控制性别之前的系数。再具体结合表5,可见: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家庭决策模式对知识生产力的影响,在不考虑子女性别影响时,家庭决策模式对知识生产力影响大;否则,影响较小。由此可见,一旦确定子女性别是男孩,便会强化集权教育模式,反而会降低些许家庭知识生产力,进而使得家庭决策模式对知识生产力影响降低。这说明:一方面,性别因素的确影响家庭知识生产力,中国家庭教育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另一方面,因为子女性别是男性,反而增加了集权教育的可能,进而会稍微削弱家庭知识生产力。
最后,为符合客观实际,了解影响家庭知识生产力的因素来源及其综合作用,回答上述问题,进行了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将原知识生产力因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为新知识生产力变量:1=知识生产力低(二本及以下院校);2=知识生产力高(二本以上高校),自变量先采用向前:Conditional方法进行信度筛选,然后综合判断得出如表5分析结果。该回归方程Nagelkerke R2=0.217,达到0.2~0.4设计要求,除家庭人均收入变量外,其它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5,达到信度要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6 逻辑回归方程中的变量
由表6可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影响家庭知识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有:家庭权力模式、子女性别、家庭决策氛围、家庭规模等。其中,家庭决策权力模式是最重要因素,家庭民主决策比集权决策会增加324.2%概率提高家庭知识生产力(P=0.000);第二,子女性别男性比女性会增加229.2%概率提高家庭知识生产力,显明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浓厚(P=0.000);第三,家庭决策氛围对知识生产力有正向作用,满意度每提高1分(5分制),将增加71.1%概率提升家庭知识生产力。家庭和谐美满将有益于家庭知识生产力(P=0.012);第四,出人意料的是,家庭规模对家庭知识生产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人数刻度每提高一等,将增加48.2%的概率会提升家庭知识生产力(P=0.041)。中国普遍的计划生育带来的小家庭并不有利于孩子成长,反而大家庭有利于知识生产;最后,家庭收入对知识生产看似有正向作用,收入等级每提高一级,将增加16.4%的概率提升家庭知识生产力。但是,显著性水平为0.321,没有通过信度检验。
四、结论和启示
根据上述讨论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提升家庭知识生产能力首推家庭民主教育。家庭决策模式对知识生产力具有显著影响,反映了家庭权力格局对孩子成长的极端重要性。在集权模式、民主模式、半民主半集权模式这三种不同的家庭决策模式中,半民主半集权模式环境下孩子的知识生产力最高。这一点值得注意。民主模式优于集权模式。半集权半民主的家庭决策环境更有利于孩子知识生产力的发展,最有利于孩子知识生产力的培养,这一立场呼吁走向有限自由和有限民主的家庭教育。布赖斯、杜威等学者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民主的家庭中,学生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必然运用于学习的自我管理中,继而促进学生的学业水平。作为衡量现代家庭、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文明程度的标志,民主应该从社会的细胞——家庭开始。家庭民主不单是非国家形态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民主建设的重要载体,并且是知识生产力、科技创新力的重要源泉,是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社会与国家的重要抓手。对此,在家庭教育中,尤其是家庭决策中,家长应该坚持民主精神的立场,尊重并重视孩子的主体性。
其次,教育模式的性别偏好问题。在现代社会里,理应男女平等,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家长会依据孩子的性别,而创造不同的教育环境,从而带来不同的知识生产力效果。但令人吊诡的是:尽管在家庭教育中存在性别偏好,重男轻女,但因为是男性子女,会更多地采取集权决策教育模式,反而会削弱家庭知识生产力。
第三,家庭决策氛围和谐美满有助于知识生产。家庭决策氛围越和谐越有利于孩子成长。家庭氛围和谐、决策满意,成员间对情绪的理解和反馈越正面,能够促进彼此信任感,进而内化为学习潜力和动力,其子女会越优秀。有相当部分家庭认为孩子没有决策权而将其排除在决策权限之外或者认为孩子的重心应该放在其他方面而忽视孩子的意志表达,这是典型的“家长制”思想,不利于孩子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意识和行为的培养,不利于家庭和谐,导致决策满意度低,从而降低家庭知识生产能力。
第四,发扬优良的大家庭传统,有益于子女成才。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理性的张扬,必将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迎来人情冷漠的冬夜。但中国优良的大家庭传统文化,具有良好的现代价值理性色彩。在韩国,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经济成长,三世同堂的传统大家庭逐渐流行,这是不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归还有待观察,但调查研究证实:在现代社会中,大家庭对于子女教育和成长,家庭知识生产力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五,现阶段家庭经济收入对知识生产力影响不显著。原以为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家庭经济实力对知识生产力是决定性的,但实证调查显示,经济地位对家庭知识生产力不是主要的。相反,看起来家庭经济收入越高,知识生产力反而有些许降低(P=0.108),反映“纨绔子弟少伟男”的俚言旧俗还有些许社会空间。当然,家庭经济收入对知识生产力影响不显著,也可能是受本研究样本量的局限。
所有这些结论,聚焦于中国家庭环境中的权力场,是把知识生产力研究由国家、地区、组织等引入社会细胞——家庭的一次有益尝试,走出以往家庭教育研究心理学质性研究的窠臼,基于中国情境社会学实证调查研究,分析家庭决策模式、家庭性别教育偏好、家庭和谐、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家庭知识生产力的影响,解释家庭决策模式与知识生产力等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积极有效率的家庭教育模式,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水平、创新能力的提高展开学理思考。在家庭决策权力模式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礼治秩序趋于消解、现代民主秩序尚待建立的当口,市场经济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式微的时代背景,计划生育政策小家庭大行其道的中国特色,大家庭式微小家庭兴盛不可逆转,这一切给家庭教育、社会创新和国家建设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情形下,在现代家庭教育中,适当考虑这些问题,开展这项研究,反思现代家庭教育环境,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对家庭知识生产力的提升,具有理论的、实践的和方法论意义,对建设民主社会、知识型城乡、创新型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戴理达.论知识生产力[J].贵州社会科学,2002(4):2.
[2]孙向军.知识生产力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2002.
[3]Bell J G,Seater J J.Publishing performance:Departmental and individual[J].Economic Inquiry,1980,16(4):599-615.
[4]Creswell J W.Faculty Research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the Scienc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M].Washington,D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5:27-43.
[5]Levin S G,Stephan P E.Age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 scientist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89,30(5):531-549.
[6]Tien F F,Blackburn R T.Faculty rank system,research moilvafion and 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6,67(1):2-22.
[7]Stack S.Gender and scholarly productivity:the case of criminal justice[J].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2002(30):175-182.
[8]Baird L L.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in doctoral research department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factor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1,32(3):303-318.
[9]Jordan J M,Meador M,Wakers S J K.Efforts of departmental size and organization on the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 economist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8,7(2):251-255.
[10]Jordan J M,Meador M,Wakers S J K.Academic research productivity,department size,and organization:Further result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9,8(24):345-352.
[11]Kyvik S.Are big university departments beRer than small ones[J].HigherEducation,1995,30(3):295-304.
[12]Becker G.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393-397.
[13]梁开卷.决策模式选择的权变性[J].领导科学,1996(6):4-5.
[14]Baumrind D.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J].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1991,11(1):56-95.
[15]方晓义,郑宇.初中生父母抚养方式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4):32-36.
[16]Lawrence Haddad,John Hoddinott.Women’s income and boy-girl anthropometric status in the Côte d'Ivoire[J].World Development,1994,22(4):543-553.
[17]Mouchiroud C,Lubart T.Social creativity: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6 to 11-year-old childr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2.26(01):60-69.
[18]Kager-Bone L.Parenting the gifted young scientist:Mrs.Wizard at home[J].Gifted child today.1993,16(2):55-56.
[19]Snowden E L,Christian L G.Parenting the young gifted child:Supportive behaviors[J].Report review,1999,21(3):215-221.
[20]Pohlman L.Creativity,genderand the family:A study ofcreative writers[J].Journal of creative writers.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1996,30(1):1-2.
[21]郑雪梅.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概念与创造力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09.
[22]刘金花.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4):5-9.
[23]汪玲,席蓉蓉.初中生创造个性、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关系的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02-108.
[24]肖雯.中学生社会创造性的发展[D].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08.
[25]郑剑虹.高创新能力大学生的特点及影响因素[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23-27.
[26]张珊明.民办院校大学生家庭环境测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4,(11):80-83.
[27]Venu Gopal Rao T,Satyapal D.Socioeconomic status,scheduled caste and creativ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Management,2011,1(4):17-26.
[28]Parsasirat Z,Foroughi A,Yusooff F ,Subhi N ,Nen S ,Farhadi,H.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emersion adolescent creativity[J].Asian Social Science,2013,9(4):105-112.
[29]师保国,申继亮.家庭SES、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30-34.
[30]万兴松,费龙才.影响城市中学生学习成绩的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2003,(1):45-46,44.
[31]吴晓颖.家庭环境影响学生创造力和学习成绩的调查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