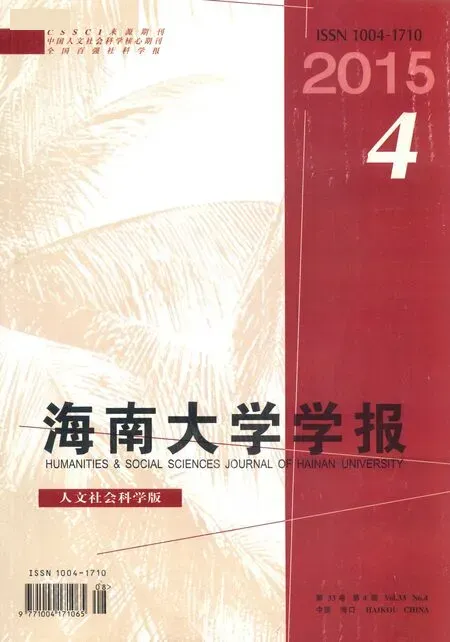黎族作家的文化乡愁与返乡之旅
詹贤武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海南 海口571100)
当代黎族社会正面临着剧烈的变革,黎族文化亦随之发生时代性变迁。面对各种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黎族文化主体产生了某些集体性的文化焦虑。黎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呼唤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归,把黎族传统文化作为创作实践的审美对象,叙写着本民族的生命史,守护着黎族人民的精神世界。
一、寻向文化身份的回归
文化身份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及文化归属的认同感,是本民族得以生存、稳定、延续的的基础。法国文化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给“文化身份”的定义是:“专属于一个族群(语言、宗教、艺术等)的文化特点之总和,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个别性,一个个体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1]。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价值体系,并且通过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伦理、宗教信仰等体现出来,由此决定每个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
呼唤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归,是黎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普遍的主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夹击下,黎族文化身份出现了模糊化、多重化的趋势。
黄仁轲的小说《最后一条筒裙》,以母亲珍藏的筒裙道出了传承黎族传统文化的困惑:“我这一生,织过无数条筒裙,除了自己穿,其他的都送给了别人,现在就只剩这么一条,原来要给你姐姐出嫁用的,可是她不喜欢。于是我把它留了下来,想给你哥娶媳妇当聘礼,可是你嫂子也不要”[2]。筒裙作为黎族女性的服饰,是黎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之一,也是其文化身份外显的物质形式,母亲对筒裙深爱与难以割舍的心情,年轻一代却难以理解,小说通过对母亲筒裙情节的聚焦,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生活与审美已汇入现代节奏,而母亲却怀着一份珍藏的筒裙晚辈不喜欢、送不出去的深深遗憾,这种遗憾里,有对民族身份模糊化的落寞和无奈之叹。
在黎族作家的身上,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会时时冒出来——他们对外界事物保持着极大的关注,同时又在心灵深处秉承黎族的文化传统。由于黎族属无文字民族,在创作中,黎族作家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于是,创作思维上实现黎汉双语之间的快速转换,既要在汉语言文化中凸显黎族文化的特性,却又无法出离汉族文化的笼罩,所以,文化焦虑一直困扰其创作活动。“用黎语思维,用汉语表达,而两者的语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写作时,确实会面临一个‘思维转换’的问题。这也是很多黎族作家在语言表达上不顺手的原因。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熟悉汉字和汉语,才可能写出好作品。”[3]在不同语境中进行双重“思维转换”的过程中,黎族作家的艺术想象多少受到了没有与黎语相匹配文字的困扰,创作自如受到思维与书写双重转换的限制,在这种随时随地需要两边思虑的“转译”中,不仅恰如其分的表达实属不易,也极易在无时无刻的“转译”中流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因此他们坚持和固守着自己的创作所要付出的努力,是汉族作家所无法想象的。
每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有特定的文化身份。一般而言,每个人的文化身份是由种族文化身份、族群文化身份和民族国家文化身份三方面内容构成的。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文化主体受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社会变迁、迁徙移居等后天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或弱化自己的族群文化身份或民族国家文化身份。事实上,每一个文化个体可以同时拥有国家归属感、民族归属感和族群归属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容、相通的,它们相互构成一个认同的整体性,在不同的归属感的层面上,有着相应的文化身份。黎族作家的使命,是唤醒黎族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以文化自强的姿态回归本民族的文化身份。
黎族作家多把人物活动或故事情节设在其熟悉的特定空间,一般以大山中寂静的黎族村庄为背景。在这种环境中,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自然地嵌入黎族山寨之中,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点也就与山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浓郁的黎族生活原生态袒呈笔端。这种特殊的空间感,不仅是黎族作家对本族生活场景的缱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回归。郑文秀认为:“这些年,我也亲眼见证着黎族地区的发展变迁,因此,我想试图用诗歌的形式去表达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许,我所抒发的只是黎族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些表象,但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民族,走进这个民族,了解这个民族,也想让这个民族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将为这个民族感到骄傲”[4]。黎族作家的叙述萦绕于黎山深寨,这里是他们生命发源和伸展的摇篮,这里的人物和故事是他们古老血脉的现代延伸,不但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在这种联系中可见黎族寄寓其中的独特身份。在创作中,通过对黎山深寨的空间设置,黎族作家希望把黎族地区大山深处的风情、以及这个千古民族的故事告诉外面世界的人们,由此加深其民族记忆,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黎族作家龙敏在长篇小说《黎山魂》中描绘了黎族两个古老部落:巴由峒和波蛮峒。两峒之间世代结仇,相互械斗,但在民族共同遭受到封建官府的欺压时,却可以不计前嫌,歃血为盟,一致对抗官府。作者把黎族人民反抗封建官府压迫的历史放在这两个部落中展开,展示了封建社会中黎族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抗争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小说中,龙敏全景式地还原了清代黎族的社会生活,描绘了诞生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等生活图景,而这些图景只能在黎山深寨中出现,离开了海南深山老林的黎寨,这样的画卷不可能展开。《黎山魂》中故事情节所发生的空间,无疑是黎族人民世世代代聚居的地方,这里维系着黎族人民的情感与生命,也倾注着作者对故土无限的热爱,因此,这一空间成为民族感情的载体,也成为其成员获得民族身份认同的要素之一。
黎族作家在小说中对空间感的强调,体现了黎族对民族意识的追求,黎族文学的创作需要通过对本民族意识的追溯,重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但是,这种文化身份的重建,不能简单地执着于对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叙写,而应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从发展的视角对民族文化重新进行审视,辨析黎族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关系,在保持着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实现黎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坦诚对话与沟通。
二、谁是黎族
文学创作是作家在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上精神立场的表达。在黎族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复杂感怀本土本族寻根的意识、乡土意识和怀旧意识,而这些都在民族认同中汩汩流淌,被黎族作家以多样化的叙事方式表现。他们通过文学手段整理、还原、重构黎族文化传统,让民族意识既诉诸文字,又从书写的世界中走出,探问“谁是黎族”、“我是黎族么”?由于文化身份的模糊,不论在书写还是在现实中,这些问题始终是黎族作家苦思的民族本源难题。郑文秀在诗作《一个氏族的生命流向》中,以深沉的诗语骄傲地赞美黎族远古祖先:
风中,母亲在一场雨后怀孕了/闪电般生长的情人/从山兰酒中悠悠走过/炊烟袅袅悬挂在树梢/放荡的笑声中泛起的彩虹/梦幻般的架在大山的窗口/你终于在悲壮的回眸中/让暴风雨的汛期/清洗了昔日的焦虑/撒开的胸怀/让大地在温暖的阳光下/构筑着氏族的牌坊,此刻/葱茏起舞的森林/打起了绿色的喷嚏/含羞盛开的花朵/在高高的枝头上对饮风月/无数个图案在跳跃,族谱上/一条生生不息的涓流/带着虔诚的古老的歌谣/豪放地奔向大海。[5]
谁是黎族?诗人眼前“无数个图案在跳跃,族谱上”,黎族没有文字,却有着氏族标志的图案,这些图案不是刻在图腾柱上,而是雕在黎族祖先的脸庞上、绣在黎族祖先的筒裙上的。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保留着文身的习俗,黎族便是这罕见族群中的一支,这种以自己肌肤雕琢而成的氏族标志是如此地与众不同,以致可使图案直通“族谱”,连接起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故事和生生不息的世代繁衍。那个“从山兰酒中悠悠走过”的情人,是黎族么?当然是,否则他就不会“闪电般生长”,否则就配不上母亲风雨中的孕育。他该是醉醺醺地有着“放荡笑声”的汉子吧,是“闪电般”匆匆来回于不落夫家的黎族女人的情郎吧?他是黎族么?如果不是,怎会有那令人难解的“悲壮的回眸”?但是,在“葱茏起舞的森林”怀抱,在彩虹如一架天桥“梦幻般的架在大山的窗口”的孟浪时分,这“悲壮”来自何方、何事、何情?
答案在——“回眸”。或许,他在世世代代流转不息的传说里,回到祖先登岛时的四顾茫茫中;他在醉眼迷离时,回望先人千古一梦的深山离群索居。这其中,有多少惆怅无法消解,有多少苦楚无处诉说,有多少悲悯百转回肠。然而,即便苦难、暴怒、隐忍,操劳、跋涉、艰辛,都被黎族坚韧地扛过历史肩头,被生性豪放地谱入年代的歌谣,流转于口口相传的黎寨古树梢头。诗歌中,黎母孕育的是黎族从古到今的独特秉性,是一缕忧郁回眸中始终淳朴豪放的黎族天性之袒露。在郑文秀跳跃的诗句中,人物虽隐约闪烁,但他们的黎族印记在这个世界中的独异色彩却是鲜明的。
谁是黎族,去问船形屋。明代《海槎余录》载:“凡深黎村,男女众多,必伐长木,两头搭屋各数间,上复以草,中剖竹,下横上直,平铺如楼板,其下则虚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栏房’”[6]。黎族民居船形屋如一艘倒扣的船篷,属于古代南方杆栏式住宅的一种,这种杆栏式民居透露了黎族与上古南方百越族之间的族源关系。千百年来,在船形屋檐下,演绎了无数黎族生活的悲欢故事,也见证了黎族亘古不变的性情,遂成为黎族传统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众多黎族作家魂牵梦绕的族群记忆。黎族作家作品中不乏对船形屋的描写,如韦海珍的《船形茅屋》、黄照良的《船形屋的倾诉》、王蕾的《远去的船形屋》、唐鸿南的《千年新娘——赠船形屋》、胡天曙的《茅草屋之歌》等。在作品中,船形屋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人物在其中穿梭,情节在那里展开,命运在里头跌宕,令人难忘的是,黎族作家笔下的船形屋始终如同母亲的怀抱,庇护着黎族儿女的成长,也把他们养育成为一代代黎族人。
龙敏是最早用小说这种体裁进行创作的黎族作家[7]51-52,他的小说《黎山魂》取材于清代光绪年间黎族头人吕那改所领导的罗活峒举义一段史实,据他介绍,作品中的“乐安城是明代万历四十四年间,崖州府派驻黎族地区的屯兵城堡,也是崖州府设在本地区的一个派出机构。它历尽明、清、民国的沧桑,至今仍有遗址存在”[8]1。小说中的黎族哈方言族群居住的地区为古崖州属地,历史上这里曾是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多民族聚居区,素有“四族八语”之称。这里的黎族人在封建官府的压迫之下,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也多次被官府血腥镇压。当龙敏回望这段历史时,仿佛看到自己的先人为了民族生存赤膊徙脚奔向勇斗的搏杀场,那段撕心裂肺的惨烈搏斗史令人心潮难平。于是,通过《黎山魂》,他对黎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叙述,呈现了黎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壮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此,张浩文指出:“黎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海南岛的原住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可由于地理隔绝,他们一直被边缘化;由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历史上一直是被别人观察和描述的‘他者’。历朝历代,关于黎族的文献记载,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大多充满歪曲和污蔑,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妖魔化。应该有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龙敏的长篇小说《黎山魂》终于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这是黎族作家自己创作的反映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长篇巨制,它可以让世人睁大眼睛看看这个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创造。”[7]53
而龙敏自己是这样说的:“凡是我祖先走过的脚印我都要写。这是我作为黎族后代的责任。无论这些脚印是大是小、是美是丑、是善是恶,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走过,留下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在黎族子子孙孙的心灵中代代相传。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引为自豪”[8]1。在笔者看来,这是龙敏的真情告白,他把血液里与先人一样执拗不屈的精神、灵魂中对先人的深切追怀,化作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和史诗般的故事,以不屈血性告诉世人——我就是黎族。
三、在文化断层与乡愁记忆中返乡
文化断层是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在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的差异性。就文化时空的连贯性而言,文化断层是当下的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中间出现了不对接、不吻合、不连续的状态,造成主体文化的传统无法延续而被迫中断。文化断层对于一个民族的传承与发展而言是一种危难,它将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体系陷入濒危之地。
黎族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存在文化断层的现象,这种断层与时代和整个中华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也与黎族自身文化的某些缺项以及边缘位置相关,这种断层让许多黎族学者扼腕叹息。龙敏基于对黎族文化的思索与清理,认为黎族文化曾经发生过两次明显的断层现象:
黎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上辈人由于不知字,没文化,只能依靠口传的方式来传播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也许,在传播的过程中,无意地使许多珍贵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了。这是黎族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层。如今,我们已经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一代,能用汉字以及一些先进设备来记录传承祖先存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能够有效地存留住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呢?随着国内外大势所趋,他们会追求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呢?他们会如何看待祖先所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断层。[9]
如果说黎族文化的第一次断层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么,第二次断层就既有外部的客观原因、也有内在因素。第一次断层的原因主要是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量的留置文化无法保存下来,而仅靠口头方式所进行的世代传递,在文化传承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变异甚至失传,何况从20 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时代,使黎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实际上逐渐失掉了其赖以存活和延续的根基——老一代文化口传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文化接承人在书写文化教育中成长、成熟,两代之间对世界的认识眼光已经不同,传承与对接之间的榫卯是否相合,仍是需要甄别的问题。就第二次断层原因的复杂性而言,从大的方面说,是黎族传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出现传承危机;从小的方面看,则接受新式教育的黎族新一代,更容易接受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本族亘古不变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动摇。从断层的程度而言,第一次断层是渐进性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可以延续较长时间,族群有充分的时间适应这一断层;而第二次断层是突变性的,发生的时间比较短,但震动剧烈,但对黎族传统文化的造就是改变性的,在两代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正如整个华夏民族百年来都告别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一样,在走向工业甚至后工业、信息文明的途中,文化乡愁不时袭面而来,“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记忆关系,由于大自然向他们提供了生活或者生存的手段后便迅速忘记了大自然,这种记忆关系才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并得到不断发展”[10]。跟许多汉族作家或其他民族作家对文化记忆的拾掇一样,黎族学者和黎族作家是黎族文化的敏感者或敏锐者,他们的研究或创作,恰如一次次回到与先人和传统对话的场景,感怀先人、接续和甄别传统,重拾在现代生活中可能被逐渐遗落的文化记忆,在文化乡愁中反刍历史的晶体,为民族的继续前行寻回坚定的目光和坚韧的筋骨。
文身是黎族文化中浓重的一笔,是黎族雕刻在自己身上的“敦煌壁画”。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渗入和改造,文身已从黎族文化中淡出,成为一种过往的回忆。如今的黎族年轻人对文身已从陌生到隔阂,对于前代人的文身习俗难以理解,黄学魁的遗作《纹脸奶奶》道出了不同时期两代人的文化沟壑:
她的脸上总刻着一张网/一张永不退色的几何形的黑网/那张黑网/伴随她走完童年走过少女走到老年/那张黑网/是她的迷茫她的惊惶她的希望她的寄托/她的归宿也是她的藩篱/那张黑网/是她的全部历史/奶奶与我之间/相同的是/承传着一样的脸谱/流淌着一样的血脉/不同的是/我的脸上,已经不再/延伸了她那张黑网/她生活在网内/我生活在网外/她隔着黑网看世界/我站在网外看世界。[11]
作家把文身的纹案比喻为“黑网”,奶奶一辈子都被罩在网里面,从少女时代一直到老年,奶奶始终走不出那张“黑网”,就像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黎山,“黑网”是她的归宿,但也成了她的“迷茫”和“惊惶”——面对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黑网”内的奶奶不知所措,那是她不知道、不懂得的世界。这种“迷茫”和“惊惶”,使她一辈子只能蜷缩在幽深的黎山,那张纹脸的“黑网”是一道她无法逾越的“藩篱”,可以想象,奶奶如果带着她纹脸的“黑网”走出黎乡,走进现代都市,马上就会成为“被看”的对象,这是她的“惊惶”所在,正是这张“黑网”的藩篱,阻隔了她走出大山的脚步。
诗中的“我”作为奶奶的隔代人,“承传着一样的脸谱,流淌着一样的血脉”,却是阳光下的网外之人,她脸不可能像奶奶那样被罩在网里,而是睁着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回眸黎乡奶奶网状般的纹脸,她或许内心疑惑,但却毫不犹豫地走向都市、走向新生活;回想奶奶困守黎山的一生,她或许心生感叹,却更可能庆幸自己具有走出的资本和能力。
然而,在网内的奶奶和网外的“我”中间,还应有另一代人——母亲,她的身影在哪里?在网内和网外之间,她的位置在哪里?在血脉相承的三代人中,网内的奶奶是如何演绎成全然置身于网外之“我”的?这个消失在诗歌中第二代人重要而神秘,正是她隐而不露的存在,留存了奶奶网内的生活,也是由于她的改变,才有了网外“我”面对外面世界的自如。如果不出所料,她应是20 世纪5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黎族人,是接受现代教育并努力走出旧式生活的一代黎族人,她伫立于三代人中间,就像一条从黎山铺出的路,奶奶在这里可以眺望外面,女儿从这里可以走向未来。那么,她是怎样的黎族人?纹脸还是不纹脸?在网内还是网外——这是黄学魁的作品留给人们的猜想,也是黄学魁所据有的位置,对黎族前身后世的勾勒。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许多黎族作家对黎族文化断层表现出深切的忧虑。黎族没有汉族那样严格的姓氏典册、尤其是宋明理学以来的婚姻制度,因此,隆闺是自古以来黎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承载着黎族人的许多美好记忆。如今,随着现代户籍制度的完善以及黎族地区大批青壮劳力涌入城市打工,情事也早已融入霓虹斑斓的都市夜色中,隆闺逐渐从黎族生活中消退。唐崛在《消失的隆闺》中感叹:“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入,黎族的婚俗观念也在变,隆闺这种婚俗文化也在现代黎族人中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它也只能成为老一代黎族人的美丽回忆,成为了年轻一代黎族人美丽的故事。”[12]在黎乡黎寨的生活变迁中,传统在现代文明的推进中不断退守,甚至可能逐渐荒芜。亚根的长篇小说《槟榔醉红了》,以社会转型变革之中的黎族社会为背景,通过王山才一家人在城市与乡村不同的社会背景中的身份转换,描写了发生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南中部山区,留在乡下的人和进了城的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下人的命运情态。“小说以复调的结构、错落的情节和多变的手法上的穿梭斡旋,在天真与浪漫、诙谐与风趣、宁静与清冷以及喧哗与骚动中摸爬滚打,时而低调行吟,时而纵情舞荡,时而放声歌哭,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描绘出当代黎族人生活的真切景象”[13]。
在现代生活中,黎族作家是敏感的,面对本族的文化断层,他们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焦灼,因而在作品中探寻古老的文化记忆,成为一程不言而喻的文化苦旅,他们一边咀嚼着传统习俗的槟榔,一边打量着渐行渐远的时代大潮,而如何在这之间平衡情感与理智、创作与思考,是不得不面对的书写难题。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12]。不管是行动上还是心灵上的重返故里——对于黎族作家而言,都并非仅仅是远方游子的回乡之行,而是他们用心灵去亲吻祖先足迹遍布的那片土地,用自己的智慧和激情抒写着黎族壮烈的生命史。这一切,从来没有停止过。
[1]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2]黄仁轲.最后一条筒裙[N].中国民族报,2010-07-23(11).
[3]杨春.“离开黎族,我就不是一个作家”——黎族当代作家访谈[N].文艺报,2013-04-03(05).
[4]梁昆,郑文秀.黎族文化深情吟唱的歌者[N].海南日报,2014-03-20(B11).
[5]郑文秀.一个氏族的生命流向.[N],海南日报,2014-07-10(B10).
[6]顾蚧.海槎余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400.
[7]张浩文.新时期海南小说创作述略[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
[8]龙敏.黎山魂[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1.
[9]龙敏.浅谈黎族优秀传统文化——古典民间文学[C]∥首届海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节暨研讨会论文集.2012:111.
[10]克劳德·拉费斯坦.欧洲文化的乡村根源和21 世纪的挑战[J].第欧根尼,1995(1):1-9.
[11]黄学魁.热带的恋曲[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28-29.
[12]唐崛.消失的隆闺[M]∥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黎族卷.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58.
[13]邢孔史.简评黎族青年作家亚根的新著《槟榔醉红了》[J].三亚文艺,2013(3):81-82.
[1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