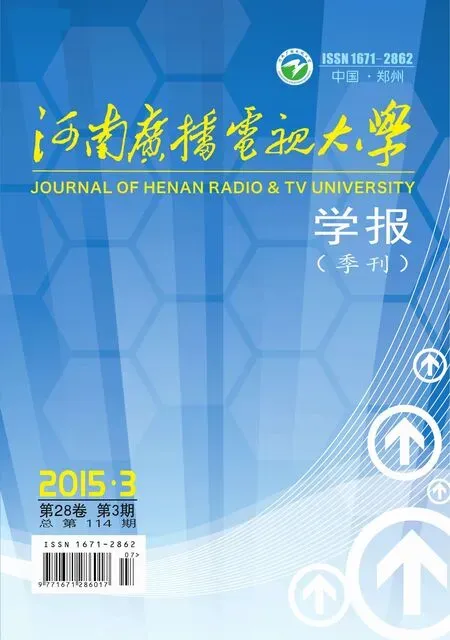浅析凌淑华小说中的类型女性
汪文琴
(赣南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项彻底的反封建文化、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启蒙运动,给整个文化领域、观念领域带来了一场规模大、具有“弑父”性特征的“辛亥革命”[1],让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女性命运改变,一批富有才情的女作家进入文坛。她们与男性作家地位平等,用同样充满艺术个性的创作直接建设“五四”新文学。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作家有冯沅君、庐隐、冰心等,凌淑华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过她是独具特色的一位。
身为女人,她们关注的都是女人命运,描写的都是女人际遇,讲述的都是女人故事,从而探索的都是女人出路。小说取材于日常生活,讲述历史转折时期,爱情、婚姻、 家庭问题的迷茫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婉顺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形象是凌淑华塑造的小说人物,并且类型多样。
一、死寂闺房及其延伸的“绣枕”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凌淑华从高墙大院、寥落闺阁里挖掘出的一群“老中国”式女人,有人把这伙女人称为“绣枕”。[1]凌淑华并没有把这些人写成古董,而是站在新角度来复述这一封建时代豪门女人的经历和命运。作者从未出阁的小姐闺秀写到媳妇再写到婆婆,将她们的故事串联成“绣枕”故事的“少女篇”“少妇篇”“老年篇”一个系列。
(一)“绣枕”故事之“少女篇”
《绣枕》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可能是五四时期唯一一篇泄露女性内心经验的作品, 它全景展示了一个以往不进入人们视线的旧式女子生活空间, 与世隔绝的死寂闺房”。[2]
作品中的大小姐,待字闺中,孤独寂寞,只有刺绣能抚慰灵魂,并以此寄予希望,大小姐的希望便是攀上与白总长家的亲事, 她相信花了半年心血绣的靠垫是亲事的关键。 为了绣品没有瑕疵, 仅鸡冠子就拆了三次,绣了三次。为了绣品能准时送到白家,大热天赶工。送去之后,开始想象着别人对父母的奉承,女伴对自己的妒嫉。可是送去白家的当天晚上,靠枕便被醉酒人吐满呕泻物,更成为他人打麻将时的脚踏垫,随后那位白少爷将绣枕给予佣人,婚事更是无从谈起。戏剧的是,两年后,大小姐得知了真相。她知道真相后的苦楚与感受不可得知, 也许比现在女生向男生表白遭拒的感觉更深刻。
绣枕是精致的,正如大小姐的典雅、娇艳,而绣枕的命运正揭示了大小姐希望的破灭,命运的悲哀。大家从这篇小说中得出凌淑华小说的“绣枕”形象,因为绣枕就是这些形象的最好隐喻。
随着时代的进步,《吃茶》中的闺阁少女芳影,结交异性朋友、享受男士的殷勤。她怀着对爱情的憧憬,遇上了同学淑贞的哥哥王斌。 留学归来的王充满绅士风度,其行为在芳影心中幻化为“爱慕”的信息,她在爱情幻影中如痴如醉,时时抿嘴微笑。可是,一个星期过后,她收到王家送来的请帖——王斌与另外一位小姐的结婚请帖,请帖让她昏惘,只有眼泪不禁流下来,这是懊恼的眼泪。后来,淑贞嘲笑跛脚小姐不懂外国规矩,这何尝不是在奚落芳影!我们不会想到王斌的所作所为是“在现代文明幌子下的肆意任情”[3],而只能说是时代进步吹来的外国风,给这段“恋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恋爱”给芳影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茶会以后》里的阿英、阿珠姐妹可以去参加婚恋介绍性质的“茶会”。走出闺房的她们,相当时髦,讲着西洋话,渴望成为“茶会”的焦点。但姐妹俩又摆脱不了传统闺训的影响,男女授受不亲思想使她们鄙弃那些与异性谈笑风生、眉来眼去的小姐们。这样的包袱,使她们没有成为茶会中心,反而因阿英不懂规矩地坐在一位小姐旁边,招惹其他女性的耻笑。她们已经走出旧的生活方式,可是新的生活方式对她们来说又是如此陌生,她们抓不住什么她们想要的东西,剩下的只是灵魂的孤寂,以及对未来的茫然,两位精神失语的悲剧闺阁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二)“绣枕”故事之“少妇篇”
《女儿身世太凄凉》 中的婉兰是从闺阁少女成长起来的少妇。未出阁的她坐在贵妃床上,欣赏园中春色,虽是青黄的病容,却有“长眉细目”,显出“多病佳人的风致”。得知自己的未来夫君是花花公子,与丫头苟且之事没有遭到严惩,反而得到家长的默许,婉兰就反抗不从。 母亲却认为:“女儿终归系人家的人,这次得罪他们,以后更难做人了。”
过门之后,丈夫让她寸步不离,可丈夫几次在客人面前亲热被拒绝后,便说她“没情的女人”,惹来婆婆的怒目瞋视。劝诫丈夫收丫头为妾,却被骂成“贪图贤德的名”,婆婆也怪她“假惺惺”。为了安稳度日,婉兰帮丈夫藏定情信物,婆婆却骂她“狐狸精”。丈夫要娶妾,央告她与母亲说,被婉兰拒绝,便说她“吃醋不贤”。在夫家,婉兰如同丈夫与婆婆的奴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媳妇,她无法适应夫权与婆权的相悖定律,妻性相伴她一生。
《小英》中的三姑姑回门那天,三姑姑没有像新嫁娘一样,向父母诉说自己新婚的幸福,而是哭着对母亲说自己在夫家的辛苦,在夫家所受的奚落,可这一切无法改变,她必须回到夫家去。与婉兰的命运之苦不相上下。
(三)“绣枕”故事之“老年篇”
讨论“老年篇”之绣枕,我们要认识《有福气的人》中的章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和大小姐、婉兰相比,真的是有福气:出身大家,没有病怏怏的身子,不用绣靠垫来寄托对未来婚姻的期望, 老太太轻而易举地嫁入同样富足的章家,丈夫年轻时虽不好读书,差事也是老丈人帮他谋的, 但没有婉兰丈夫的荒唐过分,老太太更没有一个百般虐待她的婆婆。丈夫虽有两个小老婆,但作为明媒正娶的她,不仅毫无异议,还大方地认为大户人家里没有两三个侍妾是不成体统的,那争风吃醋是小家子气的人才做出来的,这博得公婆“明大义”的赞言和丈夫的佩服尊敬。时年六十九的她,有丈夫的陪伴,更有她自己都数不清的孙子外孙。
作者用许多篇幅描写老太太的福气,可这只是表面上的福气。有一次章老太太无意间听到儿子儿媳的私房话,才明白家人们对她侍奉至今全是为了她的钱财家产,才知道她的“钻石帽花”“碧绿翡翠的朝珠”充满魔力,自己成为儿孙哄骗掠取的对象。人生得意、家庭美满的信念此刻变得一文不值。由此看来,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并没有多少幸福,她只不过是被这个封建家庭玩弄欺骗的人。
《搬家》里的四婆,一个人独居,子女都在城里做事,虽然他们偶尔会来看望她,但寂寞孤单无法被排除,这时,枝儿的存在对四婆来说尤为重要。她们之间的感情也超过了亲爷孙的亲情, 可是枝儿要回北京,四婆将要独自生活。没有章老太太的财富苦恼,却也无法躲避孤寂的命运。
以上作品中, 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是悲剧性的,她们虽然是不同年龄的女性, 但她们是一个继承的整体,有着共同的时代命运,是对“绣枕”案例的最好诠释。
二、迷失或自救的太太
凌淑华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绣枕”系列的悲剧女性形象,她对太太这一角色也同样的重视。
(一)庸俗无聊的家庭主妇
近代中国,是旧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新的价值体系替代的时期,家庭主妇也在发生改变。传统的家庭主妇如《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她意识里不仅不相信夫妻感情,而且对命运听之任之。苦心经营的家庭破碎离散,她一味地相信迷信,认为是丈夫在中秋夜没有吃团圆鸭,打破供神的花瓶造成的。敬仁太太是个没有灵魂的不幸家庭主妇。这种家庭主妇是不受时代支持的,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但是这个特殊时代又赋予了这个群体不一样的特点。她们继承了旧式女性依赖家庭寄生虫般生活的传统习性, 又吸收了追求享受放弃责任的现代糟粕,总体来说是懒惰、庸俗、无赖的。
《太太》中的太太,热衷赌牌,不打理家务,女儿的脚生了冻疮,她顾不上买棉鞋,儿子因为没有运动服要被先生赶出学堂,她视而不见。为了筹集赌资,当掉了家里最后几件值钱的东西, 甚至为了所谓的面子去捞本, 将丈夫要穿去参加上司寿宴的袍子当掉,被丈夫问起衣服的时候,还对丈夫撒谎,当知道这关系自己“衣食饭碗”的时候,才着急起来。但当丈夫骂她不配做孩子母亲时, 她却嚷嚷着丈夫当着孩子的面糟蹋自己,丈夫被气走之后,她置一家老小的穿衣吃饭问题于不顾,仍旧赴牌约去了。这是一个爱慕虚荣、放纵享乐,把家庭抛在自己生活之外的家庭主妇,似乎不再受“三从四德”的束缚,却有着庸俗市民的恶习, 是个既无独立精神又无传统女性良好品德的形象。
《送车》里的白太太、周太太聚在一起,不是无聊地谈论佣人厨子偷油偷米,就是对新式太太们评头论足。身为丈夫孩子奴隶的她们,只能对唯一身份低于她们的佣人百般挑剔,以此来满足“主子”的优越感。时代的变动,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婚姻的危险,于是对那些自由恋爱的新式太太羡慕嫉妒恨,表面上,透露自己对新式太太的鄙夷, 这些不过是掩盖生活的无聊,以及不安的心。她们“主子”身份的优越感和明媒正娶太太身份的优越感, 揭示的正是她们的劣性,她们是一群庸俗无聊的家庭主妇。
这是凌淑华小说独有的女性形象, 被人赞不绝口,因为和同时代女作家创造的女性形象相比,凌淑华小说中的女人要世俗得多。因而对照庐隐的自我沉迷,冰心的虚幻之爱,冯沅君的叛逆激情,凌淑华的女性世界要切实得多。
(二)自我超越的知识女性
除了庸俗无聊的家庭主妇,凌淑华在创造太太形象时,为知识女性留下了一片天空。她们都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挣脱了种种封建传统的束缚,不管是思想还是行动都有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解放。
《花之寺》中的燕倩扮演着安分守己的妻子身份,却又瞒着丈夫去充当不安分的情人,并发出男人为什么不愿同夫人恋爱而更愿意同外面女子恋爱的质问,这是对男权社会的质问,是燕倩们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
《酒后》中的采苕,在酒宴散席后,看到喝醉后睡在客厅的友人子仪,她被朋友酒后温润优美的容貌倾倒,于是向丈夫永璋提出kiss 子仪的要求。在丈夫面前亲吻异性,说明她是极具个性的新式女性。在得到丈夫的允许后, 走到子仪面前却放弃了最初的动机,面红心跳也转为平静。笔者认为,她得到了丈夫的“准许证”,追求的权利已经到手,至于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上亲吻,已经不重要,个性已经张扬,也说明采苕们已有了某些主体性。
不管是身兼两角的燕倩, 还是亲吻异性的采苕,她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向“新”跨出了一步,是新式家庭里的新式太太。至于她们是否在行动上完全自由自主,在那个时代还是没有条件的,她们也只是主体性不充分的知识女性。
三、狭隘与美丽的世俗母亲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父权社会,母亲扮演着道德母亲和神性母亲两种类型形象。“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是代代相传的道德母亲形象,但是我们在翻阅文学作品时,我们很难找到闪耀光辉人性的母亲,不仅如此, 在我们脑海中涌现出来的是一大堆的“恶母”“丑母”形象: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之母、戏曲《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之母等。虽然她们身上泛着母爱的因素,却在维护封建伦理秩序中,扮演着千百年遭人痛恨的“丑恶”母亲角色。
当“五四”文明之风吹到中国之后,那些传统的道德母亲无法再给现代女性创作带来灵感,“五四”女性对母亲与母爱的写作,是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4],她们创作两种母亲类型:“一类是年迈体弱苦难的现实母亲,她的生活过错是不觉悟所致;另一类是仁慈博爱的理想母亲,她被描绘为爱者、慈母、为子女操劳牺牲,庇护女儿心灵,懂得女儿心曲。”[1]凌淑华较早对母亲进行理性审视,她创造的母亲形象震撼人心。
(一)狭隘的母亲
凌淑华没有沿袭“五四”的母爱歌颂形式,而是以独特的体验与视角,创造出一种狭隘的母爱,塑造了令人怜悯又鄙弃的母亲形象。
《杨妈》中的杨妈早年丧偶,剩下一个儿子。为了送孩子上学,她从农村来到城市,当帮佣。与天下的父母一样,她怀揣着望子成龙的愿望,但事与愿违,儿子不但不好好读书,不认真做事,甚至整天和流氓混在一起,所干之事无法启齿。对母亲也没有敬意,除了要钱,并无他事,最后对杨妈不辞而别。养了白眼狼的杨妈,并没有对儿子产生半点怨恨,只有深深地爱,夜里给他缝衣制鞋,白天求人四处打听。主人劝杨妈不要这样,应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考虑,并指责孩子心中并没有母亲。可是固执的杨妈给自己找理由,自我安慰,堪比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最后,在不知道儿子确切栖身地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寻子的征途。如果抛开儿子的好坏,此等爱子之情,真是无人可敌。可事实并非如此,儿子是个抛弃亲娘的不孝之子,杨妈此等举动并无意义,而反映出来的是杨妈身上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思想。儿子就是寡妇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无止境的母爱倾注中,才能证明自己是母亲。凌淑华在作品中注入了同情,也给予了理性的批判,塑造了一个无自我、无独立人格的狭隘母亲形象。
当然,除了狭隘的杨妈,还有《一件喜事》《八月节》中软弱无力、缺少人格魅力的母亲,更有《小刘》中偏袒男孩,具有性别歧视的母亲小刘。这一批都是凌淑华作品中的无美感的母亲。同时,在她的小说中还有一类闪耀人性光辉的美丽母亲。
(二)美丽的母亲
凌淑华小说中有一类美丽的母亲形象,《古韵·母亲的婚姻》里的义母潘少奶奶便是代表。早年丧夫,没有留下孩子,后来她在人贩子那里买来一个小女孩作为义女。没有再嫁的她,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与其他寡妇不同的是, 她将自己的空虚寂寞放在了家务中,将家中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人际应酬中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她把爱转移到义女身上,潘少奶奶不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义女,还充分尊重义女的人格尊严,所以当孩子的亲生母亲寻到孩子时,她忍着不舍之情,将决定权留给孩子自己,而姑娘的选择是买自己养自己的潘少奶奶。在这篇小说中,凌淑华对于千百年沿袭下来的血缘关系发出挑战,义母之爱战胜骨肉之亲。当然,更集中表现的是潘少奶奶身上中国女性的善良人性。
美丽母亲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一席之地,如《生日》《搬家》《小哥俩》中的母亲,她们是美丽母亲的典范,她们的健全人格也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孩子,作者对母性这一角色进行的思考及创作,给这些后来的读者予以教育,是像杨妈们一样溺爱,还是像潘少奶奶们一样尊重孩子?
综上所述,凌淑华的小说中不仅塑造了高墙内的闺中少女、少妇、老妇形象,还描写了交替时期的庸俗家庭主妇、新式家庭的知识女性太太,更刻画了狭隘与美丽的母亲,构成了她小说独特的女性世界。横向观察,三个不同群体的她们共同生活在“五四”新旧更替的时代,展现着她们的生存现状。纵向观察,她们无外乎女儿、妻子、母亲三种不同的社会女性角色,而她们是一个女性经历的不同阶段而已,大小姐们婚后也许就是婉兰,芳影可能成长为庸俗的家庭主妇,而庸俗的太太们可能变成重男轻女的小刘,她们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而互为一体的。与其他“五四”女作家作品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女性比较,凌淑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尚不够鲜明,也不是大家所推崇的,但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缩影,是对那个时代女性生活最贴切的描述。还未成名的她,在1923年就向周作人倾诉要写“老中国”女人的意愿:“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 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5]从她创作的成绩来看,她当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不仅如此,她作为“五四”时期女作家中的一员,有一份独特的贡献。在20 世纪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凌淑华的地位独特而重要,其写下的一个个女性形象激荡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1]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8.
[3]庄晓敏.论凌淑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88):3.
[4]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54.
[5]张彦林.凌淑华·周作人·《女儿身世太凄凉》[J].新文学史料,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