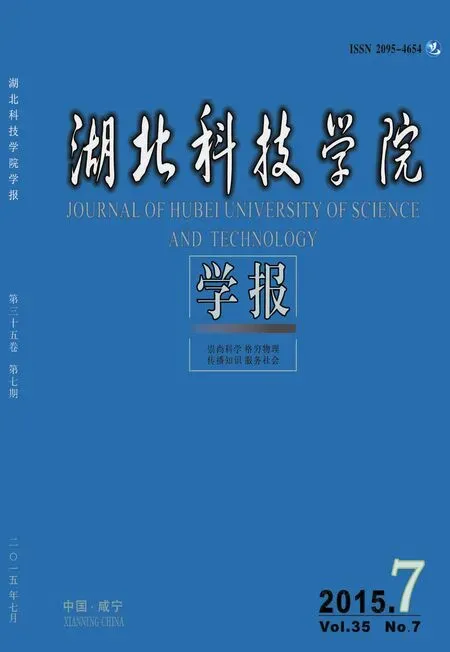《诗经·卫风·淇奥》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陶 娟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诗经·卫风·淇奥》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陶 娟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诗经·卫风·淇奥》作为我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一篇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中国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外部表现为中国文人好竹、佩玉,在内部表现为文人们比德于竹、比德于玉,反映出中国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以及追求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文化品位。
淇奥;文人;影响
作为第一部诗集,《诗经》对中华文学和文化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然而不管是文学史也好还是文化史也好,它们的推动和传承都是靠人来实现的,因而也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文人。
生长在同一片沃土,有着相同血脉的中国文人,不可避免地拥有着相同的集体无意识:嗜竹如命,爱玉成痴,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对于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有人说源于孔子的提倡的“君子文化”。实际上,最早的来源是《诗经》,更确切一点说是《诗经》“卫风”中的《淇奥》。
一、《淇奥》与中国文人嗜竹的传统
竹在我国历史悠久,据史学家考证已有6 000多年的历史。从《说文解字》“竹”部所收录的150多个字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竹以及竹制品已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与先民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进入文学作品也是比较早的。我国最古老的民歌《弹歌》里描述的就是先民们用竹制作工具进行捕猎的事,不过这里主要体现的是它的实用性。而这种实用性还不足以让它在文人中产生较大影响,真正决定它在后世文人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当它作为一种审美而存在时。而它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现今能看到的典籍中,最早的就是《诗经·卫风·淇奥》。
《淇奥》共三章,每一章开头都以“绿竹”来起兴,分别是“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这里使用“绿竹”,虽然主要作用是为了引起下文,但绿竹清逸的外在姿态,心虚节直的内在美质,已经和文中要赞美的君子产生了审美上的联系,足以让人想见到那位君子挺拔如修竹般优雅的风姿,并且使这种优雅的风姿从此种植于中国文人的心田,生根、发芽,并经过历代文人的浇灌、培育,最终开花结果,形成一种文人嗜竹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为:
1.外在行为上,文人们好竹
单从个体的喜好上来看,中国文人的嗜好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陶渊明好菊,李白好酒,王维好佛,周敦颐好荷,陆游好梅,李渔好兰,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计算哪个物种能得到大部分文人的喜爱,竹无疑名列前茅。
翻开历代典籍,我们能看到很多文人好竹的故事。《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徽之非常爱竹,他的房前屋后种满了姿态不同、品种不同的竹子,开创了文人种竹的先河,并且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竹称为君子。另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第46则记载,他曾指着竹对朋友说:“何可一日无此君?[1]”可见他爱竹爱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说始于《诗经·卫风·淇奥》的文人爱竹的引子,在王徽之这里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竹的最早形象代言人。
继承了这种竹痴情怀的还有宋代文豪苏轼。据他自己的文章记载,他的生活环境中处处可见竹,门前有“万竿竹”(《答任师中家汉公》),官舍有丛竹。即便在贬谪的路上选择寓居之所时,也要与竹为邻。他甚至称竹为“夫人”。竹俨然是他平日生活里不可替代的一员。他曾在《于潜僧绿筠轩》中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而他空闲时最爱做的事便是,“徘徊竹溪月”(《游净居寺》),听“风来竹自潇”(《定惠颙师为余竹下开啸寺》),赏“竹外桃花三两枝”(《惠崇春江晚景》),“散发临修竹”(《安国寺浴》)。
像王徽之和苏轼这样爱竹的还有被称为扬州八怪的郑板桥。他在《题小玲珑山馆》这幅对联中,说自己对待新竹“直似儿孙”,爱护新竹“如教子弟”。他四十年如一日地把竹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良朋益友,白日里种竹、护竹、赏竹、画竹,夜晚则听竹、思竹、咏竹,最终给我们留下大量的关于竹的艺术作品,以及“胸中竹”“眼前竹”“笔下竹”的艺术创作理论。
其他的文人虽然没有像上述几人那样把竹视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对竹也多表现出喜爱之情。“竹溪六逸”和“竹林七贤”自不必多说,就连整日里慨叹民生多艰的杜甫也曾在诗作《寄题江外草堂》里表示“嗜酒爱风竹”。“诗佛”王维也表示自己最喜“独坐幽篁里”(《竹馆里》)。元代吴镇则称赞说“野竹野竹绝可爱”(《野竹》)。清代蒲松龄也说“尤爱此君好”(《竹里》),同时代的王世贞亦表示“何可一日无此君”(《题竹轩》)。
2.内在心理上,比德于竹
如果说“好竹”只是文人从行动方面表现了自己对竹的爱好,还处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而将竹的自然属性与人的操行品德进行比照,则从更深刻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文人的嗜竹传统。
对于竹之自然属性如何人格化为人之品德,唐刘岩夫《植竹记》里总结出了竹之八德:刚、柔、忠、义、谦、常、贤、进,而这八德也正是历代文人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竹的德,白居易在《养竹记》里进一步补充,他认为“竹本固,性直,心虚,节贞”[2],可以给文人以人格修养上的启发。
由这样两篇文章的铺垫,竹成了高雅、正直、廉洁、气节的代名词,中国文人比德于竹的传统也正式形成。文人们经常借歌咏它来展现自己坚韧、刚直、高洁的情怀,以及不与世俗为伍的志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竹无论在哪个朝代中国文人的笔下都是受尽宠爱,这种宠爱一部分源于它的实用性,更大的一部分是源于它的审美性契合了中国文人心理上的审美需求。而它作为审美存在即是从《诗经·卫风·淇奥》开始的,因此我们说,《淇奥》开创了中国文人嗜竹的传统,没有《淇奥》,中国的“竹文化”将会黯然失色。
二、《淇奥》与中国文人尚玉的传统
据史学家考证,玉在我国的历史至少已达8千年,比竹的历史还要早。与竹以其实用性及普遍性而被各个阶层广泛使用不同,玉因其稀有性及精美性在最初的时候被作为祭祀用的礼器而成为贵族的专利品。不过,与竹相同的一点是,它作为审美存在第一次也是在《诗经·卫风·淇奥》里。
《淇奥》里,每一章第二层都把文中所称赞的对象与“玉”关联,盛赞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这里虽是作比,但这实际上也是诗中盛赞的君子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玉”也因其审美的关照契合了中国文人的心理需求而受到青睐,进而形成文人们尚玉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为:
1.外部行为上,佩玉
中国文人历来有佩玉的习惯。《礼记·玉藻》记载,古代的君子出门必定要佩戴玉器。而这种佩玉的习惯,据考证从西周时期(距今约3000年)开始,与《诗经·卫风·淇奥》出现的时间大致一致。这里“君子”指的是当时的士大夫及贵族阶层,这些人也是当时文人的主体,而伴随着佩玉习惯的流传,玉的佩戴者已不仅仅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也包括寒门学子了。
正因古之文人多佩玉,所以《礼记·玉藻》又说君子“行则鸣佩玉”。《大戴礼记·保傅》亦说,古时文人“以佩玉为度”。有相关记载的还有:叔仪“歌佩玉而呼庚葵”(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朱衣玄冠,佩玉舒徐”(元好问《范文正公真赞》),“任纡朱拖紫,围金佩玉”(张元干《沁园春·梦与道人对歌》),“﹝刘文正﹞真有冠冕佩玉之风”(沈初《西清笔记·纪文献》)。
上述诸多“佩玉”,有的是名词,意为“作装饰用的玉器”;有的是动词,意为“佩戴玉饰”。但无论是哪种意义,拥有或佩戴玉饰的主体都是文人。而百官又是文人中的杰出代表,以至于陆游在《立春前四日谢雪方拜天庆庭中雪复作》一诗中以“佩玉”来指代百官,“佩玉珊珊谒众真,竟烦一雪慰疲民”。
2.内在心理上,比德于玉
如同文人们好竹只是嗜竹传统的一种外部表现,而竹的自然品性契合了中国文人的审美心理需求才是深层次原因一样,佩玉也只是文人尚玉传统表现出来的外部行动,文人尚玉的根源也在于玉的品性(孔子所谓的“玉德”)契合了中国文人内心深处对于“德”的渴求。
对于“玉德”如何比照为“人之德”,有不同的看法。春秋名相管仲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玉有“九德”:仁、智、义、廉、行、洁、勇、精、容、辞。孔子把它丰富为“十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道。西汉刘向在《说苑·杂言》中将它称为“六美”:德、智、义、勇、仁、情。东汉许慎在其字书《说文解字》中释“玉”时则认为其有“五德”:仁、义、智、勇、洁。
实际上,不管是玉有“九德”、“十德”“五德”,还是“六美”,在中国文人的心中,玉与人已为一体,玉如人,人亦如玉,而开启这种联系的最初源头就是《淇奥》。后来,人们便用“玉洁冰清”或者“玉洁松贞”来称赞文人的节操高洁,用“玉润冰清”或“温润如玉”来形容人的形神之美,用“玉堂金马”来表示文人众多的翰林院,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来赞美那些宁愿为正义牺牲而不愿苟全性命的人,用“一片冰心在玉壶”来盛赞文人的淡泊名利,不慕功名的品格。
可以说,《诗经·卫风·淇奥》开创了我国比德于玉的先河,在此之后,经过管仲、孔子、刘向、许慎等人的升华,逐渐形成了文人比德于玉的传统,使得文人甚至国人尚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之一。
三、结语
以上简单分析了《诗经·卫风·淇奥》对中国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外部的行为层面,以及内在的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只是表象,内在的精神诉求才是主因。这种影响跨越千年,反映出中国文人高洁、旷达的文化心理,以及追求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文化品位,这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不竭的动力。
[1]刘义庆.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095-4654(2015)07-0083-03
2015-04-10
2014年度安徽省“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计划”之“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中华文化 实现中国梦想——高职高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施策略研究”(2014zdjy172)阶段性成果
I22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