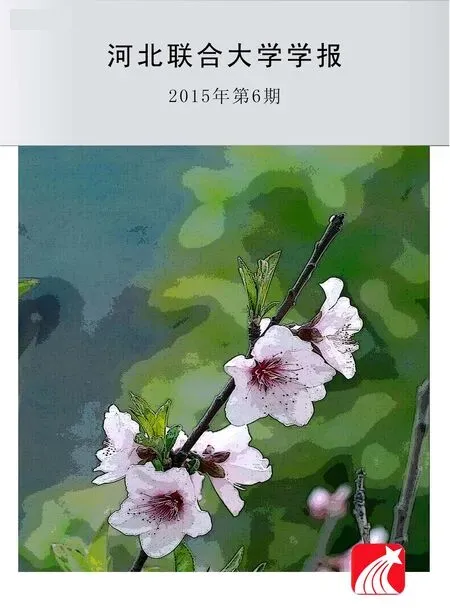放纵、迷失与悲悯—文学伦理批评审视下的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
乔传代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十堰442002)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犹太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多产的作家。自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后,罗斯便开始在文学的殿堂里勤恳耕耘,并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和殊荣。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32部作品,荣获了美国文学界的多种大奖:普利策奖、两次全国图书奖、两次全国书评奖和三次“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等等。他也是唯一一位由美国书院为其出版权威版全集的至今健在的作家,享有3L的美誉(即Living Literary Legend活着的文学神话)。罗斯的作品题材广泛,寓意深刻,创作手法多样,因此备受关注和热议。同时罗斯也因其作品大胆“反叛传统文化”、“挑战人类承受极限”而备受争议。罗斯的作品有着严肃的伦理道德指向,他总是“尽可能地去把握和刻画影响每个人的复杂的道德和社会因素”。[1]他在作品中常常将主人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结合后现代和新现实主义于一身,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主人公或随波沉沦,或奋力抗争,或趋于淹没,一切都源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主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罗斯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最初的族裔身份、意识形态批评发展到从伦理书写,文化批评等多方面多角度赋予罗斯作品以丰富的内涵。
《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是菲利普·罗斯“凯普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该小说以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与他的学生古巴女孩康秀拉的性爱纠葛为主线,为读者展示了美国的性开放文化,反思并批判了性开放文化对美国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美国社会中家庭伦理道德,公共伦理道德的嬗变,体现了深刻的伦理道德指向。[2]197同时作为一位犹太作家,罗斯继承了犹太传统中对死亡的终极探讨,将主人公凯普什置于萨特式的极限环境中,不断地选择和适应,为我们抒写了一种年老与青春,爱欲与死亡的博弈。
本文主要基于文学伦理批评的角度对罗斯作品《垂死的肉身》中的道德伦理因素进行分析,解读其中不同的伦理现象,挖掘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做到“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考察,并以历史的辩证阐述 ”,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3]
一、放纵肉欲:精神的沦丧——对美国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在《垂死的肉身》中,罗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一位作家兼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和他的学生康秀拉之间的情爱关系,通过不同个体悖离传统婚姻爱情关系混乱的性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代美国性文化的全景图。
小说中的“我”是美国开放性文化的崇尚者和实践者。在性上,“我”是一个绝对的泛滥者。“我”曾在一次评论中提到,“放荡的狂欢乱舞与无神论者,陷入极度淫乱与堕落的生活”,吸引着“我”直从牛津直接奔向美国。十几岁时,“我”就与一个放荡的女子发生关系,为此还曾染上了性病。上大学时,“我”便与众多女性进行着“性”实践。即便是结婚后,我还是经常偷偷出去寻找性对象。为了追求自由,“我”抛弃家庭,独自居住,一味地沉溺于性开放游戏中并乐此不疲。“我”周旋于卡罗琳、康秀拉、埃琳娜等众多女性之间,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作为一个头戴光环的大学教授,博学绅士的“我”拥有众多的女粉丝,她们都自愿作为我的猎物。而“我”也沉醉其中,纵情肉欲。在每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下来后,“我”会在公寓里举行一次鸡尾酒会,召集所有的学生前来参加。这其实只是一种借以获取猎物的机会。经常会有一些女学生因对“我”的好奇而在聚会之后留下来与我发生关系,对此“我”也照单全收。一次,在凌晨两点钟当所有的学生都已离去,“我”准备休息时,班里一个叫米兰达的女学生从浴室里走出来,坦言要和我发生关系。并且在“我”面前脱掉衣服,展示迷人的胴体。而“我”一向“在女性美面前表现十分软弱”。对她们的心态和动机,“我”了如指掌。像这样的女孩很多,她们几乎从14岁左右就开始有性生活,并乐于不断地变换对象进行着性体验,性对于她们来说普通得犹如家常便饭。她们主要源于好奇心而与我这样62岁的老男人发生关系,事后会急切地将此事告诉室友,借以炫耀。表面上温文高雅的康秀拉,也坦承自己17岁时曾同时和两个男孩在酒后发生关系,而这样只是为了感觉成长。还有“我”的好友牧师兼诗人乔治,本应严格遵守传统道德规范,却背叛妻子,沉醉于性淫乱中,步入暮年的他依然可以在早晨喝咖啡时和年轻的女孩调情,在人生终点时,他依然奋力得想要触摸妻子凯特的胸部,凯特之后悲伤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把我当作谁了。”
小说中以“我”为首的众多男女个体对于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和行为活生生地演示了美国性文化的开放和腐化。这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是分不开的,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只是那个时代的影射。20世纪6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美国深陷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和越南战争的残酷现实,再加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身亡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紧张窒息,频于崩溃。为此,很多年青人不满现状,发起了一场反文化的运动,以酗酒吸毒、崇尚性开放等来宣泄内心的郁闷和恐慌,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越战期间,大学生宣扬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以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得很多人产生了以争取性自由来实现摆脱约束、追求平等幸福的观念。未婚同居和离婚成为流行和普遍。传统的家庭责任被淡化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放纵肉欲,回归原始本能。人们纵情肉欲,鼓吹性爱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很多年轻人婚前甚至婚后随意发生性行为,在公共场所裸体,甚至群交,“人们脱下内衣,大笑着四处走动”[4]63,毫无道德底线,家庭和公共伦理道德沦丧殆尽。受时代和环境的感染和熏陶,“我”和身边的人自然不会掩饰自己的性放纵,以实现“本我”对“自我”、“超我”的解构,借助发泄肉欲来对抗和逃避现实。[5]“我”感觉“只有在性交时,你才能彻底地,或许是暂时地向生活中你不喜欢的和击败你的一切报仇雪恨。”
性开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对于高压政策和动荡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强烈渴望。但正如罗斯所言,它的负面影响是巨大而可怕的。这场革命就如同癌症隐喻一样,蚕食了人们的精神,人类欲望放纵,情感缺失。性开放使得婚姻关系变得不稳定,淡漠了人们传统的家庭观念,使亲情疏远。它使家庭个体尤其是子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伤害;性病得以蔓延传播;社会犯罪率急速上升。各种社会问题如未婚小妈妈﹑人流﹑性交易等等严重冲击干扰着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正面发展。小说主人公“我”沉溺于性泛滥中,虽然获得了短暂的肉体欢愉,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家庭关爱的丧失﹑内心的极度空虚﹑对疾病死亡的愈加恐惧等等,这些都促使“我”对美国性文化和自身性堕落进行了深刻反省。性开放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脱离了理性文明的社会生活,是文明的倒退。它背离了传统的婚姻道德,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思潮。同时小说名字The Dying Animal也是对作者态度观点很好的诠释。”而作者让康秀拉最后患上乳腺癌,也暗含一定的寓意,康秀拉美丽的乳房指代了美国性文化的开放,而患病的乳房则隐喻了病态的美国性文化。[2]200作者借康秀拉美丽乳房的切除暗示人类对自身性泛滥所必须承担的后果---失去最美丽的东西甚至生命。
二、跨越时空伦理的爱恋
任何一部小说,无论是叙述外部形式还是剖析情感世界,都无法摆脱时间和空间这一带有终极性的根本问题。“文学必须以语言符号呈现人类在现代性变革之中的时空体验……”[6]乔国强教授曾经指出,传统伦理学中侧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范围上可以扩展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在时间上扩展为人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7]菲利普·罗斯是一个对时空感觉敏锐的作家。他在《垂死的肉身》中为我们构建了极其丰富的时空层次。通过从个人时间到社会时间,秘密空间到国家领域,罗斯全景式呈现了个体与时空的冲突,揭示了个体在不同时空中所遭遇的欲望与道德的冲突和生存困境。[8]年过六旬的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凭借着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化权威形象、社会地位以及不俗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二十四的古巴女孩康秀拉,两人不可自拔地陷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爱恋中。然而他们这场穿越时空的爱恋注定是有悖伦理的。首先他们之间的巨大的年龄差距是硬伤。年龄是个体社会经验的基本时间体现,是每个人身心状态的基本参考标准,也反映了个体之间的时间差异。对于年轻的康秀拉来说,“时间总是由过去构成”,时间是可以挥霍的,所以她可以有足够的资本去消耗,去体验。对于未来,她是满怀憧憬的。然而对于暮年的凯普什来说,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康秀拉似乎时刻在提醒着自己的苍老和死亡的临近。尤其是在与康秀拉的情爱关系中,他总是摆脱不掉这种忧伤和死亡的阴影。因为自己正在接近死亡,所以无法为康秀拉遥远而广阔的未来担负更多的责任。他们两人缺乏对时间同步性的共性,导致了彼此对未来理解的差异,这使得他们无法获取正常合理的爱情期望。处于不同的时间坐标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很难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和谐。两人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康秀拉就明确得表示他们是不可能结婚的。听到康秀拉谈到之前曾有五个年轻男友时,凯普什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和嫉妒,这其实是丧失时间优势的嫉妒。两人之间巨大的时间差距使他患得患失,他感觉自己终究要被时间抛弃,而康秀拉则会被另一个年轻人发现并带走。这种担忧加剧了内心的恐惧。康秀拉年轻的身体总是让凯普什感受到自己的衰老,他尤其担心自己性能力的丧失,因为性是他唯一能证实自己存在和感受世界意义的方式,性的丧失就意味着身体的枯竭与死亡的逼近,意味着个体意识的丧失和整个世界的消亡。时间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两人的关系始终见不得阳光,凯普什不知以何种身份去参加康秀拉的毕业聚会,而康秀拉也不愿意和他双双出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公共场所,头戴时间枷锁的他们努力而艰难地行进着。然而时间距离同时也让他们两人彼此相互吸引。凯普什在年轻的康秀拉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青春和活力,通过身体上征服她,他要证实自己的强大以及与时间和死亡的顽强抗争,“性是对死亡的报复”。[4]78对于康秀拉而言,两人年龄的巨大差距恰恰吸引着她,年老的凯普什的学识、见地和修养正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下来的,巨大的年龄差距允许她仰慕和顺从,和他发生关系使她得到了顺从的愉悦,同时也得到了一种主宰的优越感。通过和凯普什这样一个充满魅力和权威的男性发生情爱关系,她证实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也证实了自己对于他的重大意义。因此当凯普什对她邀请其参加毕业晚会的失约时,她异常得悲伤和失落,她觉得他是对自己情感的无情拒绝和人生意义的否定。愤怒失望之余,她大声朝他吼叫,两人的关系戛然而止,至此八年之间再无联系。
此外,罗斯又为我们打开了空间的窗口。多年以来凯普什一直生活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在办公室空间,他尽量地以一个长者、教师的身份出现,避免和学生过分亲密接触,他严格地遵守着规定:期末考试之前绝对不和任何学生有私下接触。他这样做,一方面恪守师德,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某些过分行为使自己面临道德指责的尴尬境地。因此,在教室和办公室的空间里,循规蹈矩的他是一副博学、严谨而风趣的师长风范。可是在自己的私人寓所,他褪去了权威的外衣,他的伦理身份便变发生了改变:他不是老师、家长和名人,而只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男性个体,他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自如的关系。这种伦理身份在空间的转变将导致师生之间产生有悖伦理的问题。所以,在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凯普什在自己公寓里举办鸡尾酒会时,便会有一些崇拜他的女学生留下来过夜,无论是米兰达还是康秀拉。凯普什对此也毫无忌讳,完全听从自己身体欲望的驱使。在狭小的私人空间里,当康秀拉看到“我”的珍藏众多的书画,“我”的钢琴,倾听着“我”略带磁性的哲理性的言语,她感受到了“我”因年老而颇具沧桑和成熟的魅力和智慧,她留下来了。而“我”也被她不俗的高贵气质所吸引,两人始于一夜情,此后便纵情肉欲,不可自拔。但身体的欢愉之后,更多的言语交流和心灵默契让他们由性爱升华到了情爱,达到了身心的交融。但他们的爱依然受空间的约束,仅限于凯普什狭小的私人公寓和陌生的场所。他们的内心时时处于矛盾、煎熬和苦闷中,因为他们骨子里无法接受公共空间的伦理失序,两人也尽量避免出现在公共场合。凯普什将康秀拉偷偷地“金屋藏娇”,只将他们的关系告诉自己的诗人朋友乔治;而康秀拉在公共咖啡厅看到乔治和年轻女孩接吻时感到不可思议,而自己此刻也正挽着一个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老男人的胳膊。当最终康秀拉决定邀请“我”参加她的毕业晚会,将“我们”的爱由狭小的公寓搬到公布聚会的大舞台时,“我”退缩了,“我”没有挑战公共空间伦理的勇气,“我”有太多的顾虑。为此“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真爱八年的失联,八年的思念,八年的荒凉!“我”一直活在时间与空间的隔离,道德与不道德的边缘。
八年后的千禧之夜,康秀拉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此时的她已患乳腺癌,成为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了。面临着死亡的逼近,“我们”终于步入了同一轨道,一起迈向生命的终点。“她的时间感现在已经和我的一样了,死亡在加快,甚至比我还要绝望”。[4]165死亡让“我们”跨越了世间和空间的隔离,“我”为康秀拉拍照,将她的美永远地留下来,陪着她去医院做乳房切除手术。我有限的生命时间给了她欣慰,在死亡的道路上她将不再孤独,我们的未来变得那么的和谐。“时光飞逝。我们游泳,沉没在时间里,直到我们淹死离世”。[4]164
三、“父与子”的代际隔阂
凯普什在年轻时为了追求性自由、性开放,不惜与妻子离婚,抛弃家庭的羁绊。他的性放纵导致了家庭的解体,给年幼的儿子肯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阴影。作为父亲的凯普什有着致命的缺陷---对家庭的背弃,对父亲责任的逃避。这使得肯尼始终无法释怀,他对于父亲的性放荡以及对家庭的不负责任非常憎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几乎多年都不与父亲见面,父子亲情异常的淡漠。其实在肯尼的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父亲是一个毫无家庭责任感、整日纵情肉欲的堕落鬼,在生活中与很多放荡女孩发生关系,并且不断地变换性对象。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几乎没有出现过,心里想要的只是坚持自己放荡的生活。因此在父亲面前,他是一个“桀骜不逊的偏执狂”,总是在严厉地“斥责”着父亲。另一方面,犹太血脉里父亲权威意义依然存在,“我是他无法战胜的父亲,是个只要在场他的威力就会被压服的父亲。”肯尼总是在失落犹豫时不由自主地去向父亲求救,或者向他倾诉。他渴望获得父亲的建议,但又总是坚定得放弃他的建议。肯尼心地善良,有道德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父亲放荡的“前车之耻”,他发誓绝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作为父亲,凯普什理解儿子对自己的愤恨,对于儿子的伤害,内心也怀着内疚。但悖论的是肯尼最终也步了父亲的后尘,成为父亲的翻版。他在上大学时使女朋友怀了孕,为此父子曾进行过长谈。父亲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没有必要为此陷入道义的深渊,因为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个体的自由是首要的。正是由于父亲的建议,肯尼坚持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义无反顾地和女友结了婚,并且有了四个孩子。但婚后归于平淡的生活使得他在42岁时出了轨,爱上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徘徊在妻子和女友,道德和真爱之间,肯尼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他不由自主地敲开了父亲的门,告诉他实情想寻求指点。在父亲面前他一再澄清,这不是不负责任的偷情,他对自己的外遇有承诺。起初父亲劝他结束这段危险感情,他告诉父亲自己对这段婚外恋非常投入,情人使他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可是当父亲建议他结束婚姻时,他又借此愤怒地指责父亲对家庭的背叛和抛弃,最终两人不欢而散。一方面,肯尼的理性告诫自己决不能像父亲那样抛弃家庭,应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割舍对情人的迷恋,难以回归到平淡的家庭生活中。父亲的双重角色---具有权威的父亲形象和充满肉欲的色鬼,势必会持续在儿子肯尼的身上。即使他在拟定的“道德”的标杆下辛苦地前行着,人性中的欲望也无法在道德的框架内归于认同和泥灭。[9]
四、死亡威逼下垂死的肉身
《垂死的肉身》以凯普什与康秀拉的性爱关系为主线,反映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对普通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影响,同时小说也渗透着另一个主题---沉醉于性爱的主人公无时不刻面对着死亡和疾病的逼近![10]108凯普什内心是及其矛盾的,面临着死亡带来的焦虑,他不断放纵着“本我”以对抗“自我”,以性作为身体一种存在形式来对抗死亡和衰老。[5]“没有比性更大的力量!不论你多么博识,怎样思考,如何谋划、计算,你都无法超越性”!性不仅给他带来了身心的愉悦,也带来了抗拒死亡的力量,性是一种打破固有秩序、激发生命渴望的欲望的真理。[11]然而,当他不可自拔地迷恋着康秀拉年轻丰满的身体时,两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却使他失去了自信,陷入莫名的恐惧中。“我就这样耗了一年多,这样的恋情就像云霄飞车,但像飞车一样,迟早都要靠站”。[4]84在衰老和死亡的逼近之下,凯普什不断反思自己追求性爱自由是否能继续。面对死亡的逼近,徘徊在性爱和道德之间,他进行着伦理抉择。最终他选择了逃避,他无法找回逝去的青春和活力,无法面对自己日渐衰老和即将到来的死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普什自身恐惧的死亡却在之后威逼着情人康秀拉,要夺走她诱人丰满的乳房甚至生命。千禧之夜,他接到了康秀拉的电话,得知她患了乳腺癌,需要马上动手术,切掉乳房。罗斯巧妙地安排了这样反讽的对比,让一个深陷欲海、但在时间面前日益惧怕的老人和一个风华正茂但恶疾缠身的年轻生命一起去面对死亡的逼近,不同的生命轨迹在死亡这一可怕的点上得到了交集!“她的时间感现在已经和我的一样了,死亡在加快,甚至比我还要绝望”。康秀拉让凯普什给自己身体拍照,想要将自己的美丽影像永远地留下来。但拍照人和照片里的人都在感受着死亡的逼近。凯普什虽然身体健康,思维敏锐,但毕竟年过七十。康秀拉虽然美貌年轻,但却身患癌症。在死亡的阴影下,两人都倍感活着的珍贵,但却必须面对自己垂死的肉身。为了烘托死亡降临的压抑气氛,罗斯在小说中使用了指代时间的意向——节拍器,“滴答滴答,一切按部就班地发生”,并以此来凸显时间的飞逝和死亡的逼近。“滴答滴答”飞快运转的时间象征着世间永恒不变的时间,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生命的即将消逝助长了时间的加速运转,展示了个体有限的生命与其无限膨胀的欲望之间不可调和的悖论。[10]110
深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性开放运动影响,以凯普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沉迷于性开放的迷途并乐此不疲,在实现个体身心愉悦的同时,却违背了家庭和公共伦理道德,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亲情的丧失、同事的鄙视、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自身心灵的极度空虚。尤其是与古巴女孩康秀拉的一段忘年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青春的逝去与死亡的逼近,他开始回归理性生活与传统文明社会,重温现实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也是人类生存所经历的真实处境。
[1]BLOOM H.Philip Roth[M]//MCDANIEL J.Distinctive Features of Roth’s Artistic Vision.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2003:55.
[2]张明爱.对美国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评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J].译林,2012(6):197.
[3]袁雪生.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J].外国语文,2009(2):42.
[4]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史元辉,陈进封.《垂死的肉身》: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反抗[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4):113-116.[6]王炳钧.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J].外国文学,2006(4):76-87.
[7]乔国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管见[J].外国文学研究,2005(1):24-27.
[8]柳文文.时间、空间与伦理 ——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中的时空伦理观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2012(5):64.
[9]杜淑娟.人物与意象菲利普·罗斯“凯普什系列”释义[J].山东大学学报,2012(5):16.
[10]苏鑫.死亡逼近下的性爱言说---解读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J].外国文学,2010(6):108.
[11]王小翠.追求欲望的真理:解读菲利普·罗斯的《垂死的肉身》[J].文学界,201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