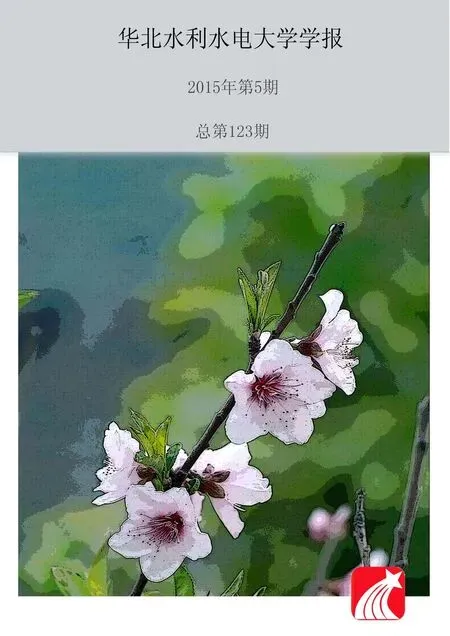乡村个体的群体突围
——以《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为例
尚亚菲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乡村个体的群体突围
——以《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为例
尚亚菲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李佩甫的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代表了一个序列的文学形象:艰难进城的乡下人。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乡村个体,冯家昌富有极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沿着冯家昌对“他者”的追逐这一情节线索,依据作品对道德的超越、文本对象征修辞的使用、作者对故事结构的时空安排,以及读者对文本进行的形态各异的解读,可以重新认识这部作品、这个人物,以及冯家昌背后的整个群体。
李佩甫;《城的灯》;冯家昌;个体;群体
李佩甫的《城的灯》问世已逾十载。作为一部象征意义显著、具有丰富内涵的作品,这十几年中,《城的灯》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解读、被言说。作品中陆续登场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冯家昌无疑是被作家着墨最多的。作家不遗余力地详尽书写,批评界对文本的不断重读、解释,这两方面的有效互动之后,一个意蕴复杂、个性突出的冯家昌的形象自然地就成为了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个体与群像的存在。
一、放弃“自我”,成为“他者”
整部小说的叙述几乎是围绕着冯家昌的心理变化的轨迹展开的。作品开头,作家就直入主题将冯家长子冯家昌置于一种无助尴尬的境地:六岁的他亲历了懦弱的冯家被人夺树的场景,感受了老实巴交的父亲求爷爷告奶奶讨公道时遭遇的冷漠无情。作家以“会跑的树”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展开故事的叙述,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上梁孤姓冯家日常生活的处境。可以想见,六岁以前的冯家昌必是经历了无数次“会跑的树”这样的事件[1]1,这些缺乏美好与温情的童年经验构成了作为个体的冯家昌对于世界的直观理解与感受。随后,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幽会事发时的活秋千、入伍后小个子连长的几次告诫、军区大院里侯秘书的几番点拨等又作为刺激物不断敲打、刺激着冯家昌的内心世界。当外界刺激作用于内心感受之后,冯家昌终于意识到一己之力的单薄微弱。彼时的他,别说把全家人“日弄”出去了,即便是想要成为“四个兜”[1]51,顺利迎娶刘汉香已实属艰难。在环境的逼迫、野心的引逗之下,冯家昌终于屈服了,他开始在部队里钻营算计,甚至抛弃在农村的初恋情人刘汉香,与李冬冬——市长的女儿——结了婚。对“爱情”进行比较、选择之后,冯家昌的内心获得了短暂的平衡。但对他来说,这种平衡状态总是转瞬即逝的。他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平衡要克服:要安抚躁郁的李冬冬,要处理险象环生的官场仕途,要把弟弟们带离上梁……在不平衡与平衡的摇摆不定中,最终,除了爱上刘汉香又不愿出来的老四,冯家昌成功地将其他的三个蛋儿“日弄”出来了[1]67,冯氏一门终于摆脱了曾让其受尽屈辱的上梁,毅然决然地挺进了城,成了“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冯家了[1]403!在这个从乡村向城市的大迁徙的过程中,冯家昌是摇摆的,他摇摆于情感与欲念之间,经过反复的挣扎与怀疑之后,在冯家昌的天平上,情感的砝码逐渐被欲念吞噬,冯家昌终于在不断出卖情感之后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整个过程辛酸和惨烈。
二、道德之外的可能性解读
这个表面上的一个当代陈世美背信弃义的故事,由于作者对冯家昌的心理状态的体贴关注,对人的生存背景的的细致书写,终于使我们得以见到道德故事之外的各种复杂关系的缠绕。正如何向阳所说:“我们的文化太多时候要求于个人,个人也承担了许多历史本该担当的责任,有没有一种文化,去反思那个个体如何是这样的个体的原因。如果有一天,我们从水土上去发现人的秘密,而不仅以道德评判个人;如果我们理解底层农民的宗教,不是信仰,而是权力,是城市架构的精神自尊,是那个巨大的生存落差显现出的人的处境的不公平,那么,我们或可从人性的角度原谅冯家昌,我们或可不拘泥于已成传统的道德律令,而看一看于此中挣扎、较常人几倍、几十倍付出、直到付出自己正直人格的这个羔羊。”[2]这一解读并非为冯家昌们背弃土地时的各种动机进行开脱,也并非说以经济为尺度的城乡丈量中占据劣势的乡村就可以用经济的落后掩盖精神的贫瘠。“事实上,文化精神上的匮乏才是更深层的疾病,不然的话,冯家昌可以用‘贫穷’为自己辩护,杀人的小痞子也可以用‘贫穷’为自己辩护。”[3]这种观点只是向读者展示了被裹挟进城镇化浪潮中的乡村人的心理状态,进入城市的冯家昌更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只有交出自己的武器、盔甲,才能实现“投降”,成为“他者”中的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与“他者”在现存条件下绝无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但“繁华的都市压迫着他、排斥着他,他必须重塑一个自我才能融入城市”[4]。显然,简单的“道德”二字无法传达在城市中左右奔突的复杂的“人”。作家对惯常的、简单的道德认知的超越并非是偶然而为之的,在《羊的门》中,呼天成、呼国庆等人的行为并不为传统道德所容,但当作品写到他们与城里人较量中的种种算计和心机时,似乎这些人也并非如当初那般面目可憎了。而在李佩甫的新作《生命册》中,不论是远走他乡的“我”“骆驼”,还是上梁的“老姑父”、梁五方、春才,他们都在时代漩涡中迷失了自我,走向了自我的反面。道德内涵不足以概括这些活生生的生命。作家李佩甫擅长“把他的人物置于各种道德规范和人情原则错叠的焦点,以价值间的牴牾和碰撞来彰显某种深度和厚度,进而给我们带来一种阅读的新鲜感”[5]。
三、象征:关于冯家昌的选择
在《城的灯》的叙述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冯家昌的人生道路基本是逐步脱离乡村、挤进城市的过程,而与其相关的两个女人,刘汉香和李冬冬除了作为女性的个体而存在之外,也可以理解为乡村和城市的象征物。当年谷垛里的刘汉香如同当年的上梁一般给过他难堪,当冯家昌在仕途中一路昂扬前进时,象征着乡村的刘汉香已然成了他继续高奏凯歌的羁绊,于是冯家昌决绝地选择抛弃这个替他尽长子、长兄之责的刘汉香,当年扎在脚上的十二颗蒺藜此时又扎进了冯家昌的心里。在与城市女孩李冬冬交往时,冯家昌是谨慎而又自卑的。与李冬冬的第一次约会,冯家昌做足了功课,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照相,给自己补课,以便让自己看起来博学而又谦虚。如果说此前的冯家昌为进入城市的所有努力是为了穿上“四个兜”,迎娶刘汉香,表明他对上梁还有最后一丝牵挂的话,这次颇费心机的第一次约会就预示着破釜沉舟的冯家昌已经决定切断对上梁的最后一丝牵挂,踏上这条成为城里人的“不归路”了。与李冬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冯家昌起初是带着要“征服”李冬冬的心态进行的,不成想最后却被这个城市女人占了上风。当晚两人之间的肌肤之亲与其说是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乡村在城市面前溃不成军的象征仪式。冯家昌意识到,他进入了城市,却失去了尊严。在冯家昌的概念里,李冬冬是和城市划等号的,而刘汉香则是他竭力要摆脱的乡村。冯家昌最后对二者的取舍也显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现状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煎熬。“《城的灯》表现的是城乡冲突、灵肉冲突。前者是具象的,后者是深层的。二者又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共同完成人在生活的围城中左冲右突的人生图景。”[6]
四、结构:对内容的丰富
除了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城的灯》在小说结构形式上的探索也值得我们注意。李佩甫在叙述这个故事时,采用了一种双线并行式的讲述方式,两条线索围绕刘汉香作为长嫂在冯家的活动及冯家昌一步步从小兵到首长的艰难升迁展开。类似于曹雪芹《红楼梦》中宝玉成亲时的叙事手法,一边宝玉欢天喜地地拜天地,一边黛玉伤心吐血、气绝而亡。也类似于元末著名南戏《琵琶记》中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蔡伯喈入赘牛丞相府后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另一条线索是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艰辛度日。在这种讲述方式的支撑下,《红楼梦》将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无限放大,凸显了作品的悲剧主题。随着两条线索的推进,《琵琶记》则将赵五娘的善良无私、任劳任怨和蔡伯喈的优柔寡断、委曲求全两种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很大的推动作
用。《城的灯》中这种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产生的强烈的反差将紧张情绪烘托到极致,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城的灯》既有对这种文学传统吸收借鉴的部分,也内含有当代小说的探索精神。在借鉴传统文学资源横向的双线并行之外,作品也在关注纵向的个人成长的心灵史。这种纵横交错的双线叙述模式,取代了作家仗义执言的议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自觉思索和强烈共鸣。另外,个人的成长这条线索,也纵向地产生了一条时间轴,透过这个时间轴,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冯家昌、刘汉香们的心灵史。这种叙事策略的使用也使文本关于乡村政治权利的书写产生了生态学意义上的价值。尤其是对冯氏一门以冯家昌为代表的“五个蛋儿”的成长经历的再现,我们得以理解磕磕绊绊的童年经历在冯家昌心里投下的阴影。鉴于此,冯家昌一心想将“四个蛋儿”从上梁村“日弄”出来的愿望似乎也变得不难理解。
五、经典:阐释的魅力
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城的灯》也有其丰富的内涵。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是千姿百态的。作为文学文本的《城的灯》,带给读者的更多是有关城乡关系的思索,以及对个体心灵和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在“城的灯”的映照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丢盔弃甲的乡村艰难地突围城市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包括从物质上进城的冯家昌,也包括刘汉香毅然选择回乡培育“月亮花”,试图从精神上征服城市,当然还有坚守精神故土的老四冯家和。但文终冯家昌和几个兄弟在刘汉香坟前的一跪,刘汉香临死前发出的“谁来救救他们”的呼喊[1]397,冯家和被村人视作异类,成了冯疯子,城市和乡村似乎成了不可沟通的、失语的两极,只有无休止的不可言说、无法化解的对立。李佩甫仿佛已经用篇名向我们阐释了这部作品的主旨是以城乡对立为切入口来烛照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乡村。根据《城的灯》改编的电视剧最终定名为《下辈子做你的女人》。显然,导演认为“城的灯”这样一个有些拗口、令人费解的标题不适合商业化运作的电视剧,不能满足快速化消费时代的电视观众的猎奇心理,故而将作品提炼成为一种男欢女爱式的爱情故事,将其作为增加收视率的一个筹码。而该片的主演之一任程伟——冯家昌这一人物形象的直接诠释者——对于这样的易名行为显然不甚满意,他认为这完全忽视掉了冯家昌的个人奋斗历程,是对一个励志故事的亵渎。我们无法对这些观点妄下论断,因为正是对文本的多样解读才最终构成《城的灯》这部作品的内在张力和艺术魅力。但是,作品所提出的关于城乡问题的思考是无法回避的,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作品对于人性的叩问是发人深思的。
《城的灯》是一部优秀的有关人性思考的作品。无意于对某个人物进行是非对错的判定,只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浇铸着人性的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人,至于其中的爱恨褒贬就留待读者去细细体味吧……
[1]李佩甫.城的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2]何向阳.羔羊生命册上的绳记——评李佩甫的《城的灯》[J].南方文坛,2004(3):56.
[3]雷达.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十七[J].小说评论,2003(3):6.
[4]侯运华.“城的灯”映出人性的阴影——论李佩甫都市题材的小说创作[J].理论与创作,2010(3):61.
[5]李丹梦.李佩甫论[J].文艺争鸣,2007(2):147.
[6]刘绪义.家政治:城乡冲突中的生态符号——以李佩甫的《城的灯》为例[J].理论与创作,2005(3):98.
(责任编辑:王菊芹)
Introduction of the Rural Individuals and Groups’Breakout Based on Feng Jiachang of City Lights
SHANG Yafei
(College of Arts,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Feng Jiachang is the image of Li Peifu’novel named City Lights,which represents a series of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s: the peasent going into city with difficulty.As a rather controversial figure,Feng Jiachang has rich explanation space and value.Feng Jiachang’s pursuit of“the other”,the new content beyond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choice of symbolic rhetoric,timeliness arrangement,structure of space and works full of the charm of the interpretation,through analysis of the aspects,It will make great sense to rediscover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 and the group which Feng represents,has a positive meaning.
Li Peifu;City Lights;Feng Jiachang;individual;group
I206.7
A
1008—4444(2015)05—0128—03
2015-07-21
尚亚菲(1989—),女,河南宝丰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