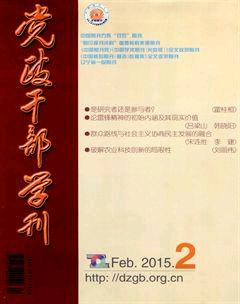是研究者还是参与者?——对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学术起点的一个批判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2-0004-07
[作者简介]霍桂桓(1963-),男,河北深州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
近十余年来,R·舒斯特曼及其“身体美学”不仅在国际美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文艺学界和美学界都已经有不少知名学者开始重视这种理论,纷纷与之展开对话或者撰文评述其理论观点,甚至有人开始将其当作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来看待。那么,R·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理论真的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吗?否!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我看来,尽管舒斯特曼本人自称出身于以追求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精确性著称的西方分析哲学传统,而且,他本人也自认为一直都在“追求表述的清晰和推理的逻辑性” ①,但是,由于他所主张的、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的、彻底批判和抛弃西方哲学研究的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做法,本身便隐含着把研究者和参与者混为一谈的根本性失误,因此,无论他所提出的“身体美学”及其一系列研究结论从表面上来看有多么兼容并包、左右逢源,其最终都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亦即最终都难免以牺牲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为代价、导致流于肤浅的研究结论的结果。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以机械的方式反对和彻底批判抛弃身心二元论所容易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通过充分强调所谓的“身体”和所谓身心合一,来削弱理性的地位,而这样一来,只要研究者不通过进行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而实施清晰的学术定位,那么,“研究者抑或身体美学的建构者本身究竟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参与者而出现的?”这样一个事关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性起点问题,就会变得含糊不清了——或者换句话说,在这里,由于不进行清晰的学术定位而把研究者和参与者混为一谈,因而使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丧失殆尽的危险,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尽管囿于篇幅,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一篇文章来系统全面地探讨和分析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各个主要方面,但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概略考察,我们就有可能对他的这种根本性失误看得比较清楚了:第一,反身心二元论的后果是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强调身心合一隐含着将研究者与参与者混为一谈;第三,唯一出路在于进行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清晰的学术定位。
一、反身心二元论的后果是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有必要充分强调的是,这里所谓“反身心二元论的后果是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之中的“反身心二元论”,主要是指西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乃至哲学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一种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以机械的方式对身心二元论进行彻底否定和全盘抛弃的倾向 ①,而不是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倾向的“反身心二元论”。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前者已经作为某种事实而实际存在并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而后者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思路而存在,实际上未必会作为学术史上的事实而表现出来,因而具有多种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尽管当今的绝大多数中外文艺理论界、美学界、乃至哲学界的研究者,都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研究者都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个颇具关键性重要意义的问题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的确都在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和全面抛弃在哲学研究之中由来已久的身心二元论倾向,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主要作为新实用主义美学家登上国际学术舞台的R·舒斯特曼,自然也并不例外。
那么,这种已经作为学术史上的事实而实际存在并不断发挥其作用的、以机械的方式对身心二元论进行彻底否定和全盘抛弃的倾向,真的会导致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结果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便需要从概略考察究竟什么是身心二元论谈起。一提到身心二元论理论,绝大多数中外哲学研究者首先想到的,便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提出的、认为心灵和肉体是截然不同、分别独立存在的两种实体的一系列观点;接下来,这些研究者便通过指出这种身心二元论所具有的、在具体结论方面和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的这样那样的缺陷,接着便像抛掉一条死狗那样把这种观点彻底否定和全面抛弃了。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实际上,仅仅就其思维方式来说,这种理论的思想萌芽、特别是其在认识论研究方面所使用的二元分裂对立思维方式的萌芽,早在西方哲学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实际存在并不断发挥作用了——比如说,无论是早在古希腊时期的知识界就曾经盛行一时的真理和意见之争、还是柏拉图通过极力贬低感性世界而对理念世界的推崇和多方面阐述,无一不包含着这种二元分裂对立的思维方式。如此看来,要想比较全面地探讨和研究身心二元论,研究者所应当涉及的就不仅仅是这种主要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论,究竟采用了什么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究竟通过何种推理过程而得出了什么结论,以及这些结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同时还应当涉及这些方面的源流,因而形成尽可能全面清晰的认识。
不仅如此,要想真正通过对身心二元论进行系统透彻的把握而最终加以扬弃,研究者还必须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正如古希腊的学者们进行有关意见和真理的争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贬斥意见而得到真理那样,这种理论本身也同样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认识过程而掌握更多的真理;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二元论、身心二元论,还是它们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本身首先都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实际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果研究者仅仅抽象地关注二元论本身、抑或仅仅关注身心二元论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是从其作用和意义的角度出发,把它当作被研究者用来追求真理性认识的一种手段来看待,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依然是难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在我看来,它有可能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在以机械的方式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作为手段的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及其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同时,把作为其根本目的的对真理性认识的追求也一起否定掉了!
那么,二元论抑或身心二元论真的曾经作为一种认识手段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吗?或者更加明确地说,难道已经在当今西方哲学界声名狼藉的二元论或者身心二元论,曾经有过、今后还会有什么合理之处吗?
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即使并不以引经据典的方式详尽无遗的考察古希腊有关意见和真理之争的方方面面,而是完全从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看,我们也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任何一位认识者、研究者要想形成对其认识对象抑或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恰当的真理性认识,第一重要的便是必须通过自觉地采取尽可能客观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坚持和贯彻“价值中立”的基本立场,来努力避免来自于自身的所有各种不利于这种理性认识过程的顺利进行的主观因素,而绝对不是、也根本不应当是对这样的对象采取包括实践性功利态度、伦理性主观评价态度和审美性好恶态度在内的任何一种非客观的态度,更不用说与这样的认识对象抑或研究对象“打成一片”、甚至是所谓“合为一体”了!毋庸赘言,只有这样,研究者抑或认识者才有可能通过取得真正恰当的研究结论抑或认识结果而最终实现自己的初衷,亦即形成真理性认识并由此而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而这样的基本要求所蕴含的,显然就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认识者必须与作为被研究对象或者被认识对象的客体拉开必要的距离、形成二元分裂对立的基本状态——尽管这里所谓的“对立”仅仅是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根本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因此,一言以蔽之,任何一位研究者或者认识者要想对其特定的对象进行恰当的理性研究或者理性认识,就必须以努力形成并确立这样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二元分裂对立状态为首要条件!否则,最基本的认识过程都完全有可能由于必定存在的种种主观因素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何谈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甚至进而建立更加深刻和全面的哲学?!
由此可见,无论二元论、还是身心二元论,都根本不是绝对的一无是处,而是自有其有效性、自有其合理性之处的——因为它们本身首先主要是对这样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二元分立对立状态的指涉和规定!因此,它们的有效性限度 ①实际上就在于,它们能够对研究者或者认识者在进行研究过程、进行认识过程的时候与其对象形成的主体-客体关系,亦即对这里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二元分裂对立状态,进行明确的、因而是卓有成效的规定和说明!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质上作为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出现的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既是对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的基本前提的某种明确规定,同时也因此而变成了使理性主义认识论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基本前提!而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和全面抛弃二元论抑或身心二元论,必然会彻底否定其所指涉和规定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二元分裂对立状态,因而必定会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削弱这种理性认识过程的基本前提、削弱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而使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极大的削弱!
因此,即使我们并不以颇为令人厌恶的贴标签的方式指出,诸如此类彻底否定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的举措都是“非理性主义”、甚至都是“反理性主义”,而是完全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来进行严肃和严格的批判性考察,我们也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乃至哲学界的所有各种研究者,无论其所探讨和研究的是何种对象、所凭借的是何种研究视角、所采用的是何种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秉承的是何种善良愿望,只要他们通过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和全面抛弃身心二元论来展开其具体的研究过程,他们都必定会因此而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所应有的地位、所有的产生的作用,从而使其理论研究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而作为这些探讨和研究之中的某种“新秀”而出现的、舒斯特曼及其“身体美学”,自然也不会例外。
二、强调身心合一隐含着将研究者与参与者混为一谈
既然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和全盘抛弃身心二元论会极大地削弱理性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我们初步判断舒斯特曼及其“身体美学”也采用了这样的做法因而其从学术研究起点上便产生了根本性的失误,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我看来,虽然就我们迄今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材料而言,舒斯特曼是在并没有对他所批判和抛弃的、以所谓“柏拉图主义”为突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所倡导的身心二元论,进行深刻、系统和全面的批判剖析的情况下,亦即实质上是在并没有对绝对应当加以彻底清理的学术基础和前提进行必要的清理的情况下,便以这样的反身心二元论倾向作为其“身体美学”的学术起点的,但是,通过概略考察其有关“身体”和“身体美学”的主要观点,我们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者那里,反对身心二元论实际上便直接意味着突出强调所谓“身心合一”,而后者则无论如何都会隐含着这样的研究者必定把自身与本来应当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实际存在的参与者混为一谈!
(一)“身体”实质上就是人的肉体
从严格的学理角度出发来看,谈论身体、尤其是从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反对所谓身心二元论的角度出发谈论身体,进而以之为主要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可能不以肉体和相应的感官欲望为主要内容的,因为只要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理性,那么,真正能够剩下来的自然也就只有各种感官欲望及其载体了。在我看来,在舒斯特曼那里,“身体”实际上就是肉体,而“身体”在其理论体系之中实际上既是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其理论枢纽。
那么,究竟什么是“身体”呢?
尽管舒斯特曼用所谓“Soma”来指涉他所说的“身体”,同时主要用“Body”表示肉体,试图因此而表明他所谓的“身体”“包含了精神、主体性和意图多个层面” ①,因而这似乎表明他不是以肉体为其理论核心的;但是,实际情况则根本不是如此!之所以进行这样决绝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初看起来,舒斯特曼明确指出其“理论核心是身体意识和身体感知” ②,但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名称便是Body Consciousness(即《身体意识》) ③,而不是Soma Consciousness;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我经常选用‘身体’这个术语来指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这种意义上的身体是我整个身体美学研究课题的核心” ①。因此,尽管他表面上由于各种理由而不喜欢用“肉体”这个语词,但是,如果所谓“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不是指人的肉体,又能够指什么呢?!
第二,我们说舒斯特曼的所谓“身体”指的是人的肉体,绝不仅仅是依据他的著作的标题;实际上,他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之中涉及“身体”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人的肉体,诸如“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它经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各种需要、种种习惯、种种兴趣、种种愉悦,还塑造着那些目标和手段赖以实现的各种能力。所有这些,又决定了我们选择不同目标和不同方式”、“当我用食指触摸自己膝盖上的一个肿块时,我的身体主体性被引导着去把身体的其他部分感受为探索的客体。这样,我既是一个身体,又拥有一个身体” ②,而且,他有关情欲的讨论 ③也是如此——我们几乎用不着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所谓的“身体”完全可以说就是人的肉体,否则是什么呢?!
第三,由于既对以“肉体”来表示他所谓的“身体”不满,又无法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到本来也不可能找到的更加恰当的表达方式,于是,舒斯特曼便用“Soma”来指涉他所谓“身体”了,而这实际上是根本无济于事的。且不说在英语之与“body”相比,“Soma”的原意主要指涉的就是“体细胞”、“细胞体”、“躯体”、“肉体”等生物学含义,它仅仅在与“精神”相对的意义上才指涉“身体”,而这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他所谓“身体”是指“肉体”的本义 ④,即使按照他所强调的颇为勉强的说法来看,亦即按照所谓“Soma”“包含了整个人”,因而“身体美学更大的想法是,它(即“身体”——引者注)比整个人更宽,它包含了整个社会、整个环境” ⑤来看,人们实际上依然无法确切地把握这样无所不包的所谓“身体”应当如何理解,因为这种没有经过任何分析和论证而进行的颇富独断论色彩的表述显然实在是太宏大了!正因为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研究尤其是美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在这里即使不能说荡然无存,实际上也所剩无几了 ⑥。
可见,舒斯特曼所谓的“身体”实际上就是指人的肉体;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不仅由于依然沿袭了其所希望加以彻底否定的,与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设定“本体”为理论原点完全相同的设定“身体”为理论原点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做法 ⑦,实质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而且,其本身也是独断的含糊不清的、因而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的!或许正因为如此,特别是由于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其所谓“身心合一”实际上便只剩下了作为肉体的“身”,因而为将研究者和参与者混为一谈埋下了伏笔。
(二)“身体美学”是如何把研究者和参与者混为一谈的
既然有关所谓“身体”的观点是如此独断、含糊和宏大,那么,“身体美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舒斯特曼指出,“身体美学”是“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学科概念”,它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aisthesis)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 ①
从这种定义式的论述出发,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三点:
第一,这种“美学”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而按照我们在上面的考察来看,也完全可以说是以人的肉体为中心的;
第二,它是对“身体经验和作用”进行的“批判的”和“改善的”“研究”;因此,这样的“美学”不仅仅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还致力于对“身体”加以“改善”——那么,究竟由谁来进行这样的“改善”呢?!又通过何种方式来进行呢?!显然,这种“改善”是应当由“身体美学”家来进行的,而且是应当通过所谓“身体美学”来进行的!
第三,这种研究的基本目标是“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方面,即作为一个方面的有关“身体”改善的“知识、谈论”,以及作为另一个方面的“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几乎用不着进行特别深入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这里的前一个方面的所谓“知识、谈论”并不是哲学研究层次上的、而只能是具体理论层次上的,因为其直接目的就是应用,因而与其说这种“身体美学”是舒斯特曼本人也承认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实际上不如说只能是具体知识乃至有关肉体训练的规则和诀窍。而后一个方面实质上则完全是对这种知识和诀窍的具体运用过程了,因而不仅不能是抽象和深刻的哲学层次上的学术性探究,同时甚至也不能是理论层次较低的具体理论性学术探究,而完全变成了实践性操作 ②!
因此,人们显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这里,舒斯特曼事实上已经把哲学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际性操作完全混为一谈了!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各种“身体美学”的研究者和拥护者来说,研究者和身体力行的参与者之间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区别的!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所谓“研究者”或者“美学家”看来,作为研究者的自身与作为参与者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随时进行转变!因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进行过严格剖析的,通过“身心二元论”体现出来的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了!而这样一来,这种“身体美学”实质上连普通大众通常所说的“卖什么吆喝什么”的基本标准都还没有达到,更何谈进行必须保持学术的严肃性和严格性的理论研究,乃至进行更加严格的、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的哲学研究?!而在根本没有真正严肃和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自己获得的主观感受,甚至仅仅凭借打坐参禅式的冥想而建立起来的“身体美学”,究竟又能够有多少学术含金量呢?!
行文至此,不明真相的读者或许会产生下列疑问,即舒斯特曼怎么说也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者,同时又号称是脱胎于分析哲学研究传统,他怎么会通过进行如此缺乏学术严肃性和严格性的“学术研究”来建构所谓“身体美学”呢?要想回答这样的疑问,我们或许首先可以非常肯定地指出,并非所有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者所进行的探讨和研究,都在自觉地努力秉持学术研究所要求的严肃性和严格性态度——比如说,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尤其是其中的“女权主义”研究者,实际上便往往把我们所说的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区别彻底抹煞,从而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既然如此,舒斯特曼这样做了,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舒斯特曼这样做也是和他所设想的“哲学观念”相一致的:“这种哲学观念不仅认可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和其他的经验科学对哲学研究颇有价值,而且通过回想古代作为一种身体实践、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概念,进一步强调哲学不只是理论。由所有相关科学形成的、指向改善生活品行的哲学理想,……当然不可能通过普通的课堂教育而实现。” ①看到这里,我们似乎便能够“恍然大悟”了:原来他所谓的哲学乃至“身体美学”并不是严肃和严格的学术研究,而完全可以是某些感受 ②,是某种“理想”!既然如此,以从事真正严肃和严格的哲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为己任的研究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毋庸赘言,舒斯特曼之所以秉持这样的“哲学功能”,如此进行“身体美学研究”,是与他所继承的分析哲学传统、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和所谓“实践哲学”传统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囿于篇幅和论旨,对这些哲学传统的批判剖析尤其是对舒斯特曼本人所进行的“接受过程”的批判剖析,都只能留待以后的机缘了。
三、唯一出路在于进行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清晰的学术定位
囿于篇幅,与我们在上面为了比较充分地揭示舒斯特曼的所谓“身体美学”就学术研究起点而言存的根本性失误而进行的分析和论述相比,我们的结论只能是非常简略的:
第一,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想彻底否定身体研究在美学研究中所可能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也同样根本不认为美学研究只能固守原来的研究领域而不能有所拓展!但是,无论是确定并突出强调身体研究对于美学研究来说所可能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还是对美学研究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真正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拓展,首先都必须在研究者秉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态度的前提下来进行!否则,研究者所进行的任何一种努力及其结果,都不仅实际上会事与愿违,而且完全有可能导致在国际美学界哗众取宠、在国内美学界招摇撞骗的恶果。
第二,无论是一般的二元论还是身心二元论,实际上都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无论在对待它们的时候,还是在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曾经在人类学术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又由于各种原因而声名狼藉的理论观点的时候,我们都必须通过既着眼于它们本身及其源流,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考察和判定它们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从而通过对它们进行系统、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通过清楚地认识其有效性限度,来真正实现对它们的清晰严谨的学术定位!否则,无论是以肤浅抽象的方式简单地看待它们,还是由于它们的缺陷而以机械的方式彻底否定它们,都只能给我们自己的研究及其进展带来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
第三,研究者要想对其所要加以继承抑或加以突破的,包括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在内的任何一种学术观点,进行清晰和严谨的学术定位,就必须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刻的哲学批判反思,舍此别无他途!这样的批判反思对象不仅包括研究者所面对的学术观点,包括这种学术观点所隐含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而且,还必须包括这种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必须包括其在人类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今后依然有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只有通过从严肃和严格的学术研究态度出发来进行这样的哲学批判反思,研究者才有可能清晰准确地确定这样的学术观点的有效性限度,进而通过扬弃之而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朱立元、张贵宝:《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该文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
即使仅仅进行一番比较系统的勾勒,对这种基本倾向在近70年间的发展演变过程的阐述也会构成一部篇幅可观的论著;囿于论旨和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把这项工作留待以后的机缘了。
毋庸赘言,讨论二元论、身心二元论的有效性限度与讨论其他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结论的有效性限度一样,都不能仅仅涉及其有效和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其无效和消极的一面,从而把能够标定其有效性范围的界线清晰地展示出来。但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二元论、身心二元论的有效性限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只能留待以后的机缘了。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朱立元、张贵宝:《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该文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朱立元、张贵宝:《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该文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
此书的英文版全称为:Body Consciousness: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thetics(《身体意识:有关警觉的哲学和身体美学》),该书中译本定名为《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一版。
参见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译本序”,第1页。
参见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同上引书,第13、14页。
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朱立元、张贵宝:《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该文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以及舒斯特曼、曾繁仁:《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该文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或许作为美国人的舒斯特曼不了解“Soma”在英语之中所具有的这些含义和用法?!我们不得而知。
参见舒斯特曼、曾繁仁:《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该文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比如说,舒斯特曼并没有、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回答下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在得出如此富有独断论色彩的结论的时候所使用的学理性依据是什么?他是通过哪些研究过程和推理步骤而得出这种结论的?即使这样的“身体”真的能够“包含了整个社会、整个环境”,究竟如何才能对它进行恰当的探讨和研究?如此等等。而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又一次看到了他的“身体”观是缺乏哲学研究的严肃性和严格性的。
遗憾的是,囿于篇幅和论旨,我们对于这一点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更加深入的剖析和论证的。
参见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彭锋译,2002年9月第一版,第348、354页。
或许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舒斯特曼的著作之中,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并不罕见——比如说,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的第19-20页,他把“瑜伽、太极拳、坐禅和亚历山大技法”都看作是所谓“改善身体”的重要方法;而在《实用主义美学》的第369页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身体美学声称不仅要从事有关身体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而且要进行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此外,通过身体美学的实践维度,它甚至还从事……身体训练:武术、时尚、美容化妆、健美、节食等等。”
参见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第369页。
参见舒斯特曼下列包含着大量同语反复色彩的话:“我坚决主张:任何敏锐的反思性身体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总是通过身体自身。集中感受某人的身体,意味着将之置于其周围背景的最显著的位置上;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进行这样感受,才能构建那种被体验到的背景”,《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第20页(用黑体字表示的强调意味是原有的——引者注)。
——以罗蒂和舒斯特曼为中心对实用主义美学的一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