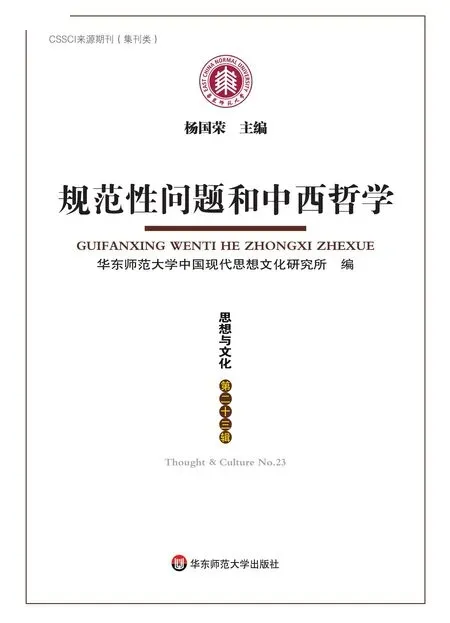经验与语言
——以罗蒂和舒斯特曼为中心对实用主义美学的一个考察*
●
在近几十年来的英语世界中,新实用主义美学展开为两大阵营的对峙,即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t)与文本主义
(textualist)的对峙[注]Bryan Vescio, Reconstruction in Literary Studies: An Informalist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49.,按维西奥(Vescio)理解,这一对峙实质上是经验(experiences)与语汇(vocabularies)之间的对峙。本文主要聚焦舒斯特曼,尤其是他在身体美学立场上对罗蒂的批评。舒斯特曼所说的经验,尤指身体经验,所以我们将之刻画为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这也是舒斯特曼用以刻画自己的术语,在实用主义脉络中,即身体实用主义。文本主义是罗蒂曾用来刻画自己立场的术语,语汇也是罗蒂后期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在更广泛的语言转向脉络中理解罗蒂的工作,且语汇是一类语言,故本文将罗蒂的立场刻画为语言实用主义。[注]M.吉海勒也使用身体实用主义和语言实用主义刻画舒斯特曼与罗蒂。参见M.吉海勒:《拓展经验: 论舒斯特曼在当前实用主义中的地位》,王辉译,《世界哲学》,2011年第6期。
在推进实用主义美学研究的过程中,舒斯特曼发展了一门被他命名为“身体美学”的学科,并认为“一种实用主义美学必然要回归身体本身”[注]舒斯特曼、张再林:《东西方美学的邂逅——中西学者对话身体美学》,《光明日报》,2010年9月28日。,他试图提供一个后罗蒂的实用主义美学类型,因此,对罗蒂的批评构成了舒斯特曼版本的实用主义美学的起点。用舒斯特曼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从文本主义到身体美学的过程,既承认了罗蒂对他的重要性,也暗示其对罗蒂的超越。[注]R. Shusterman, “Pragmat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From Rortian Textualism to Somaesthe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41 No.1 (winter, 2010): 69-94.其中理解与解释之争,具有根本重要性,其实质就是经验与语言之争。本文将说明,在这一问题上,舒斯特曼对罗蒂的批评并不成功。[注]舒斯特曼对罗蒂的批评是多方面的,除了指责其诠释学普遍主义之外,他还指责罗蒂是精英主义,混淆偶然性和任意性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指责都不成立,这需要另文处理。罗蒂亦曾简洁地回应舒斯特曼在语言观、公私领域区分等问题上的批评。就语言问题而言,罗蒂认为,他并未在语言的审美维度和理性维度间建立不必要的二元论;对于语言的不同使用,只是出于不同实践目的的需要,并没有在这些语言使用中排序,进而陷入认识论或本体论上的基础主义。关于非推论经验,他只简单地反问肉身的愉悦和阅读的愉悦之间可有什么有趣的区分?见Matthew Feststein and Simon Thompson (eds.), Richard Rorty: Critical Dialogue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p.153-157。
一、 从语言到经验: 舒斯特曼的方案
如果说,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宣告了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复兴[注]伯恩斯坦并不认可有所谓实用主义复兴一说,他认为,实用主义一直都在,其精神弥散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哲学实践之中。R. Bernstein, “The Resurgence of Pragmatism,” Social Research, Vol.59 No.4 (1992): 813-840.,那么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1992)则宣告实用主义美学正式走上前台。舒斯特曼的身体实用主义美学以对罗蒂的语言实用主义之批评开始自己的建构。[注]就美学或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国内学界倾向于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立场的似乎更多,代表性的如彭锋、陆扬、张再林等,支持罗蒂语言实用主义立场的似乎更少,代表性的如汤拥华等。对于舒斯特曼和罗蒂的关系,吉海勒认为,舒斯特曼的身体实用主义美学完成了对语言实用主义美学的超越[注]M.吉海勒: 《拓展经验: 论舒斯特曼在当前实用主义中的地位》,王辉译,《世界哲学》,2011年第6期。,国内学者普遍接受这一立场[注]支持此图景的,如彭锋:《舒斯特曼与实用主义美学》,《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彭锋:《实用主义与生活美学——舒斯特曼美学述评》,《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陆扬:《走向一种新实用主义美学?——舒斯特曼美学与中国的“生活”热情》,《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刘德林:《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第二章第四节,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韦拴喜:《论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的建构路径》,《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韦拴喜:《身体转向与美学的改造: 舒斯特曼身体美学思想论纲》,第二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就目前所见,主要有姬志闯: 《经验、语言与身体: 美学的实用主义变奏及其当代面向》,《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此文在语言与经验问题上,从古德曼角度批评了舒斯特曼。王伟: 《解释学转向: 价值与争论》,《理论与现代化》,2014年第4期。此文逐条批驳了舒斯特曼对诠释学普遍主义的批评,但未深入到语言观的差异。霍桂桓: 《是研究者还是参与者?——对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学术起点的一个批评》,《党政干部学刊》,2015年第2期。此文批评舒斯特曼对二元论等基础问题的讨论缺乏根基。。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舒斯特曼的工作并不成功,保罗·泰勒(Paul Taylor)指出,舒斯特曼混淆了审美经验概念的直接性和非推论性、非语言性[注]Paul Taylor, “The Two-Dewey Thesis, Continued: Shusterman’s Pragmatist Aesthetics,”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ew Series, Vol.16 No.1 (2002): 17-25.;莱博尔特(G. Leypoldt)认为舒斯特曼对罗蒂公私领域的区分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注]Günter Leypoldt, “Richard Rorty’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World-Mak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39 No.1, Remembering Richard Rorty (winter, 2008): 145-163.;维西奥从审美教育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实用主义更有优势[注]Bryan Vescio, Reconstruction in Literary Studies: An Informalist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49-73.。本文赞同后一立场,但认为之前研究者并未对舒斯特曼的具体文本展开深入分析,论及理解与解释问题,也未将焦点放在语言与经验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舒斯特曼为何聚焦于理解与解释、经验与语言问题?笔者认为起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当代美学史角度看,实用主义美学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分支或一种形态,其复兴和走上哲学、美学之前台,离不开罗蒂的鼓吹,他在建构实用主义哲学时提出了“从认识论到诠释学”的方案。伯恩斯坦同样试图以诠释学和实用主义沟通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罗蒂、伯恩斯坦等人,一开始就把诠释学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在此背景下,被归入实用主义美学的学者,普遍都关注理解和解释问题,这构成了舒斯特曼美学思考的当代背景。第二,从舒斯特曼美学建构的哲学逻辑上看,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语言诠释学(在舒斯特曼的论述中,罗蒂亦在此脉络中),以语言为轴心建构的美学体系,与舒斯特曼所提议的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美学相对立。对其的理解与批判,是舒斯特曼美学体系必须完成的工作,甚至说,这部分工作的成功与否,是其理论立足点。
舒斯特曼对理解与解释问题的讨论,通过对诠释学普遍主义的批评而展开,最后落实为语言和经验问题。他认为诠释学普遍主义是这样一种立场:“简单地以任何方式理智地去感知、阅读、理解或行为,已经是且必须要一直去解释。他们坚持只要我们有意义地经验什么,这种有意义的经验总已是一种解释的事情和产物。”[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8页。译文参照原文有所改动,下同。另参见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m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2nd e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论说,诠释学普遍主义认为,“我们不只是透过解释看每一件事物,而是每一件事物事实上都是由解释构成”[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58页。。舒斯特曼将罗蒂和尼采、伽达默尔捆绑归入其中。他将此线索放在反本质主义的脉络里考察,认为在传统基础主义中,理解被视为是基础的(不变的),解释被视为是非基础的(可变的),而一旦持反本质主义立场,就容易将理解看作是无基础的,因而就是解释,从而导致把“没有理解是基础的”和“所有理解都是解释”混淆。他的工作就是要论证这一混淆在理论上的错误,提出并论证一种非基础的理解,即非解释的理解、非语言的经验。
舒斯特曼对诠释学普遍主义的批评,是由对伽达默尔名言“所有理解都是解释”的批评而展开的。从其叙述中可见,罗蒂是其标靶。其批判可重构如下:
(1) 舒斯特曼认为,理解是可变的,不必将之等同于解释而后才是可变的,这一理解的可变性,表现为(2)和(3)。
(2) 理解本身的视界是多元性的和局部性的。
(3) 理解总是有偏见的,不是中立透明的。这种可变性表现在行动过程中,即(4)。
(4) 所有理解都是选择性的。
(4*) 有些理解是无意识的、非反思的;解释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5) 诠释学普遍主义视理解为积极主动的(即有意识的、自觉的),进而将感知视为主动选择的或建构的,因而必然包含解释。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预设是,因为
(6) 诠释学普遍主义认为,所有理解都是语言的,因为所有理解都包括要求语言的概念。
(6*) 舒斯特曼认为,语言的理解,总是一种通过意义和句法规则对约定符号的解码、翻译或解释,因而语言的解释是极度形式化和理智化的图像。他区分“直接和简单的理解”和“解码、翻译及解释”。只有后者与语言相关,前者可以是非语言的。这种非语言的直接理解,在舒斯特曼那里指向身体经验,即:
(6**) 舒斯特曼认为,即使我们承认语言的理解都是解释,亦不能推论出所有理解都是解释。这假设了另一个前提: 所有理解的经验和有意义的经验都是语言经验。但身体的意识或理解形式的存在是事实,它们本质上是非语言的,动作不需要翻译成概念化的语言就能被理解。
我们看到,理解和解释问题,最后被落实到了语言和经验问题,并表现为
(a) 理解/经验可以是无意识的、非反思的(4*)。
(b) 理解可以是非语言的(6**)。
二、 何谓语言?舒斯特曼语言观辨析
在直接考察语言和经验问题之前,作为出发点,考察“理解”与“解释”概念是必要的。舒斯特曼对诠释学普遍主义批评的出发点,是伽达默尔的名言: All understanding is interpretation。[注]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Revised Edition)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 (trans.), Continuum, 2006, p.390.中译为:“一切理解都是解释。”[注]伽达默尔: 《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25页。要阐明其中的意蕴,我们得回到德语原文: Alles Verstehen ist Auslegen。[注]Hans-Georg Gadamer,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J.C.B. Mohr (Paul Siebeck)Tübingen, 1990, p.392.就我们在此所关注的理解与解释问题而言,这里涉及德语词Verstehen、Auslegen。将Verstehen译为understanding和“理解”在此并无争议。而英译本将Auslegen译为interpretation,中译本对译为“解释”。问题在于,与英文词interpretation对译的应该是德文词Interpretation。Auslegen一词,在英文中并无固定的对译词,或译为explanation、interpretation,都存在偏差。当汉语学界说到“解释”时,一般就指interpretation,就诠释学而言,实际上遮蔽了Auslegen和Interpretation两者的区别,为示区别,潘德荣将Auslegen、Interpretation分别译为“解释”、“诠释(阐释)”[注]据潘德荣: 《西方诠释学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余论第五、六节;潘德荣: 《走向理解之路》,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潘德荣:《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认知与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理解、解释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当舒斯特曼用understanding、interpretation来理解“理解与解释”时,实际上已经混淆了Auslegen和Interpretation,而这两个词是存在重要区别的。陈嘉映、王庆节对这一区分做了说明:“Auslegen……与另一个常用概念Interpretation、interpretieren[阐释]相近。但比较起来,Auslegen常常在‘解开而释放’的意义上使用,而Interpretation所指的解释更具体系性和专题性,所以我们将前者译为‘解释’,而将后者译为‘阐释’。”[注]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3页。我们看到,舒斯特曼对英文词interpretation的使用更接近于德文词Interpretation。当他说语言的理解是“一种通过意义和句法规则对约定符号的解码、翻译或解释”[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72页。时,就是此意,而这对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一脉的“Auslegen”,则有所遮蔽。
上文主要就词语翻译而言,若抛开翻译问题,从义理上说,其问题何在?回到上文已经提及的舒斯特曼对理解的两个界定: 即理解的无意识性和非语言性,在舒斯特曼处,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验如果经过语言中介,就是有意识的、反思的,反之亦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语言:舒斯特曼是如何理解语言的?罗蒂又是如何理解语言的?
舒斯特曼在回应伽达默尔“人类对世界的所有经验根本上是语言化的”[注]罗蒂认同伽达默尔此一观点,见R. Rorty, “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 Gadamer’s Repercussions: Re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ruce Krajewski (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21-29。这一观点时,表达了自己对语言的看法。为使讨论得以顺利展开,我们要先明确他们共享的观念,以此作为我们下面考察的前提。如果说,对于理解是否是语言性的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对于解释必然是语言性的,舒斯特曼与罗蒂、伽达默尔等人并无争议。舒斯特曼说:“理解——甚至高级的智力理解——经常是非反省、非思想,甚至是无意义的(即使总是有目的的),而真正的解释包含了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思想: 某些晦涩或含糊的东西的澄清、符号的译解、矛盾的解决,先前未言述的诸要素之间的形式和符号关系的清晰表达。”[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81页。与之相似,他区分了“直接和简单的理解”与“解码、翻译及解释”。前者是非推论的、非反省的、无意识的,因而是非语言的,后者则是语言的。这幅语言图景中,语言整个和认识联系在一起,虽然舒斯特曼亦批评传统知识论,但在此他共享了传统知识论的语言观。在传统知识论那里,只有与语言相联系的认识或命题性知识才是认识论上有价值的或有意义的,在舒斯特曼这里,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样被局限在这一领域。一种非认知的语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表现在其行文中几乎不加区别地使用非反思的、非推论的、非认知的、无意识的等词汇上。语言就是有意识的、反省的、使用推论的命题。[注]舒斯特曼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母语使用是无意识的,而外语使用才是有意识的,这两者是理解与解释的区别。参见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第172页。这种语言观,可以称之为命题语言观。当舒斯特曼承认认知领域、知识领域完全是语言性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注]舒斯特曼: 《哲学实践》,彭锋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并且对舒斯特曼来说,对“所与神话”的批评,即对非语言的基础主义的批评,并不构成对他的反驳,因为“所与神话”仅限于认识论,而哲学的范围远大于认识论。虽然在认识论上,经验必然是推论性的,因而是语言的,但在认识论领域之外,比如在审美领域中,非推论的经验是可能的。而罗蒂的语言实用主义,强调语言的无所不在,“鼓励一种不健康的唯心主义: 将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等同于语言行为,从而倾向于忽视非推论的身体经验,或将它彻底文本化”。[注]舒斯特曼: 《哲学实践》,第199页。又,伽达默尔认为:“如果人们援引世界的自在存在来反对唯心主义——不管是先验唯心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语言哲学,那就纯属误解。因为他们认错了唯心主义的方法意义,而其形而上学形态自康德以来就已经被克服了”。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630页。更进一步,他还将罗蒂的语言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逻各斯、理性,将罗蒂等人对语言的推崇视为对非语言、非理性的压制。
解释典型地旨在语言的系统阐述,旨在将一个有意义的表达翻译为另一个有意义的表达。有关某些言说或事件的一个解释的标准,就是能用某种明确、清晰的形式去表达所解释的东西。……相反,理解不要求语言的清晰表达;一个适当的反应,一个耸肩或一个抖动,就足以表明人们已经理解了。我们经验或理解的某些东西,从来没有被语言捕获,不仅因为它们的独特感觉拒绝被语言充分表达,而且因为我们甚至都没觉察到它们是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是我们开始清晰表达或解释时所预设的感觉背景。[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82页。
首先,舒斯特曼将他的命题语言观表现得淋漓尽致,理解和解释的区别在于语言,这种语言是“系统阐述”(formulation)、“清晰表达”(articulation)的陈述。正如我们上文已提及的,这一“解释”,对应于德文词“Interpretation”,“解释”是更具体系性和专题性的,当舒斯特曼说语言的理解是“解释典型地旨在语言的系统阐述……就是能用某种明确、清晰的形式去表达所解释的东西”时,这对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一脉的“Auslegen”,有所遮蔽。按照这一严格的命题语言观,舒斯特曼自然不会认为耸肩是一种语言性的行为。甚至音乐、舞蹈等,也自然被排除在外,这也表现在他对古德曼认知主义符号学立场的艺术概念的批评上。
其次,这段话蕴含几个重要的混淆,表明其语言观和非语言经验概念的含混。郁振华区分了: 1.“可以表达的东西和不可以表达的东西”;2.“原则上可以用语言手段来充分表达的知识和不能用语言手段来充分表达的知识”; 3.“事实上被言说的知识和未被言说的知识”[注]郁振华: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与之相关的结论是,默会知识关注后两者,分别涉及强的默会知识和弱的默会知识。强的默会知识认为默会知识并非命题性知识所能把握;弱的默会知识,只是说,有些知识未被命题表达,不论是“格式塔式的默会知识论的意义上的被了解,还是在认知局域主义论的意义上被了解”[注]郁振华: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42页。。借助上面的概念工具,我们再来审视舒斯特曼这段话。当舒斯特曼说“理解不要求语言的清晰表达”时,可以指尚未被清晰表达,也可以指不能被清晰表达。这涉及对上面第2、3点的混淆。当他说“从来没有被语言捕获,不仅因为它们的独特感觉拒绝被语言充分表达,而且因为我们甚至都没觉察到它们是可以描述的‘东西’”时,“拒绝被语言充分表达”,似乎是说不能被语言完全清晰表达,而非不能被表达;“没有察觉到它们可以描述”,似乎既可以指它们原则上不能被语言表述,也可以指尚未被语言表述。这涉及对上面第1、2、3点的混淆。舒斯特曼若要证明非语言经验,则应证明1,但其刻画几乎都游弋在2、3之间,这表明舒斯特曼对于语言和经验(理解)之间界限何在的立场是模糊的。一方面他声称,理解是外在于语言的;一方面,又不能使自己实质上区别于弱的默会知识论,这种立场认为原则上只存在已被明述的知识和未被明述的知识。他一直视为典范的“亚历山大技法”的身体修炼技术,要求一种背景性知识作为展开的前提,能够在弱的默会知识论中得到定位。由此可见舒斯特曼的语言观,既是狭隘的,也是不融贯的。
三、 何谓语言?罗蒂语言观辨析
罗蒂并没有陷入舒斯特曼狭隘的命题语言观中。[注]罗蒂的学生,巴里·艾伦,曾指责罗蒂陷入命题性语言观。他认为,罗蒂虽批评传统的符合论知识观,即knowing-of,却认同了knowing-that,即陈述句,有真假的命题;罗蒂终结knowing-of的时候,认同了knowing-that,因而仍然落入窠臼之中,即命题性知识。见Barry Allen, “What was Epistemology,”Rorty and His Critics, Robert B. Brandom(e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但罗蒂的knowing-that似乎是广义的命题,即语言。郁振华在批评艾伦的时候,也指出了这一点,见《人类知识默会维度》,第365页。但是罗蒂的语言观同样是含混的,需要我们辨析。陈亚军区分了罗蒂的两种语言观:(1)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语言,语言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工具,使用语言的活动是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在此活动中,“语言既是敞开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自身的内容。在实践活动中,语言和世界融为一体”。(2)强调语言的自我融贯,无意中又滑入了传统哲学的陷阱之中,在那里,“语言”和“世界”再度被打作两段,我们只能谈论语言,而不能谈论世界。[注]陈亚军: 《“世界”的失而复得——新实用主义三大家的理论主题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28—32页。如果我们做同情的理解,可以说,罗蒂抛弃的是康德意义上的作为物自体的世界,而在语言哲学中,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讨论的世界,是已经在推论语义关系中的世界。布兰顿对“做”和“使用”的区别,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工具,来帮助理解罗蒂的语言观。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布兰顿区分了“做”(do)与“使用”(use):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做”,但只有在一定语言游戏之中的行动,才可被称之为“使用”,“使用”是在语言游戏之中被界定的。一个人只有知道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才知道如何“使用”,人类的理解只有在一定的语言游戏之中才是可能的,语言之外的理解,就如私人语言一样不可设想。[注]陈亚军: 《将分析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布兰顿的语言实用主义述评》,《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69页。
沿此思路,从广义上理解罗蒂的语言,它类似于语言框架或语言游戏规则。康乃尔·韦斯特对之有精彩刻画。[注]有关此段论证更细致的展开,见黄家光: 《康乃尔·韦斯特的“预言实用主义”及其限度》,《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5期,第76—77页。他认为,罗蒂所谓语言转向从来不是说,除了语言我们一无所有,罗蒂不至于倒退到传统唯心论上去,认为语言构成了世界,而是说,我们无法离开语言与世界打交道。在此,有必要回到塞拉斯对“所与神话”的批评,这种神话认为,有一种我们可以直接感知,而不需要经过语言的直接经验(所与),它构成了我们知识的基础。塞拉斯正确地指出,人们混淆了理由的逻辑空间和自然的逻辑空间、因果关系和证明关系,实际上“所与”是语言事件,也是社会实践问题,忽视这一区分,导致了“所与神话”。在此,韦斯特恰当地指出了这一语言与维特根斯坦“舞台-背景”的相似性,这一“舞台-背景”是“对非推论性现象的性质做出可靠‘观察’所必须的东西”[注]康乃尔·韦斯特: 《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 实用主义的谱系》,董山民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2页。。韦斯特的这一理解,在讨论罗蒂时得以延续:“总是存在大量的解释规则或为事物命名的潜在方式。……这种潜在的东西不需要(也不能)完全地被实现出来,或被排除。”[注]康乃尔·韦斯特: 《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第295页。在此作为知识背景的语言、语言规则,就不是单纯的命题性语言了,而是一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注]有学者认为,罗蒂的“语言”或“语汇”是库恩范式概念之发展。见吉尼翁、希利: 《理查德·罗蒂和当代哲学》,载吉尼翁、希利(编):《理查德·罗蒂》,朱新民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没有范式,社会实践、运作是无法理解的。
四、 非语言经验之困境
在考察了罗蒂与舒斯特曼的语言观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舒斯特曼批评罗蒂时的核心概念“非语言经验”。在此概念中,语言与经验的对立被直接呈现出来。舒斯特曼认为,非语言经验是一种感性的、直接的非推论经验,它“存在于主题化的意识和语言之下”[注]舒斯特曼: 《哲学实践》,第186页。。他认为,有语言经验,也有非语言经验,而所谓的语言经验,是指“思考、谈论、写作”[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74页。,这些都是可以用命题化语言来表述的语言行为。而且,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里的合法哲学,即都是在推论中,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通过语言来决定位置的语言活动。这种哲学对“前阐释反思地拒斥,一个理智主义者对普通经验中非反省、非推论的维度是盲目的,是高傲的精英主义和狭隘的不加鉴别的偏见”[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80页。。而非语言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比如说舞蹈,“在本质上是非语言的,实际上拒绝被语言充分描绘……(人们)不需要将它翻译成概念化的语言术语,就能理解一个动作或姿势的意义和适当性”[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73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文我们已经辨析过的狭隘的命题化语言观如何限定了舒斯特曼对于非语言经验的理解,在这样的概念图景中,塞拉斯、伽达默尔、罗蒂、德里达都因为提倡语言的首要性而被认为是理智主义者,压制非推论、非语言、非理性的经验。[注]舒斯特曼: 《哲学实践》,第199—200页。
问题在于,舒斯特曼狭隘的语言观中的非语言经验,在罗蒂的广义语言观之下,是否是非语言的。正如舒斯特曼已经提及的,在罗蒂那里,语言有非推论的应用,例如语言创造的实践[注]舒斯特曼: 《哲学实践》,第198页。,但舒斯特曼认为这种语言创造的实践与语言无关,他认为学习语言使用是“对有效参与一种生活形式中的反应的驾驭”,而语言则是“对一个解释记号的符号规则系统的驾驭”[注]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第172页。。但若我们接受布兰顿在“使用”和“做”之间的区分,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语言实践活动要在语言游戏之中才能被理解,不论你是否有意识或自觉反思。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加反思地接受、使用一套语言游戏规则的,因此,这些规则常常是隐含着的。
同样,我们理解一个身体活动,并非如舒斯特曼以为的那样是直接的。泰勒指出,舒斯特曼混淆了直接性与非推论性。舒斯特曼所借用的杜威的经验直接性概念,其本意或者是与理智主义相对,指我们应该就近选择语境来理解经验,而不能用最远端的科学概念来解释;或者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直接性,这种感知是有理论负载的,就算是无意识的,也不是非推论的。就此而言,直接性不等于非推论性,即非语言性。[注]Paul Taylor, “The Two-Dewey Thesis, Continued: Shusterman’s Pragmatist Aesthetics,”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ew Series, Vol.16 No.1 (2002): 22.舒斯特曼的另一个批评对象,古德曼,也曾批评那些看似直接的理解,比如说动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习俗和文化塑造的结果”,而对于舒斯特曼所依仗的舞蹈的例子,古德曼直接说“思想狭隘的和业余的观看者可能当作本能和不变的东西,专业演员或导演却知道是学来的和可变的”[注]古德曼: 《艺术的语言》,彭锋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页。。舒斯特曼当然不会认为本能是不可变的,但古德曼提示我们,所谓的人类本能,已经是语言化的经验,就算有时候太过临近未经反思的使用,也不能认为它是非语言的,它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是一种语言化了的经验或本能,与动物式本能并不相同。这一点,对古德曼基本持认同态度的罗蒂也会同意。以上的分析,亦可视为人与动物之别。舒斯特曼在证明身体经验的优先性时,不断强调人与动物具有连续性,认为在动物性的理解中不需要解释,在人的理解中,同样存在非语言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伽达默尔对于世界和环境的区分[注]见伽达默尔: 《诠释学Ⅰ: 真理与方法》,第623—624页。,我们就会看到,动物的理解是属于环境的,而人的理解则是在世界之中完成的,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究其实,是不同类型的理解。舒斯特曼的类比是一种范畴错置。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舒斯特曼只看到了人与动物的相似性,因此强调人与动物的连续性,而对其中的差异估计不足,即对人类理解中的隐含的规范性、语言性维度的基础性作用估计不足。罗蒂在回应舒斯特曼的批评时,也曾提到承认生活大于理解和承认伽达默尔的“所有理解都是语言”并不矛盾,那些非推论的东西并不构成人类之于动物的独特之处,有意义的人类活动或愉悦,已经是语言的。[注]Matthew Feststein and Simon Thompson (eds.), Richard Rorty: Critical Dialogue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1, pp.155-157.我认为,只有在人禽之辩的框架里,才能适当安置罗蒂所谓的语言本质主义,其背后是人道主义。
舒斯特曼要反驳罗蒂,所需要做出的证明应当是存在一种非语言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在人类语言游戏之外,且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理解的,因为一旦进入语言游戏中,就已经语言化了。说舞蹈、手势是非语言的,在罗蒂这里是不得要领的,因为这些只有在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中才可被理解。因而非语言经验要么成了一个物自体式的概念,重新陷入语言与经验的二元对立,要么非语言经验仅指暂时未被语言表达的经验或未被语言充分表达的经验,但这实际上不是非语言的。
五、 余论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美学类型,是从批评罗蒂的“文本主义”美学(语言实用主义美学)出发的,这是其自我身份和合法性的根基。但是经过本文的考察,我们看到舒斯特曼的批评并不成功,他试图通过罗蒂而超过罗蒂,走向一种“后罗蒂的实用主义美学”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语言实用主义美学,并未被舒斯特曼超越,不仅在罗蒂的案例上如此,在古德曼的案例上同样如此。姬志闯从语言与身体之关系入手,比较了古德曼和舒斯特曼的美学,聚焦点同样落在了舒斯特曼所推崇的“非语言性的身体经验”这一概念上,分析其内在困境,而得出舒斯特曼并未超越古德曼的结论。在此意义上,本文同意其结论,一种语言化的美学,“能为实用主义美学的未来面向和路径选择提供一个审慎而又可能的视域”[注]姬志闯: 《经验、语言与身体: 美学的实用主义变奏及其当代面向》,《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9页。。基于此,我们不是将以罗蒂、古德曼为代表的语言实用主义美学作为一个已经死去的美学-哲学传统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美学-哲学与之展开对话。与之相应的结论是,经验实用主义美学也许是一条可行的方案,但是舒斯特曼并未为其提供可靠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