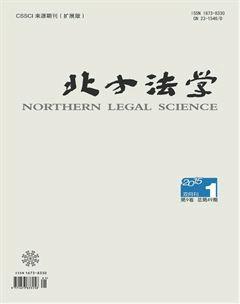论见义勇为的侵权法调整
王福友
摘要:我国立法将见义勇为行为放在民事责任的框架下加以规范,总体上形成了以“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为主、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为辅”的调整模式,其实质是在见义勇为者、侵权人、受益人三者的微观关系中赋予见义勇为以法律意义。《侵权责任法》第23条创设的侵权人法定侵权责任与受益人的适当补偿制度,均难以实现保障见义勇为者权利之目的。见义勇为行为的价值在于其属社会公共善,应在社会法的层面对其予以规范,应废除《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见义勇为基金会应调整其现有功能,成为对见义勇为者及时赔偿的平台;见义勇为者亦可选择依过错归责原则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
关键词:见义勇为无因管理社会善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1-0069-07
一、我国相关立法之检讨
见义勇为行为总会在社会出现,即便是仅仅将其视为道德问题而没有受到法律的调整;但若将其视为法律问题,法律调整模式的选择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见义勇为者的心态,甚至会对人从事向善行为的动能造成挫伤。现代社会风险的几率和强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人们总难免或者经常陷入危难境地,若有人挺身而出既会帮助受害人,亦会对侵害人形成震慑而避免更多侵权行为。故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调整当无疑问,但究竟采取怎样的调整路径深值研究。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我国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民法领域,期间几经制度变迁,但按照民事责任的机理对其予以调整的逻辑始终没有改变。其旨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侵权人、受害人三者之间配置权利义务关系,强调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权利予以保护的立法重心。见义勇为行为为传统道德所支持,尤其在防止、制止国家、集体财产受侵害时鼓励人们付出积极的努力。民事责任乃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法定或者约定原因产生的微观责任,与见义勇为行为所具的宏大社会效应并不相称,实践中常见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甚至面对侵权行为之正在发生而旁观者巨、见义勇为者甚少等社会现象,人情冷漠之景象展露无疑。故对我国相关立法应予以深刻检讨。我国民事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调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法通则》的规定。其第109条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见义勇为行为改变了传统侵权法确立的两项原则:一是主体主动将自身置身于危险之中,应由其自身承担责任;二是侵权人之承担应以其存有过错为前提,其中侵权人的可预见性、可避免性乃衡量其行为过失的主要标准。若囿于这两项原则之束缚,侵害人恐无需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故《民法通则》明确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应属构成对其第106条关于一般侵权行为规定之例外。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并未构成其法定义务,见义勇为者据此从受益人处得到补偿恐无保障,但该规定本身却与见义勇为行为对受益人的道德意义相契合。第二阶段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的规定。该规定第142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在侵权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该条与《民法通则》作同一解释当无疑问;但在受益人的补偿问题上却与《民法通则》不同,补偿不再是纯粹的主观选择而变成了可被法院责令的对象,性质上应属民事责任之范畴,且赋予法院利益衡量之权限。该条同时为利益衡量之运用设定了前置条件,即仅在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时,见义勇为之情形往往发生急迫,让见义勇为者先判别是否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难为现实,其结果必然是限制见义勇为者获得受益人补偿的机会。第三阶段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该解释第15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进一步限缩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损害应为人身损害,且受益人补偿责任之承担被限定在受益范围内,该规定较《民通意见》规定了更明确的利益衡量适用原则。何谓“受益范围”难以确定,甚至是否存在都值得怀疑,受益人本身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其所体现出来的是实际损害。所谓受益,其实质是应该受到的损害状态减去实际受到的损害状态,但是“应该受到的损害状态”因并未实际存在而无法确定,仅属推测。该条规定的结果就是,受益人在对见义勇为者补偿后,其实际承担的损害包括了实际遭受的损害与补偿给见义勇为者的总和。从财产损失的角度观察,受益人并未因见义勇为行为之存在而获益,仅是以金钱之损失替代了人身伤害。第四阶段为《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该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总体上,我国民法对见义勇为行为形成了以“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为主,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为辅”的独立调整模式,与一般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制度相分离。前者已如前述,就后者而言,“从制止侵害行为的特殊性来看,《侵权责任法》第23条专门对其加以特别规范和调整,使之从一般的无因管理制度中剥离出来,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分离出来进行专门调整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使受益人在特定的条件下,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对制止侵害行为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①笔者认为,对《侵权责任法》第23条作出如此评价,显有不妥,使见义勇为行为从一般的无因管理制度中剥离出来,应始于《民法通则》而不是《侵权责任法》。且在制度上作出这样的判断亦缺乏根据。一般认为,无因管理制度调整的主要是助人为乐行为,其与见义勇为行为并不相同。②“法律确立无因管理制度的直接目的,是赋予无因管理行为以合法性,而对于不合无因管理要件的对他人事务的干涉行为则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无因管理实质上是法律赋予没有根据地管理他人事务的某些行为以阻却违法性”。③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在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为他人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依法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管理事务符合本人的意思,若本人能够管理时必当管理,是否管理事务乃本人享有自主决定权,故无因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仅具有微观善的价值,只能理解为是管理人代本人行使管理权,且即便在管理人自为管理的状态下,其因管理不善或者疏于管理而使自身受到损失亦难以避免,在此状态下避免本人权益损失仅对其自身属于“善”的行为,在社会层面观察其仅具有“中性”的价值,故无因管理制度在法律上采取准契约的方式予以规范,以在管理人与本人这一微观法律关系中实现对助人为乐行为之肯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特设无因管理一款(“民法”第172条以下),以之为本人与管理人间债权债务发生之独立原因。④但有学者以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为例,认为“无因管理之债,虽非契约,但无因管理人须有管理意思,与契约规定甚为相近,效力上且准用(委任)契约之规定(173Ⅱ),故早期制度有准契约之称”。⑤就无因管理内部权利义务关系观察,认其采取准契约之方式并无不当,以表明无因管理行为虽属于对他人事务之干涉,但却依法具有阻却违法性。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上从一般无因管理中剥离出来,旨在摆脱准契约的立法模式,其实质是因见义勇为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助人为乐行为的价值。将《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确立的规则认为系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无因管理的一般规定相较,不合之处较多”。 ⑥见义勇为行为是针对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行为之防止、制止,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并非见义勇为行为的直接目的,对此难谓是管理他人事务。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被定性为是“恶”的行为,防止、制止该行为乃社会之“善”,故理应将见义勇为行为从准契约调整模式的无因管理制度中分离出来。
二、《侵权责任法》第23条之解释
见义勇为行为并不总是法律希望人们做出的行为,英美法系就对其采取了不鼓励的态度,突出体现在不鼓励人们做好撒玛利亚人。“英美侵权法认为行为人只有在侵害了他人利益时才需承担责任。这一观点可以更好地阐述为:一般而言,一方没有义务使另一方受益。因此,即使在某人几乎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即可避免灾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义务帮助陌生人或者保护他们不受伤害”。⑦事实上,见义勇为行为在英美法上也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侵权人是否对见义勇为者承担侵权责任,依一般过失侵权行为加以判断,并无特别之处。立足于对见义勇为结果的科学评估,在现代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对侵害他人行为的防止或者制止,很大程度上是专业性或者专门化的行为,而不是依靠热情即可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见义勇为行为在侵权法上也是“中性”的行为,因为见义勇为者的热心和勇气,恐难以真正起到制止、防止侵权行为的效果,甚至使事态变得更糟。“在早期,普通法曾经认为引起损害的人无需对自愿救助危险或受害人的救助者承担责任,其理路不外乎通过否定行为人对救助者负有关注义务或者认为救助者自愿承担了损害的风险。但从上世纪初开始,法院就已经转变了态度,不仅认为引起危险的行为人对自愿救助者负有关注义务,而且也不再对救助者适用同意或自愿承担风险抗辩——对一般救助者如此,对专业救助者如消防队员等也不例外”。⑧Haynes诉Harwood案(1935年)、Baker诉TE Hopkins & Son Ltd案(1959年)法院均认为:当被告过失地引起危险情势时,有人试图提供救助是可以预见的,被告提出救援人员自己愿意承担风险或者救援人员构成介入原因的主张不可能得到支持。以此判例承认侵权人对援助者负有义务,使侵权人对救助者承担侵权责任成为可能。“因被告所制造的危险,为抢救他人而进行的救援活动(rescue)中遭到损害的人,只要其救援行为是合理的,被告就不得对这些人援用同意抗辩”。⑨但是救助者因实施救助行为而导致的损害并不是绝对不承担责任,也存在救助者自己对事故受害者负有义务的情形:(1)根据“有害信赖”原则,当救助者开始救助行为时妨碍或阻止了他人的救援行为;(2)当救助者恶化了事故受害者的状况时,救助者对事故受害者就负有了义务;(3)一般来说,帮助急需救助的人不会产生义务。但是,当救护车接受了999急救呼叫,并且病人的姓名和地址已经确定,则义务产生。⑩英美法通过对抗辩使用上的限制,为救助者向侵权人主张责任扫除了障碍;同时,并没有因为其行为的高尚而封闭了救助者对受害人承担责任的可能。德国立法亦不鼓励基于公共利益的行为赋予当事人以侵权请求权,“在德国联邦法院BGHZ64,178判决案,被告等人系法律系及神学系学生,见原告在火车站前摆摊出售色情刊物,劝原告搬离,原告拒绝。被告等乃强行取走书刊,并损毁其设施,原告诉请损害赔偿。被告主张正当防卫。德国联邦法院认为正当防卫不能成立,强调个人人格虽为宪法所保障,人民的道德价值亦应受尊重,但此并不表示每一个公民于他人从事悖于善良风俗或违反刑法之行为时,皆得采自卫的方法加以排除。被告采取攻击行为,使公益成为私事,使自己成为维护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检察官,不受宪法的保护。在一个法治国家,维持有秩序社会的社区生活,乃国家的职务,不能借助私力救济”。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直接的立足点在于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以此弘扬见义勇为者为社会公共善之义举。具体体现在:(1)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该规定超越了《侵权责任法》为一般人追究侵权责任的规定要件,属于法定的特殊的侵权责任。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见义勇为者欲追究侵权人的责任,至少应证明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与侵权人之侵害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存有过错。见义勇为者证明这两点几乎不可能。第23条之规定应属于建立在推定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无过错责任,因为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与侵权人行为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因果关系。该规定虽然有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但也仅是在侵权法理论上达到了这一效果。为见义勇为者创设侵权请求权,使其权利保障完全取决于侵权人的责任能力,见义勇为者从事壮举后,却不得不面对侵权之诉带来的诸多司法困扰,这一制度选择难以认为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充分褒奖。(2)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受益人的补偿责任应不属于侵权责任之范畴,其责任基础到底如何理解并不显见。依文义解释,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主要是因其自身从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如果不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被侵权人也不会遭受损害,当侵权人逃逸或者侵权人根本无力赔偿时,被侵权人由于见义勇为行为而遭受损害得不到任何赔偿和补救也不公平,不利于社会助人为乐良好风气的形成,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精神,因此,为了较好地解决矛盾、平衡利益、分担损失,让受益人适当给予被侵权人补偿是可以的”。基于道德层面的理由阐述,明确了受益人的这一责任并非侵权责任,但其承担的补偿责任却是最终责任,第23条并未规定受益人对侵权人的追偿权。其结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侵权人逃逸,或者采取各种手段证明自身无力承担责任;甚至见义勇为者都会更愿意从受益人处得到补偿。存有疑问的是如何处理第23条与第18条第2款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此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没有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形下,见义勇为者死亡的,若受益人支付了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则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二是在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形下,见义勇为者死亡的,受益人应依第23条之规定承担补偿责任,故其无权对其支付的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请求侵权人赔偿。第23条与第26条之间的关系亦值得深入研究。见义勇为过程中,若见义勇为者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侵权人有权根据第26条之规定,主张减轻自身责任。但在适用第23条第2句时,受益人是否可援用第26条之规定主张减轻补偿责任不无疑问。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第23条第2句规定的责任是受益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代替侵权人承担责任,故其无权享有侵权人的相关权利;受益人承担的是法定的补偿而不是侵权责任,故不能适用侵权责任上的过错相抵原则。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若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构成对受益人的侵权责任,那么第23条第2句规定的受益人补偿责任是否仍然存在?第23条并未将见义勇为者没有构成对受益人承担侵权责任列为适用的要件,解释上应将二者视为不同的责任分别予以追究;但是,受害人之所以成为受益人是因为其在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第23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不同,其不以受益人实际受益为要件,亦无需对受益人受益与其遭受见义勇为者损害间予以衡量,故即便是在见义勇为者构成对受益人侵权责任时,仍然不能排除第23条第2句之适用。
第23条关于见义勇为行为之规范,与国外立法相比:一是就见义勇为行为者与侵权人之间的关系观察,外国立法尤其是英美法系仅是注意到见义勇为行为系主体自愿将自身置身于相对危险的境地,但鉴于对该行为之支持,通过排除同意作为抗辩事由之适用而扫除了侵权责任构成之条件,但该侵权责任仍然是停留在普通的意义上。见义勇为行为在该法律体系下,仍然主要被视为普通侵权行为,并没有因此改变陌生人间的关系及其信赖,突出体现为并没有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特别保护。在此情况下,见义勇为者若仍然主动为见义勇为行为,就仅仅使其实现内心的满足感,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制度性的庇护,甚至是得到另外的荣誉、利益等。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则规定了超出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侵权行为。二是增加了受益人的适当补偿责任。第23条总体上是立足于表彰见义勇为行为,并尽力维护见义勇为者之利益。在侵权法领域如此的制度安排,却易于造成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位出现偏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受益人付出代价实现对受害者的补偿,其仍然囿于侵权法视野,在损害与填补框架内考虑问题。总体上仍坚守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责之原理,仅仅是将该行为的结果由单独对受害人负责裂变为对两个人负责。见义勇为者从事了对社会有益的事务,但却不得不通过普通的侵权责任机制实现救济,其获得赔偿的结果仍然受制于侵权人作为债务人的履债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3条又在受害人与受益人之间形成了新的紧张关系。因见义勇为行为的存在使得受益人获得益处,但在通常情况下又要考虑与受害者之间的补偿关系,若双方不能就补偿达成协议,又会引致纷争。受益人的名称亦不准确,其原本不应受伤,受益无从谈起,最大限度仅是可能受到损害但实际没有受到,只是虚拟受益,其仍然是受害人。受害人身份转向受益人缺乏合法性证明,构成对见义勇为者的义务人亦有违法律。不能因其受到的伤害与应然状态相比较小,而认其为受益人,使其对见义勇为者负担补偿义务,实质上造成其并未因此受益,且有强制受益人感恩之结果。
三、“社会善”的法律调整模式
见义勇为行为的重点不在于避免受害人的权益受到损失,否则容易在“见义勇为者——侵权人——受害人”这一维度考虑对见义勇为的制度安排,使其无法脱离侵权责任的视野。见义勇为的法律意义在于不为民事主体设定贡献于“社会善”的法定义务,也许尽管对其仅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要沿循“善”而不是“恶”的定位予以调整。其目的不仅仅是考虑其受到的损害该如何获得赔偿的问题,而是在法律领域建构起促进个体如何为社会善做贡献的路径。实现这一目的有赖于法律调整视角的转换,侵权法乃权利保护之法,其能够解决的仅仅是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问题,但见义勇为者的权利保护在价值判断上应该具有超越于主体权利保护的一般规定的价值,因其是为了维护他人利益而做出的牺牲。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的特别规定加以实现,《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规定的初衷即是如此,本预使见义勇为者具有超越于一般受害人的侵权法地位,但其无法实现这一结果,侵权法受制于自身的调整手段和运行机理在解决社会善的问题上恐无能为力。在侵权法上不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特别规定,并未排除见义勇为者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的可能,只是使其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加以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承担补偿责任亦为不妥。在受益人——见义勇为者二者之间微观法律关系领域考虑问题,显然是将该问题视为普通的民事关系,等同于见义勇为者之行为仅仅是旨在避免给受害人造成更大的损害,若停留于此,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调整应服从于对无因管理的一般规定。见义勇为行为因属社会善而具有了被法律单独调整的理由,因见义勇为行为的存在使得更多潜在侵权行为得以避免,且在社会层面形成有限利他的行为方式,社会因此而得利。故应从社会法的视角完善见义勇为行为的调整,以更好地展现和落实见义勇为所具社会面向的法律价值。但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价值必须被定位在适当的层面上,个人促进社会善应该以其权利得到切实维护为前提。倘若制度安排将见义勇为行为放在了崇高的位置上,可能会导致见义勇为制度在主体之间产生博弈,甚至以牺牲个人权利来促进社会善的实现,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主体行为上过分强调利他之倾向。
我国社会法的层面上对见义勇为行为亦有所涉及和调整,但是制度安排对见义勇为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有待检讨。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见义勇为而致的损害问题留给了《侵权责任法》,即通过第32条加以解决,全国各地成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均是以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为主。“目前,一些省、市建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专门鼓励那些为了国家、集体、他人利益舍身相助、见义勇为的人”。从全国层面上有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该基金会《章程》第34条规定:本会财产主要用于:(一)表彰、奖励、抚恤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和抢险救灾中贡献突出的全国范围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二)宣传和推动见义勇为事业的发展;(三)表彰、宣传、募集工作所需开展的各项活动;(四)业务活动成本、筹资成本和管理费用;(五)理事会决定的其他费用。基于此,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重点并不在于解决因见义勇为而导致的损害该如何赔偿,是否能够得到赔偿的问题,而主要是针对表彰、奖励等。见义勇为基金会与《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之间不是针对相同问题,不具有共同适用的可能。二是社会力量对于见义勇为行为主要是侧重于对其予以政策性优待,甚至为见义勇为者配置某种社会资源。2012年8月,民政部等6部委制定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重点规定了包括保障低收入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提高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保障水平;扶持就业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就业;加大对适龄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受教育的保障力度;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住房困难等在内的完善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政策措施。同时,规定了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包括:对见义勇为死亡人员,凡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依法评定为烈士,其家属按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待遇。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属于因公牺牲情形的,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予以抚恤;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有关规定支付,遗属特别补助金由当地财政部门安排,民政部门发放。不属于上述情形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放一次性补助金,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落实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会同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发放,所需资金通过见义勇为专项基金统筹解决;尚未建立见义勇为专项基金的,由当地财政部门安排,民政部门发放。见义勇为行为得到的这些方面优待政策,使得见义勇为行为者得到了更多的超越于普通受害人的待遇,二者相较过程中的差别待遇是否正当值得怀疑。对见义勇为者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因自身道德追求而拥有的心灵宁静,甚至被迫成为公众人物,其生活及权利保护问题都要受到新的拷问;成为社会效仿的对象,在个体权利维护与保护缺乏社会普遍性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性的方式培育见义勇为行为无疑在方向选择上存在着错误。应常态化地看待并对待见义勇为行为,并将真正的见义勇为行为与履行具有法定、约定义务的救援等行为区别开来,“受害人如就防止或制止他人人身、财产遭受侵害负有法定或约定之义务(例如:警察、消防人员、老师及其他救护人员或保镖等)者,是否仍有本条所定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权利?解释上,除有特殊例外,似乎应予否定,以免混淆公法义务与私法权利应有之界限,并不当扩大行为人之责任”。由此,既能避免见义勇为行为的泛化,且有利于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具有专门化的救助方式。
基于此,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规范应立足于常态化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将调整的重点放在如何真正有效保护其权利的问题上,要在私法与社会法相结合的层面上,实现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结合。笔者认为,应废除《侵权责任法》第23条之规定,依法完善见义勇为基金会制度,将其功能定位于见义勇为者的权利保护,从而在见义勇为领域建构起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多元救济机制。见义勇为者基于从事见义勇为行为这一事实,可直接从见义勇为基金会获得损害补偿,当然其亦可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只是见义勇为者的一个备选请求权,与普通民事主体权利享有别无二致。使见义勇为者对侵权人主张的侵权责任回归为一般侵权行为,受到《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统一调整。若选择向基金会主张,基金会应该予以补偿,并依法享有对侵权人的追偿权,以明确侵权人对此应承担的最终责任,实现社会法与私法的有效衔接,并保障不因该制度设计而弱化对侵权人的责任追究。去掉关于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责任,以通过祛除二者间的利益关系还原见义勇为行为的道德属性,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感恩情怀永留心中,切实醇化社会风气,以减少制度安排对见义勇为行为道德性的消减。改变现有见义勇为基金会主要用于对见义勇为者予以表彰等功能,使之成为能够对见义勇为者就其所受损害予以救济的平台,只要确认见义勇为行为就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损害补偿;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见义勇为者的损害赔偿问题,依社会法的调整路径解决私人对社会善之贡献问题,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害赔偿达到个人道德水平与社会需要间的平衡。
Regulations on Acts of Good Samaritans by the Tort Law
WANG Fu-you
Abstract:The acts of Good Samaritans are regulated by civil obligations in our country with a general mode that “the tortfeasor assumes the tort liability primarily while the beneficiary bears compensation obligation complementally”. This legislative mode actually confers legal meaning to acts of Good Samaritan in the micro-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ood Samaritan, the tortfeasor and the beneficiary. However, according to Article 23 of the Tort law, neither the statutory tort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tortfeasor nor the proper compensatory obligation assumed by the beneficiary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the Good Samaritan. The value of acts of Good Samaritan lies in the social public good which should be normalized by social laws and thus Article 23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foundations for acts of Good Samaritans should exercise the present function, acting as the platform for proper compensation to Good Samaritans and they can also claim against the tortfeasor for tortious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Key words:acts of Good SamaritanNegotiorum Gestiosocial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