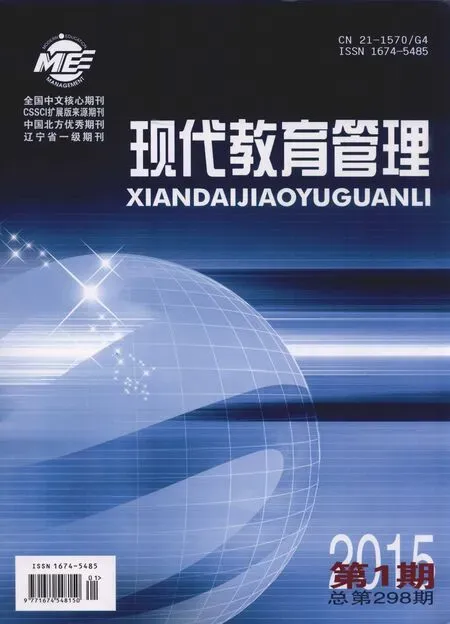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运动思维”①
徐吉洪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运动思维”①
徐吉洪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从大学愿景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繁荣与忧思并存。当前,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陷入了“运动思维”的陷阱,呈现计划秩序的行政主义、言必称希腊的拿来主义与过度的制度崇拜主义等倾向。这种“运动思维”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秩序、诱发了高等教育“公地悲剧”、异化了一流大学的价值旨趣。要走出“运动思维”的陷阱,我们需要从重建高等教育自发秩序、加强大学理念反思、提高大学文化自觉等三个方面努力。
世界一流大学;运动思维;公地悲剧;计划秩序;自发秩序
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繁荣与忧思
改革开放初期,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繁荣的春天,萌发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这首先是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的。1985年,清华大学正式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确立到2020年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远景目标。1986年,北京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在1994年的党代会上坚定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志。此阶段,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国大学的“院校话语”成为了一种大学愿景。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标志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意志。1998年时任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号角。此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文件与会议都重申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意志和决心,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政策保障。
进入21世纪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热议的“大众话语”:政府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社会支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学者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规划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高校从最初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渐扩军为“2+7”、“2+X”,直到当今39所。此阶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备了“大众话语”的身份,成为了当下高等教育界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我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上也有“出色”的表现。2012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1]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我国大学的序位比较“抢眼”。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时下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一种标签,这引起了学界的深深忧思。一是建设规模可谓“宏大”。从最初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在经历了“2”、“2+7”、“2+X”的纷争模式与利益分配,到现在的39所“985工程”高校(占我国高校总数的近2%),都有追求“世界一流”的“远大理想”。而事实上,要实现世界一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都不知我国大学是否入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马丁·特罗先生早就提醒世人——“规模是一切问题之源”。正是如此,世界高等教育头号强国的美国也只有1%的高校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二是经费投入巨大,引起高等教育不公平。由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战争思维,政府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按照较大比例切给了这39所大学,而其他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很难“分得一杯羹”。巨额的投入与并不理想的产出,引起了社会广泛的非议,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不公平。三是发展模式固化。由于“985工程”已正式“关门”,使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39所“985工程”高校的“专利”,这些高校制定“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这种封闭式的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
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思维”的表现
“运动思维”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意指运用“激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用突变的方式推进事物发展、用人财物的规模集中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方法”[2]。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运动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计划秩序的行政主义
“计划秩序”也称“人造秩序”,是制度学派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类事务中的秩序乃是以一些人应当颁布命令、另一些人应当服从命令为必要条件”[3]。这种“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依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4]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言的“人造秩序”(制度学派称为“计划秩序”)。计划秩序的行政主义反映了我国高校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不得”的热切心理和时间紧迫感。殊不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急不得”的文化心理过程。一方面,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上来看,回顾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最早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作为一种“院校话语”出现的,反映的是大学的发展愿景。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潮是在1998年时任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大学校庆讲话后兴起的。这符合“计划秩序”的内涵与特点,但与大学作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相背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偏离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一种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行为,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而非高等教育的自发行为,因而未能形成自发秩序。另一方面,从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大学内部行动来看,这种“计划秩序”的行政主义也处处可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大学都制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线图”、“时间表”甚至是“任务书”。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制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N步曲”。在时间节点上,我国部分优秀大学均“计划”在2020年前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使得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了“2020年猜想”。究其实际“效果”,这种“猜想”也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谜团”。
(二)依葫芦画瓢的拿来主义
在回应“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我国大学都非常“一致”地“目光朝外”。在教育“面向世界”口号的指引下,我国大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自己的“偶像”,纷纷寻找自己的跟踪对象从而陷入依葫芦画瓢、言必称希腊的“拿来主义”陷阱。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部分优秀大学都陷入了模仿发展、同质化发展的陷阱。在“偶像”的选择上追求“高大上”,部分“985工程”高校都将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MIT等世界最顶尖的一流大学确立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在学习方式上以跟踪模仿为主,缺乏内涵建设,还停留有形无神的阶段;在发展情结上“综合性”、“全科式”情结较重,普遍追求“学科门类齐全”、“万人规模校园”。而事实上,在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中,还有在校生只有2000余人的“袖珍大学”,但这并丝毫不影响其牢固的一流地位。过度模仿、崇拜外国大学,不仅打击民族大学的自信心,而且还会形成“言必称希腊”的惯性思维,这不利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拿来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大学沉浸于“跨越式”发展的“喜悦”之中。但是,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外力使社会转型加速,我
国的“跨越式”发展打乱了自然进化的秩序,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漂移于传统旧模型与现代新模型之间的交叉状态或过渡状态[5]。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不是“跨越式”发展起来的,而是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经过数百年的熏陶才得以建成的。
(三)过度的制度崇拜主义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制度根本狂热”。有人将“现代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视为真理性的公式。事实上,即使有了科学的大学制度,一流大学也还需要经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艰难转型。一方面,“以制度创新建设一流大学”的制度崇拜。不可否认,持论者理性地看到了现代制度对建设一流大学的作用,但有些过于痴迷。因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何为“现代”大学制度、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大学制度”等具有价值判断意味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如何遵循世界高等教育规律、如何彰显民族高等教育特色等深层问题缺乏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对于大学发展来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只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其他问题就会顺理成章”[6]的制度迷信。在这种制度迷信带动下,有人提出“中国引进现代大学制度10年内可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设想。翻开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无不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熏陶才造就了今天的辉煌,区区10年能够打下扎实基础就已经很不错了,更遑论建成一流大学。
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思维”的危害
(一)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秩序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存在的“运动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秩序,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讲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7]。这种“无序”状态导致了我国使高等教育迷失了发展方向和丧失了基本品格。“运动思维”在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秩序”和“计划秩序”。这样的“秩序”其实是曲解了秩序的本真要义,在哈耶克看来,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加强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8],这样的“秩序”是与“计划秩序”相对立的“自发秩序”。而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按自身逻辑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有机体”,是在长期的自发有序中成长、成熟起来的。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作为社会集体更新发育的一个部分和结果,大学是一个“非人造组织”[9]。世界一流大学的诞生和发展绝不是设计和计划的结果。大学作为“底部沉重的组织”,整体上并没有集中的权力控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有组织的无序”具有三个普遍的属性,即“未定的偏好、不清楚的技术和不固定的参与者”。[10]这样的组织是“若干思想的一种松散的集合,(而不是)一种连贯的结构;与其说它是根据偏好来行动的,倒不如说它是通过行动来发现偏好的。”[11]大学是具有独立精神的自律性和自为性组织,任何强制的外来干涉都与学术发展的自主逻辑相悖逆;这就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存在着科层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
(二)诱发高等教育的“公地悲剧”
如上文所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用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与“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这就不可避免地将高等教育原本就并不丰裕的优质资源向极少群体高校“倾斜”,这不仅会引发高等教育不公平,而且还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的“公地悲剧”发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式和制度安排严格规定了谁有权力从公共池塘资源(教育经费)提取一定资源(“生存卡路里”)的权利。而根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观点,公共池塘资源要合理地一代代延续下去,必须满足七个设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与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12]。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型”资源配置方式,“985工程”高校作为一个封闭式的俱乐部,缺乏外在的竞争,这容易引发高等教育的公地悲剧。因为每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大学都希望中央财政增加投入、扩大投资,在扩大大学规模方面可谓不计成本。这不仅加剧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公平,而且还让部分高校背上了沉重的“一流债务”。
(三)异化一流大学的价值旨趣
受“计划秩序”的影响,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成为了政府“想要的”(wants),而并不一定是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needs),异化为“以各种捷径甚至歪门邪道在创世界一流口号之下捞取‘政绩’”[13]。我国大学对于创建“世界一流”的标签非常焦虑,甚至患有严重的“内分泌失调症”。正如阿特巴赫所指出的那样:“过于强调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可能会损害某一特定的大学或院校系统。这样做有可能使得精力和资源偏离更重要并且可能更现实的目标。它或许会使人们牺牲大学的入学率与为国家服务为代价,将精力更多地投在了建设研究型大学也就是精英大学上。它也可能导致提出一些不现实的期望,以致有损教师的信心和工作表现”[14]。在这种“运动思维”的影响下,大学把任何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都设定为错误的,相反,为了某种实在的好处它可以出卖那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大学的使命不再是教给学生人生哲学,而是赋予他谋生的能力;大学教育不再是帮助学生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美好生活,而是挣更多的钱以获得世俗的幸福;大学的存在不再是为人类提供自我完善的场所,而是被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油站[15]。大学的教育目标,不应只着眼“人力”,而应着眼“人性”,培养有学识、有智慧、止于至善的人。正如比尔·雷丁斯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16]。
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思维”的消解
(一)重建高等教育自发秩序
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存在着“计划秩序”的倾向,其后果是带来“大学行政化”趋向。典型的就是我国出现了31所“副部级”大学,可谓是“中国特色”。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具有“目标模糊性”特征。因此,我国大学需要建立自发秩序,这种秩序“不是经过人为设计和计划而形成的,也不是自上而下地被强加的,而是在社会内部自生的”[17]。要建立高等教育的自发秩序,一是政府要给予大学自由、自治的发展环境,给予我国大学追求“闲逸的好奇”的环境空间。二是社会要给予大学更多的宽容,主要是时间上的宽容。毕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犹如“罗马之城”——“并非一日建立起来的”。从生态学上来讲,“大学的进化很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18]。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我们不能走的“太急”、“太快”、“太远”,而要“慢慢走”,一步一个脚印走踏实。
(二)加强大学理念反思
在我国举国上下唱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题曲”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已开始在反思自己国家的大学,如美国哈佛学者哈瑞·刘易斯就公开批评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认为哈佛已“失去灵魂的卓越”,耶鲁教授安东尼·克罗曼则痛斥大学面临着“教育的终结”,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在这种反思浪潮下,西方学者开始批判“现代”大学,如《废墟中的大学》、《濒临毁灭的大学》、《扼杀大学灵魂》、《道德沦丧的大学》、《圣殿里的骗子》等。在国人专注于大学满足人的欲望的同时,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对大学的未来忧心如焚。
因此,我们需要彻底的大学理念反思:谁需要世界一流大学?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需要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国力能建成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远?特别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我们要作出理性的判断。因为“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要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与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所需要的(needs)”[19]。或许联合国提出的“前瞻性大学”理念和“必要的乌托邦”哲理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大学必须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保留其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价值的追求。
(三)提高大学文化自觉
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对于我国大学而言,尤其需要使命自觉、视野自觉和情怀自觉。首先,我国大学要树立崇高的真理使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以追求真理为立校使命。因为“大学的意义及价值在于追求真理”,因此,我国大学,要“以真理为友”,致力于真理的发现和探索,因为“真理”才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
的最要紧的要素。其次,要具有全球视野。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关怀全人类发展,培养世界领袖。因此,我们需要以全球视野为人类造福,以全球视野来培养造福世界的精英人才,从事全球环境、人类健康、知识经济的研究,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有责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全人类在不久的将来过上和平、繁荣和有意义的生活”[20]。再次,要富有本土情怀。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与成功需要肥沃的本土土壤。美国世界顶尖大学汇聚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学的发展和真正福祉从来都是与我们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一流大学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一流的贡献。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很值得当今大学反思与借鉴,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印记的世界一流大学。
[1]田锋.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方向研究[J].江苏高教,2014,(1):52-54.
[2]徐光.论中国共产党“三种思维”方式的变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4):18-22.
[3][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199、200.
[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1.
[5]张红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困境[J].高等理科教育,2011,(5):1-5.
[6]杨东平.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特质[J].中国高等教育,2003,(23):15-16.
[7]胡建华.从“无序”到“有序”——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J].教育发展研究,2002,(12):26-29.
[9][17]李静蓉.高等教育秩序的逻辑:自发秩序理论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07,(7-8):84-88.
[10][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5.
[11]Michael Cohen.A Garbage Can of Organization Choi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3):1-11.
[1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2.
[13]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J].读书,2002,(3):133-140.
[14][美]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28-31.
[15]王建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4,(2):1-9.
[16][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
[18][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0.
[19]Abraham Flex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3.
[20][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变革世界中的大学——在哈佛大学2011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J].世界教育信息,2012,(4):16-17.
(责任编辑:杨 玉;责任校对:李作章)
The Research of“Movement Thinking”to Build the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XU Jiho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has become the nation’s will and government’s ac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vision. There are prosperity and anxie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Currentl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our country has in the“movement thinking”trap,presenting the tendencies such as plan order,borrowing and system of worship. The“movement thinking”ha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rder of higher education,induced tragedy of the commons,alienated the value of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To overcome the“movement thinking”trap,we should rebuild the spontaneous order in higher education,strengthe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and improve the univers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movement thinking;tragedy of the commons;plan order;spontaneous order
G640
A
1674-5485(2015)01-0063-05
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13JZDW00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东部率先发展的浙江地方高校发展战略研究”(KT2011007);2013年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项目“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特征研究”(201307)。
徐吉洪(1979–),男,江西吉安人,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助理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