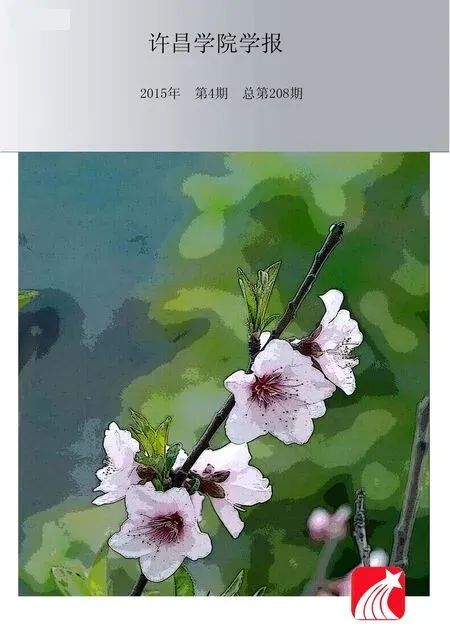论曹禺《原野》的神秘主义
肖 庆 国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0)
论曹禺《原野》的神秘主义
肖 庆 国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0)
曹禺的《原野》中充斥着许多神秘主义的元素,它们错综复杂,或明或暗,历来为许多评论者所诟病。神秘主义的面纱遮住了《原野》的真实面目,也造成长久以来评论者对于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误读。从文学观念层面和创作方法层面着手,对剧作中的神秘主义给以详尽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原野》。
曹禺;《原野》;神秘主义;文学观念;创作方法
正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所倡导的革命文学席卷文坛之时,曹禺却创作了耐人寻味的《原野》,这似乎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所以自从《原野》一问世,便遭到了当时批评家们几乎一致的指斥。而在众多的批评声中,有一种不能被忽视的存在,即批评《原野》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质。神秘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是截然对立的,批评家们的“不接受”也就此“阉割”了曹禺的戏剧创新。从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时代语境的不断开阔,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评价《原野》的艺术成就。所以,其中的神秘主义元素也理应被重新阐释。我们认为“神秘主义”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间直接交往,并能从这种交往关系中领悟到宇宙的‘秘密’。”“现代西方流行的一种文艺倾向。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幻象,或某种超自然的幻觉,使艺术创作服从于盲目的本能和神秘的愿望。”[1]3464-3465
实际上,《原野》的“神秘主义”是有章可循的,并且呈现为一定的整体性,本文试图从文学观念层面和创作方法层面来对《原野》中的“神秘主义”作出分析。
一、文学观念的神秘性
文学观念的不同,往往会带来文学世界的差异性。在《原野》里,曹禺有意地选取了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对象世界,比如巫术、鬼神、梦境等,这些都可以归于宗教或民间信仰。我们认为是曹禺所选取的文学对象自身的神秘性增加了《原野》的神秘戏剧氛围,这主要是戏剧家在其独特的文学观念下的刻意的选取。
《原野》中的巫术主要表现为“木人扎针害人”、“烧纸钱安神”和“唤魂”。如果我们来探讨巫术的神秘性,似乎就陷入了脱离戏剧文本来独立谈巫术之神秘,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巫术本身就是神秘的,“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加强影响或控制的活动”[1] 4152。问题的关键在于,剧作家选取巫术来营造剧本的神秘氛围,其背后究竟暗含着什么用意?
在第一、二幕的开头详细介绍了焦家的陈设,这里剧作家有意地营造了一个鬼神的世界:焦阎王半身像、香案、祖先牌位、菩萨等。而这一切无疑都是作者在独特的文学观念下“刻意的选取”对象世界进行文学表达。试想,有谁家会挂着死人的“巨阔、油渍”[2]379的半身像并且“旁边挂着一把锈损的军刀”?[2] 379又有谁会在家里供奉“三首六臂的”[2]379“油亮的黑脸上,显得狰狞可怖”[2]424的菩萨?即便是寺庙里也很少有黑脸的菩萨,焦家被描绘得没有一丝人气,倒更像是供奉鬼神的祠堂。
焦母的一个梦境可谓是鬼气森森,她梦见了焦阎王穿着孝衣浑身是血远道而来,抱了小黑子不放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有一股迎面而来的逼人的神秘感,还混杂着另一个感觉——恐惧。以往对于《原野》神秘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将神秘与恐惧作以区分,二者常常相伴而生(如鬼神给人的感觉),但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我们试想焦阎王活着的时候,这梦境在现实中进行,焦母只会觉得恐惧,但不会有多少的神秘感。这情景为何在《原野》里表现得如此神秘?因为这是在梦境中所发生的,梦的本身就具有神秘色彩,并且焦母将她的梦作为对现实未来的一种神秘的“指示”。
巫术、鬼神和梦境都是与焦母紧密相关联的,因此焦母的人物形象也长期饱受着亵渎:“焦氏几乎成为一个充满恶毒心机的化身,由她在那里布置全套,诱使金子和仇虎就范。”[3]132“其他的人物有焦阎王之妻焦母,是个毒如蛇蝎的瞎子。”[4]80然而细读文本,倒并没有一处能说明焦母参与了焦阎王对仇虎一家的祸害。老中国乡村里丈夫在外谋事,倒并不一定与妻子事先商量好。焦母深知仇虎的出逃带着两家的血海深仇,会对焦家的人有血光之灾,她就立刻报告了侦缉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焦母对花金子的疑虑,在后来花金子“帮助”仇虎杀害自己的丈夫时也得到了验证。这样看来,焦母首先是无罪的,她的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可是,《原野》最后终于还是将焦母的一系列的“挣扎”击打得粉碎,我们认为巫术、鬼神和梦境自身的神秘性背后深藏着人类普遍命运的神秘性。正是焦母(一个瞎老太婆)对于自己(乃至于焦家)的命运的无法掌控,她才借助于媒介——巫术、鬼神和梦境等——来做无谓的“挣扎”,以试图掌控神秘的命运。
二、创作方法的神秘性
《原野》的神秘主义不仅仅限于剧作家文学观念的层面,还体现在其所努力运用的创作方法层面。《原野》曾经被誉为“中国化的琼斯皇”,与其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是相关联的,而象征主义却被曹禺从《雷雨》中便保留了下来。此外,《原野》里曹禺还精心地刻画第六感,并促成种种巧合,并调用了色彩来绘成神秘的画面。
《原野》序幕在一开始便不惜用大量的笔墨对原野进行了一番描绘,作者主要描写了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我们选择对其中的巨树来展开详细的论述,因为它见证了仇虎复仇的始终,也最具象征性。
巨树外貌的高大、苍劲,暗喻了主人公仇虎的形体特征与内在气质。“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2]353,巨树又被比作被禁锢的普绕米修士,羁绊在石岩上,这与仇虎的“镣铐”有相似之处。
《原野》中的象征意象随处可见,比如火车、镣铐、野塘、黑云等等,而这些扑朔迷离的意象的综合,又统一为某种意象群,使得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而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文学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它所要阐释的是个人主观的内心世界,用以表达令人难以捉摸的幻觉,其内容是神秘主义。
《原野》令人最感觉神秘的地方,应该是一直不断被人阐释的“走不出的黑森林”。在黑森林里剧作家综合了许多的表现主义的戏剧舞台效果,比如灯光(红灯笼)、音乐(唤魂、鼓声)、假面(人形)等等,终于将《原野》的神秘主义推向了极致,整部剧所展开的戏剧冲突也在这里走向了高潮。表现主义强调“闭上眼睛”来看自己的灵魂,探究个人的内部视野,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和抽象化,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神秘的内心隐秘。仇虎“走不出”的表象是“黑森林”,而其内在实质是走不出自己被命运所设的圈套。命运赋予了他复仇的责任,而焦阎王的缺席使得他的复仇失去了直接对象,终于在“父债子还”的传统文化律令下违背着自我的良心去杀害焦大星——一个懦弱的老好人。剧作家从而将仇虎复仇的外部冲突转化为了心灵的冲突,命运的神秘在表现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达到了顶峰。
《原野》中有少数的几处巧合,比如“焦花氏:(望着她)昨儿格,我梦着大星回了家。”[2]400“焦大星:(烦恶地)哭!哭!哭!今天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简直是哭我的丧。”[2]425“焦大星:(低声)——他仿佛死了似的。”[2]427等等,然后紧接着这些随口而出的“预言”却都变成了真实:大星回家了,焦大星丧命,小黑子死了。还有,焦大星被仇虎杀死的时候喊着“好黑!”[2]470,仇虎进入黑森林的时候无意地重复着这句话;仇虎在焦家的时候唱着《妓女告状》来恼焦母,进了黑森林中却被白傻子《妓女告状》的声音如同魔咒般纠缠。这些巧合都给《原野》获得了神秘感。曹禺曾经在《雷雨》中构造了太多的巧合,可是《雷雨》采用的锁闭式结构使得三十年的恩怨集中在一天里发生,强烈的戏剧冲突所产生的紧张感使得“过分的巧合”被掩盖了。吸取了《雷雨》“太像戏”的教训,《原野》散文式结构下的巧合便被设计得轻微不留痕迹,从而表现得似乎更加接近“真实”。这份“真实”仿佛告诉读者,乃至剧作家自己,人的命运被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主宰。
我们再来对《原野》中的颜色,作出如下谱系归纳:
黑色系列:黑黑的两条铁轨、白磁箍上的黑线、黑云、黑坎肩、黑森森的密云、黑香案、乌黑的香炉、黑脸的菩萨、暗黑的墙、黑缎裤、黑缎袍、菩萨油亮的黑脸、黑林子、胸前黑茸茸的、黑布褂、森林黑幽幽、黑团团的树丛、黑色的肌肉、黑袍、乌黑的山峦、黑郁郁的树林。
红色系列:血湖似的云、幽暗的赭红的云、红红的灯火、红云、红色的绸帘、红拜垫、红棉托、暗红的旧式立柜、红绸袄、红丝线、血红的里子、红花、乌红柜、红灯笼、血红色的紧身、半裹了红布的手枪。
蓝色系列:蓝线带、蓝布褂、蓝布的裤、青蓝火焰的萤火虫。
白色系列:白磁箍。
灰色系列:灰布褂。
不难看出:整部《原野》主要被黑色和红色主宰。整部剧似乎在用一幅幅颜色艳丽、怪异的油画,向我们传达着神秘色彩。
“红色可以从绝对的否定生命(侵犯、杀戮、血债血还)到绝对的肯定生命(生命力、爱情、健康)。”[5]19-20黑色似乎从来就是不祥的代表,“黑色是否定生命的颜色,对所有的积极的事物的拒绝,对发展的无条件的否定。”[5]135“黑色首先是与长年重病、衰败和死亡同等意义的。”[5]136而除此之外,《原野》的所有矛盾冲突几乎被安排在“黑暗”中进行。《原野》共分为三幕,总的时间是秋天,序幕是立秋后一天傍晚,第一幕是下午六时,第二幕是夜九时夜十一时,第三幕是夜一时后、夜二时后、夜三时后、夜四时后、六时后。即使第一幕是下午六时,也终究是雾太大。人类对黑暗的恐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黑暗代表着未知和死亡,而无论是未知还是死亡,都充满了不可言喻的神秘。
曹禺在独特的文学观念下,借助现代的文学创作方法,给《原野》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下,剧作家仍然能潜心地沿着五四探究“人”的命题而“我行我素”,创作出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剧本,这是难能可贵的。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 傅光明.曹禺剧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
[3] 田本相.原野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4):122-141.
[4] 陆炜.《原野》中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原野》新释[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2):78-84.
[5] [德]哈拉尔德·布拉尔姆.色彩的魔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5-02-15
肖庆国(1992—),男,江苏盱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
A
1671-9824(2015)04-0081-03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