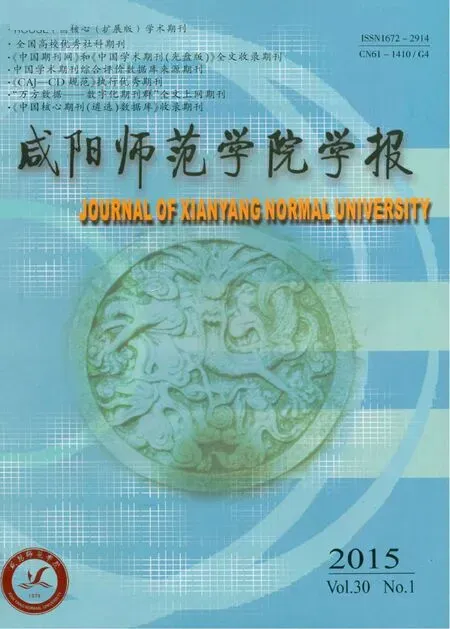“体自然”与玄言、山水诗的消长
张甲子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作家作品研究]
“体自然”与玄言、山水诗的消长
张甲子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尽管在时间上看,玄言诗、山水诗的出现及兴盛有先有后,实则两者内在的“自然”精神是一致的。玄言诗乃是用诗体的形式去体认自然,而山水诗则在描写山水景致中散怀自然。
体自然;玄言诗;山水诗
目前的文学史研究,在面对玄言、山水诗风交替变迁的文学现象时,仍多从诗运转关的角度来讨论,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为切入点,探究晋宋间诗风的沿革脉络,往往将焦点定位于玄言诗、山水诗两者的内容不同、诗风有异,以及它们的接续关系上。[1]247-261这种秉持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视角,对创作者的主观性,即两晋士人何以从玄言转向山水的精神需求关注不足。若从精神层面审视这一诗学转关,不难看出,其正是在“儒玄双修”的大背景下对“体自然”有意识的追寻,也是“自然”玄思成为了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后,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自觉延伸。[2]85-96当“自然”思潮移植到诗学中,一是触发了玄言诗,借助世间万物与玄理结合,阐释孕育其中的“自然”之道,诗体不过是外在的包装形式;二是率先认定了山水景物是“自然”的最佳代表,突出诗中的山水描写来表达玄意,独立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1 “任自然”“体自然”与两晋士风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针对两晋士人的诗风特点,予以过“礼玄双修”的精准论断,认为士人们在谈玄、理玄和体玄之时,从未彻底放弃过儒家思想,反而在某些合适的契机下,更是推动了礼学,乃至于经书经术之学的研究。[3]357-395所谓的“礼玄双修”,是“儒玄双修”在某些细节上的放大,对礼制、礼度的肯定,乃是对儒学的另一种守护,儒、玄从来都像双生花似的,面朝不同方向,但却不能舍此留彼、舍彼留此。而从士人的心理接受以及士风的普遍养成来看,“儒玄双修”就更耐人寻味,正因为儒、玄两者在人生观上的最高境界,同样都推崇“自然”,从西晋对玄风的有所抵触和“任自然”过度接受的两端,到东晋时依靠“体自然”说,将“儒玄双修”内化为士人的精神气质,“自然”成为了士人们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愉悦追求。
西晋的“儒玄双修”是士人被夹在生存与梦想中间,对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一方面,晋武帝以“名教”立国,尽管有其不尽的虚伪狡诈之处,但作为新立的封建王朝,尤其是还实行过古制的封国食邑的王朝,此时去维持国家政体之稳定,乃为首要之务。西晋位居高官的中朝名士,傅玄著《傅子》、杨泉著《物理论》、刘寔著《崇让论》等,根本是站在儒家经世治国的立场上,以仁义礼教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要务。另一方面,理论毕竟不是现实,往往是现实政局的残酷使得入世道路步履维艰,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山涛、张华等权臣,心灵也需要有个寄托地。“名教”与“自然”重要的不是在学术角度上的高下论辩,而是探索政治出处与人生理想中关键的一环。
不同的政局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心境,西晋士人更多选择了性好《庄》《老》,“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4]478他们的心态,一脉接近于《易》与《老》的结合,尚谦、柔、顺。位列竹林七贤的山涛,沉稳谦和、含蓄内涵是由内而发的。世人对其的评价,王戎论“山巨源如璞玉混金,人皆钦其宝,莫能知其器”,“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5]501又注引顾恺之《画赞》:“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5]500从儒学视角看,他是人伦典范,位至宰执且勤于政事,身名俱泰又不失性格中的清正平和。山涛的人生实践已然指明了“儒玄双修”道路的可行性,既能积极入世、行不违俗,又能以柔克刚、为而不恃。
另一脉偏向于尚《老》《庄》的结合,体现为旷达。《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嵇氏谱》中,嵇喜为嵇康作传言:“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还言其“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6]605又《晋书》本传有论:“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7]1370但嵇康依旧逃不开被迫害的命运。还有同与嵇康打铁的向秀、“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阮咸,[7]1362皆是真名士自风流。可以说,竹林名士的不遵名教,是不与世俗合污的介然不群,视功名利禄为浮云;竹林士人的个性不羁,是滤除虚伪礼法的行为斗争,视真情流露为真意,是内心的坦荡与淳致。
除此之外,有些士人走向极端,单纯为了保全自己而保全自己,完全丧失了儒者的正直精神,倒向了道家思想的消极面。如以王戎为首的元康放达派,既舍不得“名教”能带来的功名利禄,也放弃不掉“自然”带来的个人自由逍遥。他们不是真性情下所表露出来的放达,而是一味求“任”字名头下的放浪形骸。从清高逸旷走向庸俗没落的低谷,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荒淫放荡。《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注引王隐《晋书》云:“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5]29-30是硬生生要在恶俗之外贴上玄学的标签,“达”而要作,那么已不是“真达”,而是借“自然”为无限自由的代名词,所谓的“任自然”成了“士无特操”的挡箭牌。
士人这种混沌一团的精神状态,很快便被永嘉南渡惊醒,政局的震荡触发了学者的思考,当视角转向去寻找西晋覆亡的原因时,已走上歧路的玄学被推进了批评的角落。陶侃痛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7]1774孙盛从“道不可得”的角度出发,认为“按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骈拇咬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那么后人的崇有、贵无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8]各有所失,亦未为得;王坦之主张“自然”,但不能废“敦礼崇化”,“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7]1966还有士人在亲身经历中得到的教训。王衍言:“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先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7]1238总结出虚诞谈玄的不可取。应詹将“永嘉之弊”归于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7]1858;熊远指出“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不过是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的“俗吏[7]1887;戴逵则从“放达为非道”的角度出发,批评元康士人的“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7]2457说明西晋后期,将一代人才的实底都掏空了。干宝则在《晋纪总论》中言:“学者以庄老为宗首,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9]1368称玄风多半是浮薄虚幻、玄远涉冥、名理高深、不着边际的议论,以不婴事务的玄远为清高,丝毫不触及实际的问题,几乎对玄学在现实中折射出的各个方面均不认可,贬斥之意显而易见。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含义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士族精神文化的调整。如果说西晋士人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着去用“自然”来解脱自己,那么东晋士人则是要先得到“自然”解脱的基础,这是在“任自然”变成了消极恶果之后,东晋士人精神世界里出现的自我反省,于是方有了“体自然”的风尚。关于“体”的涵义,见王彪之《水赋》:“寂闲居以远咏,托上善以寄言……泉清恬以夷谈,体居有而用玄。浑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9]193庾阐《闲居赋》:“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静因虚来,孰测幽朗。”[9]388
“体”即要在闲居生活中去体验玄理。再如,顾恺之论“体虚穷玄”,[10]141戴逵论“道乖方内,体绝风尘”,[10]650这种“体于玄风”的意识,已然是时人共同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看来,无所不在的玄意,只有士人躬身实践,“体”之一方取自生活自然,“玄”之一方取自于老庄思想,寄意于形骸之外、游心于变化之端,方才能达到“浑万象以冥观”“忽即有而得玄”的境界。
王、谢、庾、桓等门阀士族子弟,逐渐褪去西晋士人身上的虚无放荡,转而追求调达的作风与恬静的情致,颇有曹魏尚通脱的余绪味道。但与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相比,东晋文人更追求精神的超越。如善于言谈,性好老庄的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是性情稳重、不妄举止之人,其弟庾冰也以“雅素垂风”为时人所赞;多将领之才的桓氏中,桓温“豪爽有风概”,桓冲“性俭素”;多文士之才的王氏中,王导“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王湛“冲素简淡,器量隤然”,王承清虚寡欲、无所修尚,他们从玄思中吸收了清虚简约的一面,使得高世旷达、幽然玄远变为士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体自然”思潮走向对于士风最大的影响,即在于真正地把“自然”作为高尚人格来推崇,使得士人不需要外在狂狷的行为、肆意的表现,精神的满足也不再站在社会礼教的对立面,把不婴世物、高洁自许看做是超然物外的潇洒风度,而是将“自然”放在人生境界的视角下讨论,把外在的礼乐修养、内在的自然性情相互结合起来,追求世间大化和个人精神的统一,是为缄默冲淡、顺应大道的“自然”。
2 体认自然与玄言诗的倾向
东晋文士重视“体自然”的精神特质,本应是有利于诗歌发展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玄言诗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从艺术表达,都算不上优质的诗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文学毕竟不是哲学,在文学中反思哲学问题是可行的,但以哲学主导文学,用抽象思维统摄形象思维,却缺乏对性情的反映,抽掉了诗歌的原动力,使诗歌的艺术色彩被消解。
第一,许多玄言诗人在写玄言诗时,未必是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自觉,如孙绰、许询等人,除玄言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诗歌的创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们是借用诗歌体式,沿着“微言剖纤毫”的思路,阐明演绎“玄言”“微言”“妙言”“清言”“虚言”中的玄义。孙绰《赠温峤诗》:“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11]897尽管玄学中普遍强调“言不尽意”,玄理很难通过“言”或者“象”表达出来,但认为存在着“微言”可以用之探求玄理,追求形上妙旨,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玄意。所谓的“盛道家之言”、“贵道家之言”,正是士人们的雅致情趣。
第二,“自然”命题本身蕴含的多重性质,在玄言诗的内容中也表露无遗,但孙绰、许询、庾阐、郗超等人的思想基点仍来于前人旧说。郗超《答傅郎诗》:“森森群像,妙归玄同。原始无滞,孰云质通。悟之斯朗,执焉则封。器乖吹万,理贯一空。”[11]887“妙归玄同”是因为顺应自然,“理贯一通”乃因依照大道,“始自践迹,遂登慧场”,将自己人生也融入到大化中,在万物齐轨中体验自然。这些有关“自然”的玄学理论并不复杂,但在结合实践的许多细节上,包括在玄、佛合流的过程中,玄言诗却能够点点深入,字里行间体现出被“任自然”观念浸润了的痕迹,试图在诗里解释“自然”究竟如何脱胎为对人生至高境界的追求。
“自然”让士人看透了生死。朝廷中不断的政治动乱,让这种对老庄“自然”的情节不断加深,愈加要在诗中倾吐心声。如刘琨在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时写《答卢谌诗一首并书》:“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11]850希冀“齐物”以跳出生死之界。卢谌的回赠诗更耐人寻味,《赠刘琨一首并书》:“因其自然,用安静退……是以仰帷先情,俯览今遇,感存念亡,触物眷恋。”[11]880以“自然”“安静”为要,劝导刘琨彻底看破兴亡。就像苻朗的《临终诗》:“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11]932即便性命存百年,也不觉得是有始有终,而是一切委运天化。带着这样的心理状态,玄言诗里表达的感情绝不会如水涌喷泉那么激烈,更应是静水深流、心若无尘的淡泊。
“自然”是士人在逃避尘俗时对自得、逍遥心境的追求。与玄言诗同时,还有部分游仙诗的主题与“自然”精神一脉相承,其中透露着“山路是我乐,世路非我欲”的意念。郭璞《游仙诗》:“青谿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飞泉。”[11]865他们想效仿隐居在山林里的道士,因为许多山林之物不仅“自然”,还能将人灵化、神化。庾阐《游仙诗》:“赤松游霞乘烟,封子炼骨凌仙。晨漱水玉心玄,故能灵化自然。”[11]875《观石鼓诗》:“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缘涧漱岩间。”[11]873赤松、晨溪、翠树、绿苔等,都是超凡脱俗的意象。不难看出,玄言诗在其中受到的影响,是涤除掉俗气,融合进了闲情雅致。
“自然”代表了士人对质性、品格的个性塑造。玄言诗中经常提到后稷、巢由、太公、叔夷、伯齐、张房、武侯等古人,还经常出现达人、至者、冲漠士、冲希子等称呼,如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至人远鉴,归之自然。”[11]483陶渊明《饮酒》:“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11]997康僧渊《又答张君祖诗》:“中有冲漠士,耽道玩妙均。”[11]1076他们认为这些人能参悟大道,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秉性自然,这种“自然”表现在遗物、遗情、抱真、耽道、纵目玄览等过程中。干宝《百志诗》:“壮士禀杰姿,气烈有自然。”[11]853“自然”是内在的气质;王胡之《答谢安诗》:“清往伊何,自然挺彻。易达外畅,聪鉴内察。”“妙感无假,率应自然,我虽异韵,及尔同玄。”[11]886孙绰《赠谢安诗》:“谈不离玄,心凭浮云。气齐皓然,仰咏道悔。俯膺俗教,天生而静。物诱则躁,全由抱朴。”[11]901谈及谢安的人品,皆以玄学的抽象性为主要特征;王胡之《赠庾翼诗》:“友以淡合,理随道泰。余与夫子,自然冥会。”[11]885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也能用“自然”概括之。玄言诗基本不涉及具体事物,跳出了形象的束缚,让人觉得是单刀直入的透彻,是不加掩饰的真实。
“自然”不单是玄学内的范畴,也与佛理、道教相互渗透。东晋时有不少释氏写有玄言诗,将其格义与佛教义理相融合,其中不乏佳作。如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八关斋诗三首》,直接以“玄”的境界去赞佛、颂佛,“祥祥令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11]1077道教与玄学可谓同出一源,仙道之人的言辞,更是容易与玄言诗水乳交融。羊权《萼绿华赠诗》、杨羲《云林与众真吟诗》《玄垄之游》《辛玄子赠诗》等诗作中都有“自然”之义,见支遁《咏怀诗》:“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11]1081葛洪《法婴玄灵之曲》:“妙畅自然乐,为此玄云歌。韶尽至韵存,真音辞无邪。”[11]1091虽然对“自然”义理没有进一步的阐释,但这足以证明“自然”义理的互通性质,也证明了玄言诗重理之所在。
以上由“自然”引出玄言诗诗意淡泊、诗风雅致、重抽象、重义理的四类特征,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可以说,“自然”的渗透,不仅让玄言诗中有了独树一帜的内容,也让玄言诗树立起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
其一,玄言诗展现出“清”的特色。卢谌《答魏子悌》:“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11]884陶渊明《赠羊长史诗》:“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疎。”[11]979孙绰《答许询诗》:“贻我新诗,韵灵旨清。”[11]899可见,“清”是诗人对艺术美的感性认识,还可以用来鉴赏及评判音乐,李充的《嘲友人诗》:“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11]856杨苕华《赠竺度诗》:“清音可娱耳。”[11]1089杨羲《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清唱无涯际。”[11]1106具体表现在诗中,一方面,诗歌语言的选择是“清言”“清话”“清文”“清趣”,大多选用素净寡淡,好像既无味、也无色的抽象词汇,暗合玄学哲学中的中和之质;另一方面,在意象的修饰上,如“清泉”“清风”“清帷”“清涧”“清岫”等俯仰可见,给人感觉既有澄澈明亮、流光溢彩的晶莹感,同时也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空灵感。
其二,玄言诗展现出“虚”的特色。玄言诗往往借用简单的意象,以游历赏景来品味妙谛,它们最显著的特点是虚合之象,也可称为“泛称意象”,[12]226即以自然现象和动植物为主体,加上相对的时间、地点、范围、状态等方面的修饰所组成的若干个小型意象,如山谷、水露、风云、草树、庭园等,在玄言诗中出现的概率非常高。它们带有想象及美化成分,这些景象未必是诗人亲眼所见,就像郗昙《兰亭诗》中说的那样,是“端坐兴远想,薄言游近郊”。[11]908诗人没有步入山林、走向田园,仅仅是端坐在斗室内,睡卧在几榻上,遥想神游、心在天地间。庾阐《三月三日诗》:“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悠想盻长川,轻澜渺如带。”[11]873王羲之《兰亭诗》:“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11]895这种诗要求作者以表现天地自然的气概来思索创作,于是拉开了与具体化社会的距离,也就有了深厚感、迷蒙感、淡泊感,耐人咀嚼和深思。
其三,玄言诗展现出“简”的特色。东晋玄言诗曾出现过四言诗的回流,四言的感染力、表现力并不强,可对于说理谈玄而言,并不需要多少衬字和形容词,也没有复杂的变化,反而让四言有了它的优势,那就是简朴质素,意到而言尽,意不止而言已,更突出了扼要、精练的“简”的特点。王胡之《答谢安诗》:“利交甘绝,仰违玄指。君子淡亲,湛若澄水。余与吾生,相忘隐机。泰不期显,在悴通否。”[11]886全诗没有任何繁复的字句,只用了三十六个字,就把两人间的君子之谊与相忘江湖的道理,如镜子般的透亮地折射出来。不仅如此,玄言诗的意象也是“简”的。如果说“虚”出自于士人对意象的想象,那么“简”则出于士人对意象的构造,也就是付诸笔下时的择取。玄言诗中的意象是一个为一个,极少有两句对仗写同一意象,其优点则是以神似写形似。最典型的数得上是郭璞的《幽思篇》:“林无静树,川无停流。”[11]867八字写出的山水风韵,丝毫不输给后世的山水诗。
3 散怀自然与山水诗的蜕变
山水诗能成为晋宋间文学创作的焦点,在表层看来有很多的干预因素,如外在生活环境的改变,门阀士族政治命运的变化,江南的山明水秀形成留连山水之风和隐逸遁世情怀等。①朱光潜认为,山水是在游仙寻道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山水诗乃游仙诗的继承者(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载《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林庚认为,山水诗是在南朝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水陆交通发达的条件下,才得以产生的(林庚《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曹道衡、袁行霈认为,山水诗导源于隐逸思想和隐逸生活(曹道衡《也谈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袁行霈《陶渊明研究·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钱志熙认为,晋宋之际玄言山水的诗运转关,主要原因在于门阀士族的政治命运的变化(钱志熙《论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山水诗艺术中的体现》,载《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若深入去挖掘,最根本的还是统摄于“自然”思想的映照。士人普遍拥有这种情节,主动在诗歌中大量写着山水,并不是简单的对旧有作品中的山水内容的渐次发展,而是在“自然”观念的启发下,把对自然的体认践行在山水中,又将这种观念入之于诗,成为诗歌创作的思维习惯。
诗歌中存在着对山水风景的观照,是从“与天地万物同一”的理路中引申出与山水同乐的态度,多为寻求仙境逍遥、希冀隐逸山林。张华《赠挚仲治诗》:“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流,恬淡养玄虚,沉精研圣猷。”[11]621对山水之间沉浸着的空无之道进行赞美,此诗用两句概括出景色特征,但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描写,和玄言诗颇为相类。但若去看张华的《杂诗》:“逍遥游春宫,容与缘池阿。白蘋齐素叶,朱草茂丹华。微风摇茝若,层波动芰荷。”[11]620已注意到了对外物景色细节的展现,对其澄明之美进行描绘。潘岳在任途中所做的《河阳县作》:“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归雁映兰畤,游鱼动圆波。”[11]633景物中没有寄托充沛情感,却寄托了宁静淡泊的理想状态。张协《杂诗》:“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寒花发黄采,秋草含绿滋。闲居玩万物,离群恋所思……至人不婴物,馀风足以时。”[11]745在视觉物象与自然之道中寻找交叉点,对自然意识的深化体现在对景物动态的抓取中。左思《杂诗》:“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11]735《招隐诗》:“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11]734白云皓月、清泉流水充满了美感与生机,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山水有清音”,是高踞在它们本体之上的自然之道。
逮至东晋,诗歌中比以往更多、更细致地表现山水,不仅引领其将精神融合于运化,还因为江南山水本身的秀色可餐和勃勃生机,让士人悠然其怀、乐在其中。孙绰在《太尉庾亮碑》中说,士人是“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9]647此处的“玄”除了意出“玄之又玄”外,更重要的是士人以“体玄”“体自然”之意去理解山水。王徽之《兰亭诗》也说:“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二奇。”[11]914玩味其中的虚幻灵动之美,山水是“质有而趣灵”的,士人目亦同应,心亦俱会,与山水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共振、心物交感。王羲之和之:“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1]895王玄之和之:“松竹挺严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11]911士人受到山水自然精神的触动,能体验到精神愉悦,静悟自然的运迈牵化,山水不期而然地扮作了逍遥散怀、陶冶性情的角色。
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晋宋间玄言诗和山水诗是接递而出的,但两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动因,诗风可以不尽相同,却不阻碍思想上的共鸣:一在于士人所尚“自然”之义,为求精神上的逍遥解脱;二在于崇尚山水中的“自然”,士人“体自然”悟到的玄理,多从其中而来。托之于诗体,前者是“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后者则是摆脱不掉玄言尾巴的山水诗,但两者是在同类思维方式的因袭下形成的从自然到山水、再从山水得自然,进入物我合一,展现士人内心情致的文学创作意识。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玄言诗、山水诗的相异之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两者间在表达方式上的承续、在描写手法上的革新。
其一,山水诗中的自然之景,已从“虚”逐步转向“实”。一种方式是将某些内容细节化,比较典型的是写山林、写池水,或者是描写更细微的月、荷、蟋蟀、寒蝉等,前者继续奠定山水诗的基础,后者则发展成了南朝的咏物诗。另一种方式是写真实的登山临水,反映诗人在某一时刻、在特定地点的亲眼所见。
先以临水为例,李颙《涉湖诗》:“圆径萦五百,眇目缅无睹。高天淼若岸,长津杂如缕。”[11]858因为有了“湖”作为对象,在缩小的诗人的视线同时,也让描写对象更加集中化。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11]944没有直接写南湖之水,但“白沙”“青松”都是围绕着它的,更能突出南湖的与众不同。再如,谢混《游西池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11]934谢瞻《游西池诗》:“惠风荡繁囿,白雪腾曾阿。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11]1134谢混是“始改玄风”的重要一环,在面对着同样的“西池”时,与刘宋时谢瞻较为成熟的山水诗相比,毫不逊色。
再以登山为例,庾阐《登楚山诗》:“拂驾升西岭,寓目临浚波。”[11]874《衡山诗》:“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11]874就全诗来看,两者都是八句,也都是只有一联写到山景。只有将这一联的内容不断扩大化,方才能从玄言诗逐渐转变为山水诗。庐山曾是玄学名士与佛教高僧共游之地,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等人创作了许多的“游庐山诗”。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11]1086整段的序文交代了参与者,赏玩的时间、地点,以及详细的经过,基本上可以视为简单的山水游记。虽然此首诗中没有相关的内容,仍旧是单调的玄言诗,但这种对“实景”的体悟,马上要蔓延到诗歌的创作意识中。慧远《庐山东林杂诗》:“崇岩吐清气,幽岫棲神迹。”[11]1085王乔之《奉和慧远游庐山诗》:“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11]938大概就是如此。宗炳的《登半石山诗》:“清晨陟阻崖,气志洞萧洒。嶰谷崩地幽,穷石淩天委。长松列竦肃,万树巉岩诡。上施神农萝,下凝尧时髓。”[11]1137这种以诗作叙写实际登山活动的演变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其二,山水诗中的自然之景,已从“简”渐渐转向“繁”。如果说从“虚”转“实”是从表达内容的角度入手,那么,从“简”转“繁”则是从表现手法的角度入手。东晋、刘宋后渐起的山水诗创作潮流,如湛方生、支遁、慧远、谢混等人的诗歌,乃是以实景山水为描写对象,在表现“自然”的基础之上,诗人在摸索中使表现技巧、艺术手法等更加得力,如具有了全景描绘的意识,“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对山水意象的工笔修饰词愈加的巧妙,“巧构形似之言”;诗句中对仗的增强、偶句的应用、注重譬喻及炼字,使“声色大开”。正是这些因素,在不算长的文学史时间内突发了质变,于不久之后的谢灵运诗中,得到集大成式的展现,相关的理论也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得以系统的总结,奠定了此后山水诗艺术的基调。
[1]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陈道贵.东晋诗歌论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许逸民.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释道宣.广弘明集[M].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9]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Experience of Nature”with Growth and Decline of Metaphysical Poetry and Landscape Poetry
ZHANG Jiazi
(College of LiberalArts,Shangqiu Normal College,Shangqiu 476000,Henan,China)
Althoug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the metaphysical poetry and landscape poetry had appearance as well as prosperity before the other,in fact,the inherent spirit of“nature”in these is basically consistent.The metaphysical poetry had philosophically interpreted“nature”,that used the form of poetry,and the landscape poetry had realized“nature”with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scene.
experience of nature;metaphysical poetry;landscape poetry
I207.22
A
1672-2914(2015)01-093-06
2014-11-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W05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qn-640)。
张甲子(1984-),女,辽宁葫芦岛市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汉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