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修建钱塘江大桥 为开路之人开路
文 / 本刊记者 陈楠枰
抗日烽火中修建钱塘江大桥 为开路之人开路
文 / 本刊记者 陈楠枰
开栏的话:
1942年1月,长沙会战开始。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在岳麓山阵地用炮火压制敌人,弹药穷尽于炮战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第九战区司令官长官部急电重庆,要求运输弹药,可司令部的回答却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战略通道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把战略投送力量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才能适应作战空间拓展的需要。而交通运输具有生命线作用,建立完备的战场交通设施,方能保障作战力量的有效运用,具备有效的战场保通能力,才能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
在浴血奋战的勇士背后,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上,一支特殊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力量,凭借着智慧和对祖国的热爱,用“无形之枪”开辟着中国抗战的敌后交通战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为开路之人开路。


时光之镜映射着历史的痕迹。78年前,钱塘江大桥第一次横亘于冰凉的江水中,置身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时的建造难度几乎是空前的。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更在战争烽火中,中国先进爱国知识分子用智慧和责任创造出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巨大能量。
有人说,这里印证了工人阶级的辉煌。我们可以由它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一段社会经济发展史,一幕曾遭受凌辱和侵略的悲剧,一部不屈的民族浴血奋战纪实,一曲工人阶级发愤图强的凯歌……
也常有人说,钱塘江大桥配得上所有的礼赞与致敬。
有路,就有希望
1934年,刚刚获得美国卡内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的茅以升被推荐为钱塘江大桥总指挥。
一年前,正在北洋大学教书的茅以升忽然接到杭州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打来的电报和信函。这个被称为“中国铁路巨擘”的唐山路矿学堂老同学在铁路界是个“腕儿”,邀茅以升立即前往杭州共商筹建钱塘江大桥之事。
没几天,被誉为“浙江公路奠基人”的浙江公路局局长、茅以升的留美同学陈体诚亦致信他,来信中鼓动道:“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钱塘江上建桥,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却从未有人敢将想像落实到行动。这个天方夜谭痴人说梦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且“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潮头壁立,咆哮而来,威力之猛足能把堤岸上1500公斤重的镇海铁牛冲到10米开外。
历史档案记载,1929年,江南药王胡雪岩于杭州三廊庙边“浙江第一码头”——“义渡码头”,日送旅客多达11000人次,全年高达4000万人次,年货物运送40万吨,甚至汽车都经此轮渡。
钱塘江上架桥有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国列强视中国为盘中餐,为抢掠中华财富后有畅达的通道,强盗们死死地把持住中国铁路桥梁的建造权。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接信后的茅以升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与时任民国政府铁道部副部长、浙江建设厅厅长的曾养甫进行商谈,并经过多次勘察及听取多方意见,写就《钱塘江桥设计书》。
茅以升经反复勘测后涤荡谰言:“在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与时任铁道部顾问的美国人华德尔所出具的造价758万银元的人行道、公路、铁路三种路面并行单层联合型桥梁相比,茅以升设计的大桥是公路、人行道与铁路分为上下的双层联合型,造价510万银元,孰优孰劣根本不用说。
曾养甫“半蒙半骗”地为大桥拉来了好几家“赞助商”,挺直腰杆对外宣布:大桥完全由我们国人自行设计。
1934年4月,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与如今由当地行政一把手挂帅特大项目不同,曾养甫给予茅以升极大自主权。茅以升的工程团队全部来自技术和施工一线,没有一位地方官员挂职,最大限度规避了政府腐败给工程带来的影响。

“一壶水能把泥土冲出个洞,那么能不能把江水提起,从高处猛冲下去,把江底冲出个洞穴呢?”
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开工仪式举行,“钱塘江大桥修不好,出了问题,第一个要跳钱塘江的,是你;第二个,是我。”建桥之初,总工程师罗英对工程总指挥茅以升放了这句狠话。
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国东北地区,并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虎视眈眈,妄图亡我中华。
“八十一难取真经”,众志成城奇迹生
与桥梁开建随之而来的,是一堆乱麻。交通船倾覆60多人死亡;沉桩困难,对地质因素估计不足;钢板桩围堰因水流急,宜受冲刷失败;沉箱多次走锚……
钱塘江上造桥,难度与唐僧取经不相上下,甚至更大。茅以升常拿母亲的教诲勉励自己和团队,“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要经历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如意金箍棒,一样能度过难关。”
“当初我父亲建造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时很艰苦,没有工艺、没有设备、没有经验,天上还有日本人的飞机。”茅以升之女茅玉麟说。即使这样,工人们为大桥建设所提出的“创造性意见和办法还是举不胜举”。
因缺乏详实的钱塘江水文资料,工程接二连三遭遇各种困难。曾养甫甚至一度急得要与茅以升一起“跳江”。直到一个名为来者佛的年轻人在《浙江新闻》报上发表七期连载文章《钱江水势与钱江大桥关系》。
原来,生长于钱塘江边爱看潮水的私塾先生来者佛也去大桥开工奠基现场凑了热闹。在其子来光明所保留的《钱江水势与钱江大桥关系》手稿中,记者看到,来者佛于文中记录下了发表文章的缘由。他看到“来宾中名人钜公,各有演说,但多以桥工落成,交通便利及各业发展为演讲之中心要点,而江水之奔腾,山水之涌注,对于江岸如何卫护等,并为道及片语……”
而“近日以来,钱江水势与昔大异,桥工委员对于泛滥预防之记载文字,则尚未有一见。”这位“潮痴”注意到,“四月六日,杭市青年会请茅以升博士演讲钱江铁桥,对于钱江水势亦未略及,虽水势与工程,问题各殊,但其连紧性颇为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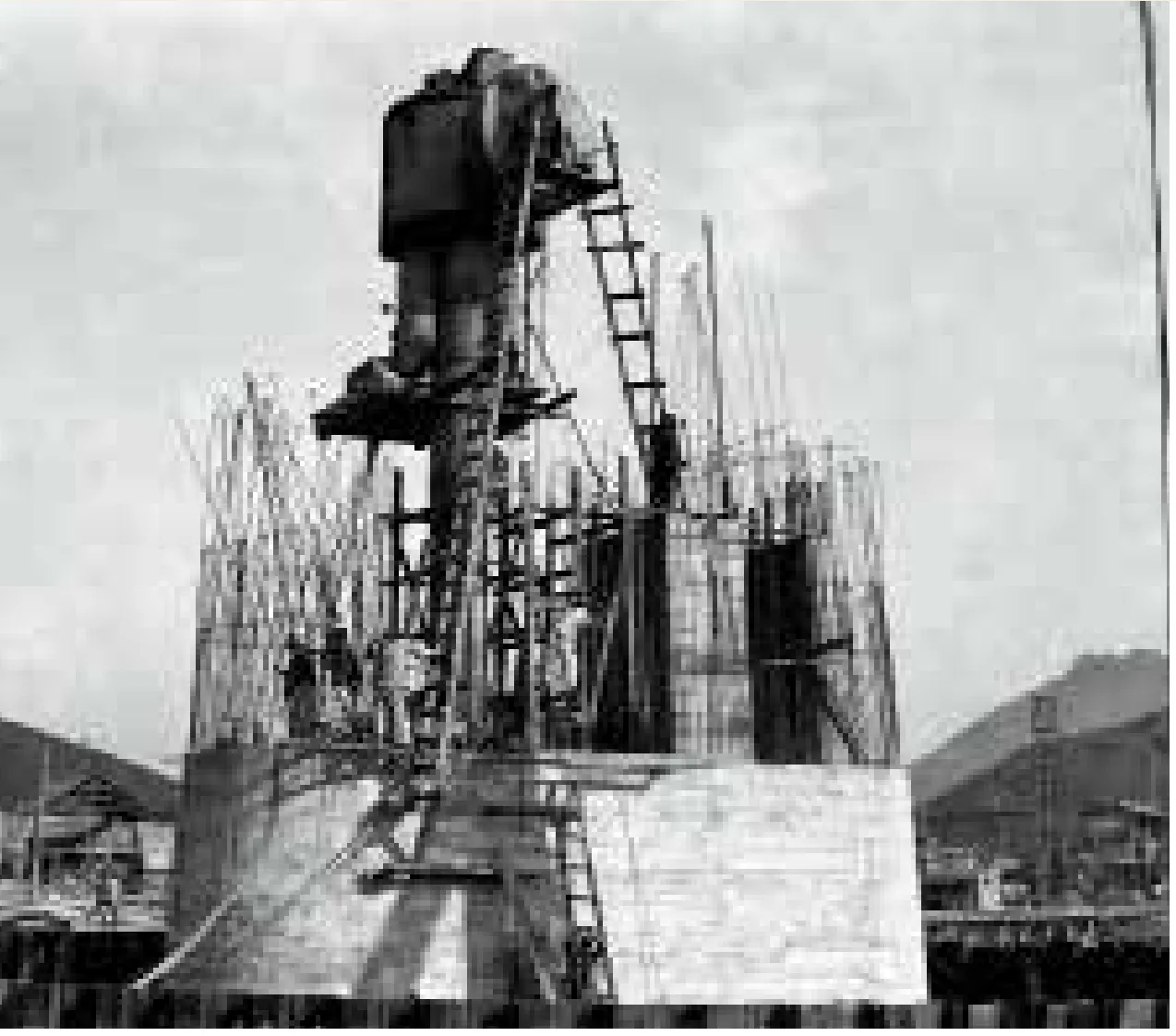
来者佛深觉“若竟含隐不言,殊恐有碍将来。”文章分引言、钱江水系源流、今昔江流地带、江沙淤积原因、冲刷程度我见、桥墩阻流力量和补救方案陈述等七方面详尽阐述,为建桥人进一步了解江水活动规律和江面施工提供了有利参考。
传说“钱塘江无底”。细微而飘摇不定的细沙常年被江水冲刷,木桩打下站不牢,甚至越打越下陷。气锤打松了,木桩下不去,打重了,却又容易折断。160根木桩如何站稳脚跟?桥梁精英们抓耳挠腮时,茅以升之女茅于燕的一个小报告给了愁眉苦脸的父亲灵感。
茅于燕告诉父亲,“一壶水能把泥土冲出个洞,那么能不能把江水提起,从高处猛冲下去,把江底冲出个洞穴呢?”
射水法由此而生。果真,施工人员一昼夜就打进去了30根木桩。
“沉箱是建桥的重要基础,沉箱站不住桥墩就无法浇筑。”如何将做好的600吨沉箱运到指定地点,成为让工程师们头痛的问题。
其中,“不幸”的3号沉箱更是经历千难万险才运到指定位置。在钱塘江大桥建桥工程师李文骥之女李希的记忆中,父亲回到家后曾告诉母亲,“这只沉箱来回乱窜折腾了六月之久才安顿下来。”

沉箱不稳的问题解决不了,工程进度就会被推迟。一位工人提出,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的混凝土锚,乘海水涨潮时把沉箱放下水,待落潮时赶紧让它就位。经过一试,难题终于迎刃而解。
茅以升在1963年所著的《钱塘江建桥回忆》中专门写了《工人伟绩》一章:
工人们的劳动确实是伟大的。桥工不比一般建筑工程,不但是在水上、水下工作,处处都有危险,而且全部都是露天进行的,不管风霜雨雪,都得工作……
钱塘江桥的工人们发挥了集体智慧、集体力量,胼手胝足,战胜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个所谓不可能的“钱塘江造桥”工程。
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
“七·七”事变后,日寇将战火蔓延到钱塘江,大桥自此沾上了“火”。8月13日,上海爆发淞沪战役。
翌日,茅以升与罗英在水下30米深的6号桥墩沉箱室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攻关。高温和三倍正常人的大气压下,工人们正在用锄头把污泥清除掉。
突然,电灯断电,箱内一片漆黑,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如果没有高压空气,水就会涌入沉箱,威胁几十人的生命。直到两分钟后水没进箱,众人才略感踏实。
半个小时后,电灯终于再次亮起。一位工人顺着梯子爬下来大声地说:“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干吧!”和这名工人一起爬回地面的茅以升上来后才发现,四周空无一人,工地上亦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机器的轰鸣。
8月15日的上海《申报》登出一条惊悚的消息:“日军于14日下午3时许,从台湾派重轰炸机11架飞至杭州投弹……”那天,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上空,第一次落下了震悸人心的钢铁炸弹。
当被问及三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大桥时,“为什么不躲躲?”朴实的工人回答:“我是管闸门的,沉箱里有那么多人在干活,我怎么能离开?”茅以升回忆:“没有这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安全,我们早就葬身江底了。”
战火中,茅以升率领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工程技术人员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出无比的冲天干劲加速赶工。他们说,一定要把桥完成,支持上海的抗战。
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随着一声火车长鸣,大桥通车,民众涌向大桥两岸,为在苦难和战火中诞生的民族钢铁桥梁而欢呼。
为了让大桥免遭敌机轰炸,公路没向行人和汽车开放,并在公路上堆放了许多杂物,从空中俯视,好像大桥尚未完工,以迷惑敌人。
当被问及三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大桥时,“为什么不躲躲?”朴实的工人回答:“我是管闸门的,沉箱里有那么多人在干活,我怎么能离开?”茅以升回忆:“没有这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安全,我们早就葬身江底了。”
据记载,大桥竣工当年,日军的骑兵已经出现在钱塘江大桥北岸。竣工后的89天里,桥上一直拥挤着从杭州撤退下来的士兵、物资车辆,还有大批难民,多达百万人。有人统计,在这89天里,经大桥运送的抗战军用物资、民生物资就可再建5座钱塘江大桥。而仅12月22日这一天,过桥撤退的火车有300多辆,客货车2000多辆。
但令无数人震惊的是,殚精竭智千日功,通车之日却炸桥。
同年11月13日,上海《时报》发布头条消息:“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中,艰苦抗御至前晚11时,终以工事被毁,无坚可凭,乃奉令撤退,我大上海完全陷入敌手……”上海沦陷。
11月16日,南京工兵学校一位教官将一份“绝密”文件面呈茅以升。文件称,为防日军南渡,命令即日炸桥。
尽管这座大桥所面临的命运茅以升早有预感,却没想到来的如此快。“七七事变”之后,茅以升在14号(南岸第2个)桥墩预留了一个方形大洞,作为必要将桥炸毁时预留的炸药孔。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他并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
炸药孔的浇筑和引爆工作交给了来者佛。17日清晨,经过一个通宵的努力,埋放炸药工作全部完毕。接线工作时,火车照常放行,但预先通知,由今日起,不许在过桥期间加添煤火,更严禁落下火块,“并说明军事秘密,不得泄露。”为更多百姓顺利逃难,大桥公路开放通行。
12月23日午后1点,炸桥命令传达,100根引线被接到爆炸器上。5时许,隐约听到敌骑来到桥头,才断然禁止行人,茅以升一声令下,轰然巨响中,14号桥墩上部完全炸毁,5孔钢梁一头坠落江中,“敌人是无法利用大桥了,要想修理,也非短期内能办到。”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茅以升说了这句话。曾经参加过港珠澳大桥、杭州湾大桥建设的桥梁建筑专家冯永明说,很多人将这句话理解为悲壮,但现在来解读,这更是一种对桥梁本身生命力和质量的自信。
涅槃,重生
战争年代中,五行无“火”的钱塘江桥“火”事频频。当年建桥时只用了924天,可后来断断续续的修桥却用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9月,钱塘江大桥才算全面修复。
当年的“潮痴”来者佛有一阵子成了手持《良民证》的“良民”。那是日军占领大桥,杭州沦陷,桥工处集体南撤到金华的一个月后,来者佛带着6岁大的大儿子来兆民回到杭州,在靠近大桥的黄沙虞村办起私塾。
原来,来者佛受茅以升秘托,利用当地人身份作掩护,暗中保护大桥剩余物资,密切关注日军修桥动态。来兆民回忆,父亲曾将所得一手资料写成《敌伪对本桥之动态》,秘密转送到大后方手中。
为了让已经转移的茅以升能够更好了解大桥现状,来者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一个晴好天气绘制出一张《毁桥图》,为避开日寇严密的信件检查,用黑点替代大桥,寄给远在四川的茅以升。

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图为茅以升在纪年碑前
吴照林是唯一一名自解放前护桥而至今健在的护桥工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吴照林说:“我这辈子没什么故事可说,除了修桥。”1948年,十几岁的他作为小木匠被编入维修钱塘江大桥的队伍中,此后,他所有的人生故事,都在大桥中跌宕起伏……
吴照林说,虽然是解放前建的桥,但这个桥载荷和安全范围的提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点点增加起来的。比如,脚钉、窝钉都是用钢丝围起来,再用最好的水泥浇注。
据他介绍,1948年,他开始参加修桥,那时火车时速只有5公里。此后,每年都会提高通过速度,到了1958年,铁路通车时速达到80公里。“当时我们是按照你能跑多快,我就能保证你跑多快的速度载荷修建的。”
“现在没有哪一座大桥在建成后,建筑工人还会为大桥质量守一辈子,所以,钱塘江大桥才这么结实。”冯永明如此评价。
“这是一座炸药不放对位置都炸不掉的桥,各项数据都在不断突破设计极限。” 来海刚承担大桥的维护保养工作已经近27年,他的父亲、爷爷也都曾是大桥的养护工。
当然,岁月在铸就大桥荣耀的同时,也在不可逆转地催其老去。2008年,杭州工务段总工程师刘芳曾带领团队对钱塘江大桥做了一次动静态检测,结果显示:目前桥梁还可以继续运营,但也必须考虑到如今钱塘江大桥已处“高龄”,部分杆件锈蚀严重,应尽可能予以更换。
刘芳表示:“这就好比人的身体,如果整个身体都已老化,把整个身体的部件都更换一遍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进行实时监控,保证随时了解它的健康状况。”
上海铁路局杭州工务段钱塘江大桥车间里,就常年有30多名养护工负责养护大桥。据来海刚介绍,2012年初,大桥安装了实时响应安全评估监测系统,以利大家快速了解大桥的“健康指数”,及时调配火车通行总量、速度等。
令大桥车间主任何光明骄傲的是,他们工务段车间有这个“巨人”身上20多万颗螺丝钉每一个钉子的健康档案,俗称台账。每天通车高峰过后,30多名养护工就来到桥面上,用锤子敲敲打打,看看水分,看看冲刷情况,看看有没有腐蚀。除了这30多人的护桥队,还有管电力、铁轨、路面的五六个小组,一起维护这个大桥,不下上百人。“比保养私家车都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