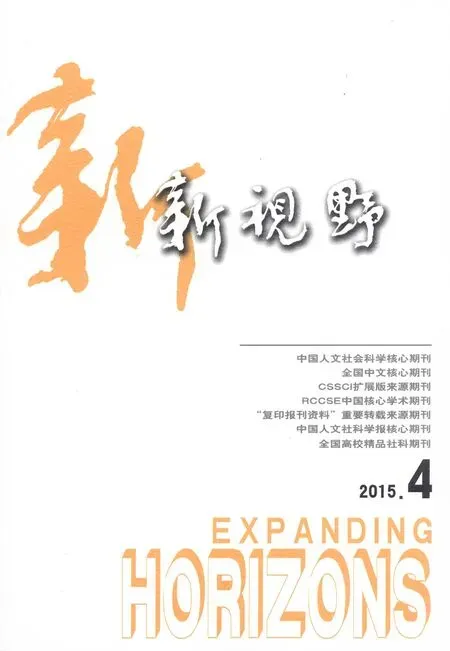中国外交“新常态”新在哪里?
特邀主持人: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外交“新常态”新在哪里?
文/董向荣许亮
特邀主持人: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稳步发展,目前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那种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朝着大力参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方向改变。考虑到中国的体量规模、发展速度、历史积淀、文化品格、政治特性和社会现状,上述新的态势在带动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重大改观的同时,也必然推动包括外交转型在内的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探讨全球变革和中国外交转型。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对“新常态”下中国外交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引起读者关注和争鸣。
摘要:近年来,中国外交出现了诸多新迹象:定位上,彰显自信的大国姿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理念上,积极主动,奋发有为;机制上,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外交的顶层设计、决策与协调;布局上,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把中亚和东南亚作为优先方向,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上,更加亲民,注重与世界相通。这些新迹象逐步成为“新常态”,将影响未来中长期内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关键词:中国外交;新常态;“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稳定而言,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可谓不巨大,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国际秩序。基于此,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动调整已经开始,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从定位、理念、机制、布局、话语体系等方面重塑中国外交。
一 外交定位:大国定位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定位是定义自己,是定义己与他的相对关系,定位变了,全局则变。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首先源于对自身的新认识、新定位。与以往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同,中国政府新的提法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等等,[1]在深刻认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的前提下,突出自身的大国定位。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理应在外交中展现大国形象。
中国的自身定位,不仅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自信的大国”。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在经济影响力之外,政治的、文化的软实力明显增强,展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在外交舞台上,还有一个自信,即领导人的自信。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所言,习近平正在告诉世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great power)并将开始扮演大国角色。[2]
与对自身的新定位相联系,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新型大国关系是处理包括美、俄、欧、日等所有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但从其来历、发展和具体影响来看,在处理对美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美国前夕表示:“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欢迎美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我们也希望美国充分尊重和容纳亚太国家的主要利益和合理关切。”[3]此后,关于“太平洋”的描述成为中美外交领域流行语。“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2013年,习近平再度会晤奥巴马,对中国所理解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主要特征,希冀稳定成熟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一直以来,美国掌握着定义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克林顿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建设中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小布什上台初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到其第二任期,美国称中国为“利害攸关方”,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奥巴马曾将中国视为“非敌非友”,中美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美国放弃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那样的简单判断,代之以比较复杂的、两面的形象描述。比如,1993年江泽民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分析中美关系:“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美国对华政策历来具有两面性。本质上,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我国合作。”[4]21世纪开篇,中国没有对美国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只是把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作为对美外交的目标。受制于两国实力差距,中国只能对美国的角色分配做出被动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局面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中国正尝试掌握中美关系的定义权。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清晰的一面就是我们不要旧有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的、对抗的大国关系;模糊的一面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新型”关系还不是很明确,“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说的是一种期待,还不是明确的定义和战略。阎学通教授指出,未来十年,仍将是中美密切互动与合作的十年, “两极化趋势将在2023年之前定型为两极格局”。[5]
外界评论,中国的崛起完全是在不被美国价值认可的模式下发生的,这对美国的软实力是个严重挑战。美国方面的不适应、质疑之声频现。[6]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野心与不确定性: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为题目展开热点讨论,[7]表现出对中国新变化的敏感和对中国未来的迷茫。近两年来,美国仍然在用旧眼光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的影响力,出现了明显的误判和应对不力。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问题上,美国始料未及,尽管对盟国施压,依然无法挡住他们参与中国主导的新机构的脚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坦言,美国在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上“搞砸了”,“我想我们失算了,没想到其他国家也想加入中国的倡议”。[8]
二 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中国长期奉行“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基本方针,其基础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的两个判断:第一,关于战争的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第二,关于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对策是:第一,“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战争我们并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第二,“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9]此后20年,“韬光养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理念。
今天,邓小平关于外部世界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是客观的,关于战争问题、关于政治稳定问题的基本判断,仍是中国外交政策之本。差异在于,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此之外,至少有两个因素直接促成了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第一是周边安全局势的挑战。比如,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动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蓄意生事,使得中国过去奉行的“搁置争议”政策饱受质疑,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政府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外界则将中国的维权行为视为中国外交告别“韬光养晦”的标志。2010年,一位韩国媒体人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外交界正在出现分化。还是有不少人支持原来的韬光养晦,可是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变化,因为现在的情况跟原来不一样。中国已经是G2之一了。”[10]第二是中国利益遍布全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直接投资遍及世界各地,且主要分布在一些安全环境堪忧的亚非拉地区。海外政局动荡、战争、突发事件等成为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重大威胁。2011年利比亚发生危机后,中国动用各种外交资源,紧急撤侨35860人。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超过1.14亿人次。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由安排领导人互访,迅速变成了海外利益维护和领事保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还只是近十年来的新事物,但是这个新事物成长如此迅速,对外交转型的需求如此强烈,足以对原有的外交布局形成挑战。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和政策界开始不得不重新思考“韬光养晦”的外交理念。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学者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通篇没有提到“韬光养晦”,并引申认为,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外交为经济服务论等思维定势都面临着转型,“讲话是对‘二十八字方针’的超越,预示着中国外交全面转型的开始。这些思维定势赖以存在的政策基础将逐渐消失,因此,它们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1]阎学通教授曾明确表示,中国外交正发生着方向性的根本变化,“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12]国外有不少学者的解读亦如此。比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撰文指出,习近平在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表明,中国正加速远离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13]
三 外交领导决策新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安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机制创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在中国外交工作中扮演决策和指挥角色。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撤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中央外办作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中央外办同时作为其常设办事机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其职责主要是协调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涉外工作,就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制定相关政策,并向中央做出决策建议。[14]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往,中国也曾经尝试建立类似的机构,但是未能建成,原因一是紧迫性不够,二是执行力不强。从紧迫性来讲,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从执行力上讲,新政府上台之后在反腐败等问题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执行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基于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而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为应对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集中高层权力,统筹协调指挥相关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顺利设立和开展工作,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强大的执行力。从定性上来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安全政策的顶层设计问题,将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新政府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表述来看,新安全观的提法采用的是罗列法,力求比较全面地展示影响国家安全的诸多层面,力求从更宏观、更全局、更战略的角度来阐释新政府的安全构想。同时,新安全观寻求在战略推进中寻求平衡,对于国内安全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诸多需要协调、权衡的方面都加以强调。
四 外交布局调整:“一带一路”新蓝图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稳定的周边是中国的战略依托。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随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就周边外交工作召开如此高级别的会议,并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国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逐步得到彰显,发挥世界性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议题设定能力和世界影响力。这一倡议提出后,立即引发各界持续关注,不仅成为国内热点,也成为世界性的议题。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一带一路”涉及面广,包含欧、亚、非等主要大陆,涉及国家60余个,人口超过世界的半数。第二,中国作为倡导方,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建、共赢,自身也具备了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实力。第三,“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基础设施领域内的互联互通,而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的特点,拓展全方位的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倡导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涉及的区域内,原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信会议(CICA)等。历史地看,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还对除联合国外的多边机制比较谨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多边机制,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东盟—中日韩(10+3)机制等。进入新世纪,中国开始根据自己需要创建新的多边机制,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在多边舞台上,中国还从未像现在一样多方位地参与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内新的构想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发展,参与构建、主导一些多边机制。“一带一路”的提法整合了原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等,更具有战略性、协调性,使得中国西向和南向外交上呈现新布局、新轮廓。
即便是在原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之内,中国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在APEC,中国也从一个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从入局开始,转变为一个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向着主导者的方向迈进。如今,任何一个大的国际制度安排,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它只能算是半壁而立,中国大可以从容一点,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当今的APEC中,中国的作用显而易见。外交部长王毅在蓝厅论坛中表示,2014年APEC经济体提出了超过100多项合作倡议,其中中国方面提出的超过一半。中国如此大范围地参与APEC的议题设定,姿态之积极、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
如果说金砖国家银行是中国尝试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第一次试水,那么亚投行就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内的扬帆远航。截止到2015年4 月15日,有57个域内外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国充分发挥了自己外汇储备充裕、经济发展强劲、制造业发达等各方面的优势,牢牢掌握亚洲经济发展的需求变化,推出了金融领域内新的机制安排,有效地吸引诸多国家,包括英、法、德、韩等美国盟国的参与。这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制衡,也是中国发挥议题设置能力和游戏规则制定能力的体现。习近平在蒙古、在拉美等多个场合,都曾提到“独行快、众行远”,从各国对亚投行的反应可以看出,世界上想与中国结伴同行、合作共赢的国家为数不少,可能超出了美国人的意料,也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期。中国还需要对自己的影响力有更深刻的认识,做到有责任,有担当。
五 新的外交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令人耳目一新。习近平在阐释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惯于用朴实的语言、用外国人能听得懂的语言,用接地气、富于亲和力的语言,与世界进行沟通。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有国际视野,刚柔相济,传播效果明显。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习近平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的话语结合起来,比如他多次阐述中国的“和”文化,以此来破解西方的思维定势。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习近平外交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刚柔相济。针对日本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做法,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在同日本的外交交锋中,中国将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升到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高度,占据道义制高点,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时,很注意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话来表达。比如,西方对中国崛起担心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霸权。对此,习近平在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时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15]“中国梦”也是易懂的概念。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将中国的战略意图以美国人和外部世界所熟悉的方式表达出来,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早在2013年,韩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赵英男就敏锐地抓住这一关键词,以此来阐释他所理解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新动向。赵英男认为,“中国梦”的核心是“强国梦”,鸦片战争后掀起的洋务运动、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都属于“强国梦”的一环,倡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将中国式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的概念。[16]
结 语
在外交战略中,定位牵一发而动全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展现出一些新特点,关键在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新政府对自身的定位。虽然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正视人均收入还很低、国家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现实约束,但是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已经树立起与“联合国‘五常’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等影响力相匹配的大国外交理念,彰显大国姿态,扩大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与定位的变化相联系,在外交理念上,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国际国内认为中国正在走出“韬光养晦”战略的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传统的外交为内政服务的观念正在改变,逐步被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理念所取代,国际国内的边界正在逐步打破。从决策机制上看,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突出外交的顶层设计、决策与协调,给中国外交注入新的动力。在外交布局上,中国新一届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重点,把中亚和东南亚作为优先方向,由近及远推进周边外交,凸显议题设定和游戏规则制定的能力。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部署,“一带一路”构想进入实施阶段,亚投行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在外交话语体系上,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更加亲民,更加坦诚,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语与世界沟通。概言之,这些新迹象逐步成为“新常态”,将影响未来中长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注释:
[1]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人民论坛》2013年第22期。
[2]Christopher K.Johnson, “Xi Jinping Unveils his Foreign Policy Vision: Peace through Strength”,Nov.13,2014,http://csis.org/publication/ thoughts-chairman-xi-jinping-unveils-his-foreignpolicy-vision.Apr.14,2015.
[3]Keith Richburg,Xi Jinping stirs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ahead of trip to U.S.,The Washington Post,Feb.13,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blogs/worldviews/post/xi-jinpings-commentsstir-nationalist-sentiments-on-chinese-twitter-aheadof-trip-to-us/2012/02/13/gIQADPunAR_blog. html,Apr.21,2015.
[4]《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5]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6]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enry Holt and Co.,February, 2015;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26,Number 1, January 2015, pp.156-170.
[7]“Ambition and Uncertainty: China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Dec.18,2014,http:// csis.org/event/schieffer-series-ambition-anduncertainty-china-age-xi-jinping,Apr.14,2015.
[8]“US ‘Miscalculated’ on AIIB: Albright”,Apr.1,2015,http://www.chinadaily.com.cn/ kindle/2015-04/01/content_19972502.htm,Apr.21,2015.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321页。
[10]董向荣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9-160页。
[11]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
[12]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2013年11月25日,http://www.gmw.cn/sixiang/2013-11/25/ content_9596404.htm,2015年4月21日。
[13]Christopher K.“Johnson, Xi Jinping Unveils his Foreign Policy Vision: Peace through Strength”,Nov.13,2014,http://csis.org/ publication/thoughts-chairman-xi-jinping-unveilshis-foreign-policy-vision,Apr.14,2015.
[14]宫力等:《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11期。
[15]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16]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的领导力和中国的未来》,首尔:民音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俞景华
作者简介: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市,100007;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市,100006。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4-0030-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