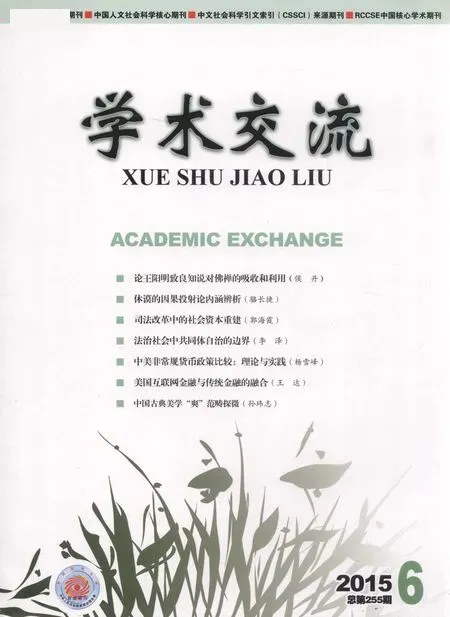町人伦理及其对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的影响
刘 韬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哈尔滨 150030)
町人伦理及其对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的影响
刘 韬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哈尔滨 150030)
町人是日本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化过程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基于独特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模式,其伦理思想与传统的儒教思想也不尽相同。作为近代日本企业家群体的主要来源,町人及其伦理规范对日本管理哲学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町人伦理的发展历程及思想特质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现代日本管理哲学。
日本;町人伦理;管理哲学
武士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群体,在作为时代分水岭的明治维新中,下级武士是主导变革的核心力量。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重建,这一群体亦是中流砥柱,因此有人认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角,而是以下级武士为主角”[1]21。在明治维新波光变幻的舞台上,最为闪耀的是高杉晋作、坂本龙马以及“明治三杰”这些新兴武士的杰出代表。与他们相比,本应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角的日本商人阶层则黯淡了许多。但是在日本经济近代化以及日本本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过程中,新兴的商人和资本家阶层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江户时代开始,作为商人前身的町人阶层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日本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使町人具备了和其他阶层平起平坐的资格;更为重要的是,町人建立了完整而实用的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为近代以来日本企业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即使在企业管理水平高度发达的当代,町人伦理依然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因此,通过对于町人伦理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日本企业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从而能够在更深刻的思维层次研究日本管理哲学。
一、町人的产生与町人根性
町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生活在町里的人。“町”(まち)在日本语里是街道、城镇的意思,在平安时代町是京都内部的区域划分单位,到镰仓时期,由于集市的衰落,商人开始在街道上的町屋里进行买卖,成为所谓的“坐商”,町人的说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町人就是居住在町的工商业者,狭义来说,町人就是指居住在町的商人。”[2]74早期的町人不仅仅指代商人,同时也包括了大量的城市手工业者。直到江户时代,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商业活动也逐渐增多,町人的涵义才开始更多地表现为商人的形象。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城市里,町人是武士之外最普遍的一个群体。从社会地位上看,町人是社会的底层,毫无政治权力。但由于其从事的经营性活动,利用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扩大资产,使成功的町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不但没落的武士阶层无法比拟,甚至到江户后期连一些大名在经济上都要仰其鼻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造就了町人特殊的生活习性,不同于武士的迂腐清高,町人思想灵活,精于算计,由于其思想和行为中的重利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征,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町人都是被批判和嘲弄的对象。日本学术界将町人的这些行为特质统一称作町人根性。
町人根性即町人自身的集团意识和生活习惯,是町人行为方式的一种直观解释。早期关于“町人根性”的表述往往是充满了贬低的意味的,代表了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社会对待町人的基本态度,“所谓町人,乃只吸取诸武士俸禄之无益之徒,实为无用之废渣。”[3]195日本学界对町人根性有过系统的归纳,其内容大致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第一,服务意识。町人合法的社会地位处在社会底层,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地位的变化。所以町人先天地具有一种自卑心理,也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经商行为。这里面的服务意识事实上带有着一种妄自菲薄的想法,即在其经商活动中与雇主或交易对象之间自己的地位是低人一等的,因此必须要通过更为殷勤的服务才能够获得对方的认可,从而维系自己的生存。当代的企业家虽然没有了这种先天上的地位的低贱,但是这样的习惯还是维持下来,所以日本的企业在服务态度和品质上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这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体面意识。虽然社会地位远低于武士阶层,但是町人所信守的道德观念同武士还有一定的相似性,“忠”“信”这些概念也是町人所信奉的守则。但这是否意味着町人具有和武士同样的道德观念和操守呢?严格来讲,町人忌讳不守信用的行为,在商业活动中保持自律,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们的体面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发自内心的去遵守这些戒律,只是因为社会加诸给他们的影响实在太过于巨大,而他们自身又无法同当时的统治阶级理念相对抗,是一种被动性的服从,也是在武士思维在社会中形成主流的情况下,为了让自己的阶层能够维系或加强现有的社会地位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此,町人的外在行为表现与其说是来自内在的道德律,不如说是来自面子。
第三,界限意识。町人的界限意识一方面体现在他们重视家族传统,对于祖业极其重视并且不肯让外人插手;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为方式上的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因此当某方面的技艺形成之后,他们的选择是不断地进行重复和完善,力争在已形成的基础上做到最好,但是对于与之相关的任何否定和质疑,都抱有极端抵制的态度。所以日本的一些早期工艺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但是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相比,其进化几乎没有,这一点在后面论述日本管理哲学的缺陷时也会作更为详细的阐释。而在本质上来说,町人最终是站在其“家”的界限的立场上进行经营活动,表面上的道德规制内在隐藏着欺诈、狡猾、奉承、贪婪等利己主义思想,他们在“家”的内外所奉行的行为标准是不一致的,诚信、信用这些准则只在内部推行,对外则会换上商人的一贯嘴脸,即使在现代企业诞生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西方国家的市民道德、公民精神并没有植根于其思想当中。
第四,平等意识。町人当然不可能具有超越其时代特性的平等意识,因此这里讲的平等指代的只是在特定的商业关系上。町人的生活是通过生意来维持的,而这也是他们最具有自信的领域,他们的智慧与狡黠被充分发挥出来,甚至是高级的贵族在这种交易关系上和町人比起来都不能占据上风。也正是靠着这种能力,町人群体才会在江户的末期形成社会优势。在町人的世界里,虽然他们社会地位低贱,但是在商业活动中任何人都是对等的,这种平等和自由民权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买卖关系中的交易平等,只存在于交易活动和町人的自身群体内部。
町人根性的存在是町人无法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进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些原因就否定町人的时代价值。町人根性不等同于町人伦理,对町人的认识要放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和审视。一方面,町人根性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涉及资本主义的问题,町人这个群体本质上就是封建制度的附属品,是日本近代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构成。在典型的重农主义文明当中,商人这个阶层的存在性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从社会构成上看他们不可缺少,但是却永远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幕府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体制中,町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其所从事的行业在社会中固然不可缺少,但由于商人重利的本性和经营中的习惯,所以町人重计算、短视、贪心等行为特点确实在这个群体中客观存在,因此被自诩道德至上的武士阶级所蔑视也就顺理成章;但是另一个方面,町人能够生存于那个时代,并且不断壮大,也有他们自身的特长。表现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安分守己,尊重并服从于社会秩序,在追逐利润最大的同时却过着尽量简朴的生活,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以此为条件主动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到了江户时代后期,随着町人经济力量的逐渐强大和社会地位以及文化创造力的日益提高,在町人中间开始滋生出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与人际关系相适应的道德意识”[4]304,这就是町人伦理。
二、町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町人伦理的形成
江户幕府基于“重农主义”的治国理念,将所有民众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商人排在最末尾,也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领主的城市建设等提供夫役和技术,经办年贡米和特产物的贩卖,以及购买供领主阶级消费的非自给性物品等。”[1]42和所有坚持“重农抑商”的文明一样,在这一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町人只是统治阶级的附属品,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对于德川家族来说,这种“幕藩体制”是坚定而又牢固的屏障,使其家族在日本的统治绵延数百年。但是对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来说,这种体制与其说是对其社会地位的肯定,倒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限制。
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前,曾经具备统一能力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已经先后开始进行“兵农分离”的活动,即将自己下属的武士从农村集中到城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在统一日本之后,除了进一步推动兵农分离之外,更把范围扩展到商农分离。这样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无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战国时代的亲历者,其成功都依赖于以武士集团为基础的强大武装,但在那个时代武士阶层“下克上”屡屡成功的例子也令他们触目惊心。因此,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杯酒释兵权”,他们在完成统一之后采取这些策略的目的都是通过限制武士的力量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江户幕府由此也表现出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比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在农村失去立足之地的商人也开始进一步向城下町集中。当然,从商人趋利性的本质来看,城下町日渐集中的财富使其主观上也有向城下町转移的愿望。在由“士农工商”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町人(手工业者与商人)看似排在社会的最底层,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导致武士不能从事经营性活动,町人在事实上具备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专属权利。而武士阶层在离开农村之后,一方面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政治实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收入上只能依赖于领主提供的俸禄,经济上的自主性也逐渐丧失。由于武士不能直接经商,甚至他们赖以生存的俸禄也必须要交给町人来帮助他们经营。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武士日趋贫穷,财富越来越多地向町人集中,两者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虽然武士依然是统治阶级,但是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町人,富裕的町人借助经商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各地的大名为了保障自己领地的繁荣也给予他们一定的经营特权,在经济地位稳定的情况下上层町人也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立足,武士阶级的没落给了他们转变身份的机会,“町人的出现,虽没有在社会政治上像武士那样形成强大的势力,但在德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实践了儒家的思想,为日本步入近代社会准备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5]
到18世纪初期,町人的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足以与统治阶级分庭抗礼的程度,他们不仅通过经营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幕府和大名之间的复杂债务关系也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町人阶级被推到了德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主角地位,成为创造日本近世文化的‘生力军’”[1]46。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催生了町人在思想文化上的发展,江户中期的元禄文化和后期的化政文化,都与町人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文化阶段当中,文化的传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流社会,经由商人的传播和庶民的普遍参与,文化的普及性和推广性已经远远超过前代,町人文化也不再是下流而为人唾弃的所谓“根性”,其伦理道德开始逐渐形成并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由于町人思想流派众多,内容也散杂在哲学、文学和戏剧作品当中,因此归纳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总体来看,江户时代的町人伦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町人伦理产生的前提:上下共利与“金钱本位”
作为江户时代最为高贵的阶层,武士阶级的道德观念亦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经过历代的演进,武士精神在江户时代同儒家朱子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完美结合,形成武士阶级共同遵守的行为守则——武士道。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武士道,如同它象征的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6]作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武士道在日本各个阶层都有深刻的影响力,但是从町人的角度来说,社会地位以及生存模式的巨大差异使其伦理思想同武士道精神有着与生俱来的差别,“武士之子受武士双亲教育,教授武士之道而成为武士,町人之子受町人双亲养育,教授商卖之道而成为町人。武士舍利德而求名,町人舍名而求利德,积蓄金钱,是以谓之道也。”[1]109-11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士重名,可以“为名舍利”;而町人重利,其伦理是“舍名而求利”。而且这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从家庭扩展到整个阶层群体的共同守则。
但是从社会分工看,作为下位阶层的町人并不具备武士的社会使命,所以武士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伦理标准并不是他们一定需要承担的。虽然在町人伦理中也包含了“义”的成分,但是在町人伦理中更多体现的是“义即利”的转换。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井竹山,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利”是“上下共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同时也区别于幕府统治者倡导的所谓“公利”。“共利”与“公利”的差别在于:在当时的话语情境中,“公利”实际上就是以幕府为代表的官方的利益,而町人阶层的利益则被归结为私利,町人伦理所倡导的“上下共利”,就是要将町人阶层自身的私利融入“公利”当中,体现出获得经济自主性之后的町人阶层追求政治上权利的诉求。但是在政治地位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这种诉求不能够通过政治上的方式来进行,町人既没有参与统治的资格,也没有政治上的话语表达权。因此这种诉求只能通过经济的方式来完成,由此对金钱的追逐成了他们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和最直接的人生目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最现实的,既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与充实的感觉,又能够帮助他们博取俗世的名分,成为后世的楷模。因此在属于自己的文化、艺术产生之前,金钱就是町人唯一的信仰,他们唯金钱至上,为了获得金钱不择手段。但是这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并不能够给他们带来终极的满足,在社会地位依然不平等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地挥霍财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由此来看,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认识,此后随着町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其金钱观也在发生着变化。江户晚期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基于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认为金钱除了传统意义的价值之外,同时也兼具道德层面的价值。“若有金银,遂致家富,愚者可变智,不肖亦成贤,恶人也变善。若无金银,智者变愚,贤者亦成不肖之徒,善者也会变成恶人。终于,诸事兴废继绝,生灭盛衰,皆以有无金银为凭,上自公侯,下至士农工商,皆以金银为保身命之第一宝物也。”[1]222这种说法一方面将金钱至上的观念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使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则将金钱同人的道德水平直接形成对应,从而抬高了町人的道德伦理水准。当然,财富和道德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人的道德水准也不会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财富。但是放在那个时代来看,这样的转换既给町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又使他们为了获利所做的那些传统道德所不认可的营生拥有了一个道德的外衣。
(二)行为准则: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
从17世纪后期开始,町人在财富上已经凌驾于武士之上,但是政权仍然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庞大的财富并没有带给町人足够的尊重和认可。同时由于产权关系并不明晰,其财产的所有权缺乏足够的保障,经常会出现幕府或者大名的一个命令就使町人倾家荡产的现象。基于这些原因,多数暴富的町人都抱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在生活上追求奢华和享乐,这种享乐之风在元禄文化阶段愈演愈烈,演化为豪奢纵欲、攀比浪费的奢靡风气。这里面固然有町人通过展露财富来展现自我价值的无奈之举,但更多则体现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由此也可以看出江户町人并不具备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引领革命的能力。重消费的伦理思想在桃山时代町人中形成影响,到元禄时期达到巅峰,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炫耀与浪费,引发了统治者的关注,号称江户幕府治下最为成功的“享宝改革”由此拉开帷幕。
“享宝改革”是德川家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位时发起的,改革的表面原因是平抑米价,稳定社会秩序,但实际上根本目的是为了限制町人的过度发展,重建武士阶级的威信。这一目标从改革中最重要的举措“俭约令”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享宝改革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倾向是压抑町人及其商业资本,所以诸如紧缩通货、统制物价、禁止奢侈、取缔风俗、禁止新产品的制造和贩卖以及加强身份制统治和大造贱商思想舆论等,均制约了町人的发展。”[1]156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大量町人的破产以及商品经济受到抑制,町人的生存和发展遇到进了入江户时代以来的最大危机。享宝改革是江户时代三次大规模改革当中最成功的一次,德川吉宗也被看作是日本的中兴之君。但是平心而论,其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享宝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抑商”来恢复“重农”的传统,从而回归江户初期的那种社会秩序。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已经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行为,町人的奢靡享受固然需要遏制,但是这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一种表现,抑制町人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领域的萧条,从而延缓社会发展的步伐。对于所有东亚国家来说,对“重农主义”的坚持是他们无法通过自发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原因。“享宝改革”的客观作用就是把町人伦理从享乐主义的极端拉向禁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而这种禁欲主义所契合的是近世儒教,尤其是“朱子学”所倡导的伦理观念,与町人的内在思维模式有着深刻的矛盾,其结果必然是破坏业已形成的商品经济环境和思维方式,这样做既不能挽救国家的前途,也不能使町人真正变得道德高尚。
(三)商人之道:俭约齐家与正直营利
“享宝改革”改变了自町人兴起以来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在此之后石田梅岩和他所倡导的日本“心学”开始兴起并获得了町人的普遍认可,被称作江户时代的“町人哲学”,甚至有学者认为石田心学所阐述的经济伦理在日本的社会进化中起到了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与之前的享乐主义相对立,石田认为:“为了世界,本需用三分者而以两分济事,此谓之俭约。为自私而行吝啬,乃贪心,非俭约也。”[1]174这个观点在强调俭约主义伦理的同时,把俭约和吝啬进行了区分。在石田梅岩的伦理思想中,俭约并不仅仅是一种控制浪费、力行节俭的过程,而通过这种俭约的努力最终化私为公,以自我欲望的节制来回报国家,推动社会发展。在石田梅岩所提出的“四民职分平等论”中,主张町人阶级在职分上、人格上与武士平等而不是成为武士的附庸,平等的前提是町人可以承担与武士相当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来自经济领域,当町人通过勤劳的付出和节俭的生活创造更大的财富时,国家和社会也会因此而获益.在石田以及之后的学者草间直方等人看来,商人“以基于组织的公正方法,努力维持着供给、货币、价格三者间的秩序关系,为国家做出了贡献”[1]229,这种贡献只是性质不同,但是实质上并不逊色于武士以武力保卫国家的贡献。
按照这种逻辑,町人最为诟病的“为了营利不择手段”的根性,其实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这就是石田梅岩所倡导的“营利正当论”。在以此为基础所构建的町人伦理当中,营利和道德是可以两全的,商人在完成其社会职责的过程中,应该获取正当的利益,以维系其事业的长久。但是在获利的方法上,町人不能为所欲为,必须为一定的伦理准绳制约,因此石田又提出了“正直营利”的观点。正直之道的核心是“利己利人”,要求町人“珍惜一分一厘钱之心,对货物细心周到,不使用任何瑕疵之货卖与顾客,获取利润应该合乎时宜”[1]172,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权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都能走向正直,社会能公正地理解町人阶层的经济行为,尊重町人所创造的经济价值。”[7]因此,正直不仅仅是对于町人自身行为的一种规范,更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町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从而使町人的行为能够真正为社会接受。
石田梅岩以俭约和正直为基础构建了适合时代发展的“商人之道”,不仅指导了町人的言行,也让町人阶层认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成为之后的社会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据此就把心学和“町人伦理”的作用等同于加尔文教派在西欧资本主义中形成的精神原动力是过于武断的看法,其作用也远远未达到思想启蒙的高度,但是“在未来日本资本主义逐渐滋生、发展时,也不失为有利其发展的条件之一”[4]307。
三、町人伦理对现代日本管理哲学产生的影响
管理哲学形成于管理者的行为和思想之中。作为早期日本企业家主要的来源,町人的很多属性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承下来,甚至在当代的一些日本企业家的行为特质上都还能看到町人的影子。与之相对应,作为封建时代的商人伦理和行为规则的町人伦理,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企业家精神,但从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看,其借鉴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町人伦理中的精华,是前人留给现代日本企业家和管理学家的思想遗产,在现代日本管理哲学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町人伦理推动了日本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町人伦理的确立意味着日本的商人阶层不再是一个个松散的个体,他们有了明确的价值指引,也具备了共同的行为操守。到倒幕运动开始之前,这个群体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表现得足够强大。如果追溯家族背景的话,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出身于町人:具有代表性的如号称“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其父亲是经商的豪农;日本最大的财阀三井财阀创始人三井高俊,其家族最早是经营当铺和酿酒业的商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同时,町人伦理也冲击了武士阶层“以经商为耻”的伦理观念,推动了很多下级武士走上经商的道路,近代企业家的群体来源也因此得到了丰富。由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幕府的抑制,因此在倒幕运动时他们成为倒幕派在资金上的资助者。而作为回报,明治政府在上台之后对这一群体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在明治政府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中,政府将自己兴办的大型企业转让给民间企业,除成就了三井、三菱、住友这些大财阀之外,一些依靠自身经营能力获得成功的普通商人,也获得了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机会,这也是他们从普通商人晋级成为企业家的重要条件。从来源上看,江户末期的町人是日本第一代企业家的最主要来源,而日本的管理哲学又产生于这些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与管理理念当中,由此可见町人伦理在推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生成和扩展的同时,也为日本的管理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二)町人伦理为日本近代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了蓝本
町人伦理中的“上下共利”、“正直营利”以及“道德营利两全”等观念,是町人能够接受并适应明治维新的时代浪潮的基本原因,同时也为新一代企业家构建具有日本特色的近代企业伦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比如涩泽荣一所倡导的“道德经济合一”的企业伦理,其依据就是商人的经营活动可以和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形成一种有效结合,“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招致自灭。”[8]这就是涩泽管理哲学中作为基础的“士魂商才”,而町人伦理正是“商才”的基本来源。同样,早期日本企业家都认同“实业报国”的价值理念,其原因可以追溯到町人伦理对于创富观念的调整。从这些近代工商业者的角度看来,经营不仅仅是让自己获利,同时也会对国家产生正面的贡献。因此从事企业经营既不低贱,也不是毫无社会意义的。
(三)町人伦理的内容直接转化为企业管理哲学
从涩泽荣一到稻盛和夫,日本自近代化以来的每一代企业家都以“哲学家”自居,强调经营哲学在企业获得成功中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独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虽然每位企业家的经营理念都各有不同,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思想放在一起进行归纳的话,我们会看到一种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而町人伦理则可以看作是这种传承的源头。从对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推动作用看,町人伦理在其产生的时代是具有先进性的,因此其影响也会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明治维新前后所产生的第一代日本企业,对现代的日本企业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俭约、正直的价值伦理以及“金钱为本”“营利至上”的经营理念等,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管理中的基本教义。生活在今天的日本管理哲学家,在进行管理哲学的理论进行阐述时,都可以从町人伦理中吸取合理的内容,从而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社会存在的町人虽然已经走进历史,但是町人伦理依然拥有其时代生命力,同时也昭示着在当代获得巨大成功的日本式管理,其实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总之,町人伦理的形成与发展,为日本式企业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町人伦理到管理哲学的转化,代表了日本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化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进化与延续。町人伦理之于日本近代化,虽没有起到类似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影响,但对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替影响之下的日本社会来说,既是坚持国民文化特质,延续历史传承的精神载体,又是兼容并蓄,吸收众家之长的理论基石。这种影响,同样包括町人伦理的局限性,“町人伦理作为当时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能不受到封建伦理的影响,町人安于身份、职业的尊卑意识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9]要突破这种封建性的束缚,需要一次全面的思想启蒙,这一任务最终留给了明治维新前后的福泽渝吉等启蒙思想家来完成。
[1]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黄晓红.石门心学中的町人伦理思想考[J].中国市场,2009,(48).
[3][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5]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3),15.
[6][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14.
[7]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8.
[8][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4-5.
[9]朱珠.论近世日本町人的伦理思想[J].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79.
〔责任编辑:冯胜利〕
B82-05
A
1000-8284(2015)06-0157-06
2015-03-20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社群主义视域下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12C016)
刘韬(1978-),男,黑龙江双城人,博士研究生,东北农业大学讲师,从事行政管理理论、管理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