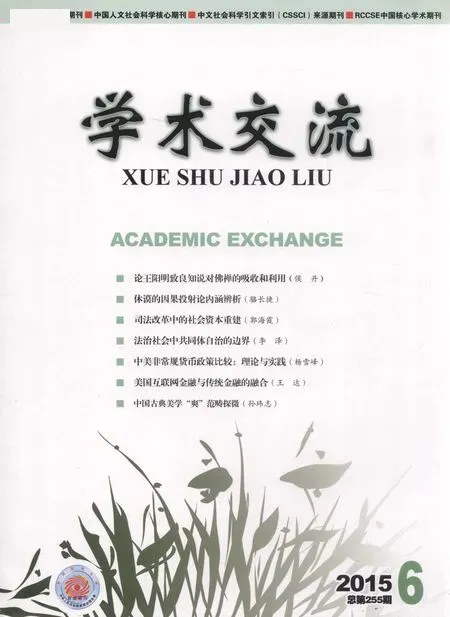休谟的因果投射论内涵辨析
骆长捷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外国哲学研究
休谟的因果投射论内涵辨析
骆长捷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某些解释被看作是一种投射理论。人们发现,这种投射理论违背休谟的意义理论,很难与其怀疑主义立场相容。然而,休谟哲学中呈现出的“意义张力”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为我们重新界定因果投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投射理论是休谟在坚持因果怀疑论的基础上,对我们何以会持有因果必然性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这一说明有助于理解日常语言为何会以直接指称的方式来谈论因果必然性,并因此折射出一种因果实在论的视角。借助于投射理论,休谟一方面在坚持其怀疑论的同时,说明了因果信念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为日常语言的合法性地位提供了辩护。
休谟;投射;意义张力;因果必然性
休谟对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人们在解读休谟的因果观时也持有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使他坚持一种因果还原论,即主张因果关系只是相似对象之间的规则性接续。当代休谟研究者则更多地从不同角度来解释休谟的因果观,投射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然而,即便人们同意休谟的因果理论中存在某种投射主义解释,对于如何理解这种投射理论,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从这一问题出发,结合休谟哲学中的“意义张力”问题,对休谟因果理论中的这种投射观点进行分析,回应不同的解释观点,并最终澄清休谟的因果投射论的本质。
一、休谟的因果投射论及其解读
西方哲学研究一直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主张我们要区分哪些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哪些是我们强加于事物的性质。洛克关于物体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就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实在论观点无不与这一思维方式有内在关联。投射主义(projectivism)也是这种反实在论观点之一。这一理论主张,某些所谓的外部对象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只是我们内在的主观感觉、情感的一种外在投射。
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西方学界发现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中同样蕴涵一种投射理论。比如,休谟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通常假定在外部对象中有一种因果力或必然联结时,曾经指出:“心灵有一个大的倾向,将它自身扩展到外部对象上,并将内在的印象与这些外部对象结合起来。……这种倾向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假设必然性和力都存在于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之中,而不存在于考察它们的心灵中的缘故;虽然当我们不把那种性质看作是心灵由一个对象的观念转到它的恒常伴随物的观念上的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对它并不能形成任何哪怕极其渺茫的观念。”[1]167休谟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客观因果关系实际上只是内心的习惯或感觉的投射,自然界中并没有一个可见的客观因果必然性与我们的因果性概念相对应。
对于如何理解和分析休谟投射理论及其地位,人们往往意见不一。巴里·斯特德(Barry Stroud)认为,休谟的这种投射主义观点很难与其经验实证主义立场相容。[2]按照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我们断言原因与结果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结,并非是因为我们真正知觉到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任何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当我们总是观察到类似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有一种恒常结合关系时,就会使心灵产生了一种习惯性倾向,或决定性的印象。由于心灵有一种将自身的内在印象扩展到外部对象上去的自然倾向,所以我们才会把内心的这种必然性印象投射到客观世界中去,并错误地相信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一种客观必然联结。这种投射的结果产生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或信念。
当代投射主义者布莱克本(S.Blackburn)则认为,休谟的投射主义解释并不必然被看作是一种错误理论,因为将经验实证主义视为休谟的最终立场并不恰当。在因果关系问题上,休谟的立场更类似于一种“准实在论”(quasi-realism)[3],即一方面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立场,拒绝承认某种对象(因果必然性、道德性质等)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又认识到日常语言表面呈现出的实在论特征,并给予其合法性地位。比如,休谟否认因果关系概念能够正当地指称某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但他又在很多时候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谈论那种不可认识的客观必然性,似乎承认那种必然性的存在。这种准实在论立场不但能够与休谟的投射理论相容,而且进一步为投射理论提供了支持和解释。
在这里,斯特德与布莱克本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与这种投射理论不能相容,而后者则主张,这种投射理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休谟在坚持其因果怀疑论观点的同时,借助其投射理论,为日常因果性语言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这种分歧牵涉到休谟哲学中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人们将这一问题称之为“意义张力”。
二、“意义张力”问题及其化解
“意义张力”问题与休谟的意义理论直接相关。因此首先我们要来弄清休谟意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我们知道,观念理论是休谟整个哲学的理论前提。“所有的简单观念都来源于某个简单印象,并且是它的精确摹仿”——这一原则被休谟确立为其人性科学的第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休谟指出:“当我们考虑到怀疑我们所使用的某个哲学名词没有任何意义或观念(正如十分常见的那样)时,我们只需考察,‘那个假定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不可能找到任何来源,那么这也就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将观念置于如此明白的观点之下,我们也就可以合理地希望去借此排除人们关于它们的本性和真实性方面的一切争论。”[4]22也就是说,一个名词的含义就在于它所表达的那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否可靠就在于它是否有一个原初印象,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个原初印象,那么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原则,休谟在谈到那种客观因果必然性时(他通常将之称为自然的神秘原则或神秘的力等),通常说这样的表述是不可理解的。乔治斯·迪克(Georges Dicker)将休谟的这一意义检验过程表述如下:“如果T是一个抽象的、具有类别性的语词或者是一个描述性语词,我们假定它有一个观念I作为它的意义,但观念I并没有任何印象来源,那么T并不指代任何观念,因此是无意义的。”[5]
然而,新休谟主义者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注意到,在休谟的文本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根据其意义理论,休谟认为,因果必然性概念并不能正当地用来意指任何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东西;另一方面休谟却借助于“因果力”“神秘原则”等说法来指称一种不为人知的因果必然性,似乎暗示它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按照他的意义理论,这种指称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比如休谟在《人性论》中谈到“自然的最终力量和效能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知的,我们在物质的一切可知性质中来寻找它也是徒劳”[1]159“它并不能使我们洞察物体的内在结构或运作原则”[1]169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述在《人类理智研究》中更为常见:“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任何有理性的、谨慎的哲学家,从不曾妄图给任何自然运作指出最终原因,或清楚地表明在宇宙中产生任一结果的那种力的活动。”[4]30“自然使我们远离她的秘密,她只使我们知道物象的少数表面的性质;至于那些物象的作用所依据的那些力和原则,自然都向我们掩藏起来。”[4]32-33。
按照斯特劳森的解释,休谟的思想似乎存在明显的“意义张力”(the meaning tension)[6]:一方面是他的观念或意义理论的严格经验主义特征以及他对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存在的认识论断言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另一方面是他使思想和语言表达呈现出实在论形态的文本倾向。
那么,如何来解释和处理这种“意义张力”问题呢?在休谟那里,这种“意义的张力”并非个别现象。不但在因果性问题上,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休谟也常常使用某些在他的意义理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概念,比如实体(substance)、上帝(god)、自我(self)、物体(body)等。我们发现,从休谟的理论意图来看,他通常是在两种层面上来使用这些概念的。一方面,他是为了批判哲学家对这些概念的误用。比如,他在反驳人们将因果必然性的含义解释为物体中所蕴含的力时,也指出:“我们可以暂且承认,在任何一个例子中,一个对象被另一个对象产生涵摄一种力,这种力与它的结果相联系。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力并不存在于原因的可感性质之中,而呈现给我们的却只有一些可感性质;我就要问,在其他例子中,你为什么只根据这些性质的出现就假设同一种力仍然存在呢?”[4]91另一方面,他更多地是在一种无批判的、日常语言的层面上来使用它们。比如他谈到“物体”(body)这一概念时说:“虽然怀疑论者甚至声称他不能凭借理性来捍卫他的理性,但他仍旧继续推理和相信,并且根据这条同样的规则,他也必须同意物体(body)存在的原则,虽然他不能依靠任何哲学论断来主张这一原则的真实性。……我们很可以问,什么原因使我们相信物体存在?但如果问物体是否存在则是徒劳的。”[1]187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层面都不违背休谟的意义理论。首先,第一种用法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某些概念不能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而可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不但不违背休谟的意义理论,相反是这一理论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假如我们在说某个概念无意义时,不能明确地指出它在什么用法上是无意义的,我们又怎么能坚持我们的论点呢?其次,在一种日常语言的层面上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使用某些概念,这也未必与休谟意义理论相冲突。休谟在陈述他的意义理论时说:“当我们考虑到怀疑我们所使用的某个哲学名词没有任何意义或观念(正如十分常见的那样)时,我们只需考察,‘那个假定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不可能找到任何来源,那么这也就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很明显,在这段话中,休谟专门提到了“哲学名词”。也就是说,休谟的意义理论针对的是哲学中所犯的概念错误以及由此对哲学本身所造成的危害,至于日常语言的各种用法,并不是休谟意义理论所能批判的对象,也不是休谟的理论意图所在。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休谟为什么需要在一种日常语言的层面上来使用一些概念呢?笔者认为,一是出于语言表述上的便利和易于读者理解的考虑。在《人类理智研究》的第四章,休谟在多处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谈论自然中的“力”,但他对他所使用的“力”一词加了一个注释,指出这里的使用只是就其宽泛、通俗的意义而言,而在第七章则有关于这一词的精确解释。[4]33也就是说,在没有精确地解释“力”这一词的含义之前,休谟姑且在一种通俗的、日常语言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但这并不妨碍休谟关于因果必然性问题的整个论证。他从根本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指出我们不能将那种神秘的力作为因果必然性概念的正当含义。二是休谟实际上为日常语言的合法性给出了解释和辩护,这一点是休谟毫无顾虑地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使用“力”“对象”等概念的根本原因。日常语言总是倾向于描画世界,当人们在谈论任何名词时都好像有一个指称对象,似乎假定了一种实在物与之相对应,哪怕我们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这些对象,这就是自然语言所呈现出的实在论特征。实际上,这种语言表面上的实在论特征与心灵的“投射”(projection)直接相关——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感觉、习惯、情感等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由此假定这些东西有一种现实的存在,从而使语言谈论它们就好像谈论某种现实的东西,然而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发现它们。我们所谓的物体的可感性质诸如声音、气味,所谓的物体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以及道德性质善、恶等,在休谟看来都属于这一类。也就是说,它们只是一些心理存在物,是我们把自己的感觉、习惯、情感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才会由此假定这些东西有独立于心灵的客观存在。
但是,按照斯特德的理解,如果这种投射使我们假定一种现实因果必然联系的存在,这不是直接违背了休谟的意义理论吗?因为按照这种意义理论,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所指涉的是一些现实存在物,那么这些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此,休谟将这样的假定称之为“心灵的偏见”[1]167。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假定只是由于心灵的投射而无任何经验或理性上的证明,那么我们就必然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拒斥日常语言的表述方式,要么从一种新的立场,比如准实在论的立场,为日常语言加以辩护。拒斥日常语言的做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认识到日常语言的实在论特征所导致的问题,与此同时又必须接纳语言的这种特征,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认可并维护日常语言的实在论特征的同时,规避它所可能导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诉诸一种准实在论立场,即当我们在谈论某种东西就好像真有这种东西时,我们完全认识到并不能在现实中找到这种东西,而我们实际谈论的不过是我们主体的投射物,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拒绝日常语言的这种用法,而只是明白这样谈论的本质是什么就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世界中没有这种东西的情况下,以一种实在论的方式来谈论这种东西,我们所要保留的只是这种谈论方式,即语言的这种实在论的表象,而对于所谈论的对象——这种东西,我们并不承认其存在。
三、休谟的因果投射论的本质
在因果性问题上,哲学家的任务有三个:第一,要区分我们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休谟的怀疑论;第二,弄清楚是什么在诱导我们去相信我们能够认识那些实际并不能认识的东西,这是休谟的投射理论所要说明的;第三,哲学家应当如何正确处理我们的理性(因果怀疑论)与信念(因投射而相信因果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休谟最终坚持的是一种准实在论立场。根据这种因果准实在论立场,投射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拒绝承认因果必然性存在的同时,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持有因果必然性信念,以及日常语言何以会呈现出实在论特征。
休谟虽然指出我们不能认识或发现一种现实的因果必然性,但他并没有否认它们的存在。他甚至允许人们用因果必然性来指涉这一未知的性质。他所反对的是哲学家假定自己真正了解这些未知性质,并且认为我们的因果必然性观念就是指称那种现实的因果必然性,继而为这一观点提出各种理论论证。休谟认为,这样一来,哲学就误入歧途。
在因果性问题上,休谟曾区分了三种层次的意见:庸众(the vulgars)的意见、错误哲学的意见和真正哲学的意见,并指出,随着形成这些意见的人们所获得的新的理性程度和知识程度的加深,这三层意见一个高于另一个。[1]222也就是说,错误哲学的意见在层次上高于庸众意见,真正哲学的意见则高于错误哲学的意见。休谟认为,真正哲学的这种意见更为接近普通人的感觉,而远离一种错误知识。他说:“人们在以平常的、粗心的方式思考时,很自然地想象,在他们经常发现为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对象中觉察到一种联系,并由于习惯使那些观念很难分离,他们就倾向于幻想这样一种分离本身是不可能的、荒谬的。而摆脱了习惯的影响、并把对象的观念加以比较的哲学家们,则立即觉察到庸众意见的错误,并且发现在对象之间并无可知的联系。……但这些哲学家们却不曾从这一观察得出一个正当的推论,即断定我们没有独立于心灵、并属于原因的力或能动力的观念,相反,他们却经常寻找这种动力所由以存在的那些性质,而对理性为说明这一观念而提供给他们的每个体系都不满意。他们有充分的才能使他们摆脱通俗的错误,即认为物质的一些可感性质和活动之间有一种自然而可知的联系;但却不足以使他们不再在物质中或原因中寻找这种联系。要是他们碰到了正确的结论,他们就会回到庸众的立场,并以一种懒散和冷淡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这些论说。”[1]223
根据休谟的上述说明,我们可以将感觉投射到外物所导致的结论区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庸众相信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庸众受习惯的影响而想象物体之间有一种因果必然联结,他们将这种必然联结与因果对象结合起来,相信它们有一种空间上的结合,或者说相信这种必然联结存在于现实的因果对象之中。但事实上,这种必然联结只是心灵的知觉,与那些因果对象并没有空间上的结合,也不存在于对象之中,而只存在于心灵中。这是庸众常犯的错误。
第二,错误哲学家虽然承认我们不能发现一种客观的因果联系,但却试图通过哲学论证来证明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即哲学家通过反思,发现在因果对象之间并没有可知的联系。他们认识到庸众所犯的错误,却没有放弃对因果力的寻找和证明。他们采用各种学说来证明那种现实的因果力或道德实体。但实际上,他们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和整个谈论都是不可理解的、无意义的。这是哲学家常犯的错误。
第三,休谟的观点:真正的哲学立场就是保留语言的这种实在论特征,而放弃我们对于语言所指涉的一些对象所持有的实在论立场。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家虽然承认并接受日常语言对客观的因果必然性的谈论,但并不主张我们能够认识它,因此拒绝承认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
如果我们在进行心灵的投射时,并不主张我们对于存在于物体中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而仅仅保留语言的这种实在论特征,那么休谟并不反对。因为这种做法“对这个世界也不会有多大影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必然性存在于外部对象之中,是因为我们心灵投射的结果,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从外部对象中发现这些性质,它们只是心灵中的知觉,那么我们就放弃了试图从物体中寻找这些性质的做法,认识到以往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在根本达不到目的的事上做徒劳的努力。于是,我们就会以一种懒散和冷淡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这些论说。
真正的哲学家不但知道庸众所犯的错误,而且也知道错误哲学所犯的错误,这正是他的意见处于较高层次的原因。他知道在因果对象中并没有可知的必然联系,也不再像错误的哲学家那样徒劳地在物体或神明中寻找或证明这种必然联系,而是认识到我们所能知道的必然联结只是心灵中的知觉。但与此同时,他却认可语言表面上呈现出的实在论特征,并清楚地知道这种实在论的特征从根本上源于人的主观投射。他既不主张我们能够认识语言背后的东西,也不采用各种论证去断言这种东西的存在,而仅仅是“回到庸众的立场”,像庸众那样来使用并看待自然语言。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休谟实际上并不拒绝日常语言的用法,他的意义理论所主要针对的是那种错误哲学,这种哲学试图发明一些学说来证明客观因果必然性是现实存在的,正如休谟所描述的错误哲学家那样:“他们有充分的才能使他们摆脱通俗的错误,即认为物质的一些可感性质和活动之间有一种自然而可知的联系;但却不足以使他们不再在物质中或原因中寻找这种联系。”
如果我们保留日常语言的用法,同时认识到我们并不能够从现实世界中发现那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因此不再像错误哲学家那样采用各种学说来论证客观的因果必然性,并且像庸众那样,对所有这些错误的论说持一种“懒散和冷淡的态度”,那么这就是休谟所谓的真正哲学家的立场。在休谟那里,对“因果必然性”的一种正确观点就是,既认可日常语言在谈论“因果必然性”时所具有的实在论特征,同时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谈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因果必然性与之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休谟所承认的只是语言的表面实在论现象,而并不主张一种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
因此,休谟的投射理论表面看来的确是一种“错误理论”。因为休谟虽然解释了人们是根据投射才相信一种客观因果必然性的,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凭借任何合理的手段去获得一个正当的独立于心灵而存在的因果力的观念。所以,仅仅根据投射去假定并坚信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是错误的,是由于心灵受到了这种不自觉的自然倾向的误导所致。但是,从语言层面来看,人们却可以根据这种投射去自由地谈论那种客观必然性,这体现了我们日常语言的用法。哲学家固然可以根据敏锐的观察断言说:“假定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同样不应当、也无法因此拒斥日常语言的用法。休谟主张,真正的哲学家在认识到我们根本不能发现一种客观因果性,从而放弃了对它的寻找和证明之后,会返回到庸众的立场。这就表明了他实际上反对的只是哲学家在因果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而并不打算根据他的哲学发现(我们不能发现一种客观因果必然性)否定我们自然语言以一种直接指称的方式来谈论客观因果必然性这一日常用法。相反,他明智地主张,真正的哲学家会回到庸众的立场,像庸众那样来看待并使用自然语言,而不去在意那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是否真有一种客观的因果必然性与我们的谈论相对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休谟的投射理论实际上是对我们何以会以一种实在论的方式来谈论客观因果必然性这一语言现象的一个内在说明。
[1]David H.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5.
[2][美]巴里·斯特德.休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319.
[3]Simon B.Hume and Thick Connexions[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0,50(S):237-250.
[4]David H.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M].Selby-Bigge,ed.P H Nidditch,rev.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5]George D.Hume’s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M].London:Routledge,1997:13.
[6]Galen S.The Secret Connex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120-121.
〔责任编辑:余明全 程石磊〕
B561.291
A
1000-8284(2015)06-0022-05
2015-02-27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休谟的因果观研究——基于对‘新休谟争论’的反思与回应”(13YJC720027)
骆长捷(1982-),女,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从事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