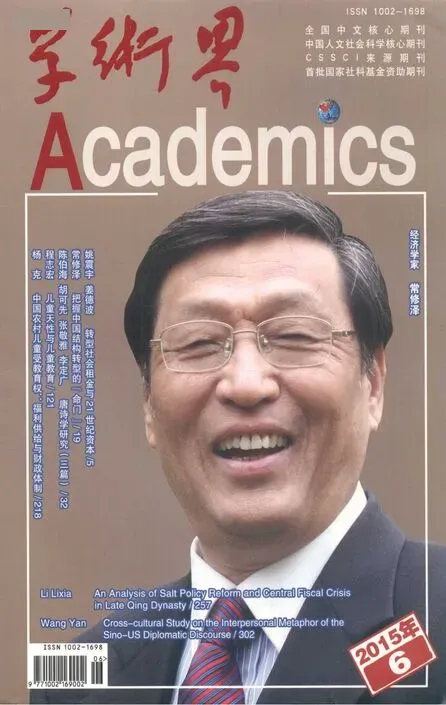论包佶、李纾与贞元诗风〔*〕
○ 胡可先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变化的分水岭,士风与文风也随之有了较大程度的转变。此后的中唐时期,更是诗歌发展急遽变化的时期。对其变化的认识,唐人就作了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的概括。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天宝“尚党”、大历“尚浮”、元和“尚怪”的具体内涵,都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唯独对于“贞元之风尚荡”尚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以新出土的《郭晞墓志》为契机,以“泾原之变”等政治事件为考察背景,以郭晞交游密切的文学人物为关注对象,探讨包佶与李纾对贞元诗坛的影响以及贞元之风尚荡的形成背景和文学表征。
一、“泾原之变”与“尚荡”之风的形成
2007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征集到郭晞夫妇的两方墓志,其中《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有这样一段话:
属贼泚称乱,皇舆外幸,公乘遽出奔,将赴行在,马仆伤足,为贼所得,称疾绝食,誓死不从。……洎大盗歼,翠华来归,依前除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诏书慰勉,恩渥如初,寻转太子宾客。养诚明之性,修调护之职,从心所欲,匪逾于法度,投足不勉,自循于礼经。道远乎哉,在我而已。况乎席元勋之业,则池□不为广;达老氏之旨,则□裳不为贵。尝与吏部侍郎李纾、秘书监包佶,弦觞风月,追方外之契。人或劝公:“家立大功,时犹右武,盍理韬略,而务宴安。”公谓之曰:“世蒙国恩,身陷虎口,既无执讯馘丑之效,又无随难羁靮之勤。朝典宥全,非曰不幸,戎马之事,已刳心焉。”君子闻之,以为知耻。〔1〕
这段文字记载郭晞为朱泚俘获之后,尽管受到朝廷的恩宥,具有重新出仕的机会,但仕进之心为方外之契所代替,与当时的文坛要人李纾、包佶弦觞风月,时人以为这是“知耻”之举。郭晞一生由戎马弓刀到弦觞风月,这一转变的契机从政治上说是“泾原兵变”,从文学上说是与李纾、包佶相互还往关系密切。因为李纾和包佶是建中以后贞元诗坛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旧唐书·路恕传》记载:“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人亦以和易称之。”〔2〕故以《郭晞墓志》为基础,以“泾原之变”这一重要政治事件为契机,从包佶、李纾切入以研究贞元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视角。
(一)贞元风气的变化,源于“泾原之变”的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通过墓志考察郭晞被俘的时间,及其由武向文转变的过程。郭晞的武略和战功,主要通过平定安史之乱和打败仆固怀恩叛军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就前者而言,墓志云:“属潼关失守,灵武望幸,尚父匡戴本朝,即日斑师,既至行在,公入在侍臣之列。及从尚父救河中,命公迎法驾于彭原,会军师于歧阳,又会战于京南,乘胜追奔,下华阴、弘农二郡。逆竖庆绪遣伪将收合败卒十五万,拒我于陕西,依高死战,王师少退。元帅遽命回纥逾险以袭其后,骤遣公引骁骑当前击之,贼徒大溃,斩九万级,遂复东周,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同正员,封隰城男。”〔3〕郭晞主要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而取得战功,受到朝廷嘉赏的。就后者而言,墓志云:“逆臣仆固怀恩,诱结二蕃,犯我亭障,擢兼御史中丞,统朔方先军以讨之。……公乃选神将提步骑三千,以当吐蕃,公自将五千,以当回纥。初则示羸不战以怠寇,迟暮乘退,伺其半涉,大破之,斩五千级。……贼退保白骥原,公以锐卒二千,伺夜犯营,余党大骇,应时宵遁。诏兼御史大夫,振旅而还,拜左散骑常侍。”〔4〕在平定仆固怀恩过程中,郭晞以顽强的战斗力,打败了背叛朝廷的联军。
就是这样的大将,在“泾原之变”以后,一变而为“弦觞风月,追方外之契”的闲散隐逸者,这无疑与他在“泾原之变”中被俘的经历密切相关。墓志载:“贼党谋曰:‘尚父德在朔方,若假晞兵权,则京西之师,势必来附。’”〔5〕是朱泚想利用郭晞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与唐军对抗。而郭晞此时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种方式,与朱泚乱军周旋,一是“称疾绝食,誓死不从”,二是“凶徒见逼,瘖噤不言”,最后逃脱了虎口,出奔奉天,朝见唐德宗。从被俘到逃脱,也表现了郭晞的睿智。郭晞被俘而逃脱虎口之后,唐德宗并没有治其罪,而是恢复原官,继续任用,依前除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郭晞由武向文转变的内外因条件。如果按照墓志中记载其官职变迁情况,即被俘以后,郭晞能够官复原职,那么他继续从武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后来他却向文转变,一方面是墓志中记载其“知耻”行为,即被俘而蒙耻,若再从武则是不知耻。同时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郭晞本身也具备了文官的素质,墓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后丁内疚,哀毁过礼,外除月,制除检校工部尚书,兼领秘书省事。公以书府编简多缺,上请集贤书目勘写,因著《新录》八卷。初,扃史称旷废久,修之为艰。公曰:‘图籍之兴,系于国本。所全者重,所略者轻。遂躬自纂阅,留为故事。’”〔6〕这是他在代宗时期曾经有的一段经历,说明在当时郭晞本身具备了较深的文化素养,这是他能够由武向文转化的内部因素。二是由于和包佶、李纾的交往,这一方面墓志与史籍都有所记载,上文已作了引证。这是他由武向文转化的外部因素。
(二)文武更化:郭晞的经历与贞元时代风气
我们还可以由此而探讨郭晞由武向文转变与文学史分期演变的关系。这样其焦点就集中于包佶和李纾身上。包佶和李纾是大历、贞元之际著名的文学人物,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有关他们的文学史定位,学术界却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著名唐代文学研究学者蒋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写了一部《大历诗风》,将大历时段的下限界定为贞元八年,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代表大历诗风的包佶、李纾等人的生活年代一直持续到贞元八年前后。而现在我们根据新出土的《郭晞墓志》,参阅上引《旧唐书·路恕传》的记载:“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人亦以和易称之。”包佶、李纾的诗风前后应有所转变,前期体现为大历诗风,后期则开启了贞元诗风之先,而这一界限就在于“泾原之变”。这样既能突出大历诗风的特色,又能体现大历诗风向贞元诗风转化的契机,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贞元诗风提供了更好的切入点。
同时,我们研究某一阶段的文学,也不必有意切断其客观的自然时段,即如贞元共二十一年,如果人为地将贞元八年之前切入大历,不仅平添困扰,于理亦有扞格之处。我们认为,从安史之乱发生始,至宪宗元和末年的诗歌发展,主要有三个段落:一是从肃宗至德元年起至代宗大历十四年止,主体是大历,堪称“大历诗风”;二是从德宗建中元年起至贞元二十一年止,主体是贞元,堪称“贞元诗风”〔7〕;三是从顺宗永贞元年起至宪宗元和十五年止,主体是元和,堪称“元和诗风”。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对于盛唐到中唐诗风的演化,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8〕对于不同的士风和文风情况,尤其是天宝“尚党”、大历“尚浮”、元和“尚怪”的具体内涵,文学史研究者都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唯独对于“贞元之风尚荡”尚没有一致的看法〔9〕。我们以《郭晞墓志》为契机,或许可以对于贞元之风“尚荡”的总体特征做出进一步阐释。下面我们列举这样几条材料以作参证,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10〕李观《与右司赵员外书》:“今之人学文一变讹俗,始于宋员外郎,而下及严秘书、皇甫拾遗,世人不以为经,呀呷盛称。”〔11〕这篇文章作于贞元年间。杜牧《感怀诗》:“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12〕可以看出贞元末的士风是崇尚放荡、豪华、奢侈。这种风气的形成,主要原因是代宗的姑息苟安政策,使得地方藩镇日益强大,致使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一场持续五年之久的建中之乱,并将德宗赶出长安。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没有复兴的希望,因而转向了侈靡放荡,车马宴游取代了弓刀征战。郭晞的经历与这一时代风气适相一致。
二、包佶、李纾与贞元诗坛
1.贞元二年进士科的文学意义
唐代的政治走向、社会风气、文坛风尚往往与科场风会相关,特殊情况下,科举中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是影响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的重要因素之一,贞元中比较明显且受人称道的贞元八年进士科就是如此,因为这一年知贡举者是陆贽,放榜的进士中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后来成为中晚唐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故而被誉为“龙虎榜”〔13〕。
我们这里研究贞元中士风与文风,将目标聚集到贞元二年的进士科,这是因为贞元二年的知贡举者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包佶。据张贾《国子祭酒致仕包府君(陈)墓志铭并序》:
考讳佶,天宝中,以弱冠之年,升进士甲科。文章之奥府,人物之高选,当时俊贤,咸所景附。洎登朝右,蔚为名臣,历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刑部侍郎、国子祭酒掌礼部□举、秘书监、丹阳郡开国公、太子少保。〔14〕
《旧唐书·德宗纪》:
贞元二年正月丁未,以礼部侍郎鲍防为京兆尹,京兆尹韩洄为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包佶知礼部贡举。〔15〕
《嘉定镇江志》卷一八《人物》:
佶,融子,进士第。……贞元二年,以国子祭酒知礼部贡举,后封丹阳郡公。〔16〕
可知贞元二年先由鲍防知贡举,尚未毕事而改为京兆尹,由包佶接替鲍防知贡举,因而放榜等程序,都是由包佶主持的。贞元二年进士的选拔及中第进士以后的发展,都与包佶有着紧密的联系。
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在唐代科举中是最为特殊的关系,座主对于擢拔的进士而言,是一种恩德,故望其报恩,而对于进士而言,则知恩图报。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独异志》所载崔群之事:“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公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17〕就门生而言,柳宗元《与顾十郎书》云:“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出者,非人也。”〔18〕对于这样的情况,陈寅恪先生曾言:“庄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19〕包佶贞元二年知贡举,其门生知恩图报之例可以用窦牟证之,因包佶死后,窦牟为作《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云:“台鼎尝虚位,夔龙莫致尧。德音冥秘府,风韵散清朝。天上文星落,林端玉树凋。有吴君子墓,返葬故山遥。”〔20〕其情感非常真挚。可知包佶知贞元二年贡举,无疑对其所录取的门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包佶既是一位政治人物,也是一位文学人物,他当年选拔的进士,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和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所考,总共有二十七人,而有姓名可考者则有张正甫、窦牟、窦易直、李夷简、李俊、李稜、张贾、张署、齐据、刘闢、皇甫镛等十一人。其中大多数是有诗文传世的文士,他们不仅擅长诗文,还与贞元以后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或政治命运相联,或文学取向一致。如张正甫为贞元二年状元,与韩愈交好,愈有《举张正甫自代状》。张署亦与韩愈交好,其卒后,韩愈为作《河南令张署墓志铭》。张署一生不得志,尤其是贞元当中,为幸臣李实所谗,与韩愈、李方叔都被贬谪南方,直至贞元二十一年征回京师为京兆府司录。窦牟与韩愈为望年交,其卒后韩愈为作《窦牟墓志》,称“愈少公十九岁,以童子得见,于今卌年,始以师视公,而终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21〕。此外,窦牟兄弟五人与其父窦叔向在中唐都有诗名,合集有《窦氏联珠集》。贞元二年进士及第的张贾,不仅有诗文传世,还在文章中直接叙述了包佶的情况。新出土张贾撰《国子祭酒致仕包府君(陈)墓志铭并序》:“考讳佶,……右揆平章事窦公、工部尚书张正甫、太子宾客皇甫镛,洎左散骑常侍张贾皆门生也。”〔22〕
总体看来,贞元二年包佶这一榜进士,大多是著名的文士,多有诗文传世,而且其中有两位门生窦易直和李夷简后来成为宰相。这些门生随后就进入了政治生涯,在贞元这一时期长达二十年,因而对于传承包佶衣钵并对贞元之风产生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2.贞元诗风的分期和诗坛宗主的接续
包佶诗歌传世很少,《全唐诗》所载仅三十六首,李纾的诗歌,《全唐诗》所载仅十三首,我们难以了解其总体风格。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各种史料与作品中找到线索并衡定其诗坛宗主地位的。这里还涉及到贞元诗坛的中心定位、贞元诗风的先驱、贞元诗坛的宗主接续等问题。
关于贞元诗坛的总体情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代表者主要是蒋寅和许总。蒋寅认为从德宗即位到贞元八年是大历诗歌由高潮转向低潮的时期,“成为划分中唐诗前后期的分水岭”〔23〕,贞元后期是以权德舆为首的新台阁诗人与方外诗人中分天下〔24〕。许总则重点突出贞元士风与文风从大历到元和的过渡特征,他在《论贞元士风与诗风》中说:“就时代而言,贞元处大历、元和之间,就诗风而言,由‘浮’到‘怪’,‘荡’居其中,亦可悟得介乎两者之间的品性。可以认为,一方面作为大历、元和之过渡,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身的特征,正是贞元诗风之价值与地位所在。”〔25〕然而二人论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贞元是从大历到元和的过渡,但他们并没有将“荡”的具体内涵清楚地表述出来,这样我们仍有必要对于贞元时期的士风与文风进行横向的空间定位和纵向的时间梳理。
我们知道,士风的改变往往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贞元时期社会风气的改变,其中心无疑先源于京城长安,而后再向全国辐射。上文所引《唐国史补》所言“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26〕,就是最为集中的说明。这种游宴的情况,还得到了唐德宗的认同和提倡,他经常对臣僚赐宴,并与游赏赋诗关联在一起。《旧唐书·刘太真传》载:“贞元三年以后,仍岁丰稔,人始复生人之乐。德宗诏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务,今方隅无事,蒸民小隙,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每节宰相、常参官共则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武及诸庙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交付,永为常制。’”〔27〕唐代皇帝赐宴最特殊最频繁的是唐德宗,“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28〕。唐德宗赐宴之作,现存《麟德殿宴百僚》一首,并有卢纶、宋若昭、鲍文姬三人奉和〔29〕。贞元朝赐宴,先是集中于三节会宴〔30〕,后又于中和节分宴〔31〕。德宗还是一个著名的奢靡皇帝,《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二《王建》条云:“建《宫词》云:‘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多。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事见李石《开成承诏录》,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皆摭实,非凿空语也。”〔32〕
贞元年号,长达二十一年,在整个唐代,除了唐太宗的贞观和唐玄宗的开元,就算最长的了。这二十余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接续大历之绪余并开启贞元诗风,中期出现代表贞元诗风的宗主,后期则为诗风之延续同时又成为元和诗风的前奏。按照这样的历程,我们也可以找出各段的代表人物,前期即包佶、李纾,中期则为权德舆,后期推孟郊、韩愈。前期以贞元八年包佶、李纾之卒为分界线,中期以权德舆成为文坛宗主为重要特征,后期则以孟郊、韩愈走上诗坛以露元和诗风端倪为标志。这三期的变化也是渐变的,或是相互交叉的,是就诗风变化和诗坛发展的总体倾向而言的。
前期以包佶、李纾为中心。包佶,《唐才子传》称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心醉古经,神和《大雅》,诗家老斫。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晚岁沾风痹之疾,辞宠乐高,不及荣利。”〔33〕包佶的诗,现存三十六首,据张强《包佶诗歌作年统计表》,作于大历前包括天宝时期者四首,作于建中兴元时期者六首,作于贞元时期者十三首加上诏补郊庙乐章十首共二十三首,年代尚难考证者四首,误收二首。〔34〕且其贞元时期作品,多为其贬官前后或主财赋时所作,其地点也多在京城。从这一统计数字看,其存留的诗作虽不能反映其诗歌风貌,但贞元时期的京城诗作占据重要地位是无疑的,故而我们与其说他是大历诗坛的代表人物,毋宁说是贞元诗坛一位开风气的诗人。
李纾,大历初任左补阙,累迁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改中书舍人。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德宗幸奉天时择为同州刺史,拜兵部侍郎。卒于礼部侍郎。李纾作品,《全唐诗》仅存乐章类十三首,无缘窥其风格。《全唐文》亦仅存《享武成王不当视文宣王庙奏》《故中书舍人吴郡朱府君神道碑》两篇,新出土墓志中又见李纾撰文《唐故中散大夫给事中太子中允赞皇县开国男赵郡李府君(收)墓志并序》〔35〕及《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颍州诸军事守颍州刺史张府君墓志并序》〔36〕二篇。但他的为人、风采以及对于门生的影响,我们通过史料的对比和相关交往诗中可以窥其一斑。
从史料而言,《旧唐书》本传称:“纾通达,善诙谐,好接后进,厚自奉养,鲜华舆马,以放达蕴藉称。虽为大官,而佚游佐宴,不尝自忘。”〔37〕《新唐书》本传称:“纾性乐易,喜接后进。其自奉养颇华裕,不为龊龊岸检。官虽贵,而游纵自如,奉诏为《兴元纪功述》及它郊庙乐章,论譔甚多。”〔38〕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李纾侍郎好谐谑,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下人呼举不正,故云短也)。”〔39〕是具有典型贞元士风的高级官僚,这样的行为举止,无疑也会对其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交往诗来看,与李纾交往且存留下诗作者有孟翔、司空曙、皎然、卢纶、包佶、郎士元、李缜、李嘉祐、戴叔伦、戴公怀、独孤及、路应、刘长卿等人。如包佶《酬兵部李侍郎晚过东厅之作》:“酒礼惭先祭,刑书已旷官。诏驰黄纸速,身在绛纱安。圣位登堂静,生徒跪席寒。庭槐暂摇落,幸为入春看。”〔40〕诗言“身在绛纱安”“生徒跪席寒”,是知李纾门徒甚众。他在大历、贞元初期的诗坛名望甚隆的地位可以想见。
包佶和李纾在贞元初期同为文坛盟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得二人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二是他们的文学影响形成诗人群体。从现存的诗中,首先看出包佶和李纾的交往,其次看出他们与其他诗人的联系。《旧唐书·刘太真传》记载:“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曰……因诏曰:‘卿等重阳宴会,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41〕这样的赐宴赋诗,规模之大,超越前代,无疑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风气朝着豪奢放荡的方向发展。而在这一群体之中,李纾、刘太真就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中期以权德舆为宗主。权德舆的政治地位、科举控制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都对中唐诗风产生重要的影响。权德舆是在贞元时期政治地位很高的文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四个朝代,在代宗大历十四年以前,主要是寓居三吴以读书求学,未冠即文章见称于诸儒间,德宗时入韩洄河南、江西李兼幕府,德宗闻其才,召为太常博士,官至礼部侍郎。宪宗时官至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舆分别在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次知贡举,所拔名士,后来成为元和以后政治和文学的中坚人物。杨嗣复《权载之文集序》:“贞元中,奉诏考定贤良,草泽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七十有二,鸾凤杞梓,举集其门,登辅相之位者,前后十人。其他任镇岳、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42〕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是贞元诗风的代表人物,尤其表现明显的“尚荡”倾向。这在下节将专门论述。
权德舆是继包佶、李纾之后的文坛盟主,他与包佶、李纾也具有一定传承关系。德舆有《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为丹阳公从事,捧持遗文,拜泣见托。”〔43〕又《卢公(坦)神道碑铭》:“某建中末与公同为丹阳公从事。”〔44〕这里的“丹阳公”即是包佶,其时为江淮水陆运使,包佶就成为其幕僚〔45〕,而张登、卢坦也是德舆的同僚。其时德舆尚有《陪包谏议湖墅路中举帆同用山字》诗:“萧萧凉雨歇,境物望中闲。风际片帆去,烟中独鸟还。断桥通远浦,野墅接秋山。更喜陪清兴,樽前一解颜。”〔46〕包佶贞元八年死后,德舆作了《祭故秘书包监文》,其中论文一段云:“又领秘邱,六艺彰明。偃息文囿,优游汉庭。雅韵拔俗,清机入冥。立言大旨,为经为纪。行中文质,不华不俚。鲁史一字,诗人四始。溯其源流,用制颓靡。”〔47〕权德舆与李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与李纾之兄李纵的关系推知的。德舆有《杂言和常州李员外副使春日戏题十首》,即与李纵唱和之作。〔48〕包佶、李纾卒于贞元八年,而后权德舆成为贞元中期文坛的宗主,与包佶、李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后期以孟郊、韩愈为代表。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49〕李肇所说的几位文人,其风格也大都在贞元时期初露端倪,而到了元和时期各自展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我们知道,孟郊、韩愈二人是元和诗坛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诗风在贞元时期已初步形成,至元和时期进一步凸显其个性,故而堪称贞元到元和诗风过渡和转变的关键人物。孟郊的年齿大于韩愈,但登第时间却比韩愈晚了四年,登第时已年近五十〔50〕。其进入诗坛较韩愈为早。孟郊实是跨越大历、贞元到元和的一位诗人。大历十四年,他已二十九岁,但在大历中,未见其有诗歌传世。德宗建中元年,就作了《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诗。孟郊在贞元二年应进士举时,有与包佶交往之作,他的《上包祭酒》诗云:“岳岳冠盖彦,英英文字雄。琼音独听时,尘韵固不同。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何幸松桂侣,见知勤苦功。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51〕这是作为举子的身份向主试者投谒之诗,也可见出包佶当时文坛宗主的地位以至为士子们所景仰的情形。贞元八年包佶卒后,孟郊作了一首挽诗《哭秘书包大监》:“哲人卧病日,贱子泣玉年。常恐宝镜破,明月难再圆。文字未改素,声容忽归玄。始知知音稀,千载一绝弦。旧馆有遗琴,清风那复传。”〔52〕从真挚的情感中透露出包佶与孟郊之间的知遇之恩。胡震亨《唐音癸签》云:“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入诗自孟东野始。”〔53〕孟郊少年贫寒而不得志,贞元十二年及第,由大悲转为大喜,其情于诗中真切地表现出来,同时科举得志的普遍心理,也在孟郊《同年春燕》《登科后》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54〕
孟郊、韩愈的诗风当然也与个人经历和社会风气相关。不仅在京城长安时如此,即使是不得志或在地方为幕僚时也有所体现。韩愈在贞元十五年为张建封徐州节度推官,当时幕府的人员文武齐备,能诗者颇多。韩愈曾写《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张建封则有《醉韩校书打毬歌》。李肇的《唐国史补》还记载张建封的幕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崔膺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监军使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诺。’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复曰:‘某有请。’监军曰:‘惟。’却请崔膺。合座皆笑,然后得免。”〔55〕崔膺这种放荡的性格得到了张建封的包容,故而当时张建封幕府罗致了很多文人与才士。这种包容性也使得孟郊对于入其幕府非常向往,孟郊进士落第时,韩愈曾引见其见张建封,作有《孟生诗》,魏本相樊汝霖曰:“孟生下第,送之谒徐州张建封也。”〔56〕孟郊也写了《上张徐州》诗。考察孟郊、韩愈在贞元时期的诗歌,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出与其前辈包佶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探讨二人元和时期凸显的“奇诡”与“矫激”特色在贞元中的渊源。
三、“贞元之风尚荡”的文学表征
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诙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5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58〕笔者以前在对于“元和体”的论述中,曾经牵涉到“贞元之风尚荡”,认为贞元士风之荡在于“崇尚放荡、豪华、奢侈”,文风之荡在于“绮靡柔弱”〔59〕。当时并没有展开,现在时过十余年,觉得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据时人柳冕的论述,“荡”由“哀艳”“诙诞”演化而来,表现出文多质少、才多伤雅的特点。李肇对于贞元之风的定位是“尚荡”,同时论述元和体的特征之一是“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说明从贞元到元和诗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故至元和时期如张籍之诗呈现出“流荡”的特征。总体而言,贞元文学尤其是诗歌“尚荡”的风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以文为戏
“以文为戏”本是中唐裴度在《寄李翱书》中对韩愈文章的批评:“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60〕裴度是一位政治家,在他看来,韩愈把文章当儿戏,违背了“以文立制”的原则。韩愈和张籍在贞元中亦曾讨论以文为戏的情况。张籍《与韩昌黎书》:“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61〕韩愈答书称:“吾子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62〕张籍《与韩昌黎第二书》:“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63〕韩愈答书:“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64〕这里裴度的非议和张籍之责难,以及韩愈之辩解,正足以说明“以文为戏”适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
不仅韩愈如此,早于韩愈的权德舆,更是以文为戏的先行者。权德舆的以文为戏,主要表现在他杂体诗的创作上。我们翻开《权载之集》卷八,其中收了一组以权德舆为首的杂体诗创作:《离合诗赠张监阁老》,并附张荐《奉酬礼部阁老转韵离合见赠》,崔邠《礼部权侍郎阁老史馆张秘监阁老有离合酬赠之什宿直吟翫聊继此章》;杨於陵《同前》,许孟容《同前》,冯伉《同前》,潘孟阳《同前》,武少仪《同前》诗;权德舆又作《酬前》后,潘孟阳作《春日雪寄上张二十九丈大监请招礼部权曹长回文绝句》,张荐《奉酬》诗。本卷权德舆又有《五杂俎》《数名对》《星名对》《卦名对》《药名诗》《古人名诗》《州名诗寄道士》《八音诗》《建除诗》《六府诗》《三妇诗》《安语》《危语》《大言》《小言》。这些杂体诗是以权德舆为首的台阁诗人群体在贞元时期“以文为戏”的最佳见证。
这种风气在当时颇为盛行,以至流行全国甚至影响海外。日本空海在《性灵集序》中说:“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马总,一时大才也,览则惊怪,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衒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其后籍甚,满邦缁素仰止。”〔65〕实则上,这种以文为戏的特点,与作为皇帝又兼诗人的唐德宗的提倡有着密切关系。德宗现存有《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这是以德宗为首的君臣分韵赋诗活动,而权德舆等贞元诗人现存诗中分题限韵之诗颇多,这与其创作回文等杂体诗倾向是一致的,都表现出贞元诗坛游戏化的倾向。
2.逞才使气
安史之乱以后,士人们经过社会的动荡,大多心理沉郁,难以振作,故而表现在文学当中,个性张扬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无论是“大历十才子”,还是刘长卿、韦应物都是如此,因而总体上缺乏逞才使气的精神。但安史之乱以后,文坛上集会唱和风气仍然沿袭且更为普遍,文人们在一起联句次韵,蔚然成风,这也表露出一些逞才使气的气息。这种气息在大历时已初露端倪,而至元和时臻于极盛,贞元则是极为关键的过渡时期,中唐险怪和苦吟之风也由此而兴。这在联句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大历时期,出现了浙东以鲍防为首、浙西以颜真卿为首的联句集团,延及贞元、元和之际,联句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并呈现出逞才使气和奇崛险怪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以韩愈为首的联句唱和活动。韩愈、孟郊联句现存十五首,大多数是长篇,最长的《城南联句》达三百零五句,这是现存唐代最长的联句。韩愈与孟郊贞元十四年作《远游联句》,开始表现出怪怪奇奇的风格。这是韩愈诗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开始,这也使韩愈、孟郊二人的诗风从此有所融合。而且韩孟的联句多用古体,个性张扬,气势恢宏,起伏跌宕,逞才使气。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云:“盖昌黎本好为奇崛矞皇,而东野盘空硬语,妥帖排奡,趣尚相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觉胶之投漆,相得无问,宜其倾倒之至也。今观诸联句诗,凡昌黎与东野联句,必字字争胜,不肯稍让;实际情况他人联句,则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于东野,实有资其相长之功。”〔66〕逞才使气是安史之乱后中唐文人的重要特点,肇始于大历,极盛于元和,而贞元时期则是连接前后的重要时期。同样是逞才使气,大历诗平熟温丽而气骨稍衰,贞元诗摆脱拘束而逞奇斗巧,元和诗雅俗兼陈而光怪陆离。
3.诙诞奇险
逞才使气的结果往往也会形成诙诞奇险的风格。而我们谈到奇险,往往列举韩孟诗派元和时期的代表作品,殊不知是孟郊这种风格在贞元时已初步形成,韩愈也初露端倪,而贞元时追求诙诞奇险已成为一种风气。较早呈现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是顾况,他以创作个性表现出尚荡的倾向。顾况与包佶交友,包佶贞元中有《顾著作宅赋诗》《酬顾况见寄》诗记载其交游,顾况则有《寄秘书包监》诗,即贞元八年包佶为秘书监时作。顾况的主要活动在大历末期至元和前期,大历末曾在永嘉任江南盐铁使属官。建中至贞元初为镇海军节度使韩滉判官,后来迁著作佐郎,约在贞元十年弃归隐于茅山,元和初年卒于茅山。他的创作活动集中于贞元时期,他的诗题材丰富,有山水诗、题画诗、音乐诗、感怀诗等,风格是奇崛、诙谐和俚俗兼之。就奇崛而言,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称:“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显而易见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67〕不仅作诗如此,而且作画亦如此:“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68〕就诙谐而言,李肇《唐国史补》称:“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69〕故其诙谐之风亦与其性格相关。《旧唐书·李泌传》亦称:“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复引顾况轻薄之流,动为朝士戏侮,颇贻讥诮。”〔70〕《唐才子传》卷三亦称其“善为歌诗,性诙谑,不修检操,工画山水”〔71〕。就俚俗而言,顾况写了一些乐府诗如《弃妇词》等,上继杜甫,重于写实,然较杜甫更加通俗化,朴素自然,明白晓畅,下开白居易新乐府的先河。
顾况而外,孟郊所作的古体诗贞元中奇崛之风已经形成,至元和更趋于极致,李益所作的边塞诗与大历以前则有所不同,衰飒之中亦时露阳刚之气,也是奇崛的一种表现。贞元诗中形成的这些奇崛风气,也与人们对于社会不平而引起情感波澜密切相关,这在韩愈贞元十九年所作的《送孟东野序》中有着极好的总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呼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72〕
四、结 语
如果说,盛唐的文化精神具有气象恢宏的特点,这种精神表现于文学上是乐观豪爽,昂扬奋发,奔放浪漫,可以用“正”来概括的话,那么安史之乱以后,文学就可以用“变”来说明。这种“变”是动态的和渐进的,大历时期是“变”之初始,故有浮薄轻疏的倾向;贞元时期乃“变”之渐进,故时而奇崛,时而流荡,时而俚俗,故总体上莫衷一是;元和时期乃“变”之极致,故名家辈出,风格各殊,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局面。白居易诗称“诗到元和体变新”,说明中唐诗之变新到元和时期彻底完成。故在中唐文风变化的过程中,贞元处于中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其地位和影响弥足重视。包佶、李纾堪称这一变化中的枢纽人物,他们前期生活在大历年间,受到大历诗风的沾染,后期因为身世和环境的改变,又开启了贞元诗风。由大历之“浮”到贞元之“荡”在包佶和李纾身上均有所体现。因为政治的角力、科举的影响、文化的熏陶,由包佶、李纾开启的贞元之风,至年代末期呈现出“以文为戏”“逞才使气”“诙诞奇险”的主要特征,凸显了流荡的风气而成为唐代文学发展的独立阶段,同时也呈现出从大历到元和过渡的文学特征。
注释:
〔1〕《郭晞墓志》全称为《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上柱国赵国公赠兵部尚书郭公志铭并序》,杜黄裳撰,郑云逵书,2007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414页载其拓片,第415-417页载其释文。按,拓片与释文首揭于赵力光、王庆卫:《新见唐代郭晞夫妇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载《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48页。《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第408-410页又载《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拓片和释文。可以参考。
〔2〕刘昫:《旧唐书》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501页。
〔3〕〔4〕〔5〕〔6〕《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第416 页。
〔7〕唐人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即以此为断限,其序云:“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十四年己未。……命曰《中兴间气集》。”(《唐人选唐诗新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451页)可见唐人即以此作为特定的阶段的。
〔8〕〔10〕〔26〕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57、60-61 页。
〔9〕涉及贞元诗风的论著,主要有蒋寅:《大历诗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方丽萍:《贞元京城群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方丽萍:《“贞元之风尚荡”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3期。
〔11〕《全唐文》卷五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95页。
〔12〕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页。
〔13〕洪兴祖:《韩子年谱》引《科名记》:“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页)
〔14〕〔22〕《千唐志斋藏志》,第1033页。
〔15〕刘昫:《旧唐书》卷一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页。
〔16〕《嘉定镇江志》卷一八,《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25页。
〔17〕李冗:《独异志》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18〕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
〔1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20〕《全唐诗》卷二七一,第3036页。
〔21〕马其昶:《韩昌黎集校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5页。
〔23〕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404页。
〔24〕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二章《台阁诗人创作论》、第三章《方外诗人创作论》。
〔25〕许总:《论贞元士风与诗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27〕〔37〕〔41〕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3、3764、3762-2763页。
〔28〕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1-273页。本文此节论述宴会的分类,参考了黄先生的说法。
〔29〕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六八,第810页。
〔30〕《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第366页)
〔31〕《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九年二月,“先是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是日中和节,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第376页)
〔3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3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67-468页。
〔34〕张强:《包佶考证》,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42页。
〔35〕杨作龙、赵水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39页。题署:“中书舍人李纾撰。秘书省校书郎郑絪书。”墓志作于大历十三年正月。
〔36〕程义:《唐〈张万顷墓志〉考释》,载《碑林集刊》第十七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题署:“右卫兵曹参军赵郡李纾撰。陈王府典军河南褚凑书。”墓志作于宝应元年九月。
〔38〕《新唐书》卷一六一,第4983页。
〔39〕赵璘:《因话录》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8页。
〔40〕《全唐诗》卷二○ 五,第2139页。题注:“时自刑部侍郎拜。”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李纾为兵部侍郎在兴元元年到贞元四年。
〔42〕权德舆:《权载之诗文集》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48页。
〔43〕〔44〕《权载之诗文集》卷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513、221 页。
〔45〕《权德舆年谱》考证,此事在建中三年。见《大历诗人研究》下册,第606页。
〔46〕《权载之诗文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47〕《权载之诗文集》卷四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7-758页。
〔48〕蒋寅:《大历诗人研究》,第417页。
〔49〕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第57页。
〔50〕《唐才子传》卷五《孟郊传》答:“贞元十二年李程榜进士,时年五十矣。”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五百家注引樊注:“《登科记》,东野及第在贞元十二年,年五十四。”而据华忱之《孟郊年谱》考证,孟郊登第时实为四十六岁。
〔51〕孟郊:《孟东野诗集》卷六,第100页。
〔52〕《孟东野诗集》卷十,第183页。
〔5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5页。
〔54〕《孟东野诗集》卷三,第55页。
〔55〕〔69〕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第34页。
〔56〕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57〕《全唐文》卷五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72页。
〔58〕元稹:《元稹集》卷五一,中华书局,2010年,第641页。
〔59〕胡可先:《论元和体》,《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第1-11页。
〔60〕《全唐文》卷五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9页。
〔61〕〔63〕《全唐文》卷六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05页。
〔62〕韩愈:《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2页。
〔64〕韩愈:《重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6页。
〔65〕真济:《遍照发挥性灵集序》,《性灵集》卷首,森江藏版,第2页。
〔66〕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9页。
〔67〕《全唐文》卷六八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13页。
〔68〕《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48页。
〔70〕刘昫:《旧唐书》卷一三○ ,中华书局,1975年,第3623页。
〔71〕《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第639页。
〔72〕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33页。
——常衮与建州茶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