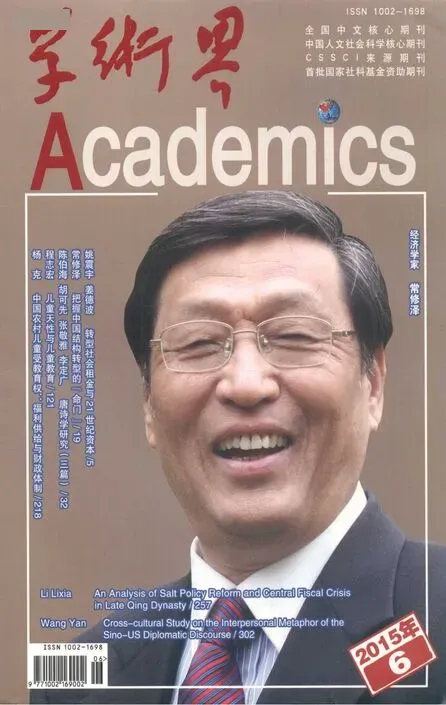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历史面貌及其当下意义
○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 民国电影研究所,北京 100024)
一、新电影出现之前的中国电影都是旧市民电影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国电影,是1922年出品的影片;而从1905年所谓中国电影诞生,直到1931年,这前后26年间留存至今,且公众能看到的影片有15部。这些影片是《劳工之爱情》(《掷果缘》,1922)、《一串珍珠》(1925)、《海角诗人》(1927)、《西厢记》(1927)、《情海重吻》(1928)、《雪中孤雏》(1929)、《怕老婆》(《儿子英雄》,1929)、《红侠》(1929)、《女侠白玫瑰》(1929)、《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银汉双星》(1931)、《银幕艳史》(1931)等——前两年刚刚在北欧又发现了一部《盘丝洞》(1927)。
只要仔细地、逐一看过这些影片就会发现,它们皆以旧文化/传统文化、旧文学/通俗小说(包括“鸳鸯蝴蝶派”小说、“礼拜六派”小说以及武侠小说)为取用资源,主题和题材不外乎恋爱、婚姻和家庭伦理,以及武侠神怪,思想上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虽有社会批评但持保守立场,艺术形式上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特征即低俗性。我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称之为旧市民电影;对它们的个案分析,新近又专门收入《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影——1922-1931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一书,读者可以审读批判。
所谓旧市民电影的旧,是与新相对而言的说法,并不具备褒此贬彼的特定的内涵——譬如政治学意义上偏狭臧否;所以,新、旧之谓,更多地体现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区分和承接。譬如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即有新、旧之分的说法。当时研究者把新电影称为“新兴电影”〔1〕或“复兴”的“土著电影”〔2〕。1949年之后的电影研究,大陆对新电影只承认或只提左翼电影〔3〕;1990年代以后,研究者把新电影称为“新兴电影”(运动)〔4〕,或“新生电影(运动)”〔5〕——在恢复旧称谓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淡化了1949年之后大陆盛行几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色彩。
193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标志之一就是因为有了新电影——左翼电影不过是新电影中的一种形态,另外还有新民族主义电影和新市民电影。作为1930年代中期的主流电影,左翼电影不仅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留下许多经典片例,而且对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有着切实的标杆和垂范意义。和当时的左翼文学一样,左翼电影不仅仅意味着革命,还意味着前卫、另类、新潮、反主流。从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来说,左翼电影肇始于1932年,代表人物是联华影业公司的编导孙瑜,以及田汉、洪深、夏衍;从1936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左翼电影逐渐被国防电影全面取代。
如果把新、旧电影看成是升级换代的意思,那么必须说,新旧交替不是一天完成的,新必然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表现在1930年代初期电影文本中,就是有的影片虽然整体上属于旧市民电影,但新的东西、新的元素已经加入并体现出来。譬如联华影业公司1932年出品的《南国之春》,主题、题材依旧,但新思想和新元素已经出现。所以,我将其归入旧市民电影并收入《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影——1922-1931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中,同时把它的“新”,与同一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啼笑因缘》的“旧”做了对比性读解,题目就叫做《大众审美、知识分子话语与新电影市场需求的时代共谋》〔6〕。
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左翼电影的真实的面貌值得注意:它既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态的必然结果,更是电影发展和艺术市场的自然产物。由于左翼电影的特征在1949年后与大陆红色经典电影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更由于1990年代第六代导演代表作品的革命性出现,因此,回望和重估左翼电影的价值就具备了无限的当下学术意义。
二、左翼电影的历史面貌
迄今为止,公众可以看到的出品于1932年的现存电影文本有3个,而且都出自联华影业公司。
第一个是孙瑜编导的无声片《野玫瑰》,金焰、王人美、叶娟娟、郑君里、韩兰根、刘继群等主演。乍看上去,影片给人以从旧市民电影爱情主题向左翼电影政治主题全码转换过渡的印象,所以笔者一开始将其视为早期左翼电影样本。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阶级性、暴力性、宣传性等经典左翼电影的重要特征无不具备,而且理直气壮、立场鲜明;尤其是王人美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其清新和泼辣不同以往,不仅奠定了左翼电影的艺术风格,也开创了新一代电影女星的表演风范。
第二个影片是《火山情血》,还是孙瑜编导的无声片,但女主演由黎莉莉担任。从外形到气质,黎莉莉与王人美如出一辙,均是长身玉腿、身材健美,神态活泼、激情四射,既与汤天绣这样的1920年代的“老”明星迥异,也与后来的新影星谈瑛有别。应该说,影片中经典左翼电影的特征即阶级性、暴力性、宣传性等均无问题,更新的一点是又为新电影贡献了第二位左翼电影女明星。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瑜不仅开创了中国左翼电影的先河,而且也捧红了一批新生代的中国电影女明星。
第三个影片是几年前才向民众公映的无声片《奋斗》,影片编导是拍摄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新锐导演史东山,男女主演有陈燕燕、郑君里、袁丛美和刘继群。由于陈燕燕也是从旧市民电影时代入道的女星,所以其表演风格和编导史东山的审美风格能够无缝对接,进而决定了《奋斗》的一仍旧贯的风貌。《奋斗》是一个旧市民电影和左翼电影的拼接合成品。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左翼电影还有一个市场性可以言说。但问题是,这是电影从一诞生就具有的先天特性,所谓艺术性不过是附加上去的。因此,《奋斗》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新、旧电影的过渡性产物。它最大的特殊点在于,这是一个比《南国之春》更为完整的、新的证据。
1933年是所谓的左翼电影年,公众可以看到5部留存至今的影片,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都有代表性作品,小公司如明月影片公司也没有摆脱时代大潮成为例外。
本年度“联华”的大牌编导孙瑜的两部影片更加具有经典左翼电影风范。首先是《天明》。左翼电影脱胎于旧市民电影,因此无需在故事结构乃至情节上下功夫,只需要将新思想灌注其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宣传性的目的。旧市民电影中的妓女只带有单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和艺术消费功能,左翼电影中的性工作者则成为新思想的启蒙者和先行者。《天明》饱含强烈的阶级意识,从头到尾灌注着革命与暴力的道德激情,因此更加具有鼓动性和宣传性。主演黎莉莉的外在形貌不仅有别于1920年代的风尘女子形象,更重要的是具有以往电影中所没有的社会革命意识。
从新旧电影形态的承接、发展的角度上说,左翼电影往往直接套用旧市民电影的架构和情节套路,但彻底改变了消费弱势群体、尤其是柔弱女性的观影心理。《小玩意》借助阮玲玉扮演的小商贩叶大嫂之口,号召民众猛醒、投身抗日救亡。弱势群体,尤其是底层中的底层即女性形象,在以往的旧市民电影中本都是被同情者、被拯救和被启蒙者,或者是被否定者,但在左翼电影中,越是出身贫贱的弱者,越有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呼唤者和先行者。这不是编导孙瑜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30年代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放弃精英阶层指导者的地位,指认草根阶层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影片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难免让位于其超常发挥的艺术感染力——而这,其实还是来自旧市民电影的伦理情怀。
本年度的第三部左翼影片是田汉编剧、卜万仓导演的《母性之光》。如果说,这一年孙瑜编导的左翼影片已然具备了经典范式,那么,《母性之光》则是在主题思想上再上层楼:将阶级意识和血统论串联通电并先行植入主题思想当中,进而完成了对人性的意识形态化的遮蔽。左翼电影与旧市民电影、以及其他新电影如新市民电影、新民主主义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对现实政治的深度介入与当下互渗。但同为左翼人士,其表现又因人而异。在当时的左翼文艺阵营中,《母性之光》的编剧田汉,与阳翰笙、洪深、夏衍等都属于更为激进,态度更为激烈的同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十几年后,左翼电影与新中国电影,尤其是红色经典电影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的逻辑关联——这四位资深编导后来都成为执掌文艺部门的不二人选。
第四部影片是夏衍化名蔡叔声,根据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影片,自然是一部左翼电影。作为资深的旧市民电影导演,程步高忠实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实质。从左翼电影的“三性”即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上看,替弱势群体即农民阶级发声,阶级性和宣传性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是暴力性。影片中的暴力性只体现在思想暴力的经济层面,即对“丰收成灾”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这个电影就显得不好看——因为左翼电影其实更多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城里人的中下层市民,对家乡和农村的不堪其实并不比知识分子更关心多少。因此,《春蚕》卖不出票是必然的结局,这也是出品方明星影片公司后来转而选择出品新市民电影原因之一。
左翼电影成为主流,就意味着必然有许多跟风之作。月明影片公司的无声片《恶邻》就是一个例证。《恶邻》也写农民,但选择了“东三省”的农民阶级和生活;《恶邻》没有写自家种粮食能否卖出去的问题,说的是“邻家”“邻村”欺负“我家”、夺我土地、偷我财宝的大问题。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部影片,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东北形势演绎。左翼电影的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以及替弱势群体说话的种种属性特征,其实还建立在一个反强权的基础之上,即对外反抗日本侵略,对内反抗阶级压迫。因此,《恶邻》就必然成为一部东北时局危急的普及性教育片——对现实政治的通俗化图解和对稀缺时政信息的即时影像传达,就是其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也是左翼电影大行其道的时代土壤。
1934年,蔡楚生为“联华”编导的是配音片《渔光曲》,此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片时代(继《姊妹花》之后)的第二部高票房影片。和史东山一样,蔡楚生也是从编导旧市民电影入道的前辈,他对左翼电影的追随和贡献,也同样是追随时代潮流的结果。但他和史东山(在艺术表现上即《奋斗》强行向左转)的“耿直”不同,蔡楚生的《渔光曲》貌似左翼电影,但更像是一年前已经出现的新市民电影(新市民电影的开山之作是郑正秋编导、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的《姊妹花》)——最大的特点是用人性超越阶级性。实际上,《渔光曲》的主题思想表现和人物塑造模式,已然表现出有意识地向新市民电影靠拢的趋势。
这一年,孙瑜为“联华”贡献了一部体育题材的无声片《体育皇后》。这个片子可以看作是专为主演黎莉莉量身订做的,因为后者出挑健美和火辣性感的身材,在传达左翼精神理念的同时,将以往的女性躯体消费转化为饱含新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视觉艺术。至于影片整体的故事框架和表现手段,依然是直接借助旧市民电影的惯常模式,即郎才女貌加三角恋爱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左翼电影对旧市民电影情色元素的大量继承和跟随时代潮流的新颖体现特征,在《体育皇后》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因为女主演短跑运动员的身份和比赛、训练场景,为女性躯体的裸露和展示撤除了观众审美窥视的道德屏障。
就1934年的中国电影历史而言,一年前不仅有声片出现,而且大卖其座,但“联华”在不全然排斥有声技术的同时,依旧对无声片制作和销售信心满满〔7〕。就此而言,公司新人吴永刚编导的《神女》,可以说为中国无声电影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足以骄示后人的句号——没有哪个研究者可以忽略或绕过《神女》,如果他要研讨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的话。《神女》的画面语言无可挑剔——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后来的公司同仁费穆可以与之比肩——主演阮玲玉的艺术成就当然不能被评论遗漏,她登峰造极的表演和吴永刚惊艳亮相的导演可谓珠联璧合。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神女》先天性的人道主义硬件配置,不仅删除了社会运行过程中变异的道德病毒,而且也将试图侵入的意识形态编码予以隔离,从而形成对艺术叙事机制的强力保护。
与此同时,孙瑜这一年编导的配音片《大路》,可谓“声”“色”俱佳。由聂耳谱曲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等主题曲和插曲,在彰显左翼电影时代精神的同时,其旋律至今依然动人心魄。由于影片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群体,基本上是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劳作的筑路工人,因此其裸露尺度之大、审美程度之康健,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电影史上都属罕见。男影星金焰的性感出镜,值得一再赏鉴肯定,可以说首开男性躯体审美的先河。这方面,环肥燕瘦的女主演黎莉莉、陈燕燕亦各逞其能,其中不乏有女同嫌疑的动作和场景,称得上惊世骇俗。从编导个人的角度上说,《大路》意味着精英阶层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自我反省与主动退离,随着左翼电影的模式化成熟,其内在思想质地开始硬化。
蔡楚生的配音片《新女性》,与他先前编导的《渔光曲》一样,始终注重左翼理念与旧市民电影结构性元素的新、旧组合搭配。就画面张力而言,《新女性》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不是阮玲玉饰演的女主人公,而是她送女儿住院后因为钱不够被迫离开的那两组镜头:一架架满当当的药品﹑一张张空荡荡的病床。对比怀中濒临死亡的可爱女孩,影片生成和传达的是极具鼓动性的视觉震撼和心理暴力。影片及时吸收引进新的电影有声技术、融入当时兴盛蓬勃的大众文艺的通俗元素(譬如大量流行歌曲的穿插使用)的做法则表明,左翼电影强盛的制作趋势和市场需求依然存在,其表现手法在向旧市民电影回归的同时,更注重在技术手段上向新市民电影靠拢。
一家由几个志同道合的理工科留美学生组建的小公司电通影片公司,与“联华”这样的大公司,一同分享了1934年的中国左翼电影制作和市场。并且,从一定程度上看,其仅有的四部作品,就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而言,有后来居上、不让前辈的趋势和实力。袁牧之编剧兼主演、应云卫导演的有声片《桃李劫》,不仅是“电通”自己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有声片时代的第一部经典左翼电影。影片的主题将批判、否定、抗争、毁灭贯穿始终,批判性、阶级性、暴力性与艺术表达的朴素性共存。叙述的大学生杀人事件及其成因表明,如果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因为秉承良知、坚持正义而在生存层面都成为社会问题,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非人道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应该被毁坏。因此,与其说《桃李劫》是对个案人物命运不公的控诉,不如说是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严厉批判。
进入1935年后,“电通”出品的有声片《风云儿女》,不仅是有声片时代经典左翼电影的巅峰绝唱,也是1949年后大陆红色经典电影的文化宝藏。后一句话的根据在于:第一,影片原作和分场剧本分别出自田汉与夏衍之手;而导演许幸之和主演袁牧之、王人美、谈瑛、顾梦鹤等,不过是忠实而完美地体现了左翼思想激进的社会批判态度和严苛的阶级革命立场。第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在14年后成为新生政权的“代国歌”。就影片而言,其融宣传性、思想性、艺术性及市场性于一体的叙事策略,也意味着左翼电影的市场化转轨。就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而言,《风云儿女》意味着制片路线开始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因此,讨论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既需要注意旧市民电影与左翼电影之间的承接关系,也需要注意左翼电影与同为新电影的新市民电影的文化关联。
1936年初,为了建立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先后宣布“自动解散”,并先后展开“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运动”〔8〕;5月间,“国防电影”的口号被提出讨论〔9〕。在一定程度上说,由于“国防电影”是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本,因此,一方面,国防电影开始进入生产流程并推向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产品生产的相对滞后性,所以,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两年间的中国电影面貌依然保持着多元性,即既有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还有新市民电影和新民族主义电影等形态的影片共存〔10〕。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1936年的中国电影,可以划入左翼电影序列的影片,只有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配音片《孤城烈女》(又名《泣残红》,但现存的VCD碟片视频并没有声音)。此片由朱石麟编剧,王次龙导演,陈燕燕、郑君里主演。从电影生产的年度上说,《孤城烈女》是“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大潮中的存留之作,是左翼电影的余波回转;从影片本身来看,它与1949年后大陆的“红色经典电影”存在着部分基因的隔代传递关联〔11〕;若再从影片的文化生态上讲,在“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大潮的合流夹击下,《孤城烈女》多少显得落后于潮流变迁。因此,其当下的解读意义在于:影片为当时左翼电影留下新时代的印痕并在最终定格于历史背景的同时,又从一个特定角度,为1949年后大陆新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和艺术资源。
1937年1月,联华影业公司出品了一部空前绝后的有声“集锦片”《联华交响曲》。所谓集锦,是因为此片由八个互无关联的短片组成,即《两毛钱》《春闺断梦——无言之剧》《陌生人》《三人行》《月夜小景》《鬼》《疯人狂想曲》《小五义》等。《联华交响曲》出品的背景原因是,一年前,“联华”的创办者之一、业务主导与艺术首脑黎民伟、罗明佑,编导吴永刚等均已被迫退出公司。因此,此片是出于凝聚人心、捆绑式打包上市的应急产品,主要是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除了费穆编导的《春闺断梦——无言之剧》极为出色且属于国防电影之外,其他大多乏善可陈。我认为应划入左翼电影(余绪)的是《两毛钱》(编剧:蔡楚生;导演:司徒慧敏;主演:蓝苹)、《三人行》(编导:沈浮;主演:韩兰根、刘继群、殷秀岑)和《鬼》(编导:朱石麟;主演:黎莉莉)。
三、结语:左翼电影的历史存在和当下的价值重估
1930年代中国的左翼电影及其背后的左翼文艺,首先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其次是当时社会生态和文艺生态的自然结果,再次,左翼电影对1949年后中国大陆电影的直接影响及其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值得重估。
19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既是处于“对峙与互渗”状态中的三大文学主潮〔12〕,也是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文艺生态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从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来说,左翼电影既然是以新文艺、新文学为主要取用资源,既然中国电影的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是在上海,那么,左翼电影的发生、源流和特征,主要是接受和转化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的结果。左翼电影是最早在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的基础上生发、脱胎而来的新的电影形态,它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客观延续,更是中国电影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谁、无论喜欢与否,左翼电影都是不容抹杀甚至不容忽略的历史性存在。
左翼电影的发起者和主创人员,主要是具有留学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而1930年代影响全球的主要社会思潮是左翼思想。作为新的电影形态,左翼电影从一开始出现就受到资本和市场的热捧,一大批新锐编导和新生代男女明星应运而生,并培养了数量庞大的新观众群体。因此,左翼电影的兴盛,与其说是处于社会精英阶层之一的知识分子的主动引领,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生态,尤其是文艺生态的必然趋势所致。左翼电影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反抗外来势力尤其是日本的军事侵略、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念,其实是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和各种政治势力集团角逐在艺术领域中的体现。
1936年国防电影(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左翼电影时代的完结,因为左翼电影的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基本被国防电影的民族性、抗日思想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启蒙性所取代。因此,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的电影制作,几乎是国防电影的单一存在形态,(并随着抗战的全面胜利而终结其历史使命)。1949年后,两岸三地的电影各自前行,港台电影暂时按下不表,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承接,大陆电影在将左翼电影的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完全浸泡于意识形态话语汁液中的前提下,割裂式地提取、嫁接和放大了左翼电影的原码基因特征,进而形成左翼电影的转基因隔代遗传症候,那就是一直延续至1980年代包括第五代导演代表作品在内的大陆红色经典电影始终占据笼罩大陆电影文化生态的结局。
什么是左翼?左翼的本意是革命、先锋、前卫、另类、激进、反主流。因此,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才是名副其实、名至实归。1949年后的大陆电影,其实更多是跨时空地抽取、变异和借助了左翼电影的内部资源和外形特征,其实与左翼电影的本质相对立——“主旋律电影”是它的另外一个新名号。因此,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只是形式上的革命〔13〕,与内容的左翼和历史上的左翼电影无涉,第六代导演才是左翼电影的正宗传人〔14〕。因为,第六代导演的特征,就艺术性而言,其视听语言在镜头、景别、构图等方面,全面继承借鉴了“旧”电影——第五代导演代表作品的已有成就;就思想性而言,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品则是对包括“旧”电影在内的大陆电影全方位的颠覆。这,与当年的左翼电影对“前辈”电影——旧市民电影的继承和反动何其相似乃尔?〔15〕

历史上的左翼电影,其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除了基于市场性即时代性之外,其实还建立在反主流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就是替弱势群体、尤其是弱势中的弱势——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沦为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和进城卖身为生的女性性工作者张目、发声。而这一特征,在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品中无不一一呈现,既受到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大陆民众的认可,也受到资本和市场的追逐,更受到当局的审查和否定。而这,又与当年左翼电影的境况何其相似乃尔?因此,如果仅仅从这一点而言,这更是重估和评价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没有民族性,何来中国?没有了现实性和批判性,何以谈电影?没有电影文本,何以谈现代性、普世价值和学术性?
注释:
〔1〕紫雨:《新的电影字现实诸问题》,原载《晨报》“每日电影”,1932年8月16日,转引自:陈播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
〔2〕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转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4》,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1385页。
〔3〕〔7〕〔8〕〔9〕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年,第 183、159、416、418 页。
〔4〕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7页;陆弘石、舒晓明:《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1页;丁亚平:《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5〕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6〕〔10〕〔11〕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如下文章:《1922-1936年中国国产电影之流变——以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作为实证支撑》,《学术界》2009年第5期,未删节版收入拙著《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的低俗性及其实证读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和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关联——以1922-1936年国产电影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4期。后两篇文章收入拙著《黑夜到来之前的中国电影——1937年现存国产影片文本读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敬请参阅。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13〕袁庆丰:《19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视觉革命与艺术贡献——以1987年的〈红高粱〉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4〕袁庆丰:《第六代导演:忠实于时代记录和叙事功能的恢复——以顾长卫的〈孔雀〉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袁庆丰:《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主体性视角流变与颠覆性的主题和艺术表达——以王超编导的〈安阳婴儿〉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袁庆丰:《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主体性视角流变与颠覆性的主题和艺术表达——以王超编导的〈安阳婴儿〉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5〕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更多个案研判,请参见拙著《新世纪中国电影读片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本书出版时,内容文字和图片多有被删减的情形)。